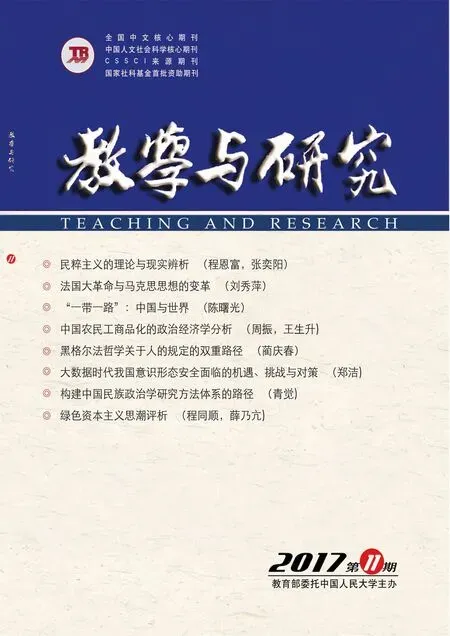綠色資本主義思潮評析
,
綠色資本主義思潮評析
程同順,薛乃亢
綠色資本主義;生態(tài)環(huán)境;市場中心主義;技術(shù)失靈
試圖解決全球環(huán)境問題的“綠色資本主義”思潮認為,利用市場手段和技術(shù)的進步可以有效地解決環(huán)境問題而沒有必要對當前的資本主義進行徹底的體系變革。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同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矛盾,在現(xiàn)實中基于市場中心主義的解決方案在資本主義的現(xiàn)有框架下是低效的,旨在解決環(huán)境問題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也不能完全奏效,這些都使得“綠色資本主義”實際上處于一個自相矛盾的境地。
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資源枯竭和環(huán)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已經(jīng)成為懸在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針對這一嚴峻形勢,學者們先后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爭論的焦點在于有沒有必要進行徹底的體系變革以解決世界所面臨的環(huán)境危機。其中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流派便是“綠色資本主義”,該思潮認為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可以實現(xiàn)環(huán)境和生態(tài)危機的全面解決。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紹綠色資本主義思潮的起源和理論特點,第二、三和四部分將分別論證綠色資本主義的內(nèi)在問題,認為資本主義同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存在著矛盾關(guān)系,市場中心主義的解決方案效果有限,新技術(shù)的進步也不足以完全解決環(huán)境問題。
一、什么是綠色資本主義?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迅猛的、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導致的環(huán)境惡化使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面對嚴峻的生態(tài)危機,現(xiàn)代環(huán)保運動如星星之火一般蔓延開來。伴隨著《寂靜的春天》一書對于殺蟲劑濫用的反思,環(huán)保主義運動達到了一個高峰。這本石破天驚的著作將保護環(huán)境的信條深深地刻在人類社會中。1970年4月22日以環(huán)境保護為主題的游行在全美擴散,這一天成為第一個地球日。20世紀70年代中期,面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壓力,美國政府為展現(xiàn)其強硬的態(tài)度,面對環(huán)境污染問題制定了一系列強制性的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但不久以后,強調(diào)自由競爭和市場的“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正統(tǒng)的理念在20世紀70年代末得到了加強,“命令與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型的監(jiān)管方法受到了新自由主義革命的沖擊。[1](P1314)此外,哈丁(Garrett Hardin)發(fā)表的《公共地的悲劇》一文也促進了環(huán)境治理的市場轉(zhuǎn)向,他認為,當稀缺資源成為每個人都可以獲得的公共財產(chǎn)時,就會導致公共資源的過度開發(fā),只有通過市場手段對于產(chǎn)權(quán)進行明晰界定并通過市場進行激勵和約束才能避免“公共地悲劇”的發(fā)生。[2](P1243-1248)1991年,世界銀行發(fā)起的旨在解決成員國內(nèi)部和全球范圍環(huán)境退化問題的“全球環(huán)境基金”,標志著“綠色資本主義”式的全球性環(huán)境計劃成為主流。[3](P3)
首先,綠色資本主義認為經(jīng)濟增長可以為解決環(huán)境問題提供有利的條件。
綠色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chǔ)來自于環(huán)境經(jīng)濟學,它是基于經(jīng)濟角度來分析和解決一系列環(huán)境問題的一門交叉學科,其基本理論形式由外部性公共產(chǎn)品、產(chǎn)權(quán)和其他微觀經(jīng)濟學理論構(gòu)成。[4](P282-297)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系統(tǒng)被認為是一種可以拆分的機械系統(tǒng),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任一部分出現(xiàn)的環(huán)境問題都可以被獨立處理,人們能夠運用經(jīng)濟價值的可分離性來分析“綠色資本主義”所面臨的環(huán)境問題。[5](P129-155)相比之下,批判這一“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傾向的生態(tài)經(jīng)濟學的研究主題往往集中于全球生態(tài)系統(tǒng)本身。它強調(diào)經(jīng)濟系統(tǒng)是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子系統(tǒng)之一,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必須放在生態(tài)系統(tǒng)這一整體之下處理才是正確的路徑。[6](P13-14)
環(huán)境經(jīng)濟學和“綠色資本主義”把增長放在第一位,聲稱經(jīng)濟的擴張可以實現(xiàn)最佳的社會福利狀態(tài)。這些學者的邏輯是,較大的蛋糕比較小的蛋糕更容易分配。然而,這種邏輯排除了生態(tài)系統(tǒng)本身的極限會將蛋糕的大小限制在某一閾值以下的這一重要前提。赫爾曼·戴利(Herman Daly)評論說,環(huán)境經(jīng)濟學忽略了有限物理規(guī)模,實際上無限的增長和利潤永遠不會發(fā)生。[7](P193)
其次,綠色資本主義提出可以通過資本主義市場原則來保護世界自然資源。
綠色資本主義宣稱人類可以成功地控制環(huán)境污染和保護自然資源,主要做法是對于地球上的所有資源進行合理的定價來反映它們的實際效用。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市場可以確保采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利用這些資源從而減少環(huán)境的惡化。[8](P1884-1885)
由于環(huán)境經(jīng)濟學的基本理論是公共產(chǎn)品、外部性和其他經(jīng)濟理論,其判斷標準是利益成本分析,強調(diào)效用和效率的概念,所以在“綠色資本主義”理論中所有的環(huán)境問題都可以轉(zhuǎn)化為對效用增減的研究。其要解決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決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導致的市場失靈,這意味著環(huán)境問題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場未能有效地分配資源,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則需要通過界定產(chǎn)權(quán)歸屬以及恰當?shù)慕?jīng)濟組織形式將外部性內(nèi)部化,從而利用市場機制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碳交易的基本思路便來源于此。
最后,綠色資本主義對于通過技術(shù)進步解決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非常自信。
綠色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保羅·霍肯在《綠色資本主義:創(chuàng)造下一個工業(yè)革命》一書中提出了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的概念,他認為全球經(jīng)濟是在一個包含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的更大的經(jīng)濟系統(tǒng)里,自然資本支撐了人類社會的經(jīng)濟發(fā)展。赫爾曼·戴利明確了自然資本的概念,認為自然資本是能為經(jīng)濟系統(tǒng)輸入可供生產(chǎn)的自然資源以及向社會成員提供服務的資本存量。在此基礎(chǔ)上,學者們將人類社會的資本存在形式概括為五種: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生產(chǎn)資本、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9](P1-11)經(jīng)濟的增長由這五者的組合所決定,某一形式資本的低效率或者減少可以通過提高其他資本的效率或者增加其數(shù)量來解決,材料和資源的消耗會由于更先進的技術(shù)和創(chuàng)新而得以控制。總之,支持綠色資本主義的人認為技術(shù)進步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對于環(huán)境和生態(tài)問題的解決起著十分積極的作用,“綠色資本主義”可以定義為以市場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為工具,同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緊密結(jié)合的旨在糾正環(huán)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二、綠色資本主義忽略了資本主義 同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矛盾關(guān)系
“綠色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對于市場和技術(shù)的力量充滿信心,他們認為在市場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作用下,資本主義能夠與環(huán)境保護共存,沒有必要對當前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進行徹底的體系變革。然而,“綠色資本主義”這一解決方案是不成功的,因為資本主義同生態(tài)環(huán)境存在著根本性的矛盾關(guān)系,這種根本性的矛盾表現(xiàn)為兩點,一是增長的極限與追尋無止境利潤之間的矛盾,二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生態(tài)系統(tǒng)對立的矛盾。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追求永恒的利潤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征,對于資本積累病態(tài)的渴求將資本主義制度與人類歷史上之前的社會制度區(qū)別開來,因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自然環(huán)境可以被視為進行資本積累的一種手段。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學者奧康納(James O’Connor)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除了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之間的矛盾外,還有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guān)系與生產(chǎn)條件之間的矛盾,這里的生產(chǎn)條件指的就是自然環(huán)境。[10](P18)
生態(tài)馬克思主義表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邏輯在于資本的本質(zhì)是不停地追逐無限的利潤,當代資本主義的“反生態(tài)”社會便來自這個邏輯。在這個社會中,技術(shù)、勞動、日常生活、消費模式和發(fā)展模式的實質(zhì)都是追求最大的利潤。[11](P87-90)為了使利潤最大化,除了不斷地擴大生產(chǎn)以進行資本增殖外,資本積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還呈現(xiàn)出明顯的金融化趨勢。[12](P3)通過金融化產(chǎn)生的資本積累不論是速度上還是總量上都遠遠超過從前在商品和服務行業(yè)的積累。綠色新政組織(Green New Deal Group)在其報告中清晰地論證了這種關(guān)系,認為全球債務規(guī)模的高速擴張不僅成為全球金融危機的最重要誘因,也助長了能源及其他不可再生資源的不可持續(xù)型消費。[13](P2)由于資本的特質(zhì)是無限積累和不斷地追求增長,那么增長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因而資本主義制度肯定會無情地碾壓阻礙其擴張道路上的一切東西。
羅馬俱樂部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模擬實驗,他們使用計算機模擬經(jīng)濟和人口增長與有限資源供應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這個實驗最明顯的結(jié)論之一是增長具有源于地球空間和資源有限性的極限。該增長模型有五個變量,即世界人口、工業(yè)化、污染、糧食生產(chǎn)和資源枯竭,其中世界人口和工業(yè)化屬于無限系統(tǒng)的指數(shù)級增長,而污染、糧食生產(chǎn)和資源枯竭是屬于有限系統(tǒng)的線性增長方式,因此人口過度增長和工業(yè)化產(chǎn)生了糧食短缺、環(huán)境退化和資源不足等嚴峻的問題。根據(jù)模擬計算結(jié)果,如果這五個變量的當前增長趨勢沒有改變,人類社會將在一百年以內(nèi)看到增長的極限,到那時全球性的系統(tǒng)崩潰將發(fā)生。[14](P10-12)基于對增長具有極限的理解,赫爾曼·戴利發(fā)展了零增長理論,提出了旨在實現(xiàn)人類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穩(wěn)態(tài)經(jīng)濟理論。要達成這一目標的關(guān)鍵在于,物質(zhì)系統(tǒng)與人口系統(tǒng)之間要達成一種動態(tài)平衡狀態(tài),這兩個系統(tǒng)只有都保持較低的流量時,穩(wěn)態(tài)才可能實現(xiàn)。[7](P185-193)穩(wěn)態(tài)經(jīng)濟所隱含的抑制財富增長速度的前提條件,與資本主義追求無限利潤的本質(zhì)是無法一致的。
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生態(tài)系統(tǒng)對立的矛盾,主要是資本主義對利潤的攫取和對經(jīng)濟增長的不懈追求往往會產(chǎn)生一種物質(zhì)變換裂縫(metabolic rift),使人類同生態(tài)系統(tǒng)逐漸對立起來。[15](P372-373)
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寫到,“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不斷交往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lián)系,也就等于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lián)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P95)
既然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如此緊密,那么當前人類面臨的生態(tài)危機就不應該被僅僅視為單純的環(huán)境問題,而應該從人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去考量。馬克思對于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的理解深受李比希提出的物質(zhì)變換(metabolic)觀點的影響。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guī)律所決定的物質(zhì)變換的聯(lián)系中造成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 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費”。[17](P919)福斯特指出《資本論》批判的就是“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的“斷裂”,并將其概括為物質(zhì)變換斷裂(metabolic rift)這一概念。[18]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出現(xiàn)了無法彌補的裂縫,其客觀呈現(xiàn)就是日益嚴重的生態(tài)危機。物質(zhì)交換過程在人和自然之間的表現(xiàn)則為勞動,勞動過程是人與自然物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的一般條件,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然而在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是異化的,異化勞動使人自己的身體,同樣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異化,從而將人類和自然對立起來。[19](P274)因此,資本主義生產(chǎn)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20](P579)資本主義通過土地圈地、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不僅控制了生產(chǎn)資料,也掠奪了土壤的養(yǎng)分,不斷地強化和深化人類和地球之間的物質(zhì)交換的斷裂。[21](P477-489)由此帶來的物質(zhì)變換斷裂在全球?qū)用嫔下樱沟萌伺c自然的對立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三、綠色資本主義的市場中心主義解決方案效果不佳
基于市場中心主義(Market-based)的解決方案在資本主義的現(xiàn)有框架下是低效的。聯(lián)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根據(jù)已觀測到的氣候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撰寫的《氣候變化2014綜合報告》,深入分析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類活動對于地球氣候的影響。其核心觀點是,人類對氣候系統(tǒng)的影響是明顯的,更為嚴峻的是溫室氣體排放量持續(xù)上升,業(yè)已達到歷史最高值;溫室效應氣體所造成的近期的氣候變化已對人類和自然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如不加以控制,將導致生態(tài)系統(tǒng)和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嚴重、普遍和不可逆的危機。[22](P3-5)事實上,對于溫室氣體的限制措施早在《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簽訂時就開始實施,但是該計劃的執(zhí)行卻舉步維艱。美國于1998年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不過2001年上臺的小布什政府卻拒絕執(zhí)行,使得美國成為最早退出《京都議定書》的國家。2011年12月,加拿大也正式退出該協(xié)議。此后,俄羅斯、日本和新西蘭也明確反對《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歐盟和澳大利亞態(tài)度曖昧。世界銀行在《全球氣候體系中的整合發(fā)展》報告中批評《京都議定書》對抑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收效甚微,該條約于1997簽訂,但到2006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卻增長了24%。[23](P233)
《京都議定書》的失敗促使許多經(jīng)濟學家和環(huán)保人士開始從市場的角度出發(fā),去尋找更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些人認為該協(xié)議的缺陷在于其“自愿”的命令控制缺乏約束力,這一缺陷在“無政府狀態(tài)”的全球體系中會被放大。因為作為一種公共物品供給的碳排放限額勢必會造成搭便車現(xiàn)象,而市場激勵可以克服“京都議定書”的弱點。[24]碳稅和“總量控制和交易”(cap and trade)是推進溫室氣體減排的兩種最主要的市場激勵調(diào)控機制。碳稅所解決的是化石燃料使用所造成的外部不經(jīng)濟問題。[25]利用碳稅定價碳排放,是政府鼓勵企業(yè)和家庭通過投資清潔技術(shù)和采用更環(huán)保的做法來減少污染的最有力激勵措施之一。同碳稅相比,“總量控制和交易”計劃更為復雜,政府為特定的污染行業(yè)設(shè)定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限(cap),每一單位二氧化碳減排量都有一個“許可證”,公司可以在將來購買、銷售、交易或存儲這些“許可證”。在這個計劃下,使用大量化石燃料從而產(chǎn)生過量排放的公司必須擁有額外的排放許可證,才能被允許進行超額排放,而能夠控制排放量或者大規(guī)模使用清潔可再生能源的企業(yè)卻擁有剩余的排放許可,這就使得這些過度排放的公司必須向能夠控制排放量的公司購買排放許可證。與此同時,政府將逐步降低總排放量的上限,增加過量碳排放的公司購買排放許可證的成本。最后,隨著污染許可證價格的上漲,使用化石燃料的成本將超過可再生能源,致使化石燃料逐漸退出市場。該方案的支持者認為,如果碳稅和“總量控制和交易”計劃能夠?qū)嵤瑴厥覛怏w所帶來的全球變暖問題就能夠被有效遏制。
從表面上來看,“總量控制和交易”計劃與碳稅是可行的,環(huán)保主義者對于方案的成功滿懷信心,但其自身存著致命缺陷。首先這兩項計劃方案都可以被視為一種綠色稅,從而增加企業(yè)的生產(chǎn)成本。[26](P213)在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中,一國企業(yè)成本的增加會使其在市場中處于弱勢地位從而直接削弱本國產(chǎn)業(yè)的競爭力。[27](P8)對于碳稅來說,其最大的問題是碳稅稅率無法確定,具有很大的彈性。[28]這就給予大型的工業(yè)公司和利益集團相應的操作空間,他們可以通過游說要求維持低水平的碳稅。煤、天然氣、石油等行業(yè)組成的利益集團為國家提供數(shù)百萬的工作崗位和上百億的稅收,如果他們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受到了限制,政府的財政收入便會受到影響,失業(yè)和經(jīng)濟停滯的壓力也將逼迫政府停止進一步的行動。除了工業(yè)公司之外,其他的社會團體也會要求低碳稅的實施,例如,工會可能因為就業(yè)崗位面臨削減而抵制碳稅,消費者也會因為企業(yè)會將成本轉(zhuǎn)移到自己身上而抵制新的稅收。所以,通過多方談判,碳稅率在最終實施中會處于非常低的水平。這對于氣候變化未來可能會產(chǎn)生的嚴重后果來說,顯然達不到人們的預期水平。如果要將整個21世紀的地表溫度的升高幅度控制在2°C以下,則需要205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10年減少40%至70%,2100年保持排放零增長。[22](P20-21)而維持原有的碳稅稅率水平是不可能達到這一要求的。
“總量管制和交易”實際上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稅。[29](P118)很多國家和企業(yè)盡可能地不參加這一計劃,而即使同意了這一方案,也會把排放上限設(shè)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的推行被譽為美國環(huán)保史上的一次重大勝利,但實際上該法案僅僅承諾在2020年之前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而不是京都協(xié)議書中所要求的1990年)降低17%。而如果與1990年的排放量相比,則僅僅下降了5%。[30]更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總量控制和交易”計劃中規(guī)定的總量上限僅僅在2020年下降1%,而且85%的許可排放量都被免費發(fā)放出去而不是在碳交易市場上拍賣。[31](P315)在德國,來自工業(yè)的壓力集團通過失業(yè)和工業(yè)轉(zhuǎn)移的威脅游說政府以謀求更高的排放總量上限,并且成功地得到了3%的額外排放量。[29](P118)日本和韓國則于2011年宣布放棄實施應當在2013年執(zhí)行的限額和交易計劃。日本最大的商業(yè)游說團體“日本經(jīng)濟團體聯(lián)合會”稱,64家相關(guān)的大型企業(yè)中有61家反對引入碳交易,這些公司認為這個計劃大大增加了企業(yè)經(jīng)營的成本,日本的優(yōu)勢產(chǎn)業(yè)面臨著來自新興經(jīng)濟體的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這些環(huán)境政策的“負擔”只會在全球競爭中拖后腿。[32]2014年,澳大利亞則放棄了一系列的碳稅政策,因為它對整個國家的生產(chǎn)力有負面影響,碳稅導致了企業(yè)的成本急劇上升,使得資源開采所帶來的經(jīng)濟增長消失了。[33]
市場中心導向計劃的失敗不應歸咎于利益集團與政府的沆瀣一氣,即使政治領(lǐng)導人有改革的勇氣,他們也不能扭轉(zhuǎn)局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世界各國正在盡一切努力實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因為只有經(jīng)濟的增長才能支持人類目前的生活,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化石燃料的消費最大化。作為一個理性的政治行為體的政府,其首要目標必定是尋求最大化的政治支持,當政府發(fā)現(xiàn)這些計劃和行動可能對其所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時,便會繼續(xù)在寬松的化石燃料政策上前進。總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競爭性民主中,政黨和政府沒有更多選擇,為了實現(xiàn)連任,得到民眾和企業(yè)財團的支持,其競選綱領(lǐng)和執(zhí)政政策只能專注于民眾的短期福利,提高就業(yè)率。
四、綠色資本主義推崇的新技術(shù)也不足以完全解決環(huán)境問題
支持“綠色資本主義”的新古典主義經(jīng)濟學家認為,新技術(shù)的誕生和發(fā)展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和資源利用率,能夠減少生產(chǎn)所需的原材料或者在生產(chǎn)過程中每單位產(chǎn)生的廢物和有害排放物的量。然而,創(chuàng)新和技術(shù)進步仍然不能完全解決資源消耗增加的問題。
智能手機對于固定電話、MP3播放器、相機、傳統(tǒng)便攜播放器具有極強的替代效應。但是對智能手機需求的急劇增加,必然導致必要的資源投入從原來的電子設(shè)備轉(zhuǎn)移到智能手機上。即使每單位的能耗由于技術(shù)的進步而下降,制造手機所需要的材料和能源總消耗也可能遠超從前。根據(jù)綠色和平組織剛剛發(fā)布的題為《失控的創(chuàng)新:智能手機十年全球影響》的報告,2016年用于智能手機的制造能耗是2007年的250倍,如果用于制造液晶屏的銦的開采速度不加以限制,那么14年內(nèi)便會枯竭。由于越來越多的手機采用一體化設(shè)計,使得舊手機的拆解異常困難,由此產(chǎn)生的巨大的資源浪費和廢棄物回收處理將成為一大難題。[34]

圖1 2007年以來世界能耗 [34]
現(xiàn)實生活中面臨的這種狀況被稱為杰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19世紀經(jīng)濟學家杰文斯在研究煤炭的使用效率時發(fā)現(xiàn),技術(shù)進步使得煤的使用效率提高了,但煤的消耗總量卻反而更多。[35]也就是說,技術(shù)進步提高了生產(chǎn)所使用的特定資源的效率,但是效率的提高卻傾向于增加而不是減少該資源的消耗。[36](P1)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是生產(chǎn)率的提高產(chǎn)生更多的利潤,更多的利潤使得資本家能夠擴大再生產(chǎn)并且增加這種資源的消耗。斯默(Kenneth A. Small)和丹德(Kurt Van Dender)研究了美國車輛里程燃料效率提高的反彈效應,他們發(fā)現(xiàn)車輛燃料效率提高5%只能使燃料消耗降低2%,這其中3%的差距是因為效率更高的燃油發(fā)動機使得美國人能夠駕駛得更快和更遠。[37](P25-51)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安托萬·德謝茲萊普雷特(Antoine Dechezleprêtre)、大衛(wèi)·荷莫斯( David Hemous)、拉爾夫·馬丁(Ralf Martin)和約翰·范里寧(John Van Reenen)研究了汽車和交通運輸業(yè)中影響技術(shù)變遷的因素,并將結(jié)果發(fā)表于頂尖期刊《政治經(jīng)濟學》,他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汽車工業(yè)中技術(shù)創(chuàng)新表現(xiàn)出強烈的路徑依賴:如果某一企業(yè)更多地接觸偏向清潔型創(chuàng)新(clean innovation)的外部環(huán)境(技術(shù)溢出表現(xiàn)為偏好清潔環(huán)保的技術(shù)),則其對于清潔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和使用有更強的偏好;反之,具有污染型創(chuàng)新(dirty innovation)歷史的公司在未來也更傾向于污染型的創(chuàng)新。[38](P1-51)目前完全從事量產(chǎn)電動車生產(chǎn)的汽車廠家只有特斯拉,電動汽車項目在其他的傳統(tǒng)汽車制造商,例如大眾、豐田、奔馳和寶馬等公司的生產(chǎn)計劃中僅僅處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因此,由于技術(shù)變遷的路徑依賴,它們投身于制造更加清潔環(huán)保的汽車技術(shù)的意愿值得懷疑。2015年曝出的大眾集團“尾氣門”事件可以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那年美國環(huán)保署查出大眾公司涉嫌在58萬輛柴油發(fā)動機車輛的車載電腦中安裝一種可用于尾氣測試作弊的軟件,允許車輛正常行駛時的污染物排放量超過法定標準的40倍以上。[39]
因此依賴新技術(shù)去完全解決環(huán)境問題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杰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對技術(shù)發(fā)展盲目狂熱的錯誤,在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上,技術(shù)進步帶來的影響同樣可能不會沿著人類預先設(shè)計的路線前進。[36]
結(jié) 論
“綠色資本主義”的擁護者試圖利用市場和技術(shù)將“綠色”和“資本主義”拉到同一條戰(zhàn)線上。他們堅信,不需要進行徹底的體系變革就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妥善處理人類社會面臨的一系列環(huán)境和生態(tài)問題。
首先,他們認為經(jīng)濟的增長就能夠為人類帶來更好的福利,但是他們忽略了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自身的有限性。資本主義的邏輯在于資本的本質(zhì)是不停地追逐無限的利潤,資本主義的消費模式和發(fā)展模式的標志是追求最大的利潤,這與生態(tài)系統(tǒng)有限性是矛盾的。在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過程中,由于物質(zhì)交換裂縫的產(chǎn)生,人與自然也逐漸地對立起來。
其次,“綠色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堅持認為,利用市場這一強有力的工具,可以有效地解決環(huán)境問題。根據(jù)這一邏輯,這些學者提出了碳稅和“總量控制和交易”計劃等措施。但是由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世界各國正在盡一切努力發(fā)展經(jīng)濟,大型工業(yè)企業(yè)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不能受到損害,同時在資本主義的競爭性民主中,政黨和政府都專注于民眾的短期福利和就業(yè)率來討好選民,因此,碳稅和“總量控制和交易”都得不到有效執(zhí)行。
最后,“綠色資本主義”認為,新技術(shù)的誕生和發(fā)展可以提高資源利用率,并且使得少量的資源生產(chǎn)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技術(shù)的進步又使得人類面臨著杰文斯悖論,效率的提高傾向于增加而不是減少該資源的消耗。除此之外,技術(shù)創(chuàng)新所具有的強烈的路徑依賴的特性也使得污染企業(yè)欠缺研發(fā)清潔型技術(shù)的動力。因此,人類應該摒棄綠色資本主義對于技術(shù)發(fā)展的盲目信念。
[1] Michael Watts. Green Capitalism, Green Governmentality[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ume 45, Issue 9, 2002.
[2] Garrett Hard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Vol. 162, Issue 3859, 1968.
[3] Zoe Young. A New Green Order?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M].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4] Robert U. Ayres, Allen V. Knees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Externalit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3, 1969.
[5] T. Weis. The Ecological Hoofprint: The Global Burden of Industrial Livestock[M]. London: Zed Books, 2013.
[6] Jeroen C. van den Bergh. Ecological Economics: Themes, Approaches, and Differences with Environmental Economics[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2, Issue 1, 2001.
[7] Herman Daly. Al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Scale: Towards an Economics that is Efficient, Just, and Sustainable[J].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ume 6, Issue 3, 1992.
[8] J. Alper.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Power of the Market[J]. Science, Volume 260, Issue 5116.
[9] Neva R. Goodwin. Five Kinds of Capital: Useful Concep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03-07, 2003.
[10] Evangelia Apostolopoulou, William M. Adams. Neoliberal Capitalism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The Dialectics of “Green” and “Un-green” Grabbing in Greece and the UK[J]. Antipode, Volume 47, Issue 1, 2015.
[11]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2.
[12] Paul M. Sweezy.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J]. Monthly Review, Volume 49, No. 4, 1997.
[13] Green New Deal Group (GNDG). A Green New Deal[M].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08.
[14] D. Meadows. The Limits to growth[M]. New York: Universe Books,1972.
[15]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105, No.2, 1999.
[1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8] 劉仁勝.約翰·福斯特對馬克思生態(tài)學的闡釋[J].石油大學學報,2004,(1).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0] 馬克思.資本論[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 Ivan Scales. Green Consumption, Ecolabelling and Capitalism’s Environmental Limits[J]. Geography Compass, Volume 8, Issue 7, 2014.
[22] IPCC.氣候變化2014綜合報告[R].2015.
[23] World Bank.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into the Global Climate Regime[EB/OL]. 2010,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WDRS/Resources/477365-1327504426766/8389626-132 7510418796/Cha-pter-5.pdf.
[24] 朱京安,宋陽.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失敗的制度原因初探——以全球公共物品為視角[J].法治與社會發(fā)展,2014,(2).
[25] 婁峰.碳稅征收對我國宏觀經(jīng)濟及碳減排影響的模擬研究[J].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shù)經(jīng)濟研究,2014,(10).
[26] James Hansen. 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 The Truth About the Coming Climate Catastrophe and Our Last Chance to Save Humanity[M]. New York: Bloomsbury, 2010.
[27] S. Chang. Cap and Trade or Cap and Tax?[J]. IEEE Spectrum, Volume 46, Issue 4, 2009.
[28] 蔡博峰.碳稅PK總量控制-碳交易[J].環(huán)境經(jīng)濟,2011,(6).
[29] Richard Smith. Green Capitalism: the God That Failed[J].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Issue 56, 2011.
[30] Brian Tokar. The Problem with Climate Legislation-Politics-as-Usual While the Planet Burns[EB/OL]. 2010, http://www.greens.org/s-r/51/51-02.html.
[31] Ashley Dawson. Climate Justice: The Emerging Movement Against Green Capitalism[J]. Climate Justice, Volume 109, Number 2, 2010.
[32] S. Keidanren. Korea Business Lobby Oppose Start of Carbon Trading[EB/OL]. The Japan Times News, 2011,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1/01/15/business/keidanren-s-korea-business-lobby-oppose-start-of-carbon-trading/#.WNadgmR96Uk.
[33] Telegraph, Australia Abandons Disastrous Green Tax on Emissions[EB/OL].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commodities/10972902/Australia-abandons-disastrous-green-tax-on-emissions.html.
[34] 綠色和平組織.失控的創(chuàng)新:智能手機十年全球影響[EB/OL].2017, http://www.greenpeace.org.cn/global-impact-of-10-years-of-smartphones/.
[35] William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EB/OL].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66. 2nd edition, revised. 2017/4/7.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jevons-the-coal-question
[36] John Bellamy Foster, Brett Clark, Richard York. Capitalism and the Curse of Energy Efficiency: The Return of the Jevons Paradox[J]. Monthly Review, Volume 62, Issue6, 2010,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0/11/01/capitalism-and-the-curse-of-energy-efficiency/.
[37] Kenneth Small, Kurt Dender. Fuel Efficiency and Motor Vehicle Travel: The Declining Rebound Effect[J]. Energy Journal, Volume 28, Number 1, 2007.
[38] Philippe Aghion, Antoine Dechezleprêtre, David Hemous, Ralf Martin, John Van Reenen. Carbon Taxes, Path Dependency,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Auto Industr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4, No. 1, 2016.
[39] 李雯.“排放門”大眾到底是怎么作弊的[EB/OL].新華網(wǎng)http://news.xinhuanet.com/auto/2015-09/23/c_128259769.htm.
[責任編輯劉蔚然]
AnalysisofGreenCapitalismThoughts
ChengTongshun,XueNaika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green capitalis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rket centrism; technical failure
The “green capitalism” thought believes that the use of market mean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effectively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a thorough system reform of the current capitalism. However, due to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olution based on market centralism in the reality is inefficient under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capitalis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imed at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not entirely effective. All this makes the “green capitalism” thought in fact a self-contradictory situation.
程同順,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薛乃亢,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