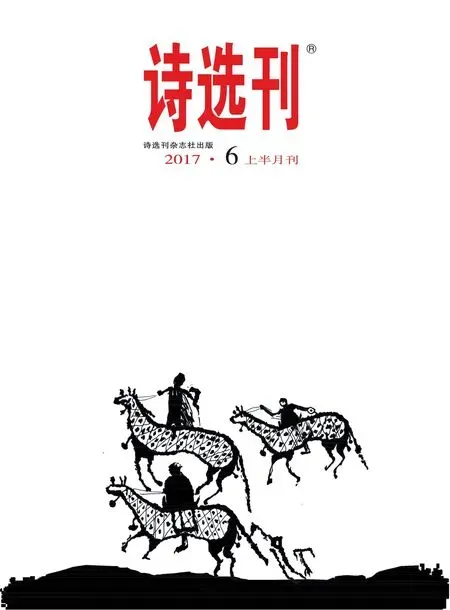北 行 記
◆◇殷常青
北 行 記
◆◇殷常青
張家口以北
張家口以北,天空越來越低,
天空越來越藍,白云一團一團堆積,
仿佛不用抬頭就可以碰到它們,
仿佛不用伸手就可以把它們拽下來。
藍天無邊,白云自由,閑散,
世界的好,就是一個人在藍天白云下,
嘗試著把血管里的江河一瓢瓢舀出,
嘗試著去做一個大海的歌手,轟轟烈烈。
張家口以北,
藍天之外的藍,被路邊的荊條系在身上,
野生的菊花,種植的葵花,
怒放的花蕊,通往天堂,
白云之下,有牛羊散漫,
有一對對翅膀,來自與你我相遇的秋天。
風吹,一朵白云散了,
有十萬朵從遠方趕來。
風吹,草木懷抱絲綢,
在拂動里,推杯換盞。
風吹,有淖爾,有莜麥,有土豆,
有避寒的去處,有隱約的星光。
張家口以北,一年一度或者兩度,
都要在詩歌里寫下它,在心里愛上它,
它的好,值得我們?nèi)ス钾摚?/p>
它的好,我們用來小酌或痛飲,
它的好,是在萬物面前的謙卑和忍讓。
藍天不是遠方,白云也不是,
在張家口以北,
我一直在仰望天空,
一直在想象著,
如何去虛度這晴朗的光陰。
張家口以北,
再北,就是更廣大的錫林郭勒了,
無邊的草原,寬闊的氣象,
就要藍到藍天里了,
就要藍到白云里了。
草地光芒
每一棵小草都有自己的光芒,
而光芒是不能掐滅的。
在內(nèi)蒙古,在錫林郭勒,
每一棵小草都不被園丁修剪,
它們隨風偃仰,浩浩蕩蕩,
讓夜晚巨大,時間沒有立場。
它們不被種植,也不會被收割,
開著繁密、細碎、自由的花兒,
猶如燈盞自我點亮,
它們沒有遠方,沒有目標,
在空曠與寬廣之中,
從四個方向一直走到天之盡頭。
它們和淖爾,和風抱在一起,
它們是野生的,自然的,
枯了就枯了,死了就死了,
但總有一些羔羊替它們活著,
但總有一些百靈替它們贊唱,
它們讓孤獨無所依靠——
廣闊的草地,細小的光芒,
每天都在聚集,綿延,
它們的秋天略大于我見過的其他季節(jié),
它們的背影略大于我見過的任何天空,
太陽升起,霜粒散落,
迎風的草地,迎著滾動,前仆后繼。
在內(nèi)蒙古,在錫林郭勒,
在波濤翻卷的草地,
我總喜歡回頭,
看看身后的起伏,那么張揚,
我喜歡在紙上寫下秋天,秋涼和蕭瑟,
并深深想念它們——
風只是經(jīng)過錫林郭勒,
經(jīng)過一棵一棵親愛的小草,
它們驚訝,躲閃,追逐,疏離,融合……
我找不到它們的陰影和破綻,
它們相互抱著,團結(jié)在一起,
像永遠不舍自己的萬千兒女。
每一棵小草都有自己的清晨和正午,
都有自己的清澈和灼燙,
當它們的青煙涌向天空,
在內(nèi)蒙古,在錫林郭勒,
我看到此時的世界——
只剩下了各種各樣的沉默。
晴朗的天空下
晴朗的天空下,
錫林浩特巨大的廣場,
站著一個蒙古族詩人,
——那賽因朝克圖,
他是一座城市的血肉,
他是草原靈魂里僅存的知音。
漢白玉的身子,
手捧翻開的詩卷——
他用半生的時光與塵世相遇,
他用半生的時光把詩寫在廣闊里,
此后,他將有自己的靜夜,星空,風月……
他將獨自回想人世間的歡聚和分離……
金色的暮靄中,
一個詩人站在巨大的廣場,
去愛陌生的人,
也去祝福將來的春秋,
他貫穿于塵世里的喜悅和悲傷,
他愛著每天都可以見到的人。
一個詩人在此刻是祖國的,
也是世界的,
他站在內(nèi)蒙古最大的廣場,
用慈悲的眼神安撫微如塵埃的人民,
和他們遇到的疼,
此刻的天空是湛藍的,云朵是雪白的。
我經(jīng)過那么多的城市廣場,
只有錫林浩特的廣場,
讓一個詩人站在了那里——
有了這座雕像,
廣闊的草原還有遠方嗎?
有了這座雕像,親愛的詩人們還需要什么?
詩人的內(nèi)心沒有廢墟,
筆尖的墨水,紙上的煙云,
像那賽因朝克圖一樣,
挺直了身子,也挺直了眼神,
那些平仄,比喻,修辭,美學(xué),
一起留給了光芒升起的草原。
仿佛時間里生長過的,停留過的——
一個詩人站在安靜的廣場,
小小的身子,仿佛永遠在等待著什么,
仿佛愛,在晴朗之下,信任著此生此世,
那賽因朝克圖,親愛的——
如果我活得比你長久,我必將好好活著。
陽光灼燙
如果沒有陽光,高原一定會坍塌,
如果沒有陽光,我看到的錫林郭勒,
一定會癱瘓在小小的淖爾里,
如果沒有陽光撲面、灼燙,
那些閃動的蝴蝶,一定更像霜花,
那些風中的小草,一定更像疾病。
高原之上,那么多此起彼伏的閃現(xiàn),
那么多迷醉,綿密,怒放,熱烈……
要在廣大與潦草之間提煉一個詞——
如誕生:草尖上懸掛的晨露,
如飛行:白云間翻滾的鷹翅……
這樣灼燙的詞,這樣奔涌而出的淚水……
高處是接近神跡的地方,
高處的內(nèi)蒙古,
高處的錫林郭勒,
是高處的廣闊,平坦,
高處的光線,從早晨就成群結(jié)隊出現(xiàn)了,
它們繚亂地,有序地,斜仄著飛行——
頭頂沒有白云,只有深厚的藍,
只有灼燙的陽光,向廣大致敬——
山坡仰躺,白楊斜出,百靈的叫聲,
在輕漾的絲綢之光上流淌,
青草的血液和野花的奶水,
仿佛一個正午,就能把它吸干。
草地寬闊,人間微醉,
高原之上,時間停頓在時間里,
陽光停頓在陽光里,
也停頓在它照亮的事物里——
兩只相愛的蝴蝶,沒有更好的去處,
像最美的詩篇,總是停頓在最美的想象里。
內(nèi)蒙古用高邁搬運陽光,
錫林郭勒用草浪醞釀灼燙,
它們隱含了現(xiàn)世以外的力量,
它們不知疲倦,煮沸了天上人間。
巨大的灼燙,如美之虛無,
巨大的灼燙,如高處的領(lǐng)袖。
高原的光明,黃金成堆,
一根根小草倒下,又站起來,
一匹匹烈馬遠去,又返回,
從早晨到正午,在愈來愈濃烈的光芒里,
你不能停留,你只是個過客,
你不能贊美,你沒有灼燙之外的新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