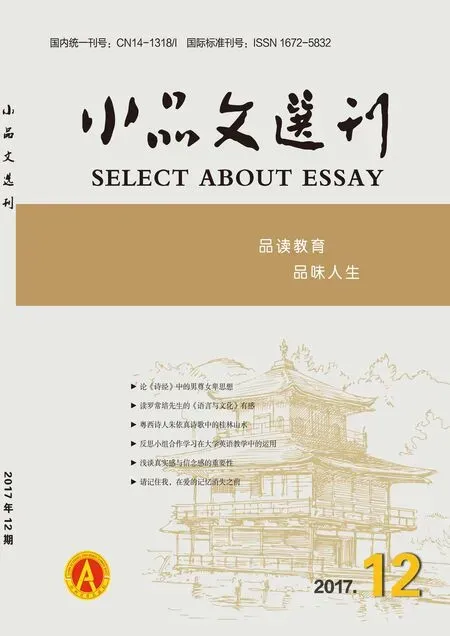再論劉勰的“風骨”觀
施 宇
(揚州大學 江蘇 揚州 225009)
再論劉勰的“風骨”觀
施 宇
(揚州大學 江蘇 揚州 225009)
“風骨”是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的一個重要概念,而對“風骨”論述比較系統完備的還要數劉勰的《文心雕龍》。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篇》中詳盡論述了“風骨”這個概念,但是古代文論具有模糊性、流變性等特征,后人對于劉勰在《文心雕龍》里提及的“風骨”這一概念的解釋有著種種爭議和分歧,本文將結合自身閱讀理解,談談筆者所理解的“風骨”的涵義。
風骨;氣;情;勁健
“風骨”最初是用來品評人物的,始于漢末,流行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的“風骨”大多指的是一個人神氣風度的特點,后來才被運用到文論中,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篇》中將“風骨”分開,他認為“《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陳,莫先于骨。”也就是說,在他看來,“風”與“骨”也是品評文章的兩個不同角度,所以筆者就分別從“風”、“骨”兩個角度來談一談自己的想法。
1 “風”與“氣”的關系
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篇》一共分為四段,無論在文章的第一段還是第二段,劉勰都在文中大量引用了另一個很宏大的概念——氣,顯然劉勰是很注重“風骨”與“氣”的關系的,那么究竟“風骨”這個概念與“氣”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微妙的關系呢?
明代的曹學佺認為“風骨二字雖是分重,然畢竟以風為主。風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風也;故此篇以風發端,而歸重于氣,氣屬風也。”在曹學佺看來,“風骨”中更偏重于“風”,“骨”依托于“風”存在,所以他只注重了“風”與“氣”的關系,當然這跟他對《文心雕龍》“以心為主”、“以風為用”的批評是分不開的。這里的“風”更多的是一種通過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社會風貌,而這里的“氣”則更偏重于內在的精神氣質,具有了陶冶、教化的意味。
而后于曹學佺的紀昀,則提出了另一種觀點,相較于曹學佺偏看重于“風”,紀昀的觀點是:“紀氏駁之謂氣即風骨,更無本末。”紀昀認為“氣”就是“風骨”。如果說將“風”等同于“氣”還比較讓人信服,但是“骨”同“氣”被視為同一個概念,還是無法令人信服的。紀昀這樣解釋還違背了劉勰將“風骨”二字分開解釋的用意,那他又為何如此言之鑿鑿呢?紀昀在《隱秀》篇中說:“純任自然,彥和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論。”紀昀推崇的是劉勰的“自然之道”,以“自然”為核心來批評《文心雕龍》,所以他才會將“風骨”歸之于“氣”。“自然之道”在紀昀眼中不僅是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具有返璞歸真的特點,“氣”作為“自然”的一個子概念,也應該如此,在紀昀看來的“風骨”更多的應該是順應自然之道,猶如“氣”一般,貫通上下、清新流暢的一種文風。
“風”應該是由一股流動的、清新的、讓人通透豁達的“氣”所形成的態勢,自然界是如此,表現在文章中也應該是這樣的情致。在《文心雕龍》中確實提到了很多關于“氣”的地方,例如“思不環周,莫索乏氣,則無風之驗也”、“相如賦仙,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等等,尤其在文章的第二段,更是推崇曹丕的“文氣說”,認為“風”同作家個人的氣質有關。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推崇的是孔融的“體氣高妙”、徐幹的“時有齊氣”,“體氣”指的是人內在的性質,也就是志趣高雅精妙,而“齊氣”則是比較舒緩的文風,不同氣質的作家所寫出的作品也各有特點,這就是文人之”氣“所帶來的對文章風貌的影響。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氣”才是“風”呢?“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也就是說“風”的一個特點是“清”。這個“清”并不是白水一碗,無色無味的“清”,而是“思想感情要表達得痛快、爽利,但這不是滑口而過,不是膚淺,要使人越品味越弄”,而劉勰認為具有”清“這個特點的是司馬相如的《大人賦》,“相如賦仙,氣號凌云,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遒也。”劉勰稱贊《大人賦》“氣號凌云”,也正是因為漢武帝讀了以后飄飄有凌云之感,所以這里的“氣”應該是一種流動暢達、貫通上下的狀態。而“風”的另外一個特點是“顯”——“深乎風者,述情必顯。”也就是說講究“風”的文章,可以使情志鮮明,既然“顯”是使得情志鮮明,這就又把“風”同另一個概念——情聯系在一起了。關于“情”與“風”的關系,歷來也是眾說紛紜的。
2 “風”與“情”的關系
黃侃在自己的書中反駁過紀昀關于“氣即風骨,更無本末”的說法,他認為“今試釋其辭曰:風骨即意與辭,氣即風骨,故氣即意與辭,斯不可通矣。”黃侃認為“風骨”指的是意和辭,“文之有意,所以宣達思想,綱維全篇,譬之于物,則猶風也。文之有辭,所以攄寫中懷,顯明條貫,譬之于物,則猶骨也。”黃侃所說的“意”指的應該是文章所蘊含的思想情感,而“辭”則主要是指使得文章呈現出剛健精煉風貌的言辭。在筆者看來,黃侃更多的是認為“風”與“情”相關,指的是文章思想內容的東西,而“骨”則側重于遣詞造句、文辭等形式的東西,黃侃的“意”、“辭”兩分說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認同。
劉永濟在黃侃的基礎上提出了“凡篇中所用‘風’、‘氣’、‘情’、‘思’、‘意’、‘義’、‘力’諸名,屬“三準”之“情”,而大要不出情、思二者。”也就是說“風”不僅是“情”,即思想感情的東西,在情感中還帶有一絲理性的思考,“情思者,發于作者之心,形而為事義。”劉永濟的“風”是帶有理性思考的,屬于內容層面的情思,而且在劉永濟看來,“骨”是事義的代表,同“風”一樣,同屬于內容層面,并且能把事義貫通全文的就是“風”。還有一種觀點是中和了黃劉二人的想法,認為“風”指的是作者的精神和志氣,“志氣之符契(符號)是對‘內’——作者自己——而言:‘風’是作者精神、志氣的表現。
可以看到這三種看法其實都在把“風”同“情”、“情思”、“志氣”這些思想內容層面的東西聯系在一起,更多的是指作者個人生發出來的思想情感,劉勰說:“思不環周,索寞乏氣,則無風之驗也。”這句話是從反面來說沒有“風”的表現,可以看到兩個關鍵詞——“思”和“氣”。筆者自己的觀點是“思”可以解釋為“思慮”,也可以解釋為“思想感情”,如果解釋為“思慮”,則更多地帶有理性思考的成分,而如果解釋為“思想情感”,那么“風”可以和情感、志氣這樣的概念聯系起來解釋。至于“氣”,這里解釋為“生氣”更好,就是文章所表現出來的勃勃生機。在現代看來,要評價一個文章的好壞,有很多方面,比如思想感情、內容結構、前后流暢等等,但劉勰只是假借一個虛的概念“風”,就將這些都涵蓋在其中,你不能具體說“風”是什么,但是你總覺得它包含的內涵極其廣闊、無所不包,古人的概括能力誠然是一流的,簡單一個“風”字,卻是說不盡也道不明呀!
3 “骨”與“勁健”
“骨”這個字的解釋同“風”一樣,也是百家爭鳴、各執一詞。今存最早對《文心雕龍》作出評點的楊慎認為“引‘文明以健’,尤明切。明即風也,健即骨也。詩有格有調。格猶骨也,調猶風也。”黃霖在解釋楊慎的這一觀點時認為“這里用了一連串的比喻來說明了‘風’與‘骨’的涵義,即文章外在風貌的生動明艷和內在品格的勁健高美”,筆者是比較贊同黃霖的這一解釋的。“骨”也是劉勰假借外物來喻比的一個概念,劉勰自己也說“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既然言辭需要“骨”,那么就說明“骨”是一個形容文辭特點的東西,“骨”給人的印象是有力度的、剛強的,在閱讀鐘嶸的《詩品》時,筆者注意到有一種風格被稱為“勁健”——“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云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鐘嶸在《詩品》中提到的這個“勁健”,氣貫長虹,彌散于天地之間,似乎是匯聚了天地間的力量,因為“勁”所以“天地與立”,“即天地亦可與之并立,如天地之終古不,因為“健”所以“神化攸同”,“則天地之存神造化,亦無不與之同功。”郭紹虞解釋的“勁健”,讀起來讓人覺得不是尋常文章所能達到的境界,但是最后兩句還是有一定的啟示的:“期之以實,御之以終”,在郭紹虞看來就是文辭要充實,情感要真摯,并且作者要始終秉持這一原則。
鐘嶸和劉勰一樣都推崇“風力”,他在《詩品序》中說“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也就是說好的詩歌要以風力為基礎,還要有好的文采,其實劉勰也在《文心雕龍·風骨篇》中提及“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用鷹隼和野雞分別來比喻“無采之骨”和“無骨之采”,同樣說明了兩者的重要性。但是和鐘嶸不同的是,劉勰并不是特別在意文采的作用,而鐘嶸卻是個極其看重文采的人,以至于對于曹操、陶淵明所寫的詩歌都認為是下品和中品,就是因為覺得他們詩歌語言太過于質樸,所以對文采的重視程度,二人還是有差別的。文章有“骨”就是有了一個站得住腳的框架,好的文章得端得起架子來。架子同血肉不一樣,血肉是沖盈文章,使之飽滿、鮮艷,而骨架是支柱,使之挺拔頂立,所以在筆者看來“骨”更多的還是力度的作用,是力在文章中的美學體現。而筆者將“骨”與“勁健”相聯系,就是看到了兩者之間同力的關系的相似之處。當然劉勰的“骨”是講作文章的一個要求,而鐘嶸的“勁健”則從更宏大的視角闡述文章的一種風格,讀起來感覺很是玄乎其乎的意味,不如劉勰的實在通俗。我們都知道劉勰推崇的風骨指的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建安風骨”,那么劉勰為何如此看重“建安風骨”呢?這大概還要從“建安風骨”本身來探究。
“風骨”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古代文論范疇,這里所列舉的各家觀點都只是龐大論述中的九牛一毛。傳統文論具有的模糊性、流變性、整體性等特點,而這些特點使得很多基本的范疇概念有著不同的內涵和外延,“風骨”也是如此,“除‘風骨篇’外,《文心雕龍》書中其他篇章運用‘風’、‘骨’這兩個名詞的地方頗多,它們的涵義和‘風骨篇’并不完全相同。”當然,在本文中談論的“風骨”還是以《文心雕龍·風骨篇》作為主要依據來提出一些筆者的想法和見解,算是讀書之余的一點思考。
施宇(1993-),女,漢族,江蘇南通人,揚州大學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文學理論。
I206.2
A
1672-5832(2017)12-003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