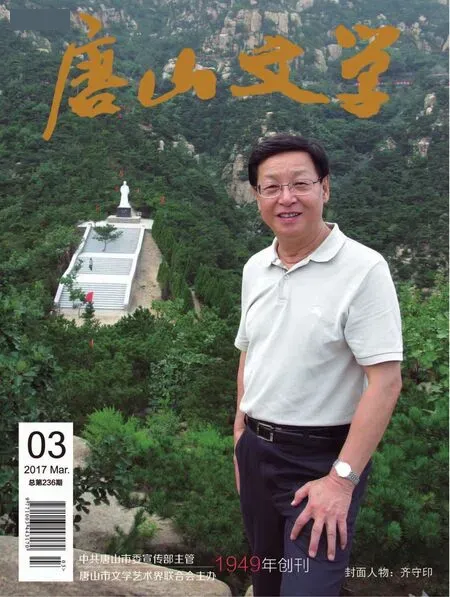與“拾”有關的記憶
張巧玲
與“拾”有關的記憶
張巧玲
童年的秋天,門前是一望無際的青紗帳,可此時不見了綠的蹤影。于是,想重拾童年的記憶。
(一)拾麥穗
那時還是公社化時代,每到夏收放忙假時,孩子們除了割麥、拉麥以外,最常干的農活就是拾麥穗了。大人孩子一字兒排開,在拉走了麥捆子,用大鐵耙摟過的田里,撿拾遺漏的麥穗。拾麥穗的時間往往是在早上,經過一夜露水濕潤,麥稈不再那么干脆,麥粒也不會因為撿拾而掉落太多,而這時硬硬的麥茬,也會被露水沾濕。早上拾麥穗時,也會把褲子和鞋弄得濕漉漉、泥乎乎的。
拾麥穗時,需彎下腰。有的人一只手拾起后,再麥穗朝上,麥稈朝下,倒到另一只手上,才能擺放整齊。有人技術熟練,左右手同時拾,拾起來后,就已在兩手中同時擺好了順序。拾到一把攥不住了,再在麥穗根部,抽出幾個麥稈捆扎起來,放在自己所拾的那一行,拾完后,再返回把自己拾的收集在一起。
一大早,往往是一群人,要趕著拾好幾塊地。在從這塊地趕往下一塊地時,或者把拾好的一把把麥穗打成捆抱著,或者左右交叉,裝在大籃子里提著,直到早晨收工,才拿著所拾的麥穗,來到麥場。在緊挨麥穗處剪掉麥稈,稱出所拾麥穗的斤兩,再按照斤兩,折合出每個人所掙的工分。那時候,農業社是按照工分多少來給社員分糧食的。這一大早,誰拾的麥穗多,掙的工分自然多了,心里也自然會美滋滋的。
拾麥穗并不是個簡單活,沒被大鐵耙摟走的麥穗,往往散落在將近半尺高的麥茬縫隙里,那些麥茬都是用鐮刀割的。割麥時,先伸出鐮刀摟住一撮,攬到懷里,再用另一只手摟住,把鐮刀放到根部,從遠到近割倒。因此那些麥茬口大多是一邊上翹的橢圓型,那上翹的鋒利茬口,就像一把把小尖刀,經常會劃傷撿拾麥穗者的手指,也會把手指劃得滿是倒簽,紅彤彤的。還有麥穗的芒刺,也經常會在胳膊上拉出道道血梁,汗水、露水一浸泡,那些傷口、倒簽、血梁,都會有熱辣辣的蟄疼感。
給隊上拾麥穗,雖然你追我趕,緊張些,但一大群人說說笑笑,卻也熱鬧。
等所有的小麥都收割、撿拾過,麥子全上場了,開始犁地播種時,人們就可以到麥茬地里,為自己家再去撿拾粗心的拾麥人,遺漏下的麥穗。那時,每撿到一個麥穗,也都會像撿到金元寶般高興。拾到的這些麥穗,可以拿回自己家里,曬干后,用棒槌敲打出顆粒。那時候,能吃上麥面饃,就像是過年了,自然給自己家拾麥穗,也就會像過年般喜悅。
這些拾麥穗的苦樂,如今也都成了難忘的美好回憶。
(二)拾豌豆
為了增加夏作物的產量,也為了給在農忙時節辛苦勞作的牛馬們上些料,也就是今天說的增加些營養吧,那時往往要種上些豌豆。有時單獨種,有時是與小麥套種。那個年代的孩子,在豌豆沒有成熟時,大多都有過偷豆角的經歷,我也不例外。小孩子們直接把汗衫統在褲子里,把偷的豆角藏在汗衫里,鼓鼓囊囊地從豆角地里走出來。
孩子們往往在晚上偷豌豆,因為到豆角能吃時,隊上就已派那些厲害的村民去看護了,那些人往往比較彪悍,白天孩子們怕挨打不敢去。晚上就不同了,天黑、地大,四面八方都可以進地,誰也看不住。不只是孩子,大人們也常常會偷的。
記得當年大批判時,大隊里有一幅批判地主(我同學父親)的漫畫,給他列的一條罪狀就跟豆角有關。畫面上他提著一個大籃子,偷了滿滿一籃子豆角,很得意地說:“人吃豆角,豬吃皮。”
吃豆角是件很過癮、很解饞的事情。嫩些的,直接從下角上分開,剝出整齊排列的豆子,放在嘴里咀嚼,一股甜甜的清香讓五臟六腑都舒坦。然后再把皮從豌豆把跟前折疊,輕輕一拉,不能吃的透明內皮就被去掉了,再把綠瑩瑩的兩塊長方形外皮,也叫“掌”放進嘴里(那時候吃田里長出來的東西,人們還沒有清洗的習慣)脆生生、甜滋滋、清爽爽,真算得上是美味佳肴了。老些的,拿回家里,即使清水煮熟了,也是很解饞的,更不用說用五香粉煮的了。
畢竟豌豆田很大,孩子們偷豌豆吃,也只是在即將成熟那幾天解解饞,最終豌豆還是要成熟的。割豌豆的時機是很講究的,尤其是割那些和麥子套種的豌豆更要講究些。成熟的豌豆夾,亮晶晶的,熟過了,收割時很容易炸開,收割套種的豌豆,還要顧及到麥子,要等到兩種作物都熟得差不多了再收。
有一次,凌晨四點,生產隊敲響了鐘,十二歲的我,也和大人一起黑蒙蒙地去割豌豆。選擇這樣的時間,就是因為有露水,豌豆莢還不是太干,相對炸開的少些。即使選擇的時機再好,可也總有成熟的豌豆粒炸落在地里。
那時候收割完豌豆后最盼望下一場雨,夏收時,也多半會下雨,等雨停了之后,往往沒有什么農活干,孩子們就拿上大茶缸,或者小盆子,甚至小籃子,去拾被雨水泡脹的大豌豆粒。
豌豆最常見的顏色是青綠色,也有白色,偶然也會有紅色。為了怕把布鞋弄濕弄臟,有雨鞋的穿上雨鞋,沒雨鞋的就光著腳,走進有些泥濘的豆麥套種地,顧不得麥茬扎腳,睜著圓溜溜的眼睛,去尋找那綠瑩瑩、白胖胖的脹豌豆。在孩子眼中,這些脹豆豆就是解饞的上等美味呢。有時候運氣好的話,能發現一堆脹豆豆,那里肯定是割下的豆麥捆曾經存放的地方,專注而又興奮地蹲在地上,飛快地撿拾著,眼看著拾到的脹豆越來越多,心情也越來越好,尤其是想著吃豌豆的香味,更是要垂涎三尺了。
這些脹豆拾回家后,用清水淘凈泥巴,一般是把豌豆和五香粉、鹽放在鍋里煮熟吃。家里條件好些的,可以放些蔥姜蒜,用油炒熟,一股油香味,吃起來才過癮呢。雖然現在也常做豌豆炒蝦仁,但總覺得沒有那時撿拾來的脹豌豆煮熟或者炒熟了好吃。
好吃與不好吃,可能與當時的愿望與衡量好吃的標準有關吧。在饑餓的年代,能吃飽的食物就是理想的美味了。在溫飽的年代,大概是稀奇、稀罕、可口的東西才是美味吧!
(三)拾柴火
小時候嘴特別饞,可要把生的做成熟的,離不開柴火。家里富裕點的當然可以燒炭火了,可那時候農民手頭很少有錢。一年從生產隊分得的麥草和玉米桿是有限的,平時烙餅、攤煎餅、蒸涼皮、打攪團,做這些需要很好掌控火候的食物時,才舍得燒麥草,那些玉米桿留作冬天燒炕,燒水、做其他的飯食,只能靠拾柴火了。
小時候住在平原,離山遠些,拾柴火相對難些。
春天,在小麥剛剛返青時,邊挖野菜,邊拾玉米根;夏天,剛割過麥子,在農忙空隙,到麥地里去拔麥茬,或者去拾犁地時翻起的麥茬;秋天,去拾道旁楸樹落下的像蒜苔一樣包裹著種子的長穗,掃樹葉;冬天去河溝、田畔旁撿拾被風刮下的枯枝。
小麥、玉米是關中的主要內作物,麥茬、玉米根又是我小時候所拾的主要柴火,它們被翻出土地時,連著泥土,要拾走它們先要把它們與泥土分離。麥根短小,連接的泥土相對少些,輕輕磕碰,就能抖落,所以夏收完或犁地時,就可以拾。而玉米根深且大,秋季又多雨,連接的大泥塊不易抖落,所以玉米根一般是在初春還沒起身的小麥地里撿拾,那時候經過冬雪的酥松,泥土與根已很好剝離了。
道旁、河溝、田畔的樹木,是秋冬季柴火的來源,什么季節看見那些樹木都倍感親切,它們就像與我共患難的朋友,感謝它們賜予我們、給予我們溫暖的能量。可是那些像結著長長蒜苔的楸樹,那些在夏秋制造陰涼的楸樹,早已在拓寬改造道路時全軍覆沒了,那些河溝、田畔的樹木也在城市化進程中漸漸消亡著。
這些柴火,做飯、燒水、取暖,成為貧窮、平淡、平常的日子,所不可缺少的物品。這些拾柴火的經歷,也是童年生活中很充實的記憶。
與拾有關的記憶還很多,比如拾紅薯、拾棉花、拾玉米,這些記憶,對于今天的孩子來說,也許都是天方夜譚吧,但對于我們來說,也都是刻骨銘心的記憶。
回到童年生活的家園,白天照顧年邁的父母,晚上坐上童年睡過的土炕上。雖然有線電視就在房間,手機也可以上網,外邊的世界隨時可以聯通,可還是打開攜帶的筆記本電腦,在家園里,輕輕敲打著,重拾童年的記憶。
在敲打這一份記憶時,心中也或多或少有些傷感,我不知道,還能這樣,在家園里生活多久。附近的很多村莊已經拆遷了,我家隔壁就住著拆遷戶,老人孩子們尤其心神不寧,不久的將來,我的家人和鄰居們不同樣也會這樣?他們失去家園后,四分五裂地寄居在別處,從此那些祖祖輩輩生活著的地方,就再也不屬于他們了,這樣的命運,要不了多久,也許會降臨在我的鄉鄰們身上。雖然我們家在這里落戶不到40年,可這方水土畢竟養育了我,在即將失去時,我又怎會不依戀?
重拾這份與“拾”有關的記憶,讓在即將失去的土地上,曾經度過的那些歲月,在心海留痕,也算是給自己留下一些念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