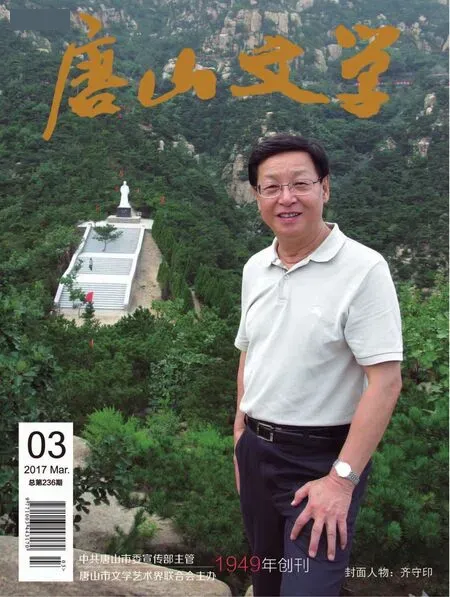鐵
耿善軍
鐵
耿善軍
家里曾經有一些鐵,不,應該說是鐵制的農具,大大小小、長長短短,擺放在門坊過道的墻邊。
在墻上的石頭縫里,楔了幾根木撅子,上面除了掛著一長辮大蒜,幾串紅紅的辣椒,還掛著幾把鐮刀,彎彎的像月芽兒。再加上摟耙,鐵锨,竹掃帚,滿滿地占據了一間不怎么寬敞的過道,擁擁擠擠的就像老老少少的一戶人家。
初春或者初秋,要收集起來檢查一下,找出磨損得禿了苗刃的镢頭,退去木把,去鄉集上的紅爐上重新添鋼,濺火鍛造。
姊妹兄弟排行,大哥是最壯的勞力,承擔起家里最沉的力氣活。那把板镢頭刃長肉厚,理應歸大哥使用。姊妹兄弟里,大哥個子最高,在一堆的農具里,大哥用的镢頭木把也最長。有一個上手的份量,再加上有一個合適的長度,一把镢頭在大哥的手里施展的呼呼生風……
紅爐是很洋氣的稱呼,方言里的紅爐師傅被稱作鐵匠。
屋漏趁天晴,耪鋤磨鐮不曠工。
在集市的一角,有煤炭的煙味飄過來,這是鐵匠師傅早早地點火生爐,叮當當當,生意開張了。
大一些的鄉集上紅爐會有兩家,小一點的鄉集就只一家。四里八下的莊稼人會早早地送來長長短短用禿了的镢頭,那個有點駝背的干瘦老鐵匠停了叮叮當當的小錘,用一把長鉗子夾著的镢頭苗重新插進炭火里;掄大錘的伙計放下大錘,用肩上的毛巾擦一把額上的汗水,在旁邊的炭匣子里鏟起兩鏟灑了水的煙煤焙在火爐里,接著拉起了風箱,呼噠呼噠。一股水氣和著一股子濃煙升起來,而炭火苗似乎是憋了許久的樣子,騰地一下躥起老高……老鐵匠解下腰里的皮圍裙,從后腰帶上抽下煙鍋,摁滿土煙末,隨手拾起一根樹枝,在紅爐的火里點著,又把煙鍋點上,深深地吸一口,一口濃煙接著呼出,就像那炭火剛起,似乎也是憋了很久的樣子。
然后,老鐵匠朝向旁邊看呆了的莊稼漢問:大鋼還是小鋼?
我的村子里也有一戶鐵匠,一個有著兔子豁唇的鐵匠。
據說,打鐵的都有一雙鉗子般的手,這是因為握著鐵錘千錘百煉的結果,也沒人敢欺負打鐵的,你要是被他抓住,一把就能把你的骨頭攥碎了!
趁著農閑,這家鐵匠就在村子里的學校院前擺弄開家伙什兒。五、六把長長短短的火鉗一溜布開,鐵砧子坐在高高的木頭墩子上,旁邊是盛著濺火的清水扁扁拉拉的鐵皮臉盆……學校的位置是在村子的中心,放電影的,耍猴戲的,有時還來一位外鄉的貨郎,還有剃頭的匠子;等剃頭匠把一塊看不清底色的布塊從前面圍起你的脖頸,左手便按住你的腦袋,右手在你眼前晃著鋒利的剃刀,也問上一句:大?還是小?
小時候五分錢剃一個頭,不分老少年幼。
我是不稀罕了那打鐵的叮當聲,除了好奇著老鐵匠是怎樣用豁了的嘴唇怎么才叼的住那桿長煙鍋,更關心的是,要鋼好的镢頭最后的那塊月芽兒般被鑿下來的封口鐵。當然,我只在遠遠地看,不讓他看出來我觀察他如何抽煙的心思——恐懼著自己細胳膊細腿,惹惱了經不起他能攥碎骨頭的手。
眼看著蹦起來小鐵塊落在了旁邊的地上,我和伙伴們一齊去搶,抓在手里,手立刻被燙熟了一溜,疼得好幾天睡不好覺。
有了搶來的那塊鐵,把它磨尖了頭,除了裝在褂子兜里隨時掏出來顯擺,還可以挖野菜,可以摳墻根縫里的螞蟻窩,可以在課桌的面上刻上我的名字,還可以在上學路上的一塊大石頭上刻:誰再罰我站誰是小狗!
我看不慣王二蛋老拽班里女同學的辮子,可我打不過他,這回我也一起刻在石頭上:王二蛋也是小狗。
有一天放學的時候,我打算再去村里鐵匠的爐旁,再豁上一次手被燙去搶一塊鐵來,可是遠遠地望見,那個豁唇的鐵匠被人們架上車子推走了——后來聽說,他的一只眼睛被蹦起來的封口鐵燙瞎了!
我的那塊磨尖了頭的鐵就裝在褂子兜里,伸手就能摸著,我打了一個激靈,立刻掏出來,使勁地扔進河里。放學的時候,走過那塊大石頭旁,找塊石片刮去了那上面刻的字。
再一次見到村里那個鐵匠的時候,他的左眼上蒙了一塊橢圓的黑布,一根布條漫過頭綁在腦袋后面,就像電影里叫做“獨眼龍”的黑社會老大。不知道黑社會老大為何不裝一只義眼,他們那么有錢,帶著那么粗的金鏈子,應該不是付不起一只假眼的錢吧?后來才知道那是故意的不裝,好顯示他的手有多辣、心有多狠。而村子里的老鐵匠的確是裝不起一只義眼,后來他摘掉了那塊黑布,一只眼睛的位置就在那里空空地窩窩著。
從此,我再也不忍心去瞅他如何把長煙鍋從嘴唇的這邊調弄到那邊。從此,他不再打鐵,剩下的一只眼睛瞄不準要鋼的镢頭哪邊該厚,哪邊該薄。
再后來的鄉集上,也不見了那兩家生著紅爐的攤子。耕種有了機械,镢頭和鐮刀已經不再是開山墾荒和收割的主要家把式了。
在家的大門過道里,也不見了那一堆鐵制的長長短短的“人家”,它們靜靜地消失在了時光的長河里。
我和哥哥,也不再一心想著怎么把地種好,荒了就讓它們荒了吧,再怎么精耕細作也賺不了幾個錢,于是抓一把土揣進懷里,遠遠的離開家,外出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