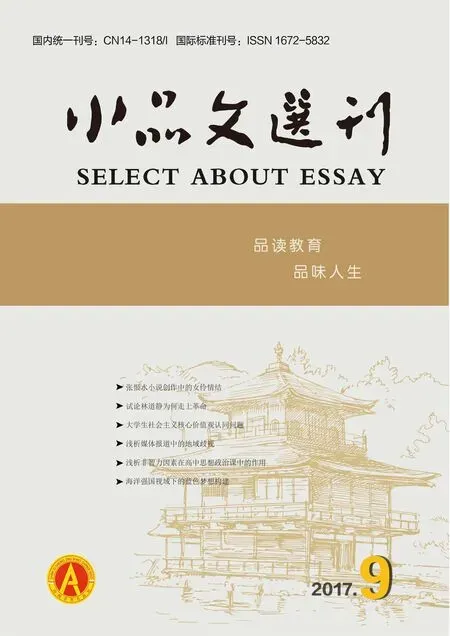咖啡館與海派文學
王儷穎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100000)
咖啡館與海派文學
王儷穎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100000)
毫無疑問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在今日上海懷舊熱潮中掀開了嶄新的一頁,他以一種不同于以往鄉村型范式對城市偏見的現代性視角,確立了一種都市文化批評的新范式。李歐梵的開創性意義在于,通過重構都市文化景觀來關照上海的現代性,作者在書中用了不小的篇幅集中論述了承載現代性物質性的公共空間:外灘建筑、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公園和跑馬場、“亭子間”等,種種景象作為現代性的物質載體,如何參與構建了城市現代性的物質想象,首次在城市文化研究中得以隆重亮相。在海派作家的筆下,電影院、咖啡館、舞廳、有軌列車等等已經進入小說并具有獨立的審美意義。這其中,相對于其他西式風格的休閑場所,咖啡館天生與文學有著密切聯系,“咖啡館”的獨特氣質與氛圍受到相當大一部分文人的歡迎,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文學作品的表達滲透出各異色彩。本文以咖啡館與海派文學創作之間的關聯為研究對象,在勾畫出上海租借文人休閑娛樂文化生活的同時,著重探討咖啡館這一現代性想象載體在海派的都市想象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1 咖啡館的空間文化特征
咖啡館的出現雖然是西方殖民化帶來的產物,然而在與本土城市經濟發展、市民消費習慣相結合方面,其繁榮程度已然超過了傳統文人消遣娛樂的茶館,并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茶館的改造。在殖民化整體時代背景下,咖啡館被視為時尚的、文明的、現代的休閑場所,相比之下本土的茶館要遜色落后的多,茶館是在何種程度上適應新興都市文化的要求進行改造或者咖啡館引進中國大陸后如何與中式本土特色相結合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筆者關注的重點是咖啡館作為帝國主義殖民化的產物是在何種程度上被視為西式先進文明的象征,知識分子是在何種程度上接受并享受著這種復雜矛盾的產物,在這個接受融合的過程中,咖啡館作為作為西方殖民國家日常消費經驗及其中所蘊含的等級秩序及權力關系又是被如何淡化及消解。
1.1咖啡館的空間特色
咖啡館最初在上海的設立是為了適應西方人的休閑娛樂的生活方式,而后慢慢融入逐漸被上海市民所接受,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咖啡本身這一新鮮事物還是咖啡館的建筑裝修風格或者咖啡的飲用方式,這對于傳統中國人來說都是極大的新奇及刺激,構成了中國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個窗口。咖啡館成為西方國家以其飲食文化入侵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一環,其在本身具有的鮮明的西方異域色彩的同時,也在不斷適應著中國本土地方特色,無論是外部建筑設施或是內部裝修風格上,均暗含著中國人傳統消費習慣,這種結合的產物便是使得30年代咖啡館在上海,不僅僅是市民消費娛樂、聚會聊天的首選場所,更是成為炫耀性消費空間和身份展示的場所,成為一道鮮明的文化符號。咖啡館在中國扎根生存,呈現出了一種全新的都市消費空間,而這構成了流光溢彩的“都市風景線”中重要的一環,進而極大的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望,制造出了人與物、人與人之間巧妙的關系,成為海派作家表現都市人性的重要背景。
1.2咖啡館的文化特色
咖啡館這種與文人天然的密切關系,與其自帶的文化特色密切相關。在30年代的上海,咖啡館的異域風貌同新型文人的外在需求、心理需求達成一種巧妙的平衡,正是在這種平衡下,咖啡館作為殖民化與現代化并存的矛盾被文人淡化,其自身所蘊含的權力關系等級制度被消解。不同于其他場所的消費性、商業性,咖啡館與生俱來的是注重藝術性、高雅性、精英性。這自然而然地迎合了文人的心理需求。在這里,寧靜浪漫的消費氛圍,輕柔舒緩的音樂,文明典雅的社交禮儀,精致的擺設餐具,溫柔動人的女侍,悠閑私密的交流氛圍,作為具有沙龍性質的社交場合,咖啡館的寧靜優雅為文人們提供了交流的私密空間。在這里他們能夠激發靈感,交流思想,表達見解,興趣相投的文人知識分子自然而然地組成不同的文化圈子,成為文學團體形成的重要中介。應該說,其在活躍市民生活、促進社會交往、培育市民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自然在文人中廣受歡迎。而這一切恰好淡化了知識分子面對殖民化與現代化并存上海時的矛盾心態,咖啡館所自帶的文化特色,在迎合新型文人對西方現代文明推崇的同時,也暗含了幾千年來傳統文人化的需求。
2 咖啡館與文學互利共生
作為城市重要符號的咖啡館為作家提供了創作的素材和靈感并成為文學創作的重大主題這是毫無疑問的,在30年代的上海,咖啡館的引進推廣對文學創作起到了極大的影響,具體表現為:首先,從文學生產過程來看,在30年代上海文人的休閑生活中,咖啡館毫無疑問充當著文學沙龍的角色,私密安靜的交流空間,熱情動人的溫柔女侍,精致典雅的禮儀體態,志同道合的文學交流……這一切都成為文學交流、創作的重要場合;其次,咖啡館作為承接文人現代性想象的物質載體,其在促進上海文人生活方式的歐化的同時,也見證著中國傳統文人從鄉土走向都市,從傳統仕途經濟走向以市場消費、公共交往為主要特征的城市生活;再次,咖啡館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文學創作所需要的常態化的公共空間以及被審美化的日常浪漫情懷,即是前文所言咖啡館自帶的文化屬性與特定時代背景相結合,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租界文人強烈的獵奇心態及民族道德意識之間巨大的矛盾與不適,換言之,即是咖啡館帶來的精神沉醉,使30年代的文人既甘之于生活常態的異化,又寄望于通過構筑精神家園來拯救失落的自我,這道“都市風景線”成為了新型文人尤其是海派作家棲息的精神港灣。
3 海派的咖啡館敘事
3.1咖啡館里的異域想象
或許是因為多數作家有親法經歷,或許是因為法租界的消費性、娛樂性更為突出,在這里帶有濃郁法國風情的咖啡館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出來,帶給人們國際化與現代化的浪漫想象。對于當時的作家來說,從文學作品切入,無疑是通過咖啡館的異域風情實現自己的異域想象最好的方式。咖啡館的特殊之處正是在于,它代表了成熟、優雅、精致的西方式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對于海派作家而言,咖啡館已經成為筆下人物感受法式生活方式的重要標志性象征,作者筆下的人物頻繁地出入咖啡館消遣打發時間,感受法國咖啡文化,體會法國人獨有的悠閑散漫的生活態度與生活方式成為海派作家筆下的常態。穆時英《貧士日記》雖以“貧士日記”為表述對象,而“面對著一杯咖啡,一支紙煙,坐在窗前,浴著陽光捧起書來——還能有比這更崇高更樸素的歡樂么?”“聽著那樣的話,心境雖然暗淡了些,可是為著這樣晴朗的冬晨,終于喝著那杯淡味的陳咖啡,依然地讀著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了。”①咖啡成了感受西方文人化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海派作家以咖啡館為幻象消費性空間進行了現代性想象,從中使消費主體完成了對法式現代都市的浪漫想象。
3.2人際交往的空間需求
30年代上海,拋開了種族、階級、歷史的差異,人與人之間剩下的只有平等的精神性的交流,此種情況下,咖啡館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作為一個人際關系逃避與結識的最佳選擇,一個既能享受孤獨又能充分交流的完美場所,一個無論休閑還是會談的交流場合,咖啡館不可避免的成為海派作家描摹現代化都市的重要場所。具體到文本中,劉吶鷗《游戲》故事發生的場景設置在公園、咖啡店和旅館,葉靈鳳《未完的懺悔錄》前四章,徑直用了三處商店、酒樓與咖啡店的名字為題(別發書店、新新酒樓、沙利文),拋開了私密性和隱蔽性,作為公共性交往空間,咖啡館除了滿足人際交往的空間需求,也提供給了文人們精神棲息地。現代都市充滿著欲望的物質,人與人的關系變得簡單而直接,丟失的確是人際交往中的那份親密放松,宣泄,多的是異化感與孤寂感,這種背景下,咖啡館成了人們擺脫這種異化、混亂情緒的重要選擇,而這一切,亦是海派作家表現的重要。
3.3物欲都市的消費性表述
對于30年代海派作家而言,一方面感受著高度發達的現代物質性文明,相比于開埠之初的冷漠與抵觸,30年代的上海市民已經充分認可西方化的現代生活生產方式,人們已然將對現代文明的各式禮儀式崇拜轉化到現實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海派作家進行文學創作在文本中會構造出眾多現代生活的消費場景,在這種背景下,海派作家的筆下自然充斥著大量的“都市風景線”:劉吶鷗的小說多取景于現代都市特有的公共社交場所,跑馬場、舞廳、咖啡館、戲院,盡情展現著現代都市特有的光感、色彩;葉靈鳳、黑嬰等的小說創作中,也都將故事的發生聚焦于現代生活的滋生地——咖啡館、酒吧、舞廳、電影院、跑馬場等等現代都市新型娛樂場所,葉靈鳳、黑嬰的文學創作往往也離不開“沙利文”,咖啡館、酒吧、舞廳等極具代表性色彩的消費場在成為新派文人日常消費娛樂的常住地的同時,也成為了作品的重要書寫對象,上海高度發達的現代物質性消費,成為了海派文人筆下重要的書寫對象。
總之,以咖啡館、舞廳、電影院等等現代性物質載體為標志,海派作家開始從都市文化的角度來想象上海空間、建構上海現代都市文化,上海便成為國人理解現代性一個永久性的文化符號與文化印記。
注解:
① 穆時英:《俄商復興館》,《穆時英精選集》,中國書籍出版社
I20
:A
:1672-5832(2017)09-01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