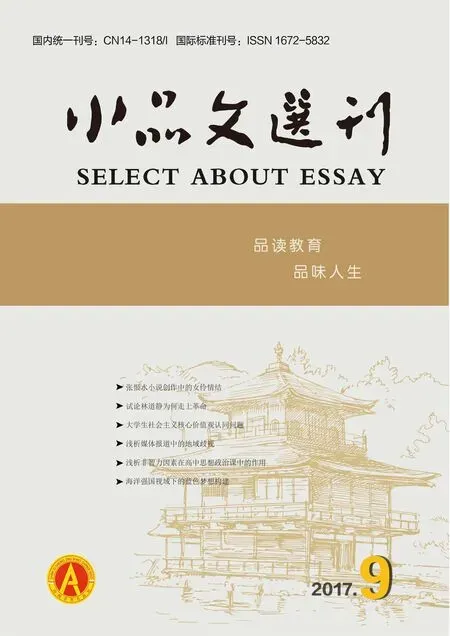淺議“六書”與“三書”
許文靜
(內蒙古師范大學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淺議“六書”與“三書”
許文靜
(內蒙古師范大學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六書”作為最早的研究漢字構造的理論,至今已有千年的歷史。經過后人不斷的改善與再解釋,已逐漸成為了比較完整而系統的學說。但是,這個理論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于是出現了唐蘭、陳夢家、裘錫圭等學者,在“六書”的基礎上,嘗試建立一種更加完備的新的理論,來更好地歸納漢字構型系統,本文簡要地歸納了這兩種學說的內容,并簡單地談談二者之間的關系,希望能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六書;三書;漢字
1 “六書”的提出
漢字是一種古老的自源文字,其產生時間應當在夏朝以前,但是研究漢字的萌芽卻是從春秋時代才開始出現的。當時對文字的考釋,多散見于表達政治理想、哲學思想的著作或記載歷史事件的文獻中,例如《左傳·宣公十二年》:于文止戈為武。但是這種零散的解釋并不成熟,也不成系統,并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但我們仍然能從中看到古代學者以形體為基礎的字義考釋的雛形。《周禮·地官·保氏》中首次出現了“六書”的名稱,“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1]但是并沒有具體闡釋其內容。
直至漢朝,班固、鄭眾、許慎等人才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六書”的說法,盡管名稱和次序均有差異,但是為傳統文字學的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后世持“六書”觀點的學者,基本上都在沿著這一條思路不斷向前探索。
一曰象形。這一類漢字保留了大量原始圖畫的特征,對事物進行客觀的描寫,對象多是肉眼可見的客觀事物。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舉了“日”、“月”兩例用以說明。
二曰指事。就是為了突出事物的某一特點,在象形字的形體上標注記號。例如“上”、“下”、“本”、“末”等字。
三曰會意。即會合兩個象形字的意義組成一個新義的造字方式。如《左傳》中所舉的“武”字,本義是“用武器打仗”,于省吾在《釋武》一文中解釋得非常明確:“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象形”是“指事”和“會意”的基礎,是原始圖畫向漢字演變的重大成果,也是漢字孳乳的重要的材料。之后出現的形聲字,則在假借字的基礎上,使漢字煥發了新的生機。漢字正式由純表意文字,轉為了可以記音的注音文字。
至于“轉注”和“假借”,則歷來爭議較大,總體上是圍繞“造字”和“用字”的爭論。清代的戴震段玉裁師徒堅持認為這是漢字的兩種“用字之法”,并提出了“四體二用”之說,影響巨大。但是到近現代,也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轉注字不是用字之法,而是漢字自身發展和延續的一條重要的法則,是漢字系統趨于完善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唐蘭與“三書”說
在“六書”研究不斷向前演進的同時,也有不少學者能夠跳出“六書”的圈子,從新的視角對漢字系統進行歸納和解讀。唐蘭在他的《中國文字學》一書中,指出了當前為大多數人所認可的“六書”系統的不足。
首先是指事。唐蘭認為這種造字方法只是在象形字中引入了一些符號,只能算是圖畫文字的一種,而不應該單列一類。其次是會意,會意是會合兩個形體的意義表達一個新義的造字方法,雖然與象形、指事有所不同,但仍是表意字的一類。形聲字在六書系統中是有著明確界定的,但是其中的一些“亦聲”字,并不能很好地和其他造字法(如會意)進行區分。至于轉注和假借,則應該只是用字之法,而不應列入造字的范圍中。
接著,唐蘭在書中又系統地論述了自己對于漢字系統的獨到見解——“三書”。他認為,根據漢字形、義、音的特征,應該分為象形、象意、形聲三種。
象形字在唐蘭所歸納的“三書”系統中的劃分是非常嚴謹的,不存在獨體象形、合體象形之分,這一類字僅指獨體象形,保留了大量原始圖畫的特征。第二類是象意字,唐蘭指出,“真正的文字,要到象意文字發生才算成功的。”[2]與象形文字相比,象意字有了更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也有了更強的表達力,代表了中國文字發展的一個更高級的階段。但是這一個階段,仍然沒有脫離圖畫文字的影響。相比起來,形聲字在漢字系統中則占有更大的優勢,它的出現,代替了本有的象形和象意兩種方法,成為了漢字孳乳的主要方式,并一直延續到現在。
關于唐蘭新提出的“三書”說,學者所持的意見不一,既有支持者,也有批判和反對的聲音,不容置疑的是,唐蘭在“六書”基礎上為我們今后研究漢字系統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思路。更有一些學者,在唐蘭的基礎上對“三書”理論做出了新的貢獻,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3 “三書”理論與“六書”說的關系
文字為記錄語言而產生,語言又是一種用于交際的社會行為,它是不可能有著極為明晰的界限的,更不可能被量化成一個個中規中矩的孤立的個體。這就導致了“六書”說在劃分漢字結構的時候,有很多字需要用“某兼某”的方式去模糊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界限。
“三書”說,其實仍然繼承了“六書”的思路,只不過它把漢字結構進一步歸納,擴大了漢字構型理論的指代范圍,這樣一來,很多游離在“四體”之外、定性不明的漢字,最終都有了歸宿。要想讓一種理論能夠涵蓋更多的實際事物,最好的辦法并不是像鄭樵、朱駿聲、王筠那樣不斷細化原有的理論,力圖涵蓋所有的漢字,而是去歸并和概括已有的漢字構型理論,擴大該理論的外延。
唐蘭之后的裘錫圭等人,也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書”理論,其本質上都是為了用更為規整和簡潔的分類方式去整理和概括極為龐雜的中國文字系統。例如陳夢家,他將漢字分為象形、假借、形聲三類,并指出,“象形、假借和形聲是以象形為構造原則下逐漸產生的三種基本類型。”[3]而裘錫圭則將漢字分為表意、形聲、假借字,并在他的著作《中國文字學概要》中分列三章,具體地論述此“三書”的構成。可以說,“三書”說的出現,是在“六書”的基礎上對漢字系統的進一步歸納和整理,雖然仍有一些不足和局限性,但是仍然為漢字結構的探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嘗試,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 楊天宇. 《周禮》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 唐蘭. 中國文字學. 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1
[3] 陳夢家. 殷墟卜辭綜述. 中華書局. 1988
許文靜(1994-),女,漢族,碩士在讀,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字學。
H02
:A
:1672-5832(2017)09-00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