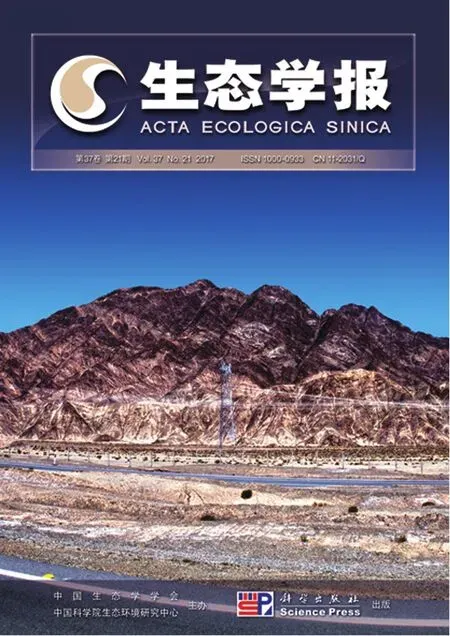關中-天水經濟區生態足跡變化驅動因素
楊 屹,朱彥臻,張景乾
西安理工大學, 西安 710054
關中-天水經濟區生態足跡變化驅動因素
楊 屹*,朱彥臻,張景乾
西安理工大學, 西安 710054
揭示影響關中-天水經濟區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因素,對建立節能型產業結構,尋求經濟與環境、生態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應用生態足跡和偏最小二乘法,在計算2005至2014年關中-天水經濟區生態足跡的基礎上,確定偏最小二乘法變量投影重要性和標準偏最小二乘法系數,比較了驅動因素的重要程度。結果顯示,影響生態足跡變化較為重要的驅動因素有第三產業增加值、國內生產總值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相比之下,常用耕地面積與全區人口數對關中-天水經濟區生態足跡驅動作用不顯著。為此提出將優化產業結構與優化能源結構有機結合起來、轉變能源利用方式、提升能源利用率、提高土地利用率、加強土地保護、提高土地生態承載力、引導低碳消費行為、推行低碳生活方式等對策建議。
生態足跡;驅動因素;偏最小二乘法;關中-天水經濟區
作為一種量化反映人類對自然資源使用狀況的研究方法,生態足跡將區域的資源與能源消費轉化為提供這種物質流所必須的各種生物生產土地的面積[1-2],已被廣泛運用于生態現狀與可持續發展的研究[3-4]。分析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因素有利于掌握經濟社會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從全國來看,2000至2010年間工業化與重化工工業化快速推進,工業主導了生態足跡的變化[5]。僅就能耗而言,一般認為工業能耗會遠高于其他產業,第二產業比第三產業對生態足跡變化的影響力大。由此提出了一個命題,產值或能耗占比大的產業是否對驅動生態足跡變化的貢獻最多。賈俊松的研究結果表明1954至2006年河南省生態足跡由第三產業主導,其中,運輸業對生態足跡變化具有顯著的驅動作用,不必要與無效率的運輸活動數量的增長大大增加了生態足跡[6]。寧夏是以“二、三、一”為產業結構特點的資源型重工業省份,但馬明德等的研究表明,2001至2010年寧夏第一產業對生態資源占用的彈性高于其他產業[7]。河南、寧夏都是以工業為主的省份,驅動生態足跡變化的產業都不是工業。從實際情況來看,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對交通碳排放與能耗有著顯著驅動作用[8],而且也推動著建筑行業的能耗增長[9],對生態足跡的變化具有顯著驅動作用。2013年以前,第二產業雖然在產值與能耗總量均超過第三產業,但應注意到,自1973年11月我國頒布第一個工業類環境標準《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以來,工業環保一直是國內環保政策的重點[10]。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近年來我國陸續頒布了《工業節能管理辦法》、《行業類生態工業園區標準(試行)》、《綜合類生態工業園區標準》、《蘭炭行業清潔生產標準》等政策,并且制訂了《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等文件。這些環保政策有效約束了第二產業的生態占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驅動生態足跡增加的作用。相比較而言,第三產業環保問題帶來的生態安全隱患不容忽視。2014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3年全國GDP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分別占比為43.9%和46.1%,第三產業GDP占比首次超出第二產業。在《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這一占比變為了40.5%和50.5%。那么,產業結構的轉變是否會帶來生態足跡驅動因素的變化呢?相比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資源需求量小、產生廢棄物少,是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產業[11],長期來看,第三產業的低碳發展有助于降低區域生態足跡[12],關中-天水經濟區(以下簡稱“關天經濟區”)是西北地區以第二產業集群為依托的國家級經濟區。自2005年以來,關天經濟區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占據主導地位。作為推動關天經濟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導產業,第二產業是否也主導著生態足跡的變化?其他因素對生態足跡的驅動作用如何?為此,結合關天經濟區產業結構與社會發展狀況,應用生態足跡和偏最小二乘法(以下簡稱“PLS模型”)探討影響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因素。
1 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關天經濟區處于承接東西、連接南北的重要戰略區位,轄區占地面積7.98萬km2,覆蓋陜西省的西安市、銅川市、寶雞市、咸陽市、渭南市、楊凌區、商洛的商州、洛南、丹鳳、柞水等部分區縣和甘肅省天水市。關天經濟區地處內陸,屬暖溫帶半干旱或半濕潤氣候,以渭河河谷為中軸線,北邊為陜北黃土高原丘陵區,南側緊鄰秦嶺山地。以秦嶺為界,北為黃河支流的渭河流域,南為長江支流的嘉陵江、丹江和漢江流域。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城市化、工業化成效顯著,2015年關天經濟區實現生產總值12872億元,人均GDP 43228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4785億元。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環境保護、資源消耗等問題。2005至2014年能源總消耗年均增長7.59%,“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和產業偏重化結構的趨勢仍將維持較長一段時期[13]”;提高城市化率直接拉動了城市建設用地的需求,關天經濟區常用耕地面積由2005年的2095.09千hm2減至2014年的2052.90千hm2,土地后備資源呈下降趨勢。渭河周邊濕地出現大面積萎縮,部分支流水質仍為劣V類,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區域內生態承載狀況不容樂觀。
1.2 研究方法
現有研究采用了IPAT[5]、STIRPAT[14-15]、一般多元線性回歸[16]等方法分析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因素,但傳統的回歸模型無法克服變量存在多重相關性的問題[17],缺乏對影響生態足跡內在機理的研究,計入模型的影響因子也較少,無法綜合反映生態足跡與社會經濟指標間的相互影響關系[18]。而PLS模型通過辨識和篩選數據信息中的噪音,提取出對因變量具有更強解釋性的變量,從而克服了多重相關性、樣本點過少等限制[19-20],因此,采用PLS模型對關天經濟區生態足跡驅動因素展開研究。
1.2.1 偏最小二乘法
在多元線性回歸中,假設有p個因變量y1,y2,…,yp,m個自變量x1,x2,…,xm,選取n個樣本觀測出的數據,構建數據矩陣,分別為Y={y1,y2,…,yp}n×p,X={x1,x2,…,xm}m×n。PLS模型基本方法就是首先在自變量集X中提出第一成分t1,從因變量集Y中提出第一成分u1,t1和u1分別是x1,x2,…,xm和y1,y2,…,yp的一個線性組合,同時要求t1和u1可以顯著提高PLS模型的精度,并攜帶數據矩陣X、Y中的變量的變異信息。精度越高,自變量的線性成分t1對因變量的成分u1的解釋能力就越強。
對模型精度的檢驗常采用交叉有效性法,以0.0975為臨界值。在提取了第一個成分t1和u1后,建立X對t1的回歸和Y對u1的回歸,如果此時回歸方程滿足這個精度要求,那么算法終止;否則繼續進行第二個成分t2、u2的提取,即在數據矩陣X、Y提取t1和u1后,對模型中未被變量解釋的部分繼續計算與提煉,直到提取的成分在進行回歸分析時能夠顯著解釋變量變化為止。最終從數據矩陣X中提取了r個成分t1,t2,…,tr,PLS模型將通過建立y1,y2,…,yp與t1,t2,…,tr的回歸式,然后再使用y1,y2,…,yp與x1,x2,…,xm建立方程式。
在PLS模型中,常使用變量投影重要性(Variable Important in Projection,VIP值)來衡量各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力,是通過主成分與權重、方差計算表現的間接關系,自變量在主成分中權重越大、方差之比越大,VIP值就越大,因而對因變量的影響能力就越強。如果自變量的VIP值大于1,可以認為這個自變量是因變量的顯著影響因子,驅動作用強;小于1的自變量認為相對不太重要,驅動能力弱[21]。
1.2.2 PLS模型指標選取
徐中民等在評價可持續生態承載時引入了萬元GDP生態足跡[22]。劉建興等以第一、二、三產業的生態足跡為研究對象,得出了產業結構對生態足跡具有一定影響的結論[23]。楊勇、李一瓊等選取GDP、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費水平、第二產業比重、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等社會經濟變量,系統分析了對生態足跡變化產生影響的因素[24-25],Wang以空間差異為角度,發現受地域特點影響,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生態足跡普遍偏大[26]。就已有研究選取的驅動因素來看,經濟指標中,作為一個能夠宏觀體現地區經濟發展整體狀況的指標,GDP對生態足跡存在較強的影響,產業結構可以反映出地區經濟發展與資源利用、土地占用等生態足跡關鍵指標的關聯性,體現生態資源供需情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地區產業結構的特征,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主要體現當地的工業企業對生態資源的消費情況。社會指標中,總人口數可用以研究區域中人口規模對生態資源消耗的影響[27],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比例、城市化率可以反映出地區人口的構成變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28],城鎮、農村人均消費支出可以反映出不同社會群體消費對地區生態環境的影響,進出口總額表現出貿易水平的變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耕地面積則考量了土地利用的影響。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統計口徑,選取了經濟、人口、居民消費、土地利用4個維度的指標(表1)。經濟方面,選取GDP作為數量指標,選取三次產業增加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作為結構指標。人口方面,考慮到市級數據統計情況,人口比例僅有2010年的人口普查的結果,不能形成可以反映地區人口結構變化的時間序列數據,因此舍棄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只選取總人口數。居民消費方面,市級數據統計中沒有詳細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因此采用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純收入進行替代,并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地區居民消費的狀況。土地利用方面,采用耕地面積作為反映土地結構的指標。另外,由于在研究生態足跡時未做區域進出口貿易調整,因而未將進出口總額等指標納入生態足跡驅動因素模型。以地區生態足跡總量為因變量Y,選取表1中X1至X11作為自變量。
1.2.3 數據來源及處理
研究數據來源于《陜西統計年鑒(2006—2015)》、《甘肅統計年鑒(2006—2015)》、關天經濟區轄區內各市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商洛市的鎮安縣、商南縣與山陽縣不屬于關天經濟區,考慮到其經濟總量與資源消耗占比較小,計算時使用商洛市數據代表商州、洛南、丹鳳、柞水一區三縣,為統一數據統計口徑,采用農作物產量替代農產品的消費量。

表1 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因素指標選取
2 結果分析
2.1 生態足跡測算與分析
關天經濟區的生態足跡測算結果顯示(圖1),2005至2014年關天經濟區人均生態足跡呈現出增長趨勢,由2005年的1.796hm2/人增長至2014年的3.117hm2/人,增長幅度為73.55%,年均增長率為6.32%。2005至2014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維持在50%左右,高于其他產業占比。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自然資本的占用與污染排放的強度進一步增加,生態足跡隨之增加。

圖1 2005年至2014年關天經濟區人均生態足跡變化趨勢Fig.1 The changing trend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of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from 2005 to 2014
2005至2014年關天經濟區各類賬戶人均生態足跡均值測算結果顯示(表2),化石能源用地人均生態足跡均值最大,達到1.271hm2/人,其余依次為耕地類生態足跡0.353hm2/人、污染吸納地0.476hm2/人、草地0.274hm2/人、林地0.040hm2/人、水域0.025hm2/人和建設用地0.006hm2/人。化石能源賬戶產生的生態足跡是生態足跡的主要組成部分,占51.39%,并且呈現出上升趨勢,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建設用地5類生態足跡相加占29.36%,污染吸納地占總體比例的19.25%,表明生態足跡的分布不均衡。
2.2 PLS模型結果與分析

得出關天經濟區生態足跡標準化數據PLS模型(式1):
Y=5.801+0.114X1+0.119X2+0.107X3+0.122X4+0.117X5+0.101X6+0.111X7+0.117X8+0.088X9+0.013X10+0.014X11
(1)

表2 2005至2014年關天經濟區各賬戶科目人均生態足跡

圖2 t1/t2橢圓圖Fig.2 t1/t2 oval figure
選取特異點分析來進一步確認PLS模型的可靠性,根據特異點識別原理繪制主成分t1/t2的散點圖,用以識別特異點(圖2)。從t1/t2橢圓圖可以看出,樣本點都分布在橢圓內部,不存在特異點,可以認為模型的擬合效果好,樣本的質量可以得到保證,不需要進行改動。
選取自變量VIP值來衡量各驅動因素對于生態足跡變化的重要性,通過PLS模型獲得的生態足跡影響因子的重要性程度,按照由大到小排列的順序,依次為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第二產業增加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民人均純收入、常用耕地面積、全區人口數(見圖3),僅常用耕地面積與全區人口數VIP值低于1,其余驅動因素均大于1,且均在1.0至1.1之間,差距較小,除常用耕地面積與全區人口數外,其余指標對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作用較為接近。

圖3 變量投影重要性輸出Fig.3 Variable importance projection output
3 結論和啟示
3.1 結論
影響關天經濟區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因素按重要性依次是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第二產業增加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農民人均純收入、第一產業增加值、耕地面積、全區人口數。
在經濟指標方面,第三產業增加值VIP值最高,對生態足跡變化的驅動作用最為顯著,第二產業對生態足跡的驅動作用低于第三產業,但仍對生態足跡變化造成了顯著影響。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最大,并且呈現繼續上升趨勢。關天經濟區內城市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工業企業的經營生產,企業消耗著大量的能源資源,排放著大量的污染廢氣物,導致地區化石能源賬戶和污染排放賬戶生態足跡大幅度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主導產業,第二產業在生態足跡驅動作用上讓位于第三產業,存在著主導產業與生態足跡驅動因素不一致的現象,究其原因,由于是渭河綜合治理、治理霧霾、節能降耗、淘汰落后產能等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制約了第二產業的生態占用,更重要的是,以生態農業、休閑旅游業、物流業等為代表的特色產業發展十分迅速,衍生出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
在社會消費方面,城鎮消費的驅動作用強于農村消費,這一結論也符合通識知識,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蔬菜、水果、肉類、奶制品的消費結構在發生變化,消費量逐漸增加,由于城鄉生活習慣不同,城市對非能源產品與服務的需求量和需求種類更加繁多,碳消費隨之提升;同時,高收入人群對公共交通的依賴較低,選擇私人交通工具的比例較高,同時伴隨著生活質量的提升,空調、冰箱等家用電器數量也呈現同步上漲趨勢,居民能源消耗因此而增加。
在人口與土地方面,耕地面積對生態足跡驅動作用不強,一方面是因為城市發展占用了較多的耕地,耕地面積在減少,耕地產生的生態足跡減少;另一方面,城市擴張會增加建筑用地,建筑用地總生態足跡在增加,二者會產生抵消效應,即,一種生態占用的減少與另一種生態占用的增加,導致了生態足跡總量沒有發生較大幅度的變動。地區人口總數與生態足跡變化呈正相關,恰恰反映出生態足跡更多來源于人類活動。
3.2 對策與建議
第一,將優化產業結構與優化能源結構有機結合起來。加強對第三產業生態環境的政策監管和用能管理,嚴格商貿、服務業的能源審計和節能減排行動。以建設低碳旅游景區、發展低碳旅游業為目標,加強西安、寶雞、商洛、天水等秦嶺山地生態旅游區的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整合旅游資源,優化旅游路線,形成歷史人文與自然生態的絲綢之路旅游走廊。推廣節能建筑,減少建筑業運行能耗,開展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機構辦公建筑空調、采暖、通風、照明、熱水等用能系統的節能改造,推動分布式太陽能、地熱能規模化的應用。以西安、咸陽、寶雞、天水為產業集中區,推廣清潔生產技術,建設工業園區循環經濟體系,打造循環經濟產業鏈,實現工業廢棄物的再生利用和無公害處理。
第二,轉變能源利用方式,提升能源利用率。關天經濟區化石能源賬戶生態足跡占比高達51.39%,而煤炭比例一直維持在70%—80%,為此,應以“去產能”為契機,實施分區域資源、能源綜合治理,實施“控煤工程”,嚴控煤炭增量,建立健全能源消耗強度與能源消費總量“雙控”制度,強化重點產業節能,有步驟地降低關天經濟區能源消耗總量,減少煤炭等高碳化石能源的消費比例,推進工業鍋爐(窯爐)節能改造、熱電聯產、集中供熱,余熱余壓利用、電機系統節能改造、能量系統優化、建筑節能、綠色照明、政府機構節能、燃煤鍋爐能效測試等節能工程建設。大力開發利用地熱能、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重點發展現代風力發電設備零部件產業化項目。
第三,加強土地保護,提高土地生態承載力。在推動關天經濟區新型城鎮化建設中,以秦嶺、渭北苔原、黃土高原為生態屏障,按生態功能重要性、生態環境敏感性脆弱性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并將生態保護紅線作為編制空間規劃的基礎,明確管理責任,強化用途管制,加強監測監管,要避免侵占優質耕地,確保現有生產性土地不被棄耕或被城市建設所蠶食,提高生物生產性土地的利用效率。堅持封山禁牧、封山育林草,依靠生態自然修復,并加強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通過灌溉轉換荒地為可耕型土地,注重維護與提高林、草生態系統的健康穩定。
第四,引導低碳消費行為,推行低碳生活方式。應引導關天經濟區城市發展綠色交通,率先在關中城市群中規劃建設公共自行車交通網絡,加強城市非機動車道和步行道建設,優先保障低碳出行。以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鞏固提高三年行動為基礎,提高生活污水處理能力,切實保障城鎮污水處理廠的處理率、污水再生利用率,同時,建立生活垃圾及其他廢舊物資回收利用系統,推進餐廚廢棄物資源化、無害化利用試點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按照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能耗狀況準確計算能源賬戶生態足跡,將有助于對節能型產業結構的理解,但由于我國目前的能源統計方式還難以按照產業類型反映能耗狀況,因此研究結果的精度受到了數據源的限制。
[1] Rees W E.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2, 4(2): 121-130.
[2] 徐中民, 張志強, 程國棟. 甘肅省1998年生態足跡計算與分析. 地理學報, 2000, 55(5): 607-616.
[3] Rees W E, Wackernagel M. Our Ecological Footprint: 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 Gabrioala, BC, Cana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6,1(3):171-174.
[4] 史丹, 王俊杰. 基于生態足跡的中國生態壓力與生態效率測度與評價. 中國工業經濟, 2016, (5): 5-21.
[5] 黃寶榮, 崔書紅, 李穎明. 中國2000-2010年生態足跡變化特征及影響因素. 環境科學, 2016, 37(2): 420-426.
[6] 賈俊松. 河南生態足跡驅動因素的Hi_PLS分析及其發展對策. 生態學報, 2011, 31(8): 2188-2195.
[7] 馬明德, 馬學娟, 謝應忠, 馬甜. 寧夏生態足跡影響因子的偏最小二乘回歸分析. 生態學報, 2014, 34(3): 682-689.
[8] 沈滿洪, 池熊偉. 中國交通部門碳排放增長的驅動因素分析. 江淮論壇, 2012, (1): 31-38.
[9] 褚智亮, 楊永標, 王旭東, 黃莉, 王冬. 基于STIRPAT模型驅動建筑能耗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 電力與能源, 2015, 36(2): 251-255.
[10] 周宏春, 季曦.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環境保護政策演變. 南京大學學報: 哲學. 人文科學. 社會科學版, 2009, 46(1): 31-40, 143-143.
[11] 王立群, 李冰, 郭軻. 北京市生態足跡變化及其社會經濟驅動因子分析. 城市問題, 2014, (7): 2-8.
[12] 楊小燕, 趙興國, 崔文芳, 丁生. 欠發達地區產業結構變動對生態足跡的影響--基于云南省的案例實證分析. 經濟地理, 2013, 33(1): 167-172.
[13] 陜西省環境保護廳. 陜西省"十三五"環境保護規劃(征求意見稿). [2016-05-26]. http://www.shaanxi.gov.cn/0/1/11/3868/215830.htm.
[14] Richard Y, Rosa E A, Dietz T. STIRPAT, IPAT and Impact: analytic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3, 46(3): 351-365.
[15] 陳操操, 劉春蘭, 汪浩, 關婧, 陳龍, 王海華, 張繼平, 李錚, 劉曉潔. 北京市能源消費碳足跡影響因素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和偏小二乘模型. 中國環境科學, 2014, 34(6): 1622-1632.
[16] 蔣莉, 陳治諫, 沈興菊, 郭娜. 生態足跡影響因子的定量分析——以中國各省(區市)1999年生態足跡為例.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05, 14(2): 238-242.
[17] 吳開亞, 王玲杰. 生態足跡及其影響因子的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與應用. 資源科學, 2006, 28(6): 182-188.
[18] 魯鳳, 徐建華, 王占永, 胡秀芳. 生態足跡影響因子定量分析及其動態預測比較研究——以新疆為例. 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 2010, 26(6): 70-74.
[19] 王惠文. 偏最小二乘回歸方法及其應用. 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1999.
[20] Jia J S, Deng H B, Duan J, Zhao J Z. Analysis of the major drivers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using the STIRPAT model and the PLS method-A case study in Henan Province, China.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11): 2818-2824.
[21] 魯鳳. 生態足跡變化的動力機制及生態足跡模型改進研究[D].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 2011.
[22] 徐中民, 張志強, 程國棟, 陳東景. 中國1999年生態足跡計算與發展能力分析. 應用生態學報, 2003, 14(2): 280-285.
[23] 劉建興, 顧曉薇, 李廣軍, 王青, 劉浩. 中國經濟發展與生態足跡的關系研究. 資源科學, 2005, 27(5): 33-39.
[24] 楊勇, 任志遠. 銅川市1994-2003年人均生態足跡變化及社會經濟動因分析. 干旱地區農業研究, 2007, 25(3): 213-218.
[25] 李一瓊, 劉艷芳, 唐旭. 廣西生態足跡及影響因子的空間差異分析. 測繪科學, 2016, 41(11): 71-78.
[26] Wang M Q, Song Y Y, Liu J S, Wang J D. Exploring the anthropogenic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orld Ecology, 2012, 19(5): 442-450.
[27] Dietz T, Rosa E A, York R. Driving the human ecological footprint.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8, 5(1): 13-18.
[28] Wang M Q, Liu J S, Wang J D, Zhao G Y.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major driving forces in West Jilin Province, Northeast China.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0, 20(5): 434-441.
DrivingfactorsoftheecologicalfootprintoftheGuanzhong-TianshuiEconomicZone
YANG Yi*,ZHU Yanzhen,ZHANG Jingqian
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710054,China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that drive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the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is crucial for developing energy efficient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for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simultaneously improve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ecolog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zone′s ecological footprint from 2005 to 2014, the importance of the PLS model and the standard PLS model coefficients were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the PLS model, and the importance of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was compared. Significant factors included tertiary industry added valu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but not local population or cultivated land area. Based on these results,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such as the combine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and energy structures, in order to improve energy utilization and efficiency. In addi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mprove use efficiency, protection, and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land and to encourage low-carbon consumption and low-carbon lifestyles.
ecological footprint; driving factors; partial least squares;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15XJL009);陜西省自然科學基礎研究計劃項目(2015JM7381);陜西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15JZ041)
2016- 09- 03; < class="emphasis_bold">網絡出版日期
日期:2017- 07- 11
*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yangyi_nwpu@163.com
10.5846/stxb201609031800
楊屹,朱彥臻,張景乾.關中-天水經濟區生態足跡變化驅動因素.生態學報,2017,37(21):7061- 7067.
Yang Y,Zhu Y Z,Zhang J Q.Driving factors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the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Acta Ecologica Sinica,2017,37(21):7061- 7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