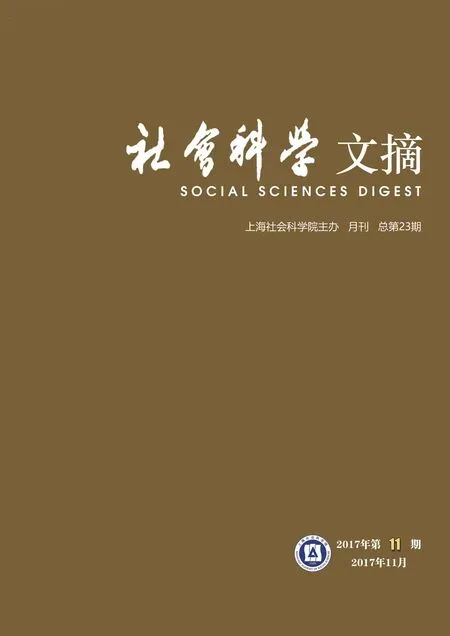堅持問題導向,抑或執著理論體系?
——再議高等教育學研究兼答童順平“一逆三自”之責
文/龔放
《中國高教研究》2016年第12期刊登了廈門大學博士研究生童順平的文章《高等教育學科建設需要放棄理論體系嗎?》(下文簡稱“童文”),對我在該刊第9期所發的文章提出質疑。童順平言辭犀利,不僅贈我“放棄論者”之號,而且分別從“學術史”“國別比較”“邏輯關系”和“研究使命”大處落墨,給我扣上“一逆三自”四項罪名,即“逆勢而行”“自廢武功”“自束手腳”和“自我放逐”。
童順平的商榷之文促使我沉下心來,認真思考相關問題,反復推敲自己觀點能否自洽,鄭重考量他人質疑是否合理。我認為,與童的爭論,關乎我國高等教育學學術發展或學科建設的一些重大原則,那就是:我們孜孜以求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詩與遠方”究竟是什么?難道就只是理論體系的構建?如何才能驗證、發展高等教育學理論進而構建科學的理論架構?是在書齋冥思苦想、在課堂上高談闊論?還是面對復雜的現實矛盾并投身沸騰的實踐研究?究竟什么才是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人間正道”?強調我國高等教育學研究的“問題導向”和“實踐導向”怎么就成了“逆勢而行”?怎么就一定會“自廢武功”“自束手腳”和“自我放逐”?
“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提法確有不妥
童文指出我的那篇文章有些表述不嚴謹、不自洽:有時用“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之詞,有時又冒出“高等教育學科理論體系”的說法,提法不一,含混模糊。童文直率地批評指出:“可知,他無意區分‘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和‘高等教育學科理論體系’,但其所指是‘高等教育學科理論體系’。”
我誠懇接受童順平的這一批評,我的那篇文章的某些提法確有不妥之處。20多年前胡建華、周川、陳列與我合寫《高等教育學新論》,胡建華在其執筆的“學科論”一章中專門辨析了“高等教育學研究”與“高等教育研究”的異同:“高等教育研究泛指對高等教育領域內任何現象、矛盾與問題的研究;高等教育學研究則特指對高等教育領域內的基本矛盾與特殊規律的研究。”我們甚至還認為存在一個,或者說將要形成一個“高等教育學科群”。而“從學科功能分類角度看,高等教育學是高等教育學科群中的基礎學科;從學科層次分類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學是高等教育學科群中的基本學科”。時隔20多年,我們所期待的“高等教育學科群”似乎并未出現,高等院校管理學、大學教學論、大學生學習學等,至今仍然只是“教育經濟與管理”“課程與教學論”等二級學科的分支或者研究方向,尚未獨立門戶。因此,我認為,“高等教育學”其實就是“高等教育原理”或者“高等教育哲學”。準確地說,我和童順平所討論的是“高等教育學”研究,或者高等教育學的學科建設問題,冠之以“高等教育學科建設”仍然含義不明,因為并不存在一個“高等教育學科”,也尚未形成一個“高等教育學科群”。
“放棄論”辯駁:我主張放棄什么?
因為主張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方略應當“改弦更張”,我被童文冠之以“放棄論”:“為簡潔和方便行文起見,本研究將其核心觀點提煉為‘高等教育學科建設必須放棄理論體系’,簡稱為‘放棄論’。”對此,我不敢茍同!因為童文曲解了我的主張。
其實,我的類似觀點曾經在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和文章中有所闡述。2008年在參加廈門大學研討會時,我曾經對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提出“而立之年四問”,其中之二就是:從問題入手,抑或從構建理論框架入手?我強調:“建構理論的意識是必要的,但理論的建樹和學科的成熟應當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應當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實踐的成功基礎之上,而不能拔苗助長或閉門造車。”是致力于高等教育理論框架的建構,抑或致力于解決重大的實踐問題?我認同潘懋元先生當年的觀點:“在問題研究中開辟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新路。”我們高等教育學研究會成立前后相當長一段時期,高等教育學研究界執著于理論框架的構建,邏輯起點的尋找,以及相關范疇、概念的辨析,曾經先后出版了不下15種以《高等教育學》或《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概論》為名的論著。與此同時,對于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現實中碰到的困惑、疑難、問題和挑戰的研究,卻著力不多,成效有限。20世紀90年代末,潘老睿智地提出“適時地轉向理論與實踐的中介研究”的建議,并果斷地調整我國高等教育學研究的目標和重點。在我國高等教育學研究的“而立之年”,我認為潘老確定的方略即“在問題研究中開辟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新路”仍然具有生命力,問題導向的研究仍然需要大聲疾呼、務實推進。2011年在《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組織“高等教育研究:學科抑或領域?”研討時,我再一次發問:“高等教育學的知識體系有何特性?是否存在一個縝密、精致、井然有序的理論大廈?”“高等教育的理論體系如何構建?對觸及高等教育本質與規律的觀念,如何作整體的思考和‘哲學性的解決’?”通過對國際高等教育界公認的三本經典著作的評述,我斗膽提議我國高等教育學研究者應當有所反思并且在“構建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方面改弦更張。上一次,在《中國高教研究》刊載的文章中,我明確無誤地闡明了我的“改弦更張”的含義,即:“必須放棄探尋、構建一個邏輯嚴密、范疇特殊、嚴謹嚴整、天衣無縫的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的目標,而將研究并解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作為首要任務。”
然而,我沒有想到這樣一個表述完整的觀點,居然被童文曲解為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要“放棄理論體系”的主張!不僅我對于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的四個定語全被腰斬,而且“將研究并解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的最大現實問題作為首要任務”也隱而不見了!
有鑒于此,我覺得需要對“改弦更張”觀點做更明確的說明:
第一,我主張放棄的,是“探尋、構建一個邏輯嚴密、范疇特殊、嚴謹嚴整、天衣無縫的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的目標。這一立論的依據,在于充分考慮到了高等教育學研究對象及其知識體系的特性。不同學科的不同研究對象決定了學科知識體系及理論體系的特性,例如,研究物質世界的學科(如化學、物理、天文學等),與研究生命現象的學科(如生物學),以及研究與人及人類社會相關的學科,就存在簡單,還是復雜;統一,抑或多樣;可以證實(或者證偽)或重復實驗,還是難以證實或重復等一系列明顯的差別!如果把不同學科的知識體系及理論體系根據以上差別排列組成一個譜系的話,高等教育活動以及以其為研究對象的高等教育學,絕對處在復雜、多樣和不確定性的一端。關于高等教育的知識體系,特別是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認識,顯然無法像元素周期表和太陽系行星運行規律等“規則性結構領域”的知識那樣確鑿無疑、精確無誤而且可以重復驗證。它往往充滿著變數和不確定性,而且不可重復,難以類比。
我們放棄構建那樣一種不切實際的、縝密、精細、井然有序且單一不變的理論體系,絕不意味著要放棄高等教育學理論研討和理論體系建構。只不過我們的理論探討,是粗線條、開放性和多樣化的,是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分析、探討,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理論。我們所追求的高等教育學理論框架,也完全不同于蘇聯時代教科書模式的理論體系。而且,真正的高等教育學理論研究,必須借助于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和實踐研究的成功,才能趨向成熟。
第二,高等教育學理論工作者應當不忘初心,直面現實,研究并解決高等教育現實發展中碰到的重大實踐問題與理論問題,進而檢驗已有的理論,提出并發展新的理論。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是為了什么?是為了認識矛盾,探索規律,解決問題,促進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續和有序發展。理論的創新發展是問題研究和現實研究的必然產物,而不是“初心”所在。即便是以研究和探索高等教育發展運行規律為使命的高等教育學研究,也需要直面高等教育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分析研究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以扭轉當下的危機,指導變革實踐。我之所以主張把研究并解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作為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首要任務:一方面是覺得紙上談兵、清談誤國的時弊亟待扭轉;另一方面是認為實踐中碰到的矛盾和問題,恰恰提供了檢驗既有理論基礎的機會,也提供了發展新理論、取得新突破的可能。矛盾錯綜復雜、問題層出不窮卻又生機勃發、希望無限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現實,是我們高等教育理論發展的源頭活水,是讓理論之劍砥礪鋒芒、永不生銹的磨刀石。
綜上所述,我所主張的放棄,首先是放棄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即“探尋、構建一個邏輯嚴密、范疇特殊、嚴謹嚴整、天衣無縫的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的目標,因為并不存在這樣一個唯一的、絕對的、永恒不變且四海皆宜的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我們當然不會也不應當放棄高等教育學的理論建樹和理論體系的建構,但這些建樹和建構所要追求的,只是有關高等教育活動本身,有關高等教育與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關系的最本質的理解、最核心的原理,就像我們將“實事求是”和“一切從實際出發”視為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一樣。而高等教育學理論的生命力,則取決于我們針對具體的國情、社情和校情,靈活、恰當地運用這些基本原理去分析現實矛盾,觀察、分析難點、熱點和焦點問題,為高等教育發展的重大決策和深層次變革提供理論闡釋和行動依據。
其次,是要放棄一種態度,就是那種自詡為“專搞理論研究”“建構學科建設體系”的角色錯位!要放棄鄙薄實踐研究、問題研究、行動研究以為不足道,以為“品位低”“武功差”的價值錯位!“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詩人陸放翁的這兩句詩所蘊含的哲理,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和反省嗎?我國高等教育學的理論研究工作者亟待放下身段,深入高校教學、科研和管理的實際,虛心向一線的大學管理工作者、教授學者乃至學生學習,從當下最普遍、最緊迫、最急需解決的瓶頸問題入手,檢驗既有的理論,提出新的發現、對策和新的理論見解。
童文也不得不承認:“顯然僅就文章文本而言”,我根據托尼·比徹等的“學科分類理論”得出的觀點“完全合乎邏輯,因為高等教育學科不是一個‘嚴密知識領域’,不存在一個嚴密的理論體系”;然而他話鋒一轉,居然又提出四個理由,試圖對此“完全合乎邏輯”的結論提出質疑。其中之一是說比徹等訪談獲得的12個學科的“初始研究的數據”僅僅“包含法學并不包括教育學,尤其沒有提到高等教育學,其對教育學的判斷可能是援引文獻或作者推斷的結果”。這就很讓人費解了。科學的訪談調查往往有一個采樣的問題,比徹是對他們所認定的四類學科——純硬科學、純軟科學、應用硬科學、應用軟科學——進行采樣的。除非你對比徹等學者所提出的學科歸屬或者采樣原則提出質疑(比徹是明確將教育學與法學和行政管理學等歸入“應用軟科學”即“應用社會科學”的)。我們所強調的“高等教育學”學科難道會因為比徹等人的初始訪談采樣并未將其列入,或者因為西方學者僅視其為一個研究領域而非學科,就具有了其他的特性,而需要重新打個問號? 這顯然是“淘漿糊”的做法。
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沿著雙軌前進”之說能否成立?
童文特別嚴肅地指出:“從學術史看,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是沿著學科建設和問題研究兩條軌道前進的,放棄學科理論體系探尋、構建是‘逆勢而行’。”“逆勢而行”之責暫且按下不表,對于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沿著雙軌前進”之說,我有兩個質疑:
其一,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是否只有兩條軌道?童文立論所依據的是我國高等教育學研究的泰斗潘懋元先生所言:“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從一開始就以兩條行而有所交叉的軌道發展:一條以基本理論和學科建設為主;另一條以解決現實問題為主,開展應用性、開發性研究。”我認為潘先生所言的兩軌,是就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實踐研究而言。這在科學研究的分類上是能夠成立的。通常科學研究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兩大類,有時還有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三分法”之說。當然,潘老將基礎研究和學科建設并提,與解決現實問題為主的應用性、開發性研究“并行而有所交叉”的提法較為謹慎,他所說的“有所交叉”,也許就指“以解決實際問題為主”的應用、開發研究也會引發或者帶動基礎理論的研究,從而推動學科建設的發展。問題在于童文將潘老的“以基本理論和學科建設為主”的研究,自作主張地縮略為“學科建設”,將其與“問題研究”并列,連“有所交叉”這樣重要的定語也完全刪除了。這樣就完全曲解了潘老的觀點,并造成了將“學科建設”與“問題研究”并列或者割裂的局面。
其二,為何“問題研究”就不屬于“學科建設”?從學術研究史看,社會科學的研究一般有四種基本路徑:文本解讀、比較研究、基礎研究、實踐研究。這四種基本路徑都在不同范圍、不同層次、不同程度地對學科建設做出貢獻。很難設想能夠撇開這四種基本研究路徑而單獨進行的學科建設!基礎理論研究當然對學科建設貢獻多多,但問題研究——包括重大的實踐問題以及與之相伴或由其引發的重大理論問題研究——同樣對學科建設、學科發展貢獻良多!
被我國高等教育學研究同仁奉為圭皋的那些經典著作,其實都不是刻意構建理論體系、精心編撰教科書式的作品。“對高等教育中的紳士傳統”作最初、最權威論述的英國紅衣主教紐曼的《大學理想》,其實是他在籌建都柏林大主教大學時的系列演講,是他在辦學過程中追問大學理想與使命并回答相關質疑和批評的結果。20世紀30年代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撰寫的《現代大學論》,是基于他1928年5月應英國羅德斯基金會之邀在牛津大學所做的三次演講,是在對美、英、德三國高等教育做比較研究后提煉出的對現代大學理念的精辟觀點。英國劍橋大學副校長埃里克·阿什比的《科技發達時代的大學教育》,更是專門的問題研究之作,包括科學與技術在高等學校中的地位問題,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相互關系問題,大學和國家(政府)的關系問題,大學及學者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問題,等等。約翰·S·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既是文本解讀(他旁征博引各家學說,將眾多權威學者對同一問題的觀點放到一起比對、分析),更是實踐研究(他選擇了讓20世紀70年代高等教育界深感危機又充滿困惑的8個問題)。這樣的例證,不勝枚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文本解讀,還是實踐(問題)研究,或者國別比較研究,都可以通向理論創新,都可以對學科建設有所貢獻。關鍵在于如何研究,在怎樣的水平上推進研究。
由此,我認為把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區分為理論研究和應用、實踐研究是可以成立的;但將“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為主”作為一軌,與“以解決實踐問題為主”的應用性、開發性研究“雙軌并行”的提法則是不無瑕疵的,即便潘老也審慎地加上了“有所交叉”的定語。因為學科建設其實包括很多方面,如學科概念、范疇的辨析,學科理論的構建,學術研究方法的探索,學術成果的評價與認可,研究成果的轉化與推廣等。而學術研究機構的建立,學術領軍人物的出現與學術隊伍結構的優化、整體水平的提高,學科人才的培養等,也都屬于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盡管我們承認基礎理論研究對學科建設貢獻很大,但怎么可以忽略甚至無視實踐、應用研究對學科建設的影響和貢獻呢?我的觀點是,因為高等教育學的研究特質,就決定了它不是在“隔音的實驗室里撥控鍵盤”,也不是在書齋和圖書館“鉆研故紙堆”,而是必須深入現場“參與工作來積極驗證真理”的。由此我認為,高等教育學理論工作者決不能輕視草根研究、輕視問題研究。相反,高等教育學理論工作者應投身實踐,與一線的實際工作者一起發現、研究和解決問題。在鮮活的思想激流沖刷和無限的創意火花激蕩中,讓理論由灰色轉為長青!
有人或許要問,強調高等教育學理論工作者也要深入實際,瞄著問題去,追著問題走,是不是將他們混同于一般的高教研究人員了?我認為不會!理論工作者所肩負的特殊責任是:努力“將相關從業者遇到的實際問題轉換成研究問題”,并盡可能使問題研究設計科學、路徑合理,以保持研究的高水平和科學性。此外,推動重大實踐問題研究“更上層樓”,即不滿足于形成調研報告、行動方案、政策建議,不滿足于在國內外核心刊物發表論文,而是設法從中提煉出獨特的概念、范疇或理論觀點,進而豐富中國的話語體系、知識體系、理論體系,去接受國際學術界的檢驗。我認為,這才是中國高等教育學學人應有的態度和追求:始于問題而又不止于問題!面向問題、解決問題,而后躍升到知識更新、理論創新的高度,最終既推動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繁盛,同時也推動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繁盛!
強調“問題導向”就是“逆勢而行”嗎?
我建議高等教育學研究同仁“改弦更張”,將研究并解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作為首要任務,也就是強調“問題導向”的研究,把“像河一樣流淌的”、松散、開放、多樣化而不是像“拼圖那樣鑲嵌無縫”的高等教育學學科理論體系的完善,置于問題研究之后和問題研究之上。這就被童文視為“放棄學科建設”的“逆勢而行”。我要反問一句,什么才是高等教育學研究的“發展趨勢”?難道強調“問題導向”為主的研究就是離經叛道、逆勢而行嗎?
(一)科學研究始于問題,此乃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的“人間正道”
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認為,科學研究的第一個特征,就是“它始于問題,實踐及理論的問題”。他甚至強調“科學只能從問題開始”,“科學和知識的增長永遠始于問題,終于問題——越來越深化的問題,越來越能啟發新問題的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問題導向的研究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土化的例證不勝枚舉。例如,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歷史階段,鄧小平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摸著石頭過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大膽質疑“一大二公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典定義,在關于“計劃,還是市場”問題的討論中,在引導中國現代化建設突飛猛進的同時,也賦予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和國際共產主義事業以新的活力、新的高度!
(二)高等教育學的經典作家尤其注重現實問題研究
他們認為,研究和解決問題與發現新知、創新理論進而提高學科水平,其實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亞伯拉·弗萊克斯納在其《現代大學論》一書中就一再討論這個問題,他強調現代大學的使命是“在最高層次上全心全意并毫無保留地致力于增進知識、研究問題(不管它們源自何方)和訓練學生”。他尤其重視對現實問題的研究:“我認為現代大學的最重要的職能,是在盡可能有利的條件下深入研究各種現象:物質世界的現象、社會世界的現象、美學世界的現象,并且堅持不懈地努力發現相關事物的關系。”
撰寫《高等教育哲學》一書的約翰·S·布魯貝克不僅明確否定存在“一種共同的哲學”,而且坦言:“更不相信會有一種可以通過共同捍衛其純潔性而永世可靠的、單一的、不變的、理想的大學教育‘理念’。”盡管這一觀點會讓有些人頗覺尷尬、略感沮喪,但他揭示了高等教育哲學(高等教育學原理)的重要特性。布魯貝克還有另外兩個與此相關的重要觀點:其一是認為高等教育哲學并非是一個先驗的、既有的客觀存在,而是發展變化、逐漸顯現的;其二,他強調教育是一門實踐性的藝術,單純的思辨和理論的演繹不能指導高等教育的實踐。因此他對高等教育哲學的闡釋就另辟蹊徑,“主要將從高等教育實踐中的矛盾和未定論的問題出發,只有當某些哲學流派確實能夠說明實際情況時,才援引他們的觀點”。布魯貝克是高等教育學研究的權威,他的《高等教育哲學》一書是幾乎所有高等教育學碩士點、博士點的經典必讀書目。他的基本思路和態度,難道不值得我們后來者重視和警醒?
(三)“問題導向”已經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堅持問題導向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追求和學術品位。問題意識成為牽引共產主義從空想走向科學和現實的關鍵。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強調:“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是合理的問題的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把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作為審視人類社會歷史、批判現實矛盾、追求思想解放和理論突破的一以貫之的紅線。
另一方面,堅持問題導向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改變世界、把握命運的實踐性、能動性特質。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是改變世界。”馬克思之前的哲學家的主要缺點是:只是從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目的出發進行研究,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能動的實踐去理解。
當前,“問題導向”已經列為新時期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就突出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
“問題導向”是包括高等教育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間正道”。當然,高等教育學研究的方法和路徑應該也完全可以多樣化,但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理所應當是解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問題。中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應當把當代中國高等教育的難點問題、焦點問題、熱點問題和瓶頸問題納入研究視野,作為首要任務。學術思想和中國問題結合,理論觀點和實踐問題契合、思想論述和時代問題互動,才是順應大勢,人間正道!
“三自”之責:過于自負卻又缺乏自信的體現
童文有關“一逆三自”的指責分別從學術史、國別比較、邏輯關系和研究使命著眼,他的這些指責是建立在曲解他人觀點、咬定我主張“放棄學科理論體系”的基礎上的。現在我鄭重聲明:需要放棄的只是那個并不存在的、唯一、絕對、永恒不變且四海皆宜的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而并非高等教育學理論建構;主張“問題導向”為先、為主,也是為了更好地推進高等教育學的理論發展。而且這條路,正是潘老12年前所倡導的“通過問題研究開辟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新路”。這樣看,童文的“一逆三自”指責還能站得住腳嗎?
童文說:“從國別比較看學科建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優勢和特色,放棄學科理論體系探尋、構建是‘自廢武功’。”確實,放眼當代國際,唯有我國的高教研究界執著于“高等教育學是一門學科,還是一個領域”之爭。我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論證高等教育學的學科性質、學科定位、學科依據,并在明晰高等教育學的范疇、概念、原則、規律等方面取得了可觀的成就。這確實不失為中國高教研究界的特色與優勢。但我們能否可以換一個思路,思考一下:為什么那么多國家的高教研究界并不在意“是一個學科,還是一個領域”的問題?為什么他們強調問題研究,注重問題研究,而且確確實實出了很多留得下來的成果,出了一些堪稱高等教育學發展歷程豐碑的論著?我們如果虛心地借鑒一二,加強問題導向的研究,不是與國際高等教育研究界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和研究交集嗎?怎么就會“自廢武功”?怎么就會“失去與世界對話的平等地位”呢?
童文還宣稱:“從研究使命看,建立科學完善的理論體系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任務,放棄學科理論體系探尋、構建是‘自我放逐’。”但是,我們的研究使命究竟是什么?我們的“武功”究竟應該通過什么來體現?又通過什么來檢驗?是手持弓矢連稱“好箭”,自我宣稱“本人百步穿楊,武功無雙”?還是需要有的放矢,一舉中的,真正解決高等教育碰到的現實難題和理論難題?
中國正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我們面前有許多問題和挑戰——既有積重難返之沉疴,也有萌生不久的矛盾,例如:如何正確處理大學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如何真正“去行政化”,提升現代大學的治理能力?大學校長書記如何“以治校為志業”,盡快實現由專家學者向高等教育理論家、實踐家的轉換?如何為大學校長的職業化、專業化創造條件,為真正實現“教育家辦學”提供輿論支持和制度保證?科技發達時代大學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什么?如何處理大學發現新知、發展科技與培養人才、造就新人的關系?研究型大學如何重構本科教育、回歸大學之道?知識生產模式的轉換要求現代大學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做何調整、變革?大學的教師的天職何在?忠誠于學科,還是忠誠于學生、為他們的成長與發展服務?能否將二者恰當地統一起來?現代大學還是如雅斯貝爾斯所云“是一個由學者與學生組成的、致力于尋求真理之事業的共同體”嗎?現代大學重構“師生共同體”的難點何在,瓶頸何在,關鍵何在?等等。
無論是洪堡創建柏林大學,還是范·海斯和他的威斯康辛思想,或者斯坦福大學開創硅谷……他們在解決自己碰到的難題的同時,書寫了歷史,并在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留下了成功的案例和豐富的思想素材。我們同樣是歷史的創造者、躬行者,我們在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推進變革的同時,也在書寫歷史,創造歷史!中國高等教育學界的同仁應當有足夠的自信心和責任心,我們不僅可以建設一個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強國,面且完全可以在高等教育學理論建樹方面留下中國的足跡、中國的豐碑,留下不遜于《大學的理想》《現代大學論》和《大學之用》的經典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