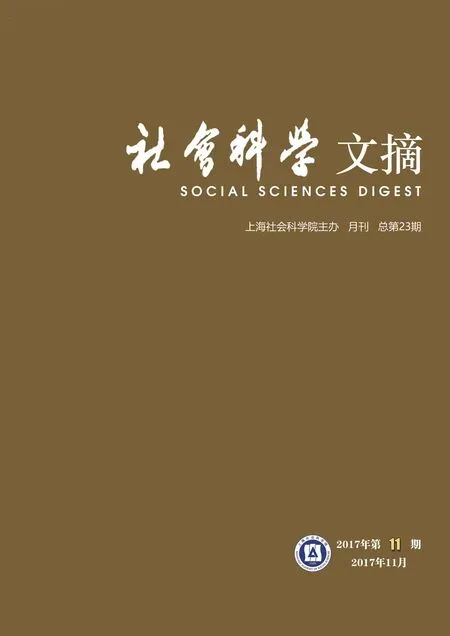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
——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中國(guó)大眾文化中的美國(guó)敘事
文/陳國(guó)戰(zhàn)
引言
新時(shí)期以來,隨著中國(guó)對(duì)外開放進(jìn)程的啟動(dòng),中國(guó)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交往日益增多,當(dāng)代文藝作品在講述中國(guó)故事時(shí),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國(guó)際視野。在20世紀(jì)90年代初期的《大撒把》《北京人在紐約》等影視作品中,到美國(guó)去尋夢(mèng)以及由此而來的跨文化生存經(jīng)驗(yàn)就成為作品表現(xiàn)的中心主題。時(shí)至今日,在電影、電視劇、暢銷書等不同類型的大眾文化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以此為主題的作品。縱觀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條明顯的變化軌跡——主人公從90年代初期奮不顧身地到美國(guó)去尋夢(mèng),到世紀(jì)之交尤其是2008年以來集體性地掉頭轉(zhuǎn)向。這種尋夢(mèng)之旅上的折返跑,與“大國(guó)崛起”“民族復(fù)興”等國(guó)家主義話語相互配合,已經(jīng)成為一種重要的敘事模式。
20世紀(jì)90年代初期,美國(guó)尋夢(mèng)成為重要主題
20世紀(jì)90年代初期,很多影視作品捕捉到了“出國(guó)熱”這一社會(huì)風(fēng)潮,紛紛將鏡頭對(duì)準(zhǔn)移民群體,探討由此引發(fā)的社會(huì)和倫理問題,如《留守女士》(1991)、《大撒把》(1992)、《北京人在紐約》(1993)等。從總體上看,這些作品表現(xiàn)出的對(duì)于出國(guó)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們將出國(guó)處理成婚姻關(guān)系和穩(wěn)定生活的破壞因素;另一方面,它們又將出國(guó)尋夢(mèng)呈現(xiàn)為一種不可逆轉(zhuǎn)的趨勢(shì),從而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感傷。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正面講述了中國(guó)人的出國(guó)故事,播出后產(chǎn)生極大反響。正如片頭所點(diǎn)明的那樣——美國(guó)既是天堂又是地獄,本片表現(xiàn)出的對(duì)美國(guó)的態(tài)度也是復(fù)雜的、愛恨交織的。一方面,對(duì)美國(guó)發(fā)達(dá)的物質(zhì)文明,它流露出由衷的贊嘆和艷羨,片頭逐一呈現(xiàn)了紐約的地標(biāo)性建筑——布魯克林大橋、世貿(mào)中心、帝國(guó)大廈等,這些建筑無不體格龐大、流光溢彩。借助飛機(jī)航拍鏡頭,電影營(yíng)造出一種讓人驚嘆的奇觀效果。但另一方面,對(duì)美國(guó)社會(huì)的文化,《北京人在紐約》表現(xiàn)出毫不含糊的不認(rèn)同。在它的呈現(xiàn)中,美國(guó)是一個(gè)物質(zhì)至上、人情冷漠的社會(huì)。比如,剛到美國(guó)的第一天,姨媽的冰冷態(tài)度就給王起明夫婦當(dāng)頭澆了一盆冷水,也將中美文化之間的差異以一種夸張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震驚體驗(yàn)。
在《北京人在紐約》中,美國(guó)文化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是作為一體兩面來呈現(xiàn)的,它對(duì)美國(guó)文化的評(píng)價(jià)與它對(d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在本劇中,阿春始終是王起明事業(yè)上的導(dǎo)師,她教導(dǎo)王起明說:美國(guó)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戰(zhàn)場(chǎng)。在20世紀(jì)90年代初期市場(chǎng)化剛剛啟動(dòng)的背景下,這種將商場(chǎng)比作戰(zhàn)場(chǎng)、將競(jìng)爭(zhēng)比作廝殺的觀念,無疑具有一種教導(dǎo)和啟蒙意味,它既塑造了很多中國(guó)人對(duì)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最初理解(顯然,這種理解是帶有偏見的),也反映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大眾對(duì)于即將開啟的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的惶恐和疑懼。
《北京人在紐約》將它所理解的美國(guó)文化、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中國(guó)人的傳統(tǒng)觀念”對(duì)立起來,并將前者指認(rèn)為物質(zhì)至上的,而將后者塑造成有情有義的。從情感上講,王起明顯然更認(rèn)同后者,但為了在美國(guó)站穩(wěn)腳跟,他不得不作出妥協(xié)。最后,他取得了商業(yè)上的成功,卻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jià)——失去了同甘共苦的妻子,費(fèi)盡千辛萬苦接來的女兒也離他而去。這種處理方式具有雙重效果:一方面,王起明通過調(diào)整自我以適應(yīng)美國(guó)社會(huì)最終取得了成功,這無疑確立了中國(guó)男性主體的自信——與他形成鮮明對(duì)照的是那個(gè)一直在街邊敲擊鐵桶的黑人流浪漢;另一方面,為了取得這種成功,王起明付出了妻離子散的代價(jià),根據(jù)中國(guó)人的傳統(tǒng)觀念,這又是得不償失的,因此又可以起到安撫國(guó)內(nèi)蠢蠢欲動(dòng)的出國(guó)沖動(dòng)的作用。
可以看出,在20世紀(jì)90年代初期的大眾文化作品中,到美國(guó)去尋夢(mèng)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重要的主題。在講述這些出國(guó)故事時(shí),它們大都將西方/現(xiàn)代文化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對(duì)立起來,并將前者指認(rèn)為物質(zhì)主義的、重利輕義的,從而表現(xiàn)出一種“西方主義”偏見。從情感態(tài)度上看,這些作品更認(rèn)同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從而確立了中國(guó)人的民族自信心,但同時(shí)也暗示西方化、現(xiàn)代化是不可阻擋的潮流。
2008年以后,“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的敘事模式涌現(xiàn)
大約在2008年以后,回國(guó)故事開始大量出現(xiàn),以至于構(gòu)成了一種可稱之為“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的敘事模式。在這種敘事模式中,促使主人公作出回國(guó)決定的,已不再是無法割舍的親情或文化上的歸屬感,而是中國(guó)蒸蒸日上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形勢(shì)和遍地的商業(yè)機(jī)會(huì)。比如,在電影《非誠(chéng)勿擾》中,男主人公秦奮當(dāng)初也是出國(guó)大軍中的一員,在美國(guó)浪蕩十幾年依然孑然一身,事業(yè)無成,然而他回國(guó)以后,不僅立即就把所謂的“分歧終端機(jī)”的專利以200萬英鎊的高價(jià)轉(zhuǎn)讓了出去,從此變得“錢對(duì)我不算事”,而且收獲了一份讓人羨慕的愛情。
此后,這種“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在電影中大量出現(xiàn),如《中國(guó)合伙人》(2013年)、《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年)、《一生一世》(2014年)、《北京·紐約》(2015年)等。其中,《中國(guó)合伙人》完整呈現(xiàn)了主人公孟曉駿從懷揣夢(mèng)想出走美國(guó),到美國(guó)夢(mèng)碎返回國(guó)內(nèi),再到實(shí)現(xiàn)夢(mèng)想殺回美國(guó)的人生軌跡,可以看作這種敘事模式的代表。在這部電影中,成東青、孟曉駿、王陽三人都曾經(jīng)夢(mèng)想著去美國(guó)。后來,只有孟曉駿實(shí)現(xiàn)了這一夢(mèng)想,然而,他在美國(guó)的生活并不如意,連在實(shí)驗(yàn)室里喂小白鼠的工作都沒能保住,不得不到餐廳里端盤子,受盡冷眼和委屈。從美國(guó)歸來后,他一度患上了“演講恐懼癥”,在美國(guó)的經(jīng)歷給他造成了無法撫平的心理創(chuàng)傷。相反,當(dāng)初簽證失敗的“土鱉”成東青卻在國(guó)內(nèi)創(chuàng)業(yè)成功,事業(yè)蒸蒸日上,并將孟曉駿吸引到自己的團(tuán)隊(duì)中。對(duì)于心高氣傲的孟曉駿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gè)巨大的諷刺。最后,三人合力打造出“新夢(mèng)想”這只教育航母,并在美國(guó)成功上市。
在這部電影中,孟曉駿曾經(jīng)無限憧憬的美國(guó)夢(mèng),到頭來被證明是一場(chǎng)美國(guó)噩夢(mèng),讓他嘗盡屈辱,走投無路;相反,他曾經(jīng)不假思索地逃離的中國(guó),最終卻幫助他實(shí)現(xiàn)了人生價(jià)值。與美國(guó)夢(mèng)相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新夢(mèng)想”,即冉冉升起的中國(guó)夢(mèng)。因此,當(dāng)他帶著自己的事業(yè)再次來到美國(guó)時(shí),我們處處可以感到一種復(fù)仇的意味——他撫今追昔,以成功者的身份再次來到當(dāng)年打工的餐廳,享受著昔日克扣他小費(fèi)的女侍者的殷勤招待;他還收到了成東青送來的一個(gè)禮物——以他名字命名的當(dāng)年辭退他的實(shí)驗(yàn)室,仿佛只有通過這種直截了當(dāng)?shù)姆绞剑拍墀熤萎?dāng)年在美國(guó)遭受的心理創(chuàng)傷,擺脫那個(gè)不堪回首的美國(guó)噩夢(mèng)。
與前面幾部電影將出國(guó)一方設(shè)置為男性不同,在電影《一生一世》《北京·紐約》中,出國(guó)的一方變成了女性,而留守的一方則是男性。在這種類型的出國(guó)故事中,女主人公當(dāng)初懷著美好的憧憬來到美國(guó),但美國(guó)并沒有給她們提供實(shí)現(xiàn)夢(mèng)想的機(jī)會(huì),多年以后她們依然生活潦倒。而此時(shí),她們留在國(guó)內(nèi)的昔日男友卻已經(jīng)事業(yè)有成,今非昔比。當(dāng)男女主人公再次相見時(shí),盡管彼此仍舊念念不忘,但由于婚姻或其他感情的牽絆,相處時(shí)總是磕磕碰碰。仿佛無法為他們的感情想象出一個(gè)更美好的出路一樣,這兩部電影都以悲劇收尾——《一生一世》中的男主人公趙永遠(yuǎn)死于“9·11”事件中的世貿(mào)大樓,而《北京·紐約》中的男主人公藍(lán)一則死于一場(chǎng)車禍。伴隨著《一生一世》中世貿(mào)大樓轟然倒塌的畫面,女主人公的美國(guó)夢(mèng)也徹底破碎。最后,她們都作出了回國(guó)的決定,然而物是人非,昔日戀人已經(jīng)不在人世,這種結(jié)局仿佛是對(duì)她們當(dāng)初出走美國(guó)的無情懲罰。
當(dāng)代中國(guó)民族主義話語的一種重要敘事策略
從最顯而易見的層面看,“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模式之所以出現(xiàn),是與21世紀(jì)以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形勢(shì)密切相關(guān)的。2000年以后,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總量的世界排名先后超過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國(guó)、英國(guó)和德國(guó),2010年更是超過日本成為緊隨美國(guó)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在這種背景下,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huì)、2010年上海世博會(huì)的成功舉辦,進(jìn)一步提振了中國(guó)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大國(guó)崛起”“民族復(fù)興”等話語逐漸深入人心。
然而,如果我們滿足于如此直截了當(dāng)?shù)慕忉專赡芫湾e(cuò)過了一個(gè)遠(yuǎn)為復(fù)雜和重要的問題,即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中國(guó)社會(huì)中民族主義思潮的重新抬頭,以及它在近些年來的發(fā)展變化。
20世紀(jì)90年代,中國(guó)社會(huì)中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靠對(duì)美國(guó)“霸權(quán)主義”的道義指責(zé)和對(duì)中國(guó)歷史文化的自信來支撐的。這在同期出版的暢銷書《中國(guó)可以說不》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這部影響廣泛的暢銷書中,作者提出,“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yùn)動(dòng),無不沐浴著中國(guó)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jìn)步,無不得惠于中國(guó)的功德”,與中國(guó)相比,美國(guó)則“沒有國(guó)家歷史觀念、沒有思想深度、沒有痛苦感受”,因此不可能是未來的先進(jìn)民族。這種對(duì)中國(guó)歷史文化的重新肯定以及對(duì)美國(guó)文化的鄙薄,既與20世紀(jì)90年代趨向保守的社會(huì)文化心態(tài)密切相關(guān),同時(shí)也是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在其他方面尚無力與美國(guó)相抗衡的現(xiàn)實(shí)處境使然。此時(shí),盡管中國(guó)社會(huì)中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再次掀起高潮,但由于大多數(shù)中國(guó)人對(duì)中美之間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對(duì)比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所以“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尚未出現(xiàn)。
2008年以來,在斷言美國(guó)必將衰落、中國(guó)必將崛起這點(diǎn)上,中國(guó)社會(huì)中的民族主義是一以貫之的,但是,這種民族自信心的基礎(chǔ)卻悄然發(fā)生了改變:20世紀(jì)90年代,這種自信主要來自對(duì)中國(guó)歷史文化的重新肯定;2008年以后,這種自信則主要是靠當(dāng)下中國(guó)蒸蒸日上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形勢(shì)和美國(guó)的經(jīng)濟(jì)“頹勢(shì)”雙向支撐的。與此相應(yīng),中國(guó)大眾文化中的美國(guó)形象也發(fā)生了很大改變——美國(guó)不再是一個(gè)文化上淺薄卻財(cái)大氣粗的傲慢的強(qiáng)者形象,而是變成了一個(gè)到處舉債、江河日下的狼狽的破產(chǎn)者形象。可以看出,從《中國(guó)可以說不》到《中國(guó)不高興》,兩者表現(xiàn)出的對(duì)美國(guó)的態(tài)度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變化,這點(diǎn)僅從書名上就可以窺其端倪:在斷然“說不”的激切反應(yīng)中,流露出的是弱者常有的不服之氣;而“不高興”則頗有些不怒而威的意味,流露出的是強(qiáng)者慣有的傲慢。
也就是說,“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模式的出現(xiàn),根源于2008年以來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總量世界排名的不斷攀升,以及同時(shí)期出現(xiàn)的全球金融危機(jī),同時(shí)也與很多中國(guó)人對(duì)“美國(guó)夢(mèng)”的偏頗理解有關(guān)。在2008年以后的國(guó)際國(guó)內(nèi)背景下,中國(guó)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空前提振,大有風(fēng)景這邊獨(dú)好之感。受此影響,中國(guó)大眾文化中的民族主義狂歡也在如火如荼地進(jìn)行。從某種意義上說,“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也加入了關(guān)于“中國(guó)崛起”“民族復(fù)興”的大合唱,成為當(dāng)代中國(guó)民族主義話語的一種重要敘事策略。
“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模式自身存在諸多問題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guó)大眾文化作品如何講述出國(guó)故事、如何呈現(xiàn)美國(guó)形象,反映出的是我們對(duì)自我身份的認(rèn)知和定位。通過對(duì)“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的分析,這些意識(shí)形態(tài)的成分同樣是顯而易見的,它們?cè)诮沂境霎?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中的一些隱秘信息的同時(shí),也暴露出這一敘事模式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
首先,“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建立在一系列文化誤解和偏見之上,帶有明顯的西方主義色彩。賽義德曾經(jīng)提出,東方主義所建構(gòu)出來的“東方”是不真實(shí)的、帶有意識(shí)形態(tài)偏見的,目的在于強(qiáng)化西方對(duì)東方的統(tǒng)治。伊恩·布魯瑪和阿維賽·瑪格里特則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西方主義”概念,在他們看來,西方主義所建構(gòu)出來的“西方”同樣是不真實(shí)的——西方通常代表著物質(zhì)至上、精神空虛、人情冷漠,雖然它創(chuàng)造了發(fā)達(dá)的物質(zhì)文明,卻缺少東方文化的倫理維度和精神價(jià)值。在“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中,這種西方主義偏見是隨處可見的。作為現(xiàn)代文明的代表,美國(guó)常常與自私、冷漠、刻板、墮落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美國(guó)常常被呈現(xiàn)為文化和藝術(shù)的沙漠。王起明到美國(guó)后,不得不放棄自己拉大提琴的音樂夢(mèng)想,剪掉一頭長(zhǎng)發(fā),與自己的過去告別;《留守女士》中乃青的丈夫到美國(guó)后,也放棄了自己所學(xué)的音樂專業(yè),而改學(xué)更為實(shí)用的商業(yè)管理;《北京·紐約》中的茉莉曾經(jīng)的夢(mèng)想是拉小提琴,到美國(guó)后卻不得不靠送外賣、當(dāng)導(dǎo)游、做歌女謀生。正如前面已經(jīng)指出的,這種對(duì)美國(guó)的偏見與人們對(d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認(rèn)知是一體兩面的,它們常常相互交織在一起,從而將人們?cè)谑袌?chǎng)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中感受到的震蕩和失落,發(fā)泄到一個(gè)臆想出來的美國(guó)形象上。
其次,在很多“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中,我們都可以找到厭女癥的情節(jié)設(shè)置。比如,在《北京人在紐約》中,王起明和郭燕的婚姻破裂被設(shè)置在王起明正走投無路之時(shí),如此一來,郭燕就難以擺脫嫌貧愛富、不能與丈夫同甘共苦的嫌疑。在相聲劇《暖冬》、小品《一句話的事兒》中,女性也都是目光短淺、嫌貧愛富的,在遭遇金融危機(jī)后,她們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國(guó)內(nèi),而昔日男友或現(xiàn)任丈夫卻不計(jì)前嫌,寬容大度地接納了她們。可以看出,“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常常將宏大的國(guó)家敘事轉(zhuǎn)換成兩性關(guān)系敘事,并借男主人公的遭遇來隱喻中國(guó)的發(fā)展歷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由于急于確立中國(guó)男性主體的自信,常常在有意無意間表現(xiàn)出對(duì)女性的偏見。
最后,“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雖然暗示如今人們的夢(mèng)想已不再大洋彼岸,而就在中國(guó),但它并沒能提供一個(gè)完整的關(guān)于中國(guó)夢(mèng)的故事,從而暴露出這種敘事模式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在很多電影中,主人公的奮斗過程都被有意無意地省略了。比如,在電影《一生一世》中,前一個(gè)畫面趙永遠(yuǎn)還在揮汗如雨地騎著三輪車販賣服裝,后一個(gè)畫面他就以大老板的身份坐上了去美國(guó)進(jìn)行商業(yè)談判的飛機(jī),中間的奮斗過程完全是空白。電影《北京·紐約》同樣省略了男主人公藍(lán)一的奮斗過程。更加吊詭的是,在電影《中國(guó)合伙人》中,幫助成東青、孟曉駿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夢(mèng)的是“新夢(mèng)想”公司,而不管是電影中的“新夢(mèng)想”,還是現(xiàn)實(shí)中的“新東方”,其主要業(yè)務(wù)都是出國(guó)英語培訓(xùn)。這也就意味著,成東青等人正是依靠向人販賣美國(guó)夢(mèng)來實(shí)現(xiàn)自己的中國(guó)夢(mèng)的;他們之所以能夠?qū)崿F(xiàn)自己的中國(guó)夢(mèng),恰恰是因?yàn)楹芏嘀袊?guó)年輕人都懷有美國(guó)夢(mèng),都想獲得簽證到美國(guó)去;當(dāng)孟曉駿終于領(lǐng)悟到美國(guó)夢(mèng)原來是一場(chǎng)噩夢(mèng),他所做的卻是把更多年輕人引渡到美國(guó)。所有這些悖論都表明,“折返的尋夢(mèng)之旅”敘事雖然暗示中國(guó)夢(mèng)將取代美國(guó)夢(mèng),但對(duì)于如何才能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夢(mèng),卻未能提供一個(gè)完整而令人信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