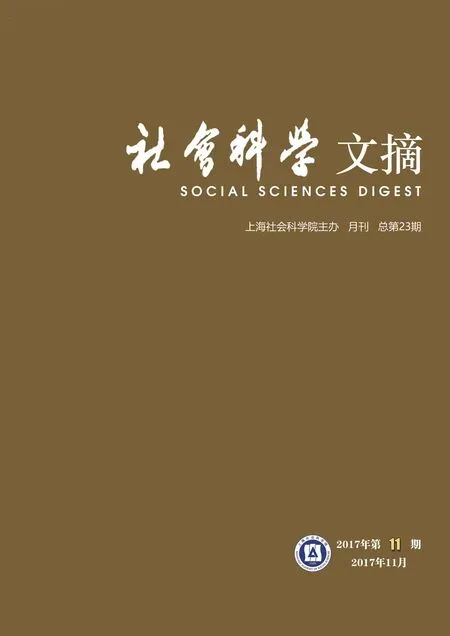日譯西學新范疇與中國哲學的近代轉型
文/郭剛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近代哲學思想產生了重要的變化和飛速的發展。這種變化與發展固然有著思想自身的邏輯依據和深刻復雜的社會原因,但是,也與此時傳入的大量西學(西方思想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赴日中國學人回傳的日譯西學為中國近代哲學的轉型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料,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哲學的近代轉型首要體現在以新范疇的傳入與應用為基點。
“和制漢詞”的創譯與傳入中國
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廣泛使用著新引進的概念,其中赴日學人引入的大量“和制漢詞”構成了中國近代哲學轉型的基本單位。
“和制漢詞”,也稱“日本造漢字詞”,是日本學者翻譯西方文化的主要符號方式。素有日本近代哲學之父的西周很早在其講稿《百學連環》等文獻中用漢字創譯出大量的西方的學術名詞和哲學范疇,成為西方哲學范疇、哲學史、邏輯學、心理學和美學的最早傳播者。如,他在1874年的《百一新論》中第一次將“Philosophy”譯為“哲學”,將“Spirit”譯為“精神”,還創譯了“主觀”“客觀”“理性”“悟性”“現象”“歸納”“演繹”等數量很多的哲學用語。在這些哲學詞匯中,一些是借用中國古語所創造的譯語,如“智”“情”“意”“意識”“權利”“義務”“演繹”“原理”“具體”“現象”“空間”“理性”等;一些是未能在中國典籍中找到出處的譯語,如“感覺”“實質”“物質”“元素”等;另一些則是以古漢語中的個字為基礎的創譯,如“哲學”“概念”“感性”“主觀”“抽象”“理想”“直覺”等。繼西周之后,日譯西學新范疇的創譯更是層出不窮。1881年,日本人首位哲學專業教授井上哲次郎組織編寫了《哲學字匯(字典)》,搜集整理出包括西周等人創譯的已普遍使用的“和制漢詞”哲學類術語,不僅在學術界、思想界中得以認可,而且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和使用。如,社會主義思想初傳日本,加藤弘之于1870年在《真政大意》一書中音譯了“socialism”一詞,西周于1871年在《百學連環》中將其意譯為“會社之說”,之后日本學者約于1877年采用“社會”一詞翻譯society,福地源一郎于1878年6月在《東京每日新聞》上第一次用漢字將“socialism”譯為“社會主義”。這樣,“socialism”一詞幾經創譯,最終被確立下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翻譯手法體現出日本學者開始用“主義”翻譯某種特定理論或系統化的社會意識形態字匯,并進一步用來合成新的詞匯。這些新范疇不僅為日本學者所熟練運用,而且也被中國赴日學人所普遍使用。翻閱20世紀初赴日學人創辦的刊物,不難發現,他們已普遍使用著“社會主義”“國家主義”“人道主義”等概念名稱。
日譯西學新范疇不同程度地被赴日學人傳入中國。實藤惠秀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曾寫專章探討日譯西學傳入中國情況,列舉了中國現代漢語來自日語的單詞784個,后增加了46個,共830個,成為當時學界所知的日語外來詞最大數目。除上面提及的哲學術語外,還有“現實”“心理”“判斷”“范疇”“意志”“歸納”“革命”“一元論”“人生觀”“生產力”“唯物論”“唯心論”“唯理論”“辯證法”“意識形態”“唯物史觀”“不變資本”“共產主義”等大量哲學詞匯。
梁啟超居日期間以“將世界學說為無限制的盡量輸入”的精神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傳入大量“西學”。他僅在《和文漢讀法》引進日語外來詞就接近200個,其中涉及有關哲學方面的就不少于幾十個,且大都作了注釋,如“經濟”(理財學、資生學,打算)、“主觀的”(內理應如是)、“客觀的”(外形應如是也)、“絕對的”(完全無比者)、“抽象”(哲學譯語,想其理由之義)、“概念”(大概想念)、“積極”(哲學譯語,陽極也)、“組織”(構成)、“個人”(匹夫)、“個人權”(各人自立權)、“具體”(實象)、“利潤”(利息)、“團體”(凡眾聚之稱),等等。同時,留日學生創辦的《譯書匯編》也大量譯注了像“權利”“社會主義”“組織”等詞匯;由黃興等人創辦的《游學譯編》側重介紹了西方政治思想理論。
除以報刊形式傳入日譯西學外,還有一些學者以著書的形式傳播之。馬君武在日本廣泛傳播了西方政治學說、哲學思想,涉及哲學、法律、公民、主權、政府等西學精神,傳入“唯物論”“無神論”“主體”“客體”“絕對”“相對”“精神”“物質”“自由”“歸納法”“演繹法”等西學新詞匯。馬君武還以《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等論文形式翻譯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著作,并提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揭示了馬克思“階級斗爭歷史之鑰”的觀點。朱執信以救國救民的理念為指引,也將目光投向西方近代以來的民權國權思想,在他的文獻中頻頻使用“國家社會主義”“權利”“階級”“資本”“利潤”等概念。章太炎在他古樸的文章中也留下大量日譯西學的痕跡,居日期間便使用了“民族”“思想”“人權”“革命”“觀念”“民族主義”“共和政體”“無政府主義”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民報》等刊物上以西學新知來宣傳自己的革命主張和宗旨,在傳播西學思想之時也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涉及“階級對立”“階級斗爭”“剩余價值”等概念,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貢獻。這些日譯術語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而在中國文化土壤中開始生根,并且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而逐漸積淀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詞匯。另外,日本人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翻譯則相對晚了些。1912年日本學者Sakai在翻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時第一次使用“經濟基礎”這種譯法,我國學者李大釗在1919年翻譯馬克思的《序言》時效仿了這種譯法。20世紀20年代,日本學者河上肇第一次創造了“上層建筑”來翻譯Ueberbau這個詞,并逐漸成為中文標準譯法。李大釗于1919年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時譯成“表面構造”,后來接觸到河上肇的“上層建筑”翻譯時采用之。如此等等。可以說,中國早期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完全依賴于這些概念、范疇,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運用和發展。在此,這些新鮮的日譯西學術語不僅為清末民初的赴日學人宣傳西方哲學思想提供了便利的語言中介條件,而且對赴日學人的思想轉型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日譯西學新范疇助推中國哲學的近代轉型
近代“和制漢詞”哲學新范疇帶來了中文概念或范疇的革新,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國近代哲學基礎理論的形成,促進中國哲學由封閉性轉為開放性,主動融入世界哲學對話的平臺上來。
首先,像“哲學”“歸納”“演繹”“辯證法”“唯物論”“感性”“理性”“主觀”“客觀”“精神”“意識”“時間”“空間”“現象”“本質”“美學”等一大批哲學新范疇,被中國學者傳入并認同,在求變、求新的時代中無疑會為中國近代哲學向前發展注入新鮮血液。
日本思想家所創譯的哲學范疇具有時代性和清晰性的特征。譬如,西周首次把Philosophy創譯為漢字“哲學”范疇,蘊涵著西學原創之意的“愛智之學”,且不偏離中國古典文獻學的意蘊,這不同于中國學者將“哲學”音譯為“費錄蘇非亞”“斐洛蘇非”等,或對譯為中國傳統儒學概念的“格物窮理之學”“愛知學”“格致學”“格學”“性理之學”等。無論是“格物”“格致”,還是“性理”,一般指心性之學,或引申出理性之學。然而,“哲學”一詞則更多蘊含著超越一切經驗科學追求形而上學的學問,是人的精神力量的總和,即人類的智慧之學。因此,“哲學”給予人的是“大智慧”。所以說,日譯西學“哲學”一詞譯語準確精練,達意吻合,內涵豐富,表征著異質文化轉譯的合理性、科學性,其時代性與清晰化是有利于近代哲學轉型的。赴日的王國維于1901年在《教育世界》雜志上使用了“哲學”概念,隨后嚴復、蔡元培、胡適等便都以“哲學”來介紹philosophy,而不再使用之前的種種漢譯名稱。如此,以“哲學”一詞的轉譯被廣泛使用為契機,標志著中國哲學轉型有了嶄新的開始。
其次,日譯西學哲學新范疇不僅嚴密、真確、清新,而且更具“句法”邏輯,能夠在邏輯性、理論性諸方面推進中國哲學的近代轉型。反觀中國傳統學術,由于句法邏輯意識不夠發達,許多概念往往含義較多模糊不清。
如馮友蘭就在《貞元六書》的“新理學”中分析了“道”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幾種涵義:第一,本義為路,“人之道”即人在道德上當行之路;第二,指真理,或最高真理,或全體真理之義,如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第三,道家所謂道,無形無名,能生成萬物;第四,指“宇宙間一切事物變化所依照之理”,如程朱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在這本書中,他也梳理了像“氣”“天”“理”“性”等傳統哲學中的其他一些重要術語,指出了概念含義的歧義多、且指向不一。金岳霖同樣認為,中國哲學的一個特點就是認識論和邏輯意識不發達,并進而影響到概念的準確、明晰。字詞準確是句子明晰性的基礎,中國近代哲學若要融入世界哲學,就必須要求概念的明晰性、邏輯性和普適性。此時,日譯西學的嚴密、清新,更具“句法”邏輯,能夠在邏輯性、理論性上帶來“清晰思想”,成為中國哲學近代轉型的主要確證。
總的來看,日譯西學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是深刻的,不僅表現為其對赴日學人的學理研究和自我改造上,而且表現其對中國哲學思想的轉型上。具體言之,赴日思想家通過譯介日譯西學,不僅將中西方哲學新范疇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哲學范式,而且能夠與其他民族哲學家進行對話、交流,從而展現出中國近代哲學的轉型特征。換言之,赴日學人思想的形成是以傳播和接受日譯西學為重要基礎的,進而助推著中國哲學的近代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