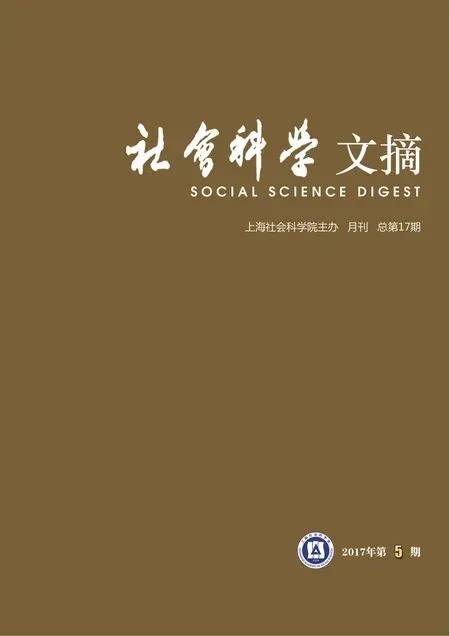法律如何保衛良知?
文/郭忠
法律如何保衛良知?
文/郭忠
2016年11月1日,《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正式實施。同年12月19日上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召開,《民法總則(草案)》進入三審階段。這兩部法律法規的草擬或出臺有望解決過去常出現的救助反被訛的道德困境問題,使好人的救助行為得到法律的保護。
“好人法”顧名思義就是促使人成為好人的法。要促使人成為好人,就需要消除善良行為的心理顧慮和外在壓力,讓良知得到充分的釋放,對此法律大有可為。在“好人法”相繼擬定出臺之際,我們有必要從更高的理論高度去探討法律為何能保衛良知以及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保衛良知,以促使法律在更廣闊的范圍內促進良知。
良知成本與良知的實現
(一)良知的呈現或沉淪:人性的兩個方面
人性有著分裂的特征,一方面是道德人,一方面是經濟人。人性的兩個方面并非毫不相干,各自起自己的作用,而是往往引起人的意識中的激烈交鋒。由于利益更顯露,良知更潛沉,因此更容易發生的是良知被利欲遮蔽、良知沉淪的現象。這種情況特別容易出現在逐利之心被大大激發,比如市場經濟你死我活的競爭環境中。
由于人對利益的追逐,而利益是可計算的,因此產生了計算理性。在逐利之心和計算理性的驅動下,良知也被納入了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之中。良知本來是不計成本的,良知行為并非是為了得到自己的收益,但是當良知導致極大的損失的時候,良知就可能被納入成本的計算中來。比如,當老人倒地,基于良知是要予以救助的,但計算理性又會對良知行為進行成本計算。如果考慮救助行為存在被訛詐的可能性,自己要為良知行為支付巨大代價時,是否要扶起地上的老人,便成為一個艱難的抉擇。
在社會生活的競爭中,良知往往并不能讓人獲得利益的增長,相反增加了獲取利益的成本,使人受到損失。在良知行為和利己行為的交互活動中,良知行為在競爭中處于劣勢,于是容易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
但畢竟良知作為人性的本真和深層的需求,是不容被驅逐的。正因為良知的真實呈現,我們才認識到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罪惡,我們才有可能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懺悔。從這種意義上講,良知是人類道德行為的原初動力。此外,一個良知被驅逐的社會,也不可能讓人獲得真正的安全和幸福,人類文明也缺失了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在良知和利欲的對抗中,一個健全的社會,不是“滅人欲”,而是要考慮如何通過制度減少良知的成本,實現利他和利己的平衡,使良知得以呈現而非沉淪。
(二)社會環境:良知的搖籃
使良知背負上成本的,不僅有利益,還有社會環境。由于人是社會的動物,人們彼此以他人為鏡子,形成對自我的判斷,而這種判斷也在潛移默化地塑造著自己,而使自己成為一個社會化的個體。人們通過模仿他人而形成自己。而一個人一旦成為異類,和大家不一樣,則可能承擔被社會孤立的后果。因此個體背離群體的成本相當巨大。
良知的生長需要適當的環境。在這個方面,中西思想家有很多重要的論述。良知受外界影響而難以呈現,也被一些心理學實驗所證明,比如“米格拉姆實驗”和“斯坦福監獄實驗”。這些實驗展現了殘酷的人性現實:通常意義下的好人也極易在某種特定的群體環境下,變得良知麻木和殘忍。
人類生存的外部環境對良知的不利影響可分兩種。一種是由于受到制度環境可感知的威逼,良知被壓迫,如良知面臨嚴酷環境(巨大的成本、被權力壓迫以及不公平的制度等)時,良知被放棄,而讓人只能釋放出人性丑陋和反社會的一面。另一種是人們未有對環境威逼的感知,而是基于社會權威和外部環境的潛在影響,盲目服從了權威,從而放棄了良知的判斷。
因此,人的良知狀態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會的烙印。如果社會一旦出現病態也會進一步演化為良知的病態。只有健康的社會才會造就健康的良知,促成個體良知的順利生長。然而,如同個體會生病一樣,社會肌體也極有可能染上疾病。如同人的疾病可能自然痊愈或服藥痊愈一樣,社會的疾病當然也可通過自發的或人為的手段得以好轉。法律就是一劑人為的良藥,把握好劑量,服用得當,即可消除社會的疾患。
通過法律減輕良知的成本負擔
良知是一種道德上知善惡的直覺。這種直覺——按王陽明的觀點——是祛除“良知之蔽”的產物,“良知之蔽”則是指對七情的執著和欲望。
法律減少良知的成本支出,并不能直接實現良知的“去蔽”。良知的“去蔽”和良知的呈現必須是通過主體自身對良知的追求才能實現。但是法律可以減輕良知遭受的內在的和外在的壓力,減輕七情之蔽的影響,使良知更容易呈現出來。良知的內在壓力在于自我利益的計較,外在壓力在于社會環境對良知的逼迫。在計算理性之下,二者都可能構成良知實現的成本。只要法律減少良知行為的成本負擔,良知就會減少自身壓力,從而更利于人們做出良知的行為。
由于良知是非理性的、活潑的、直覺化的,醫治社會的“良知缺失癥”,切不可簡單地通過道德的法律化,強制人們實施道德行為來實現。實際上強制實施道德,可能使人們的良知背負更大的成本。
雖然從秩序出發考慮,道德也需要法律化,但法律所能強制的道德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且始終只能涉及行為領域,而無法涉及意識領域。良知的領域并非法律所能強制的領域,相反,它需要呼吸自由的空氣才能順利成長。良知需要實現自由,而良知需要的自由,必須靠法律來保衛。
法律對良知的保衛主要在于為良知減負,以實現良知的自由。法律對良知的保衛要求法律充當良知抵御壓力的屏障,使良知免受各種壓迫;同時又需要法律不斷地釋放正義之善,滋潤良知生長,營造適應良知生長的環境。
法律保衛良知的方式
(一)法律防范壓善行為保衛良知
壓善行為出現于縱向型社會關系之中,即出現在權力與服從關系中,它的表現是權力或法律迫使人服從而罔顧良知的存在。
1.法律防范權力對良知的壓制
國家權力和服從者的良知之間并不存在天然的和諧關系,相反,在盲目的服從中容易泯滅良知。雖然服從是權力成立的必要條件,但是對權力的服從永遠都不應背離個體的道德判斷。完全沒有良知過濾的服從,可能成為國家權力作惡的參與者。
在納粹德國時期,一些參與屠殺猶太人的德國官員,并未被發現有任何的邪惡動機,卻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以至于最終站上了審判臺。納粹軍官埃希曼(Adolf Eichmann)被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認為屬于這樣的典型。在埃希曼身上,阿倫特發現了一種有別于“根本惡”的“平庸之惡”的存在,即缺乏思維和判斷能力,盲目服從國家權力。個體對權力的盲從,現代官僚制度要承擔責任。因為對大多數平庸之人而言,在制度的逼迫下,良知難以呈現也許是普遍現象。對個體來說,要以良知來抗拒這種官僚化、理性化的制度,實際上有著巨大的成本負擔——被排斥、被否定以及其他經濟利益的喪失。
在良知面臨現代性危機時,法律無法改變現代性的方向,但法律可以提醒人們:對權力的服從并不能免去自己良知的責任,要善于傾聽良知的聲音,要勇于運用自己的良知。二戰后,對“平庸之惡”進行的審判即是一例,它彰顯的是法律對良知積極運用的鼓勵,對盲目服從權力的拒絕。1999年重慶對綦江虹橋垮塌案進行的審判,也表明盲目服從上級領導,并不能推卸自己良知和法律的責任。法律對“平庸之惡”的審判,提高了放棄良知判斷的行為成本,從而使良知的行為成本相對減少,因此對大膽運用自己的良知有激勵作用,有利于對社會集體良知的維護。
2.法律防范自身對良知的壓制
權力對人的逼迫也可能以暴力的形式體現出來,法律就是最為典型的形式。由于法律制度總是存在著不完善性,這種不完善的進一步發展也可能導致不正義,那么對以良知名義違背法律者,法律又當如何處置?
以良知的名義拒絕服從法律,顯然和基于私利的違法有顯著不同,但畢竟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善良違法要處理的問題是良知和法律孰輕孰重的問題。前者涉及對人性的尊重,后者涉及對秩序的維持,這樣一個兩難問題答案決不是非此即彼的。我們要實現的秩序不僅僅是一種秩序,還應當是一種尊重良知的秩序。保護良知不僅要求嚴厲制裁惡性的違法,以彰顯法律的威嚴,而且要求對善意的違法予以適當的寬宥,以顯示法律對良知的敬重。通過對善良違法的適當寬宥,法律不僅釋放了它的善意,而且減輕了良知的外在壓力,減少了良知的成本。
法律防范自身對良知的壓制,還要求不得濫用利益激勵,以至于強化了利欲對良知的擠壓。一個社會往往有自己所追求的目標,但當這種目標的追求僅僅依靠對人的利益刺激,而忽視人的道德情感時,人也成為了達成目標的手段。在這種法律制度下,良知將會受到壓制,甚至被驅逐。
但法律畢竟調整的是利益關系領域,如果不依賴利益激勵顯然無法調整這類社會關系,那么法律制度就必須考慮利益的激勵盡量不要過度地去激發人們的逐利之心,以免形成對良知的擠壓。同時良知又并非完全不依賴利益,大多數人的良知行為并非不計成本,因此法律也要致力于減少良知行為的成本支出,使人們的良知行為沒有后顧之憂。一句話:法律作為調整利益關系的手段,既不要迫使人們為了利益出賣良知,也不要讓人為了良知不得不喪失利益。
(二)法律嚴懲欺善行為保衛良知
欺善行為即欺負他人的善良,并利用它獲取利益的行為。欺善行為發生在平向型關系之中,在這種關系中,沒有權力與服從的特征,需要實現公平和平等,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對等對待。
就普通人來講,如果善良待人,卻招致惡的對待,善良將難以存續。比如,當我們好意扶起跌倒的老人,卻被訛詐醫藥費;當我們無私施舍路邊的乞丐,卻發現他們把乞討當成致富之路;當我們節衣縮食支援災區,卻發現救災款物被貪污挪用……此時,我們可能不再扶起老人,不再施舍乞丐,不再支援災區。
在平向型社會關系中,欺善行為比普通不正義行為更惡劣,因為欺善行為是通過欺負他人的善良而獲得的更大的好處,同時也讓善良行為者感受到良知行為可能遭到的巨大損失,于是引發善良行為者心中針對欺善行為的義憤。義憤從根本上看源于自我利益喪失或恐懼其喪失,因此,義憤的心理動因和自利的心理動因是基本一致的,無法平息的義憤有可能進一步轉化為自利自保行為,乃至利欲沖破良知的束縛,向不義效仿,去獲取更大的利益。
欺善行為讓良知背負了巨大成本,污染了社會的善良習俗,導致惡的蔓延,給良知的生長帶來了惡劣的環境。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欺善行為針對善良行為者實施,更容易被良善者相信,因而具有較小的成本。所以,它可以用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而法律懲罰就必須以更嚴厲的懲罰,來加大實施者的成本,才能禁止這樣的行為。
從中國刑法的規定來看,法律對欺善行為的懲罰更重。比如:《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挪用公款罪”中,挪用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歸個人使用的,比普通挪用公款處罰更重。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搶劫罪”中,“搶劫軍用物資或者搶險、救災、救濟物資的”也有著比普通搶劫罪更重的刑罰。
于是,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原則:當欺善行為出現時,在有關懲罰性法律規定中,應有更重的處罰。同時,鑒于欺善行為對社會良知的嚴重危害,法律應重點針對這類行為進行懲罰,而不能任其蔓延。比如,虛假乞討騙取善心,敲詐訛詐見義勇為者,利用慈善或宗教名義騙取捐款,等等。就目前中國的“好人法”的內容來說,僅僅免去良知行為帶來損害的民事責任是不夠的,還應當從刑法角度加大對欺善行為懲治力度。
(三)法律通過揚善行為保衛良知
良知生存的外部環境不僅包括良知所處的外部社會關系,也包括良知所處的外部制度環境。而良好的制度環境主要通過法律制度來實現。
法律制度促進良知的生存,不僅靠防范壓善、欺善行為來保衛良知,而且還要通過揚善行為來保衛良知。法律所弘揚的善不是偏私之善,而是公平之善,是站在全社會的立場上公平地對待所有人之善。
一個社會的人在社會中得到公平對待時,他就會有一種對社會的歸屬感,他因自己被尊重、被同等地對待而產生愉悅感。他也因此更容易產生愛與被愛的感受,也更能夠同等地、公平地對待他人。反之,當一個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時,他會感受到自己沒有得到社會的尊重,有一種被排斥、被壓迫的感覺,最終產生怨恨的負面情感。而不公平帶來的怨恨情感容易驅逐愛和善良,更有引發暴力的可能。此外,不公平還進一步助長人性中逐利的傾向,引發計較和貪婪,從而掩蓋良知。
從根本上看,社會公平之所以有利于良知,是因為公平減輕了良知的負擔,而不公平則容易激發人性中對金錢、地位以及被愛、被尊重的強烈欲求,最終使良知在人心中被擠壓。
因此,法律以公平來揚善,首先應當通過公平立法來維護良知。法律應當從社會共同感知的公平出發,制定符合本社會需要的公平之法。其次,法律通過善意適用來保衛良知。法官適用法律時的自由裁量如果不是出于公平之善,而是有偏私的裁量,那么仍然會損害當事人的良知意識。法官對任何一方當事人有意無意的偏向,都會導致對另一方當事人的欺凌,使當事人產生怨恨、被壓迫的感受,因此法官的良知直接影響社會的良知。
敬重良知才能保衛良知
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法律實現正義,道德促進良知,而法律無法對良知產生什么作用。但實際上,法律對利益關系的調整,對正義的實現同樣關乎良知。法律能否保護良知,還在于法律是否敬重良知。
失去了良知,我們不僅失去了道德上善與惡的判斷能力,不能主動地去追求善,而且失去了和邪惡相抗衡的能力。在人類發展史上,正是因為有了善與惡的判斷能力,我們才有了關于法律好壞的價值判斷。可以說,人類良知的缺失也將導致法律的正義缺失。正因為如此,法律必須敬重良知,保護良知。
然而,當我們這個社會上,人們對利益的過度追逐、對某個社會目標的急迫期待、對社會公平的極度漠視,都有可能忽視良知,使良知背負過大的成本和負擔,使良知遭受損害。一個法治的社會雖然不能造就良知,但法律可以保護良知,減輕個體在良知實現上的各種社會壓力。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摘自《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原題為《法律如何保衛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