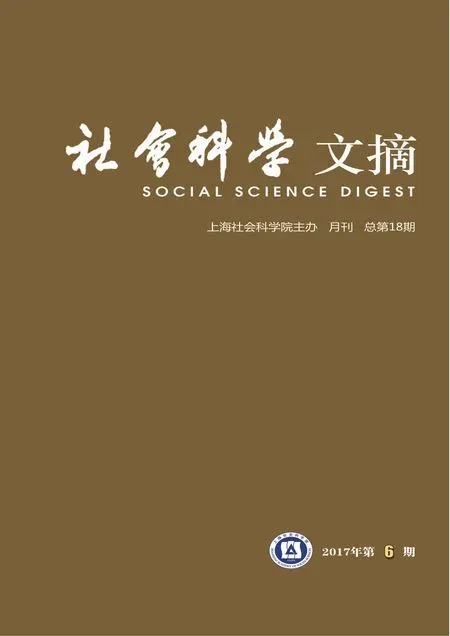家國傳統與治理轉型
文/劉毅
家國傳統與治理轉型
文/劉毅
家國傳統的社會學成因
所謂家國結構,或稱家國二元一體的結構,是華夏文明所特有的一種政治社會治理結構與主流意識形態傳統,即傳統中國在治理結構和觀念形態上,國與家遵循同樣的模式和準則,治家的原則等同于治國的準繩,政治的理念近似于家族/家庭的倫理。我們從傳統中國之“忠孝”、“親親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政治理念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國與家總是相提并論,國與家也總是相互支撐和相互印證的。
這是一種建立在血緣和家庭倫理基礎之上的政治,在這樣的政治格局中,君王即父親,臣民即子孫,國之政治帶有鮮明的家族色彩,家族的治理同樣被賦予強烈的政治法律任務。國與家是傳統中國最核心的兩個政治單元,這與現代西方所確立的國家、社會、個人的三元結構完全不同,可以說,傳統中國既沒有現代西方意義上的國家,也沒有所謂的社會和個人。不僅如此,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也迥異于現代西方的法治民主等,而是以禮治為基礎,以儒家思想為主要意識形態,建立了一套獨特的治理模式。而所有這些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典章制度與政治法律實踐,都是建立在華夏文明初期就形成的家國結構的傳統之上。
家國一體的政治社會結構有兩方面的社會學成因,一是戰爭,一是祭祀。戰爭之所以成為形成家國一體結構的原因,在于戰爭在華夏文明的初期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各部族的兼并融合主要是通過戰爭征服來實現的。此外,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我們或許可以推定,由于華夏文明所起源的區域乃是大河流域中下游地區,部族之間缺少天然的屏障,因此只能也必然是以軍事征服實現區域統一而告終,因此不同于希臘文明因地理屏障所形成的相互獨立的城邦。以戰爭實現部族兼并和融合所帶來的結果,就是原有的建立在血緣基礎之上的親族關系及其治理規則,被直接適用于新的更大規模的政治共同體,從而導致血緣宗法關系與政治治理方式的合二為一。就祭祀來說,華夏文明自始就存在著祭祀祖先神的鮮明特征,祖先崇拜又與“巫君合一”的傳統相結合,因而形成了族權、王權與神權相統一的獨特的華夏歷史文化,從而更加強化了這種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治理模式與文化傳統。而正是這種家國一體的治理模式與文化傳統,構成了華夏文明最為重要的文化基因,也形成了數千年文明演進的路徑依賴,使得此后無論華夏民族經歷怎樣的沖擊和巨變,都沒有走出家國一體結構的基本架構和范式。或者反過來說,正是由于家國一體的治理傳統,使得華夏文明的演進與發展未能實現新的突破,而只是在既有的框架內進行調整和改進而已。
家國傳統的歷史學演變
在早期中國的政治國家形態結構中,并沒有出現個體與家庭/家族的分離,血緣與政治的分離。相反,政治集團不過是家族的聚合與擴大而已,及通過征伐或聯姻等形式,從單個家族、氏族逐漸組合擴大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其間只有規模和數量的擴張,并無性質和結構的改變,這樣所形成的政治國家體制,被稱為宗法制國家。宗法制以嫡長子繼承制、宗廟制和同姓不婚制為基礎,分封制則同姓親族與異姓功臣兼而有之,天子與異姓諸侯、異姓諸侯相互之間均通過婚姻建立起政治聯系,因此異姓諸侯與士卿大夫總體上都被納入宗法秩序之中,從而基本形成了以宗法制為核心、族權與王權相重合的政治社會框架。
與宗法制的政治架構相適應,夏商周三代均建立了“以禮治國”的制度,禮之所以能夠成為宗法制國家的規范體系,是因為禮的內容與原則與宗法制正相匹配與符合。我們知道,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則就是家國合一、家國同構,家族倫理也同樣適用于政治理念,家以父權為根本,國以君權為綱目,因此,“親親”“尊尊”便成為禮的基本原則。
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家與國,“親親”和“尊尊”,并非具有等量齊觀的地位。究其根本,家須依附于國,“親親”也須從屬于“尊尊”,即家之倫理最終是為國之政治服務的。在宗法制國家治理之下,治家的道理等同于治國的原則,治家更是為治國服務的,這樣的治理模式,在古代中國之世代耕作、安土重遷,偏于內向與保守的農業社會和農耕文明背景下,便有著無以替代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因此激起百家爭鳴,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也由此揭幕。諸子百家,眾聲喧嘩,最終勝出的主要是儒、法兩家。在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奠定了儒家思想為道統,禮治、德治、人治之三位一體為政統的治理格局。但這只是制度和文化的表象,法家的思想與實踐并未隨著秦朝的滅亡和儒家的變通崛起而真的走向沒落,而是以一種隱而不彰的方式“潛伏”在帝制中國的肌體內部。儒家崇“王道”,包括“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教民以德的“教化”任務,以及由精通典籍,恪守德義的“士”、“君子”來治國的“人治”思想。而法家崇“霸道”,把秩序、強權和一個高度精密可靠的巨大的官僚專政政權的有效運作視為至上的目標。法家思想與儒家理論相互配合相互支撐,形成了儒法互補、儒法結合、外儒而內法的國家治理架構。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盡管“秦漢體制”下的帝制政治,與宗法分封制下的三代政治,有著很大的變化與不同,但是那種肇始于華夏文明初期的家國一體、家國合一的基本精神與架構,卻一脈相承地延續了下來。儒家的主張是“克己復禮”,以恢復周禮為使命,雖然孔夫子的愿望并沒有真正實現,但是“親親”“尊尊”的倫理政治原則仍得以繼承和守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精神依然被封為圭臬。
禮法結合的“秦漢模式”相比于宗法制度,可以被視為家國一體之治理傳統的升級版,更好地維護了家國一體的政治格局。由此導致的后果,便是公私不分的“家天下”和“一家之法”。
國家治理的現代轉型
通過以上從社會學和歷史學兩方面的論證與梳理,我們可以歸納出傳統中國之家國一體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自華夏文明初創以來,就形成了血緣關系與政治權力相融合的治理模式與結構,其后歷經夏商周三代之封建宗法、皇權官僚時代的禮法結合,雖有長達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但是華夏文明內在的家國一體的結構和模式不變,這是一種固有的文化基因,也形成了中國傳統國家治理的路徑依賴。當我們今天談到要實現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的時候,必然要以傳統的家國一體的治理模式為思考前提和邏輯起點,從而探索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可能性與路徑。
我們知道,現代國家是以工商業文明為主導的、以(市民)社會為基礎、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法治治理結構,其中國家、(市民)社會和個人是同等重要、不可或缺的三個主體,法治則是貫穿于所有主體和整個過程的運行邏輯。而在傳統中國的家國一體的治理結構中,現代意義的國家、(市民)社會和個人都是不存在的。此處的“國”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此處的“家”也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家庭(family)。準確來說,家國一體結構中的“國”既是封建宗法時期的“王國”,也是指皇權官僚時期的“帝國”,它是一種世襲壟斷的政治統治機制,擁有絕對權力和至上權威。與這樣的“國”相對應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是臣民。國君與臣民之間是擬制于父子關系的尊卑等級關系,是一種絕對的統治與服從的關系。而現代民族國家與其公民的關系則是一種建立在虛擬的社會契約基礎之上的授權委托關系,公民成為國家的主人或者說主權者,作為國家治理者的政府則是“為人民服務”的,公民讓渡出一部分權利給國家,國家則在政府的治理下,為公民提供必要的安全、秩序與福利。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也有人將nation-state譯為“國民國家”。
由于傳統中國數千年以來皆是農耕文明,村社和農戶是基本的生產單位,“家”或家族則自始至終是“國”以下的最基本的治理單位,在“國”奉行“君為臣綱”的政治原則,在“家”則以“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倫理準則。“家齊”則可以“國治”,這不僅是儒家圣賢的理想,也是傳統中國之農業帝國的現實。在家族體系中,無論為人父還是為人子,或有等級地位的不同,絕無獨立個體的存在,每個人都是以其在家族中的身份地位來定義其權利義務的。同理,在國家政治體系中,除君王之外,任何臣子都沒有真正的獨立主體地位,無論是封建宗法的“王國時代”,還是官僚皇權的“帝制時代”,理論上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最高政治統治者同時掌握著最高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臣民們的榮華富貴乃至身家性命,都取決于帝王的獨斷意志。因此,現代憲法意義上的公民權在傳統治理結構中是不存在的。
與此同時,在“家”之外,“國”之下,也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社會”,即由自由平等之民眾自愿組成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其原因主要在于傳統中國的農耕生產方式,以及各朝各代力推不懈的“重農抑商”的國策,中國的商業和商人階層始終未能興旺發達,同時,中國也未能發展出西方中世紀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那樣的自由商業城市,中國的城池通常只是軍事堡壘和官署駐在地而已,很少商業(集市)的功能,更不可能成為獨立的政治自治體。傳統中國雖然在禮制、法典和民間習俗中不乏“戶婚田土”之類的民事規范,但是始終未能發展出真正意義上的民商法,應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民商法的前提是自由平等的民商事主體、自由自治的市民社會和自愿、平等、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商業環境,而這些都是與家國一體的治理結構不相匹配,甚至是捍格不入的。
邁向法治的三元治理結構
傳統中國之家國一體的治理模式,固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時代的合理性,但是時移勢易,清末以來的中國已經義無反顧地走向了現代化之路,當代中國在工商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道路上已經走出了很遠,取得了巨變式的成就。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絕非一帆風順,甚至時有徘徊和倒退。從政府到民眾的法治觀念依然有待提高,現實運行中,官治、刑治和人治的歷史印記依然嚴重,符合現代國家治理觀念的憲治和民治的色彩依然淡薄。在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和現象的背后,可能仍然是歷史的慣性在起作用,是受到我們的文化基因和路徑依賴之制約的結果。
家國一體的治理模式所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難以產生獨立之個體與受保護之私產,另一方面,難以建立起真正的公共權力與公共空間。傳統中國的“國”乃一家一姓之私產,傳統中國之“家”,則無法產生獨立個體之現代公民,在國與家之外,具有現代意義的城市和商業缺乏生長發育的土壤。如此家國結構給國家治理帶來的局限性在于,旨在制衡與規范政治權力的憲法秩序無法建立,旨在保護個體私權之民法體系亦無法發展,即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在這種家國傳統的政治社會結構中,沒有生長與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傳統中國自軸心時代以降兩千多年無法自發創生出法治秩序,只能維持一種低水平和停滯狀態上的官治、刑治和人治。
因此,要向邁向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應當首先解構傳統的家國一體的治理結構,重新建構既尊重中國國情又因應現代化要求的國家治理的模式和原則。首先,重構現代國家和塑造現代公民。這就要求一方面要否棄傳統的絕對化、壟斷性的政治權力模式,將傳統的一家一姓之“國”改造為現代的“國民國家”,將傳統的以刑罰懲戒為主的刑治,改造為以維護公民權利為目的的憲治,用憲法來監督制約政治權力。另一方面,現代民主國家中,公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國家據以產生的原因和目的,成熟理性的公民也決定著一個國家政治社會的穩健和諧程度。公民絕然不同于家國傳統中的臣民,個體的尊嚴與權利得到保障是成為公民的必要條件,而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則是公民資格的充分條件,這些都需要以憲法為代表的公法體系和以民法為代表的私法體系予以保障和完善。
其次,在揚棄“家”之觀念與體制的同時,培育和建構與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相匹配的現代(市民)社會。如前所述,在農業為主導的傳統中國,工商業受到壓制,城市無法興起,市民階層更是沒有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因此,民法和商法也就沒有生長發育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家族體制和鄉族自治起到了準社會的功能和作用,但是這樣的傳統模式和體制,已經遠遠跟不上現代化的要求,也早已被百年來的革命運動所顛覆瓦解。在現代工商業時代,因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必須逐步發展培育出一個成熟自治的工商業市民社會,在其中,包括公司企業、大學醫院、宗教學術團體在內的各種社團組織(societies)能夠依照法律自主發展,自我治理和運營。這樣的一套現代社會體系,與市場經濟體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就能實現哈耶克所說的“自由擴展秩序”,從而實現財富增長與自由擴展的雙贏。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并不需要政府或國家權力之手的過多干預與規制,從而也大大減輕了國家治理的成本和人民的負擔。這也揭示出一個現代國家治理的關鍵所在,即國家治理未必需要國家時刻在場與全面規制。
第三,要注意不可簡單否定家族或家庭在建設現代治理中的作用和意義,應當從批判和繼承兩方面入手,既要否定傳統的建立在身份等級基礎上的綱常名教,同時也要看到親情血緣紐帶和鄉族信任關系,對于日漸城市化和陌生化的人與人之間良性關系的建構,具有積極的推動和調適作用,從而可以盡可能地避免因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急速發展,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疏離,以及過分個人主義造成的個體在社會中的孤獨感和被拋棄感。因此,被現代化所改造和升華后的中國式家族或家庭關系,反而可以成為建設中國式市民社會的良性的傳統資源,可以為單純商業化的商品經濟社會增添很多溫情和善意的紐帶,以彌補中國人因宗教信仰維度的缺失所造成的精神匱乏與物質沉迷。
總而言之,從家國傳統轉型為現代國家治理模式,一方面要從結構上從家國二元一體,轉變為國家、社會與公民的三元結構,而且三者之間并非隸屬與強制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相互支撐并相互制衡的關系。國家必須尊重和保障公民個體的權利和利益,必須給予社會自我治理和自我發展的空間,避免不必要的干預;公民在維護個體權利和利益的同時,亦應遵守國家法律和社會公益,履行公民義務。另一方面,要從傳統的禮法之治,轉向現代法治,其基本內容包括以憲法為中心的公法之治和以民(商)法為中心的私法之治。以憲法為中心的公法體系規制國家權力,創設國家制度,并保障公民基本權利。以民商法律體系保護公民的財產和人身權利,保障社會的自我治理和自由發展。最終,在國家、社會和公民的三元主體結構上,以法治的方式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摘自《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