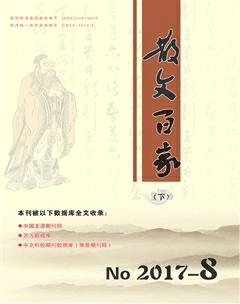涉江行
李貝卡
(一)
鋪天蓋地的黑。只聽得水聲嘀嗒,發出些空蕩的回響,遙如──晚鐘。孤獨比黑暗來得更悄無聲息,一點點纏繞包裹,溫柔到抑人鼻息,仿佛是獨步歲月靜謐流淌的河。
我緊了緊身前人的手,似握住了可視的溫暖,“你看見了什么?”我問那人。
“我們正在河里呢,河面一片乳白的濃霧,陽光正慢慢滲進來,小朵小朵的水蓮花擠在一起就好像”,那人頓了一下,“就好像,什么一樣呢……”低低一聲喟嘆。
“什么,是霧?”我伸手劃動,空無一物。
“你看得見,卻摸不著的阻礙。”
“什么是陽光?”
“溫暖的存在。”“那你是陽光嗎?”“不是呢。”我似乎能聽見那人唇邊無奈的笑意。“陽光和霧一樣,是摸不著的。”“那水蓮花是什么模樣?摸得著嗎?”“當然摸得著。”忽有一物被放入手心,耳后肌膚般細膩,柔軟而脆弱,竟叫我有些畏懼,想將它快些放下。“是雪白色的,亦如雪般是必將逝去的美好。”
我無法將曾接觸過的冰涼與手中物什作比,只攥緊了那人的手:“若我偏不讓它離開呢?”“你做不到。”“那你呢?”“我亦做不到。”
生命中總有些無可奈何。
“可明明是你……”又有什么是做不到呢?
那人反問我,“我,我們……又是誰呢?”是無數個聲音重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聽不出來,亦答不出來,只能沉默,沉默著跟隨那人,沉默著繼續往前……
(二)
眼前仍是一片漆黑,我看不清的前方,那人卻說瞧的真切,前方有燕子呢喃,有楊柳依依,有越人的歌女唱著不知名的好歌謠,采蓮的手兒于碧水中一擷,掬起一捧正好的春光來……
在那遙遙之地,一定充斥著光與熱,滿滿的,就同我握著的手心一般。可身旁卻是愈發寒涼了,我的眼已依稀能瞧見些迷蒙的光影,覺著周遭的一切,都正在變暗,然后我停下緊跟的腳步,停了下來,手卻沒松,那人亦被我拉著停下,有很多想問的,我卻沒能開口,那人亦未言語,呼吸聲,水滴聲,極緩慢的風聲……很吵。我想捂住耳朵,卻觸碰到了,如有實質的,凝滯的目光。
以及,倏然而落的冰冷液滴。
是下雨了么?曾聽那人說過的,天空落淚的時候,沒有陽光,陰沉一片,卻有著無限歡欣意味,獨屬于生命。
那么,“它們快樂嗎?”我能清晰感知到手背液滴的蜿蜒。
“本是快樂的。”人答道。
可我忽然難過起來,雨水很甜啊,會贈予膝下那清香的草綠,雨水很澀啊,會沖垮我那不知何處遠遠的城墻。
前方啊,并沒有那光明,我已篤定了,已困倦了,已不愿再走下去了,足底的水流會向后卷,將我引向最初的地方,就好像有些魚兒,毫無顧忌地,順流而下。
可我掙不開那只手。或者,并非是掙不開,只是有些難過啊,為什么難過呢,難過到不敢用盡全力,假裝那人緊抓的手的緣故,半強制地向前行。
(三)
又走了很久,很久,視野漸漸明朗,我問何是風何是云何是飛翔的鳥,那人便答何是山何是水何潛躍的魚,可我仍不識得啊,那半明半暗中一片灰白模糊的身影和面龐,我問“你是誰。”那人會說,“不知道。”簡簡單單的三個字,說出來,仍是駁雜一片,叫人無從猜測。騙子。世間又哪有人,會不知自己是何人呢?
而終有一日,不知是那人越走越慢,還是我越走越快,我竟一步越了過去,走在了前方。眼前的水域平靜如鏡,倒映了很多東西,很多很多,像是數不清的樣子,我近在咫尺的對岸,亦在其中。很亮很亮,像是擁抱了一整個太陽。
“你看,就要到了!”我反頭同那人講,湖面被言語驚起漣漪來,破碎的光影一層層蕩開,指尖的溫暖卻在一層層剝離了。在這越女采蓮的歌謠下,在這燕雀呢喃的春光里。我卻仍看不清那人的臉,拼盡全力啊,卻發現無可挽留。
極遠的地方,如雪的水蓮花雪般消融,更遠的地方,似水蓮花的雪花般的凋零。“那么,再也不見了。”觸手可及的地方,陪我涉江而行的人身軀如蓮霧般消散,話語也如蓮霧般消散,余音雌雄莫辨,若老若少,或喜或悲,皆雜合在了一起。
世間有哪有人不知道自己是誰呢?除非,這一路相隨,且歌且笑的,并不只單單一人,已有許多人,陪我走過這漫沒長河。“你說是不是?──我猜,是這樣吧。”
那一直籠罩的霧終于消散,來路歸途總歸一處,你我以為是涉江而遇,最后。
才知不過是隔江相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