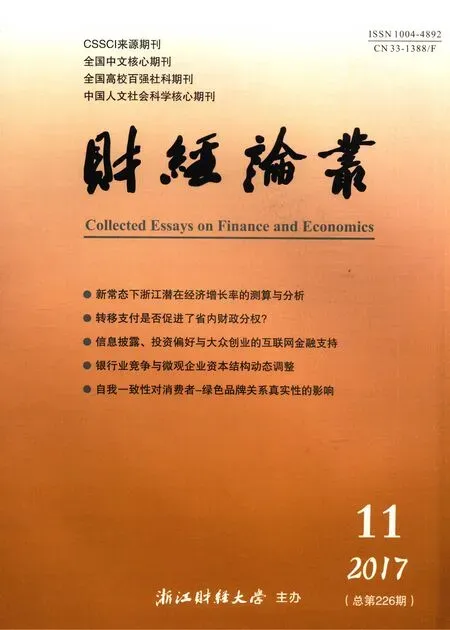土地金融、土地財政與居民收入占比下降
武 鑫,黃文禮,劉建和
(1.浙江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土地金融、土地財政與居民收入占比下降
武 鑫1,黃文禮1,劉建和2
(1.浙江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本文探討金融抑制條件下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在我國宏觀分配格局演變中的影響機理與結果。研究表明:首先,地方政府在競爭加劇的形勢下會通過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控制更多的經濟資源,以維持公共投資增長。其次,我國金融規模越大,對宏觀分配格局的扭曲效應就越明顯,居民收入占比會隨之走低,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收入比例會上升。因此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撬動更多經濟資源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應該恢復其公共部門的職能,將土地權利還給個體,將金融部門的服務重點轉向實體經濟。
土地金融;土地財政;地方政府競爭;宏觀分配格局
一、引 言

圖1 中國宏觀收入分配格局:1992~2014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的“資金流量表”

圖2 中國GDP支出法構成(1978~2015)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近年來中國的居民部門收入比例呈現下降趨勢,同期企業和政府部門的收入占比逐步上揚(見圖1所示)。居民部門收入占比從1992年的66.1%一路下滑到2008年最低的57.6%,近幾年才有所回升。我國這種宏觀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其宏觀背景原因在于以下幾點。首先與中國經濟結構失衡有密切關系。Kuijs(2005),李揚和殷劍峰(2007)已經指出,居民部門與企業和政府部門收入份額的此消彼長造成了中國內需不足[1][2]。宏觀分配結構不合理提高了資本形成率,卻壓抑了國內的消費需求。最后只能通過凈出口的形式來利用那些連國內投資也無法消化的過剩儲蓄(圖2)。在不斷積累之下中國經濟增長逐步依賴于投資和出口,難以保證增長質量和持續性。李學林(2015)指出如果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的矛盾一直存在,那經濟面臨的不僅僅是增長速度放緩的問題,極端的可能導致負增長[3]。其次,宏觀分配格局失衡會加深社會矛盾。居民收入占比和消費比例與民生息息相關,直接反映了福利水平。如果居民收入占比和消費比例長期滯后于經濟增長,增長意義和社會發展的最終訴求必然會引發公眾的質疑。中國社科院版的《2016年中國藍皮書》顯示“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1/3的財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貧富差距已經成為最受關注的社會問題。在宏觀分配格局失衡的情況下,經濟增長越快反而會積累更多的社會矛盾。
現有的研究主要從數據統計和制度根源(政治經濟學)兩個角度對我國的宏觀收入分配格局進行討論。首先從數據統計的角度來看,安體富和蔣震(2009)[4]計算了1996~2005年各部門初次分配和最終分配的比例,結果表明收入分配向企業和政府部門傾斜,居民部門收入占比不斷下降。造成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企業利潤侵蝕居民勞動報酬、政府稅收的快速增長以及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緩慢。高遠東、張娜(2016)[5]從人力資本與城鎮化的角度對居民收入的差距和驅動因素進行了討論。更進一步來看是擠占居民部門收入的不是企業,而是政府部門。任太增(2014)[6]將混合收入拆分方法運用與中國的數據,發現2004~2007居民部門收入份額持續下降,企業部門份額明顯上升,政府部門保持不變。Bai and Qian(2009)[7]指出中國宏觀分配格局失衡的原因在于勞動要素獲得的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下降,至少1996~2005年中國出現了這種現象。Chong-En Bai(2016)[8]在研究中國的儲蓄率高居不下的原因時,發現資金流量表夸大了家庭儲蓄率的上升和家庭消費率的下降,一個原因是資金流量表低估了政府收入的上升,另一個原因是低估了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
其次,很多研究從制度根源的角度挖掘收入分配格局變化的深層次原因。毛思波(2014)[9]從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制度弊病來解釋宏觀分配格局失衡,他認為初次分配體制和再分配體制不合理是造成分配失衡的首要原因。劉尚希和傅志華等(2015)[10]指出在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報酬的形成機制中市場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是居民部門在收入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政府的財政補貼向企業和資本傾斜,打破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消極作用使市場機制嚴重失效,進一步擴大收入失衡的局面。柳慶剛和姚洋(2012)[11]從更為微觀的角度看待收入分配失衡,認為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地方官員晉升機制使得政府成為重生產、輕分配的生產型政府。生產型政府的財政支出偏愛于投資生產型的公共品,擠壓其他非生產性但能提高居民效用的公共品。這種財政支出偏好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宏觀分配格局失衡。
本文認為我國存在比較顯著的金融資源配置壟斷和金融資源定價歧視等金融抑制現象(樊綱,2003;林志帆、趙秋運,2015)[12][13],在我國經濟金融程度已經大幅提高的情況下,金融抑制必然對宏觀分配格局造成影響。Liu et al.(2002)[14]的研究表明,中國官方利率至少比市場利率平均低50%-100%。儲蓄資源優先以低利率配置給效率低下的國企和地方政府,而正真需要資金的、更有活力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得到足夠的金融支持。這樣一來,有融資便利的部門因為壓低的利率相當于獲得了補貼,而提供儲蓄的居民部門卻因此無法獲得正常的市場回報。政府部門在經濟轉型中的參與和土地資源產權制度的變化使我國的金融抑制具有中國特色。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財權事權不對等,這種不對等關系會抑制隱性經濟規模(李永海、孫群力,2016)[15]。地方政府有動力通過金融系統來撬動更多經濟資源投入。在經濟的起飛階段,土地資源的配置和利用具有關鍵性的作用。隨著土地產權的界定和變化,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資源與金融杠桿的配合,釋放巨大的財富效應,因此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在中國廣泛運用。在土地公有制制度下,政府作為土地所有者,對土地的供應、土地價格的干預以及與土地相關的稅收首先會對自身的收益產生影響,然后會對其他經濟部門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馬曙光和李宏,2016)[16]。本文討論的金融抑制結合了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現象,相對于傳統的金融抑制而言,對宏觀分配格局的影響更為豐富和直接。本文將在經典的世代交疊(OLG)模型中引入制度環境約束,重點討論金融抑制下的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帶來的宏觀分配效應。主要結論是在現有政府體制結構下,地方政府的增長傾向會在金融抑制的配合下通過土地資源放大了金融杠桿。地方政府不僅獲得直接收益,并且獲得了更多的利率補貼。在這樣的框架中,金融發展的后果是居民部門收入占比越小。
二、理論解釋
(一)模型的基本架構


隨著經濟轉型的加速,經濟處于增長起飛狀態,對土地資源形成了巨大需求。由于土地的供給彈性較小,在分配關系占優勢地位,能夠分割大比例的收入流。因此,土地產權的配置將顯著影響分配格局。本文使用Lt表示土地資源每年的增值部分;用Gt增加值表示公共資本品投入量,進而代表經濟轉型進程,從而Lt可表示為Gt的增函數。如果制度性公共資本投入理順了利益分享機制,那么土地因為經濟發展帶來的增值部分會在初次分配以及再分配中被社會各個部門合理共享。但在中國現有土地產權制度下,地方政府可以直接獲得絕大部分的土地增值φ,還能夠基于此從銀行獲得抵押貸款,而居民部門僅保留(1-φ)*這個保留部分并不多,1999年前的土地管理法規定政府征地給予的補償,“不超過土地原用途三年平均所得的二十倍”。一般包括土地、青苗、附著物補償費和人員安置補助費等。。
(二)基本模型求解


3.金融部門和政府部門。本文假設在市場經濟初期階段金融部門是以銀行為主的組織形式,并且是壟斷的。銀行等金融機構(以下簡稱銀行)獲得儲蓄并貸給融資方。金融抑制表現在一方面存貸款利率都被控制在R,另一方面銀行對貸款對象具有選擇權。具體來說,銀行會根據資本按比例劃定貸款上限,即滿足Rlt≤φtkt。其中φt可以理解為政府部門對金融資源的控制程度。這種控制動機來自地方官員面臨的地區間GDP競賽的壓力和激勵。具體可以考慮一個兩地區競爭模型。地方官員有兩期任期,在第一期(t期)分別進行公共消費Ct和公共投資Gt。在t+1期的生產函數會受到Gt的影響,地方經濟競爭獲勝概率pt也是Gt的增函數。那么地方官員獲得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加強的政治獎勵Vt+1=(1+μ)Vt;如果沒有勝出,將正常退出政治舞臺。另外,用ρ表示折現率,η表示土地金融系數,則地方官員面臨的最優問題為:
maxCt+ρt+1Vt+1/(1+ρ)
st.Ct+gt=τYt+φLt+ηLt-RηLt-1
Yt=(N-n)yHt+yFt
上述問題的一階最優條件為dpt-1/dGt=(1+ρ)/Vt+1。地方官員通過增加生產性公共投入力爭贏得經濟競賽。Vt+1可以表示經濟競賽的激烈程度,也影響了公共投入的邊際效果。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收入為τYt+φL(Gt)+ηL(Gt)-RD2t-1,其中D2t-1表示政府部門上一期的貸款額。
(三)主要命題
命題1:地方政府為維持公共投資,通過“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控制更多的經濟資源。
地方政府為了維持不斷攀升的公共投資支出,需要借助更多的金融資源。一方面會通過土地金融的杠桿作用來撬動更多的金融資源。地方政府會加強對金融部門的控制力,使得金融部門的金融功能供給從實體經濟轉變到政府需求。地方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越深,對金融部門的控制力就越強,可觀察的土地金融現象就越顯著。另一方面直接利用土地財政獲得制度外收入。2002年推出“招拍掛”制度,即地方政府在賣出國有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后可以收取土地出讓金(70年的土地使用費)。2007年以前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從2007年1月1日開始,土地出讓收支全額納入地方基金預算。政府從“土地財政”中獲取的可支配收入應該是土地出讓金收入扣除依法向市、縣人民政府繳納的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拆遷補償費等費用后的余額,由于各種補償費用的數據難以獲得,考慮以出讓土地的純收入即土地出讓金占比較高的這種地方財政狀況來定義“土地財政”,在2013年土地出讓金已經達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60%左右。
命題2:金融部門發展的宏觀分配效應越加明顯,居民收入占比與企業部門、政府部門的收入比例此消彼長。
在上述模型分析中,公共投資驅動三個部門收入增加的機制是不同的。居民部門的收入占比為(N(1-τ)yHt+N(1-φ)L(Gt)+RDt-1)/(NyHt+yFt+NL(Gt)),可以發現其中無論是勞動收入還是資產收入都具有“類債”的性質。勞動力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從傳統部門流入市場經濟,在機會收入的限制下得到工資wt=(1-τ)yHt。資產收入主要是儲蓄而得的利息收入,但在金融抑制下被壓低于企業部門的收益率,為固定的回報率R。經濟轉型期的居民收入來源還要考慮土地資源的流量收入和存量財富效應。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使得居民部門對土地資產的分享比例(1-φ)被嚴重壓低。金融抑制下的土地金融規模越大,政府公共投資越有保證,經濟增長就越快。在這種情況下,居民部門收入占比與經濟增長出現了背離。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選擇
實證部分分別使用經典面板數據模型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檢驗上述命題,重點分析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對宏觀分配格局的影響。為減輕異方差的影響,對所有變量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經典計量模型如下:

(1)

(2)
式(1)、式(2)分別為考察土地金融(lnfed)和土地財政(lnldf)對政府收入占比(lngdi)和居民收入占比(lnpdi)的影響的傳統面板模型,下標i、t表示省份和時間,μi表示個體效應,εi,t是隨機項,ctrli,t代表控制變量。首先在經典面板模型的估計中使用固定效應模型(FE)和隨機效應模型(RE)兩種方法,并使用Hausman檢驗確定基準分析。此外,考慮到兩部門收入占比可能受前期變化的影響較大,增加了滯后一期的反應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形成(3)和(4)式的動態面板模型:

(3)

(4)
公式(3)和(4)中,lngdii,t-1和lnpdii,t-1分別表示滯后一期的政府收入占比和居民收入占比。對于動態面板模型,考慮到模型中新增的滯后一期變量可能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分別采用差分廣義矩估計模型(Difference-GMM)和系統廣義矩估計模型(System-GMM)進行估計。矩估計方法的優點是不嚴格要求變量是外生,并且能夠對隨機誤差項存在的異方差性進行控制。差分廣義矩估計模型最先由Arellano和Bond(1991)用于解決模型的內生性問題[18]。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又提出系統廣義矩估計模型改善了弱工具變量問題[19][20]。根據Roodman(2009),兩步GMM估計結果的標準差在Windmeijer(2005)對有限樣本標準差進行調整之前會被嚴重低估,調整后又會使估計量的近似漸進分布不可靠,因而本文將使用一步法GMM方法并使用Sargan檢驗來判斷工具變量的有效性[21][22]。
(二)指標設計和數據說明
被解釋變量包括政府部門收入占比和居民部門收入占比。繼分稅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所得稅收入比例在此之后也一直在逐年調整,為保持統計數據口徑一致,我們僅以地方財政總收入中的一般預算收入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政府收入占比(lngdi),而不考慮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轉移支付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上劃中央部分。居民收入占比(lnpdi)由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按人口城市化水平加權平均后的居民人均收入比上當地人均生產總值獲得。
核心解釋變量是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收入指標。考慮到關于土地金融的定義和指標鮮有文獻做出合理完善的說明,各省土地抵押貸款占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比例在1999-2011年期間整體呈現上升趨勢,而貸款又需要以存款作為支撐,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以銀行機構年末存款余額與當年該地GDP之比定義的金融發展水平(lnfed)替代土地金融。以地方政府當年獲得的土地出讓金*土地出讓金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土資源年鑒》中的以下名目:1999~2002年的數據為土地出讓收入,2003~2008年的數據為供應出讓成交價款,2009~2011年的數據為國有建設用地出讓成交價款。及地方財政收入中的耕地占用稅收入、城鎮土地使用稅收入、房產稅收入、契稅收入與土地增值稅收入之和作為衡量土地財政收入(lnldf)的指標。
控制變量參照主流文獻的做法,選取了城市化水平(lncity)、產業結構(lnind2)、人力資本水平(lnhr)和工資水平(lnw)。其中,以第二產業對地區GDP的貢獻率來表示產業結構(lnind2);通過職工平均工資以1999年為基期平減獲得工資水平(lnw);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人力資本水平以普通本專科在校生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計算;城市化水平用各省非農人口數占總人口數替代。另外,用以1999年為基期進行平減的人均GDP衡量經濟發展水平(lnpgdp),以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比重計算的外貿依存度(lnopen)。兩者作為嚴格外生工具變量進行廣義矩估計。
本文最終的樣本時間跨度為1999~2011年,數據來源于各省2000~2012年統計年鑒、《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Wind資訊。為避免極端數據的影響,剔除樣本中政府收入占比取對數后的值大于-2的省份(北京市和上海市),另剔除數據缺失較為嚴重的西藏自治區,最終數據只涉及28個省市。對于其他個別缺失的數據,本文使用spss19軟件中的線性插值法補齊。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描述性分析

表2 政府收入占比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
注:括號內為穩健標準差,***、**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顯著。下同。

表3 居民收入占比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
(三)實證結果分析
表2顯示了以政府收入占比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實證結果。在傳統面板數據分析法和廣義矩估計法下均能得到金融發展水平和土地財政收入會顯著提高政府收入占比的結論,這與理論分析結果一致。鑒于本文只考慮了政府出讓土地獲得的租金及土地流轉初期獲得的稅收,而未考慮現實中可能存在的地方政府通過廉價出讓土地手段進行招商引資獲得的大量間接稅收,估計結果中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收入占比的作用顯然是被低估的。傳統面板估計模型中,金融發展水平對政府收入占比的估計系數均大于0.4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了金融機構吸收的各項存款來提高本部門收入占比,且這種正向機制很可能會因為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抵押土地而較容易獲得銀行貸款及土地財政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而被放大。差分GMM(DIFF-GMM)和一步系統GMM(SYS-GMM)中,政府收入占比的一階滯后項均在1%水平上顯著,AR(2)的概率值p說明差分后的殘差項不存在二階自相關,Sargan檢驗值也表明模型所選擇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本文中使用的廣義矩估計方法是合理的。在政府收入占比模型中,其他控制變量對政府收入占比的影響相對不顯著,因而在此不作過多闡述。
表3給出了以居民收入占比為被解釋變量的估計結果。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下,土地財政收入的增加都會導致居民部門收入占比下降,且這一結果在5%水平上顯著,但在固定效應模型中下降的幅度更大,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以固定效應為基準分析。矩估計方法下,差分GMM中土地財政收入仍然在5%顯著性水平上反向作用于居民收入占比,但系統GMM中這一結果并不顯著。這說明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已經足夠大到能夠擠占居民收入占比的程度,應該引起重視。而金融部門的存款余額對居民部門收入占比的影響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居民部門由于信貸限制很難通過正規渠道獲得大量貸款用于生產投資從而大幅提高收入水平。控制變量中,以非農人口衡量的城市化水平能夠顯著拉大居民收入占比,這是顯而易見的,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城鎮居民人口比重的上升必然會提高居民整體收入比例。計量結果中職工工資水平顯著負向作用于居民收入占比,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資本要素對勞動要素的擠占,使得居民收入中通過勞動獲得的工資比例下降,另一方面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居民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GDP快速增長而工資水平沒能及時提高導致職工工資與居民收入占比呈反向變化。
四、總結與啟示
本文指出我國地方政府越來越依賴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的基本事實,以及隨之產生的宏觀分配效應。通過在地方政府經濟競賽的制度框架中引入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變量,使用包含三大部門以及金融中介的世代交疊模型分析了金融抑制和公共投資影響宏觀分配格局的具體機制。伴隨著經濟增長,表現為競賽獎勵Vt的地方政府間競爭程度會不斷增加,為了增加競賽勝出的可能性需要借助更多的金融資源來不斷追加生產性公共支出。地方政府一方面借助土地金融來撬動金融資源,同時對金融部門增加控制力;另一方面直接利用土地財政獲得制度外收入。在這種機制下,金融抑制下的金融規模擴大會強化對政府部門的金融功能供給,而居民部門獲得的金融功能弱化,收入占比會隨之走低,金融抑制的宏觀分配效應逐漸顯現。實證經驗已經表面金融的包容性發展是糾正分配失衡的重要條件(張林、李子珺,2017)[23]。
威權主義政治結構中地方政府經濟競賽具有顯著的激勵效應。但是在分權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經濟競賽也會并發其他問題,比如本文討論的宏觀分配效應。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土地和金融等重要的經濟資源還沒有建立完善的產權制度。地方政府在競賽的驅動下會強化控制金融系統,通過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撬動更多的金融資源。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分配的扭曲效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隨著十八大之后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改變上述局面的路徑也逐步清晰,即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回歸公共服務提供者的定位,回歸到經濟社會治理協調者的定位,將社會保障、教育等公共消費作為公共支出的主要內容,減少對經濟過程的直接參與。只有這樣才能斬斷地方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直接聯系,將土地權利還給個體。這樣才能將金融部門的服務重點從政府轉向實體經濟。
[1] Kuijs, L. Investment and Savings in Chin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5: 1-20.
[2] 李揚,殷劍峰.中國高儲蓄率問題探究:基于1992-2003年中國資金流量表的分析[J].經濟研究,2007,(6):14-26.
[3] 李學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理論與實證分析——基于擴展的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5,17(2):3-8.
[4] 安體富,蔣震.對調整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分配份額的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09,(25):2-20.
[5] 高遠東,張娜.人力資本、城鎮化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16,(1):70-79.
[6] 任太增.中印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比較[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1-8.
[7] Bai Chong’en, Qian Zhenjie. Who is the Predator, Who the Prey?——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he State of China's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9, 30(4): 179-205.
[8] Bai C. E. China’s Structural Adjustment from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erspective[J]. 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 Review, 2015, 3(1): 1-10.
[9] 毛思波.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江蘇商論,2014,(5):183-184.
[10] 財政部科研所區域室課題組,劉尚希,傅志華,等.以開放促發展:實現民族地區跨越式發展的新思路[J].經濟研究參考,2011,(62):2-18.
[11] 柳慶剛,姚洋.地方政府競爭和結構失衡[J].世界經濟,2012,(12):3-22.
[12] 樊綱.通貨緊縮、有效降價與經濟波動——當前中國宏觀經濟若干特點的分析[J].經濟研究,2003,(7):3-9.
[13] 林志帆,趙秋運.金融抑制會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嗎?——來自世界銀行2012年中國企業調查數據的經驗證據[J].中國經濟問題,2015,(6):49-59.
[14] Liu, X. R., Garnaut, R., Song, L., Yao, Y. and Wang, X. Private Enterprise in China[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2, 61(4): 1340-1342.
[15] 李永海,孫群力.稅收負擔、政府管制對地區隱性經濟的影響研究[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6,31(2):88-100.
[16] 馬曙光,李宏.收入分配結構調整與土地管理改革[J].財經問題研究,2016,(12):94-99.
[17]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 1937, 4(16): 386-405.
[18] Arellano and Bond.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 277-297.
[19] Arellano M., Bover O.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 68(1): 29-51.
[20] 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 115-143.
[21] Roodman, D. How to Do Xtabond2: 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ce and System GMM in Stata[J] .The Stata Journal, 2009, 1(9): 86-136.
[22] Windmeijer, F. A Finite Sample Correction for the Variance of Linear Efficient Two-Step GMM Estimator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05, 126(1): 25-51.
[23] 張林,李子珺.中國金融包容性發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17,(10):38-49.
LandFinanceandEvolutionofMacroDistributionPattern
WU Xin1,HUANG Wenli1,LIU Jianhe2
(1.China Academy of Financial Research,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310018, China; 2.School of Financ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310018,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how local governments’ public investment affects macro-distribu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Methods employed ar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control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by land finance in order to increase public investments. (2) The more the finance develops, the more distort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exhibits. Subsequently, the income share of the government sector and the corporate sector increases while that of the household sector decreas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growth-pattern based on land finance is unsustainable. It should restore its function as a public sector and finally return the land right to residents and shift the financial service focus to real economy.
Land Finance; Land Fiscal Revenues;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Macro Distribution Pattern
2017-04-10
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LY14G030013);浙江社科規劃基金資助項目(14XH008);浙江財經大學地方財政金融協同創新中心課題(CICLF2014005)
武鑫(1979-),男,安徽淮南人,浙江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副教授;黃文禮(1982-),男,浙江金華人,浙江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講師;劉建和(1973-),男,浙江紹興人,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F812.7;F124.7
A
1004-4892(2017)11-0024-09
(責任編輯: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