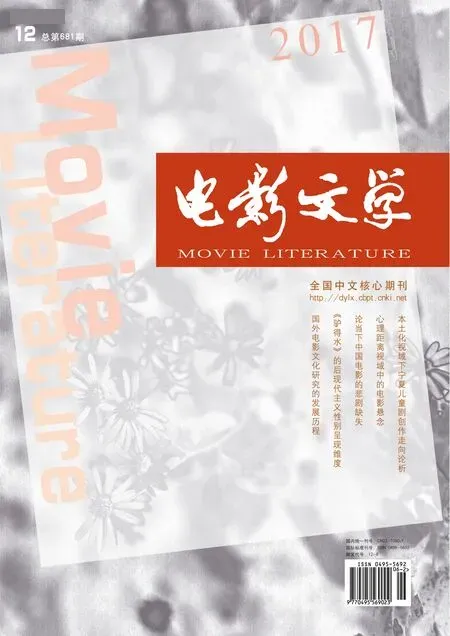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通天塔》的敘事學解讀
童美茹 (西安科技大學,陜西 西安 710054)
敘事學是20世紀60年代在俄國的形式主義基礎上誕生的學科,它著重研究的是文本中的敘事特征以及整個與敘事有關的系統,包括表述方式、敘事話語等。除文學外,電影亦可以成為敘事學的研究客體。亞歷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多最為著名的作品當屬《通天塔》(Babel,2006),電影游走于不同的時空中,借由“通天塔”倒塌的傳說,讓觀眾看到了命運的隨機性以及人類在溝通上難以克服的障礙。要在一部電影中給觀眾展現數條線索,并探討一個復雜的問題,電影的敘事模式是極具研究價值的,有必要將電影置于敘事學的角度下進行觀照。
一、敘事的錯位與并置
敘事時間是敘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克里斯蒂安·麥茨曾經指出時間在敘事中的地位:“敘事是一組有兩個時間的序列……被講述的事情的時間和敘事的時間(‘所指時間’和‘能指時間’)。這種雙重性不僅使一切時間畸變變為可能,挑出敘事中的這些畸變是不足為奇的;更為根本的是,它要求我們確認敘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種時間兌現為另一種時間。”電影是依靠在時間中變動的影像來完成故事的講述的,選擇怎樣的敘事時間直接體現了敘事結構。在《通天塔》中,全部故事都發生在四天之內,但是電影敘事的沖擊力在于,被卷入敘事的共有12個人,他們分別屬于四個國家:美國、摩納哥、日本和墨西哥。這四個國家不僅地理位置遙遠,且文明發展程度、語言、宗教信仰等各不相同。要在短短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內完成這一組角色在四天之中的命運敘事,“所指時間”自然是要極大地壓縮的。并且電影也不可能采用單線敘事的方式,電影以一種三線敘事(美國與墨西哥可以視作一條敘事線)的方式,在電影中制造了三條既錯位又并置的線索。并且這種錯位和并置,既是時間上的,也是邏輯上的。
首先來看時間上的錯位與并置。例如,當摩納哥線已經基本上宣告結束時,美—墨線才剛剛開啟。理查德和妻子蘇珊九死一生,終于等來了直升機,在直升機爭分奪秒的運送下抵達了設備先進的醫院,并且蘇珊經過搶救終于脫離了危險。這個時候的理查德感到無比疲憊、脆弱和慶幸,他滿懷著對家人的愛和思念打通了美國家里的電話,與兒子進行對話時,明明毫不知情的兒子說的都是一些學校里的普通事,理查德卻激動得淚流滿面,在兒子聽出他聲音不正常后還試圖掩飾。與理查德這邊劫后余生心情的激動不同,美國家中那邊保姆和兩個孩子卻生活在一片其樂融融的祥和之中。保姆正在計劃著穿越國境回去參加自己兒子的婚禮,她完全沒有預料到將會有一場超出她控制的劫難發生。在與自己的男雇主進行對話時,她的心態和語氣也是完全放松的。又如敘事時間上的并置。蘇珊被槍擊一案由于被美國政府認為有可能涉及恐怖分子針對美國公民的襲擊而影響很大,日本警方也因為槍支的來源被卷入案件中。間宮偵探在離開了千惠子家中后,身心俱疲的他坐進了一家小酒館,此時酒館中懸掛的電視機正在播報美國女子在摩納哥被槍擊一案。這構成一種諷刺性的敘事并置。間宮偵探履行自己的職責,然而卻無意中涉入了千惠子的家庭矛盾,面對一份他無法承受的畸形感情,這些是對他的警察身份造成羞辱的。在這個轟轟烈烈的案件中,他盡職盡責卻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局外人,并且心中塊壘無法對任何人訴說——盡管相對于千惠子來說他是一個口耳健全的人。
其次來看邏輯上的錯位與并置。電影中的12個人擁有不同的命運,在這一次命運神奇的交錯后,他們的愛情、家庭以及生活都發生了或巨大、或微妙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全可以歸類到電影黑幕時的獻詞中:最暗的夜,最亮的光。有的人被捕、被殺,或職業生涯宣告結束,或失去了健全的身體,這四天對于他們來說是最暗的夜,而有的人生命得到拯救,婚姻危機得到解除,誤會和痛苦得到了釋放,這幾天過后對于他們來說又不失為看到了最亮的光。暗和亮、悲與喜之間形成了敘事邏輯上的對立。而就并置關系來看,愛情方面,千惠子的愛情是一場鏡花水月,約瑟夫的愛情則終結于偷窺事件的敗露。家庭方面,理查德曾經搖搖欲墜的家庭在這場性命攸關的危機之后重歸幸福。千惠子和父親隨著在陽臺上的擁抱而實現了和解,而墨西哥保姆則被美國遣返,以這樣一種令人失落的方式實現了與家人的團聚。在生活方面,摩洛哥人依然生活在極度貧苦與暴虐之中(電影中摩洛哥警察對向導的訊問方式便是將他和妻子痛打了一頓),日本人(包括千惠子在內的殘疾人以及健全人,如千惠子的父親、間宮偵探等)都生活在一眾難以言說的壓抑與苦悶中,而墨西哥人既有載歌載舞、生機勃勃的一面,又有在北方強鄰面前只能是潛在的罪犯、偷渡者、非法移民的卑微一面。這些都被電影娓娓道來,在細膩的對應性、互文性的敘事中讓觀眾看到生活中的每一種痛苦。
二、陌生化敘事
在敘事學的理論中,敘事者和他所敘述的故事之間存在不同的關系,這種關系造就了敘事情境,敘事情境是敘事者為了使接受者能夠獲得某種具體的閱讀反應而對自己講述故事的方式有所選擇,從而制造出一種文本語境。這種文本語境有時是閱讀者/觀眾所熟悉的,有時則是閱讀者/觀眾陌生的。正所謂習以為常,在熟悉的語境中,一切事物與感情都容易被忽視,而敘事者有時就會采用陌生化的敘事使一切變得不尋常,能給人一種新鮮感,引起接受者一種平時沒有的關注。在《通天塔》中,大量的場景、情節以及臺詞都被陌生化了,令觀眾耳目一新。
《通天塔》所要追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問題,于是觀眾可以看到,電影中凡是需要迫切達成的、寄托著人們強烈情感的溝通基本上都是失敗或低效的,如蘇珊在摩洛哥奄奄一息,隨時都有可能因為流血過多而死,當地人卻與蘇珊和理查德語言不通。這樣的場景對于觀眾來說無疑是全新的。絕大多數觀眾沒有類似的經歷,即使有在不熟悉語言的異國他鄉旅行的經歷,也極少會身中流彈,并為其他旅客所拋棄,這是一種明顯地將常規生活進行了戲劇化處理(夸張、變形)的情節。而反過來,電影中也不乏人和人之間能夠較為流暢地溝通的場景。如在電影的一開始,摩納哥向導和牧羊少年約瑟夫的父親進行了一次有關槍的交易的對話:“給我這把槍的人說,這槍有三公里的射程。”“你要價多少?”“1000迪拉姆。”又如千惠子和她的聾啞同學興奮地比劃著手語,千惠子問朋友“為什么選角落這桌”,同學則用手語告訴她這桌旁邊坐著幾個少年,這讓她們得以默默地窺視少年,一邊又暗自得意、欣喜。無論是摩納哥的當地語言,抑或是日式的手語,對于絕大多數的觀眾來說都是極為陌生的。槍支的交易,懷春少女關于挑選聚會座位時的一點小心思這種情節本身是沒有新鮮感的,但是他們特有的語言使劇情顯得更為獨特和新奇,使情節的發展超出了觀眾習慣的生活圈子,激發出觀眾的好奇心理乃至求知欲望。
觀眾無法在不依靠字幕的情況下明白人物的語言,但是又可以從人物的表情、動作之中依稀猜到那種人類普遍性的情感,約瑟夫父親對這把槍顯然一見之下便十分中意,但又拼命掩飾自己的喜歡;千惠子羞澀地看向那幾個少年,而少年也對她投來曖昧、好奇的眼神,女孩們眉目傳情之時,男孩們也在竊竊私語。而電影的“陌生化”并沒有到此為止,導演顯然沒有滿足于僅僅讓觀眾產生新奇感。導演會讓一些不屬于他們交流圈子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即觀眾熟悉的方式)介入交流中,此時人與人之間一種深刻的裂痕便產生了,如當一個日本少年終于鼓起勇氣前去與千惠子搭訕時,千惠子因為無法聽見而讓勉強能說話的同學對他說“說得慢一點”以進行讀唇,同學所能發出的也只是在正常人聽來難以辨認的模糊聲音(但即使如此這也是千惠子羨慕的技能),這直接導致了日本少年被嚇退,并且將這一次對話當成奇妙的經歷與自己的伙伴們分享。在千惠子看來,自己成為一個被嘲笑的對象。這種裂痕最終引發的是觀眾對生活有了一種敏銳的感受——交流的雙方盡管處于同一個時空幻境之中,接受的世界觀、科學教育等是基本一致的,但是雙方卻無法進行直接對話,原本有可能朝積極、正面方向發展的情感在交流的碰撞中夭折,甚至迅速轉變為彼此厭憎(千惠子迅速以脫下內褲,掀起裙子給少年看私處的方式“報復”了少年),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
陌生化為情節制造了張力,它在大多數情況下給予觀眾的是一種美好的審美體驗(如在穿越劇中現代人與古代人鬧出了交流上的笑話),但是在《通天塔》中,陌生化卻給予了觀眾一種沉重感,讓觀眾感受到了隔閡的強大力量。
三、敘事視角與心理空間
敘事視角直接關系著敘事的“態度”,即敘事者看到的是何人何事,對所見對象持一種怎樣的態度,而被看者又擁有怎樣的態度。誰在看,不僅意味著敘事角度的問題,也意味著某種權力關系,這些都關系著接受者的召喚視野。而為了與視覺性有太過密切的關系,法國敘事學家熱奈特在1969年提出使用“聚焦”(focalization)一詞來取代視角、視點或視野等詞,但其本質上并沒有太大的區別。根據熱奈特的理論,一般情況下,聚焦可以分為零聚焦、內聚焦以及外聚焦三種。零聚焦便是所謂的全知全能敘事。而內聚焦則意味著敘事者便是片中人物,觀眾只能知道這個人物的所見所聞,而內聚焦之中又有固定式內聚焦和不定時內聚焦,二者的區別就在于敘事者是否有變動。從整體上說,由于敘事的跳躍性,電影的敘事是采用了零聚焦的,在蘇珊等人一無所知的時候,觀眾就能明白子彈來源于約瑟夫等人。但是敘事集中于單線時,電影則采用了內聚焦敘事。如墨西哥線基本敘事者全為保姆。當保姆醒來,關心地詢問兩個孩子的下落時,邊境警察卻冷冰冰地告訴她:“不關你的事。”
敘事視角的變動意味著觀眾得以轉換目光所及的物理空間,如觀眾前一刻看到的是五光十色,遍布高樓大廈,人潮洶涌,卻給人一種清冷孤寂之感的東京:后一刻看到的則是炎熱,充斥著粗糙砂礫,幾乎寸草不生的摩納哥,兩個空間都讓人感到壓抑,但是壓抑感卻是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敘事視角的變化能使觀眾進入不同人的心理空間中。千惠子回到家中,看到電視上有美國婦女被槍擊的新聞,便隨意地換了臺,這不是她關心的內容,她只關心與自己的伙伴出去玩的事。然而在嗑藥后,她意外地看到了心儀的少年在親吻自己的伙伴,陷入了絕望的她走出夜店,流落在新宿的人潮中。最后在陽臺上,脫光了衣服的千惠子盡管說不出話來,但觀眾都可以聽到她內心的吶喊。
《通天塔》以一支槍造成的一次意外事件帶領觀眾直接觸及了人類自有文明以后的亙古困境:無論人類是否能說話,是否操持同一種語言,在交流中往往總是口不能言,即使能言也詞不達意,語言往往帶來的是無盡的傷害,而不能溝通也意味著痛苦與誤會,人類因此只好默默地承受內心的諸多創痛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