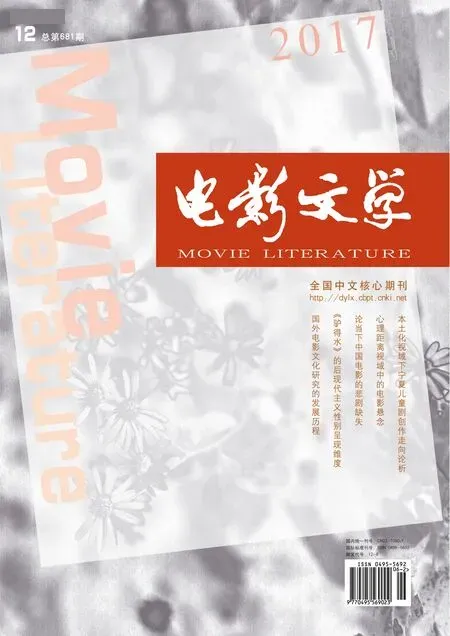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一九四二》:追問(wèn)政治真空與時(shí)間失憶
蘇喜慶 (河南科技學(xué)院文法學(xué)院,河南 新鄉(xiāng) 453003)
用文學(xué)去描寫一段發(fā)生過(guò)的歷史也許并不難,因?yàn)樵跉v史的天空,按照必然率和可然率,寫出模仿自然的事件,這在正史和野史中很容易找到可以發(fā)揮想象的素材,只要合情合理,布局成篇也可以成為“拙人的事業(yè)”(劉震云語(yǔ))。但是,文學(xué)的真正氣力不僅來(lái)自于故事依托的歷史框架,還在于作者所匠心構(gòu)造的結(jié)構(gòu),并且在結(jié)構(gòu)縫隙中滲出的思考辨析。但是文學(xué)又不能讓故事全然被理性把控,而是在感性世界里追尋直觀的訓(xùn)導(dǎo)。因而,在架空歷史的商業(yè)大片大行其道的當(dāng)下,能夠?qū)懗鲇梦膶W(xué)手段直逼歷史真實(shí)的作品,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卡西爾說(shuō):“人類文化的統(tǒng)一與和諧似乎至多只是一種善良的欺騙,而它不斷地被真實(shí)的事件進(jìn)程所挫敗。”[1]切入歷史的真實(shí),正是回歸文學(xué)的一種真誠(chéng)呈露。從這一點(diǎn)來(lái)看,劉震云的小說(shuō)《溫故一九四二》和影視劇本《一九四二》就更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小說(shuō)《溫故一九四二》與電影劇本《一九四二》,兩個(gè)相異的文本,在風(fēng)格和內(nèi)容上都做了迥異的話語(yǔ)改造,兩者相互參照,互為輔助,形成了強(qiáng)烈的對(duì)話空間。小說(shuō)中顯豁的主題命意,在劇本中隱身為潛臺(tái)詞,而饑民的碎片記憶成為劇本中最為震撼的民族肉身生存史詩(shī)。柯林武德指出:“過(guò)去的歷史不妨說(shuō)有兩個(gè)方面,即外在的具體事實(shí)和它背后的思想。”[2]政治真空與時(shí)間失憶正是構(gòu)成兩個(gè)文本互文,并產(chǎn)生思想意義的兩個(gè)重要的互涉性命題。
一、政治真空下的流民余生
政治真空是權(quán)力抽離后空間的自發(fā)改造與變革。在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孤島文學(xué)中,當(dāng)國(guó)民黨主權(quán)力被迫撤離,我們看到精英知識(shí)分子營(yíng)造的孤島文學(xué)應(yīng)運(yùn)而生。然而劉震云筆下的權(quán)力真空不同于此,它是立足于現(xiàn)實(shí)有意打撈上來(lái)的真空呈現(xiàn)。它以純民間的視角和私人化的敘述語(yǔ)調(diào),進(jìn)行著接地氣的文化解讀,這就使得文本帶有了民族備忘的性質(zhì)。在正史里,這段三千萬(wàn)人的逃荒史只化作幾十個(gè)冷冰冰的文字。這場(chǎng)天災(zāi)加人禍導(dǎo)致的三百萬(wàn)人消亡史留下的歷史拷問(wèn),遠(yuǎn)勝過(guò)地震海嘯和空難等對(duì)政治與人性的拷問(wèn)。
民國(guó)三十一年(1942年),河南淪為三不管的地界,對(duì)于災(zāi)民來(lái)說(shuō)無(wú)異于成了政治真空地帶。大旱顆粒無(wú)收,蝗災(zāi)吃盡麥苗稻秧,兵災(zāi)匪患橫行無(wú)忌。國(guó)民黨政府出于戰(zhàn)時(shí)考慮,暫緩救濟(jì)。軍閥出身的蔣鼎文催逼糧草,榨干了農(nóng)民手頭最后一點(diǎn)兒余糧。省政府尋求救濟(jì)無(wú)望,只好對(duì)災(zāi)民聽(tīng)之任之。日軍窺知國(guó)民政府放棄河南“甩包袱”的險(xiǎn)惡用心,懼怕國(guó)際人道主義譴責(zé)而暫時(shí)放緩了進(jìn)攻。對(duì)于災(zāi)民來(lái)說(shuō),在政治真空地帶,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逃離家園,背井離鄉(xiāng)求條生路。于是,在河南這條逃荒路上,少有的政治真空逼出了作為人的生存真相。
關(guān)于政治真空,嚴(yán)歌苓營(yíng)造過(guò)的“金陵”(《金陵十三釵》),有意塑造了一個(gè)空間上的政治真空——教堂,但是很快,日軍的強(qiáng)勢(shì)介入,打破了安全地帶的寧?kù)o。而《一九四二》的意義卻比戰(zhàn)幕下的南京、上海更為重大。其把空間放在了河南延津,這個(gè)最容易被人淡忘的小地方。國(guó)民政府消極抵抗,面對(duì)大勢(shì)壓境的日軍,南逃重慶的國(guó)民政府做了一個(gè)看似人道的決定,放棄旱災(zāi)蝗蟲侵襲絕收的河南,以空間換時(shí)間,讓出地盤,讓日軍接管并救濟(jì)屬于占領(lǐng)區(qū)的子民。然而,日軍也看透了老蔣的真實(shí)用意,懼怕國(guó)聯(lián)的人道干涉,而暫時(shí)放緩?fù)七M(jìn),讓災(zāi)區(qū)人民自謀生路。于是河南出現(xiàn)了傾巢逃難的悲壯場(chǎng)面。草根蟻命的生存被逼出了最為極端的征象。
從極端細(xì)節(jié)到極端情致,1942年逃荒路上的慘狀讓人觸目驚心。地主的兒媳剛生下兒子連餓帶受風(fēng)寒咽了氣,地主婆撲上來(lái)讓嬰兒趁著身子還熱乎再吸兩口奶。花枝找到了買主下家后,她和栓柱這對(duì)陌路臨時(shí)夫妻,在分別的那一刻,兩人跑到蘆葦叢中交換一件還算像樣的囫圇老布棉褲。進(jìn)入花樓妓院的星星服侍嫖客卻因暴飲暴食肚子撐得彎不下身。大量細(xì)節(jié)的真實(shí)將政治真空的時(shí)空填充得飽滿而又有分量,而反思也在表象背后伸向了現(xiàn)實(shí)人性觀照的維度。小說(shuō)中寫道,多年后,“我”去采訪那家被迫賣為妓女的家人,差點(diǎn)兒被誤認(rèn)為是商業(yè)寫書的掮客,挨了拳頭。對(duì)商業(yè)時(shí)代浮華文風(fēng)的嘲諷似乎又溢出了故事之外。其實(shí)小說(shuō)與劇本不同,它在有意地營(yíng)造歷史與現(xiàn)實(shí)對(duì)話的可能。
在災(zāi)荒生存面前,性、倫理、道德都被逼到了窘境。羞恥心、正義感在生存面前都成為被拷問(wèn)的對(duì)象。一輩子沒(méi)販過(guò)人的老東家想不到在大年三十將閨女賣進(jìn)了妓院,承載著自責(zé)和愧疚。花枝為了一塊餅干甘愿和栓柱睡覺(jué)。巡回法廳的老馬卻在洛陽(yáng)城外干起了幫助販賣人口的勾當(dāng)。瞎鹿背著媳婦花枝要賣掉兩個(gè)親生骨肉。這些不是人之初性本惡或善的抽象辯護(hù),而是在活生生的命懸一線時(shí)的存在性拷問(wèn)。
政治真空的始作俑者仍然歸于頹廢腐朽的民國(guó)政府。蔣委員長(zhǎng)在豪華的官邸里謀劃著戰(zhàn)后的世界格局和自身的出路,對(duì)于省委主席李培基的為民請(qǐng)命置若罔聞,并且在文化上他也利用霸權(quán)制造著輿論真空。《大公報(bào)》因一篇反映河南戰(zhàn)區(qū)災(zāi)情的文章而被停刊,因此河南在1942年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由于政治真空而失去了傳導(dǎo)信息的能力。生民哀鴻遍野,災(zāi)民自生自滅。當(dāng)他們失去了政府的庇佑,求生欲也吞噬了民族自尊心。小說(shuō)中寫道:難民們領(lǐng)取了日軍救濟(jì)糧,開始整連整連地解除中國(guó)軍隊(duì)的武裝,“據(jù)統(tǒng)計(jì),在河南戰(zhàn)役的幾星期中,大約有五萬(wàn)名中國(guó)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繳了械”。歷史就像一場(chǎng)荒誕的鬧劇,反諷意味值得深思。而在劇本中顯然規(guī)避了這種敘述口吻,而將災(zāi)難由私人述史轉(zhuǎn)換為宏大敘事。[3]當(dāng)劇本中打出字幕“六年之后,蔣介石失去大陸,退據(jù)臺(tái)灣”顯得意味深長(zhǎng)。劉震云寫道:“螞蚱吃莊稼,變成了人,人造反,就變成了螞蚱。”載舟浮舟的歷史價(jià)值油然而生,當(dāng)政府拋棄了人民的時(shí)候,人民也以最低賤、卑微的生命匯聚成聲勢(shì)浩大的瓦解政府的潛能。
二、時(shí)間失憶中的良知叩問(wèn)
空間上的政治失序已經(jīng)令人觸目驚心,然而時(shí)間上的失憶同樣令人震驚。時(shí)間失憶常常令人痛心,“作為河南人,我竟然從不知道1942年曾經(jīng)發(fā)生過(guò)這么嚴(yán)重的旱災(zāi),更令我震驚的是,這場(chǎng)災(zāi)難的親歷者和他們的后代無(wú)不選擇了遺忘”[4]。1942年的正史記載寥寥,而野史又不興,踏訪親歷者,得到的回答卻是一段幾乎要忘卻的支離破碎的記憶碎片。劉震云是一個(gè)熱衷于“溫故”歷史的作家和編劇。能夠把忘卻的記憶重新喚醒,把模糊的歷史影像擦拭清晰,這何嘗不是一個(gè)文人寫作者的良知所在?“文運(yùn)同國(guó)運(yùn)相牽,文脈同國(guó)脈相連”[5],以文學(xué)之筆叩問(wèn)隱藏在歷史背后的思想和根脈,這構(gòu)成了文本叩問(wèn)時(shí)間失憶、追問(wèn)歷史滄桑的感性表達(dá)。
一個(gè)民族的痛苦記憶常常淹沒(méi)于時(shí)間之維中,薩特說(shuō):“既然過(guò)去不復(fù)存在,既然它崩散于虛無(wú)之中,如果回憶繼續(xù)存在下去,它就必須作為我們存在的現(xiàn)在的變化而存在。”[6]過(guò)去歷史事件的永逝性易于被現(xiàn)實(shí)的操勞所遮蔽。而文學(xué)之維不僅喚起了時(shí)間的記憶,也通過(guò)對(duì)過(guò)去的追憶在人的直覺(jué)世界打上印記,獲得時(shí)間的永恒性啟悟。劉震云便是通過(guò)姥娘、花爪舅舅等親歷者的口述,觸摸遺忘在1942年的痛楚記憶。然而,他們的口述由于時(shí)間的磨蝕呈現(xiàn)出了時(shí)間失憶的征兆,這也正是一個(gè)多災(zāi)多難的民族最值得警惕的征兆。姥娘對(duì)于在反問(wèn)“哪一年”時(shí)表現(xiàn)出的記憶模糊和記憶力減退,被采訪人對(duì)苦難和屈辱的有意躲避,都構(gòu)成了溫故1942年的時(shí)間性張力。
劉震云寫道:“我相信她對(duì)一九四二年的忘卻,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觸目驚心,而是在老人家的歷史上,死人的事確是發(fā)生得太頻繁了。指責(zé)九十二年前許許多多的執(zhí)政者毫無(wú)用處,但在那位先生的執(zhí)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jīng)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yīng)比我姥娘更感到慚愧。……歷史從來(lái)是大而化之的。歷史總是被篩選和被遺忘的。”
故事巧妙地將國(guó)家元首與災(zāi)荒流民放在了共時(shí)對(duì)位的兩個(gè)歷史坐標(biāo)中。一個(gè)從政治權(quán)力角度和全局觀念中決定國(guó)家命運(yùn)走向的人(蔣介石),錦衣玉食,配上奢華的官邸和高雅的情趣,與三千萬(wàn)背井離鄉(xiāng)為躲避饑荒、戰(zhàn)爭(zhēng)和匪患的災(zāi)民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元首的大筆一揮也就決定了流民中三百萬(wàn)人的存亡。“掌握按鈕的人,歷來(lái)是不受傷害的。”委員長(zhǎng)思索的是中國(guó)向何處去,世界向哪方傾斜;而災(zāi)民在同一時(shí)刻思索的卻是:我們向哪里去逃荒。在1942年的中原大地,國(guó)家存亡和民眾生死扭結(jié)在了一起,底層民眾最卑微的求生呼告消逝在了歷史的天空中,當(dāng)權(quán)者的強(qiáng)勢(shì)緘默和人民的孱弱失語(yǔ)形成了一種集體的失憶。
時(shí)間失憶也映射出中國(guó)農(nóng)民“忍”的劣根性。血淚遷徙形成了對(duì)人類生存極限的最大考驗(yàn),也展示出中國(guó)底層人民的生存韌性、耐力和群體忍耐順從的生存哲學(xué)。當(dāng)親人死了,他們以“早死早托生”“早死少受罪”來(lái)安慰生者;當(dāng)糧食沒(méi)了,柴草也吃光了,轉(zhuǎn)而自賣換得活路。在那一刻,宗教信仰也變得孱弱無(wú)力。傳教士安西滿的出現(xiàn),無(wú)疑給政治真空地帶帶來(lái)了一種秩序的撫慰。他信奉著神父的教誨,深信災(zāi)荒中傳教正當(dāng)其時(shí)。東家老范家破人亡,他歸罪于不信主;長(zhǎng)垣東家老梁得傷寒死后不閉眼,他歸罪于過(guò)去不信主。于是,安西滿的彌撒儀式就具有宗教救贖的意味。然而,面對(duì)饑荒和戰(zhàn)爭(zhēng)他還是退縮了,跟隨潰兵逃離了難民,他開始懷疑上帝的威信,因?yàn)椤皩?duì)當(dāng)時(shí)的河南人來(lái)說(shuō),生存依靠的已經(jīng)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這種殘酷的環(huán)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間那點(diǎn)兒微弱的善良的光芒”[4]。電影劇本中進(jìn)行了更深入的展示:安西滿反問(wèn)主教“世上發(fā)生的一切,是不是也是主的旨意?……那上帝為什么總是斗不過(guò)魔鬼?如果斗不過(guò)魔鬼,信他有什么用?”而面對(duì)群體性災(zāi)難,信仰已經(jīng)毫無(wú)效力,最后發(fā)瘋的他怒燒日軍救濟(jì)糧,而慘遭射殺,像一位高僧一樣完成了涅槃。而此時(shí)國(guó)民的韌性已經(jīng)超越宗教精神的撫慰效能,持久忍耐也化成了對(duì)苦難史的淡忘,構(gòu)成了整體性的時(shí)間失憶。
三、追問(wèn)歷史意識(shí)的藝術(shù)沖動(dòng)
從存在論的角度看,小說(shuō)《溫故一九四二》與電影劇本《一九四二》呈現(xiàn)出不同的時(shí)空向度。“溫故”不僅包含著追溯之意,而且具有溫故而知新的現(xiàn)實(shí)反觀意義,因之我們?cè)谛≌f(shuō)訪談的記憶碎片中感受到的是往事和現(xiàn)實(shí)的雙重觀照。碎片不僅勾連起了日軍侵略中原、國(guó)民政府茍安一隅而放棄子民和領(lǐng)土的荒唐,更對(duì)歷史以現(xiàn)實(shí)的視角寄予了同情和理解,如對(duì)身處國(guó)際格局中的蔣介石的作為,作者給予了歷史理性化的解釋,這是現(xiàn)實(shí)歷史意識(shí)的復(fù)萌。而劇本《一九四二》顯然截?cái)嗔爽F(xiàn)實(shí)反觀的歷史向度,而把1942完成在歷史的多維呈現(xiàn)中。1942年本國(guó)政府的呆政、日軍的陰謀侵略、外籍人的援助(謝偉思、白修德)、難民的自生自滅,都凝縮在了故事敘述和視覺(jué)影像中。而現(xiàn)實(shí)向度的人為割裂也把歷史的深度反思留給了觀眾。
在歷史長(zhǎng)河中,戰(zhàn)爭(zhēng)是文學(xué)中最具激情和歷史感的宏大選題。對(duì)待戰(zhàn)爭(zhēng)的態(tài)度和關(guān)注的視角,凸顯出一個(gè)作家的寫作的銳力,以及對(duì)生存哲學(xué)和生命意識(shí)的體悟。縱觀當(dāng)代文壇,能夠真正從民間立場(chǎng)書寫戰(zhàn)爭(zhēng)記憶的作家其實(shí)寥寥無(wú)幾。對(duì)歷史文本的篤信和對(duì)底層感知的遮蔽,構(gòu)成了對(duì)當(dāng)代精英知識(shí)分子的雙重迷惑,對(duì)于戰(zhàn)爭(zhēng)荷爾蒙的張揚(yáng)和對(duì)于權(quán)力力比多(libido)的展示常常將人們帶入單向度的激情宣泄中。但是,劉震云不同,他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切入時(shí)常帶著一種世紀(jì)思考和鄉(xiāng)土記憶,基于“扎根生活,植根人民”的藝術(shù)信念,使得他的作品更加獨(dú)特和別致。
在歷史典籍中,戰(zhàn)爭(zhēng)常常被簡(jiǎn)化縮略為成敗雙方的斗爭(zhēng)角逐,還有一連串觸目驚心的傷亡數(shù)字。然而,戰(zhàn)爭(zhēng)陰云籠罩下的百姓生活,常常淪為被歷史學(xué)家遺忘的角落。劉震云為了復(fù)活這段歷史,從河南到山西,再到陜西、重慶,甚至巴黎,踏尋災(zāi)民逃荒足跡,走訪親歷者,探尋上輩親人殘存的記憶,并且從當(dāng)年的報(bào)紙、新聞,甚至國(guó)外報(bào)紙報(bào)道中查考自己家鄉(xiāng)的饑荒史。所以,《溫故一九四二》就像是那段歷史的補(bǔ)證和拾遺。嚴(yán)格意義上講,它不像是一部小說(shuō),更像是報(bào)告文學(xué)或者歷史散文。而劇本《一九四二》整理出了三條清晰的歷史線索,將記憶的碎片黏合在一起。一條是國(guó)民政府內(nèi)部上下社會(huì)科層鏡像的揭示,一條是追問(wèn)“我姥娘”的身世,勾起了地主沈家逃難的歷史,第三條是覬覦中原的日寇侵華史。三條線并行發(fā)展,互為映襯,與《溫故一九四二》形成了互文性的文本間性,全方位地展示出歷史的境遇和生民的生存狀態(tài)。
小說(shuō)與劇本均帶有強(qiáng)烈的歷史審判意識(shí)。政治真空不僅帶來(lái)流民的無(wú)政府狀態(tài)下的自我救贖,也激化了權(quán)力失控下的生存亂象。在西行的路線中,流民倒斃而亡,餓殍遍地,狗食人,甚至人食人形成了最為悲壯的生民血淚遷徙史。而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是國(guó)民政府上層官僚的歌舞升平,基層官員的利益瓜分,還有日軍將領(lǐng)岡村寧次的老謀深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政治諷喻不言而喻。然而國(guó)民政府政治獨(dú)裁、軍閥組閣的劣根性也暴露出來(lái)。蔣鼎文軍隊(duì)嚴(yán)陣以待,后又不戰(zhàn)而撤,軍需商趁機(jī)投機(jī)倒把,銀行加緊盤剝,潰兵哄搶災(zāi)民衣食,甚至欺男霸女,亂世加亂象成為劇本中最濃墨重彩的影像,并且以強(qiáng)烈的代入感,召喚著歷史人道主義意識(shí)的復(fù)萌。
人文意識(shí)也在文本中得到了充分彰顯。對(duì)于飽經(jīng)苦難的災(zāi)民,他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國(guó)人。在政治真空地帶,當(dāng)吃的問(wèn)題(生存)占據(jù)第一位時(shí),民族大義這個(gè)帶有國(guó)民性的特征被真空抽離。從延津出發(fā),由避難到被迫逃荒的沈殿元一家形成故事主線。軍機(jī)狂轟濫炸,潰兵趁火打劫,“他們成了最終災(zāi)難的承受者和付出者”。“早死早超生,死了就不受罪了”的韌性生存哲學(xué),構(gòu)成了苦難的中國(guó)人民在歷史長(zhǎng)河中近似幽默荒誕的生存邏輯。賣兒鬻女,易子相食,成為民眾面對(duì)災(zāi)難時(shí)的最后良知底線。劉震云坦言:“這部小說(shuō)在巨大的悲傷里蘊(yùn)含的幽默,這是中國(guó)人面對(duì)死亡的態(tài)度,也是我一直想要表達(dá)的東西。”[4]而長(zhǎng)久的忍耐也磨平了創(chuàng)傷,消磨了歷史的殘存記憶,面對(duì)歷史的模糊和面對(duì)苦難的耐受力幾乎形成了中國(guó)民間歷史緘默的集體無(wú)意識(shí)。
四、結(jié) 語(yǔ)
審視劉震云的劇本《一九四二》和小說(shuō)《溫故一九四二》,我們看到了一個(gè)互文性的文本生成空間,小說(shuō)以調(diào)查訪談的方式,打撈起沉睡在1942年的記憶碎片,劉震云說(shuō):“ 這種體裁的作品是通過(guò)外在事件的真實(shí)、人物的真實(shí)、細(xì)節(jié)的真實(shí)來(lái)達(dá)到內(nèi)心的真實(shí),作家要得到這些,需要具有笨拙的精神。”[7]而影視劇本則以人物為主線,以強(qiáng)烈的回憶代入感,展開了一場(chǎng)史詩(shī)性的鄉(xiāng)土災(zāi)荒流民史。兩個(gè)文本互為印證,互相補(bǔ)充,新聞的紀(jì)實(shí)性與文學(xué)的直覺(jué)性和哲理反思性形成了巧妙的對(duì)位、融合與呼應(yīng)。“1942”作為一場(chǎng)民族災(zāi)難的符號(hào),透過(guò)政治真空的極端環(huán)境,喚醒了久違的時(shí)間創(chuàng)傷記憶。
空間上流民遷徙,時(shí)間上苦難綿延,構(gòu)成了一場(chǎng)中國(guó)災(zāi)民的出延津記。馮小剛聲稱:“我一口氣看完,對(duì)本民族的認(rèn)識(shí)產(chǎn)生了飛躍。小說(shuō)沒(méi)有故事,沒(méi)有人物,也貌似沒(méi)有態(tài)度,沒(méi)有立場(chǎng),主角寫的是民族,情節(jié)寫的是民族命運(yùn)。”劇本的創(chuàng)作卻經(jīng)歷了17年的修改才得以定型,“我(馮小剛)帶隊(duì)選景重走長(zhǎng)征路,震云數(shù)易其稿孜孜不倦。經(jīng)過(guò)十年的沉淀,劇本的問(wèn)題被逐一發(fā)現(xiàn)并得到糾正。最大的收獲是在逃荒路上,人物之間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轉(zhuǎn)換”[8]。當(dāng)然作者的真正用意不僅在于喚醒沉睡的民族記憶,更重要的是反思導(dǎo)致時(shí)間斷裂和民族失憶的根源。多災(zāi)多難的痛苦記憶消泯在民族的耐受力之中,歷史的淡忘和積極用世的現(xiàn)實(shí)邏輯又常常使人們失去駐足追問(wèn)的勇氣。這種民族根性的揭示,帶來(lái)了這部作品難得的理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