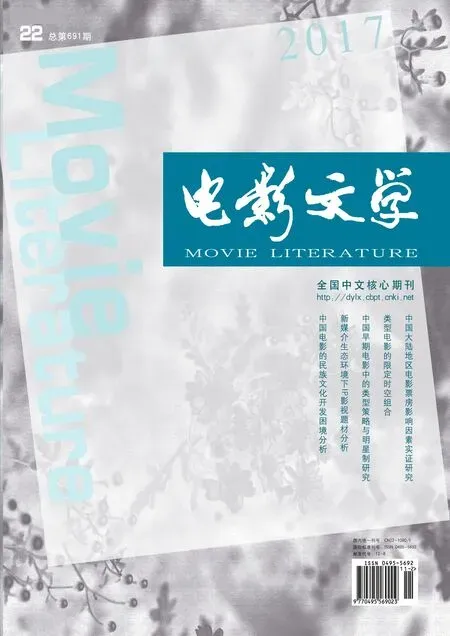論電影《裂縫》中的多重分裂
王 凱
(吉林建筑大學,吉林 長春 130000)
“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欲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世界為你而造,一切皆有可能。”欲望是人類生存、繁衍、發展、一切活動的原動力,它既是本能也是“歷史地被決定的”,因而在不同歷史條件、個體的不同階段,欲望可以表現或衍生為食色、好勝、嫉妒、獵奇、求知、渴望、貪婪……它們或潛在或自為地共生于每個個體、每個群體。所謂“裂縫”,即是難填的欲壑,未受理性控制的欲望的肆意泛濫。為了凸顯和激化由欲望產生的人性缺陷、個體沖突,導演喬丹·斯科特將電影的故事背景由原著中的20世紀60年代的南非移植到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并借由敘事空間和時代的特殊性,賦予了“裂縫”多重內涵和諷刺意味。
在幽靜而嚴苛的教會寄宿學校里,個性張揚、“見多識廣”并鼓勵學生追逐欲望的“異類”教師G小姐頗受學生歡迎,跳水隊的女孩們腰系紅絲帶以示對G小姐的忠誠和崇拜,但這種穩固的團體關系隨著西班牙貴族女孩費雅瑪的出現而逐漸分崩離析。這位真正博聞廣見、美麗友善而又有著獨立思想的女孩成為G小姐欣賞的對象,失寵的小團體首領黛對其深惡痛絕。然而,隨著G小姐的偽裝被剝離、費雅瑪的魅力被發掘,團體關系再次發生微妙的變化,費雅瑪不僅是包括G小姐在內的教師們的重點關照對象,似乎還成為小團體的新領袖。由費雅瑪的抗拒和小團體的疏離所造成的挫敗和不安逐步激活了G小姐極端化的自我保護機制,她利用青春期女孩的盲目和狂熱,編造謊言使小團體對費雅瑪步步緊逼,造成費雅瑪哮喘病發作,女孩們嚇得跑回去求助,G小姐卻趁機拿走了救命的吸入器導致費雅瑪死亡,而這一幕恰好被黛看到。結尾處,G小姐被驅逐出校而不得不“重新成長”,黛則主動離開學校,如費雅瑪般冒險探索真正的世界,以此獲得救贖。
影片以“入侵者”費雅瑪的遭遇為線索,用灰暗的筆調分別解構了個體、群體、環境三層維度的矛盾沖突,在由淺入深的分裂運動中展現人性的黑暗與暴力、兒童的殘忍與盲目、女性主義的郁結、依附人格下的集體狂熱等。
一、個體自身的分裂
“阿尼姆斯”是榮格原型理論中關于女性無意識中的男性人格的指稱,它只有在具體的情境中才會被激活,并表現出形象性、獨立性和多樣性,并可以對人發揮積極和消極的雙重影響。在單性別的教會學校里,缺失的男性激活了青春期少女們的性幻想,也激活了“阿尼姆斯”原型。這種意識與無意識的整合建筑起在此向度下的完善人格,從而使得這一特殊空間下的個體和整體分別達到和諧。
G小姐以一襲男人裝束泛舟湖上,優雅地抽著煙的出場便奠定了她與眾不同的異性氣質和異性化人格心理傾向,這既是她獲得跳水隊女孩們崇拜的原因之一,也是導致她人格異化的根本要素之一。此后G小姐也多次以“褲裝女性”示人,她同迷戀她的黛一起,組成與傳統的“裙裝女性”對立的陣營,由此也映射出彼時英國女性運動的一面。“1903年,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她的兩個女兒領頭成立‘婦女社會政治同盟’,標志著婦女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這些新上陣的女權主義者擺出戰斗的姿態,讓社會立即感覺到她們咄咄逼人的風格。”1910年前后女性穿褲子騎馬或騎自行車不再是非法行為,并且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女性要承擔絕大多數的后方工作,因此“維多利亞遺風”的約束被極大削弱,鯨骨長裙被輕便衣裙取代,時尚且實用的女褲也成為女性開始獲得社會認可、與男性平權的一種標志。在電影中,G小姐和黛的幾次褲裝打扮不僅反映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衣著變化所隱含的時代價值,更是她們男性心理的一種外化表現,而這種異性化人格傾向、女性主義的郁結正是由于社會文化的抑制造成的集體無意識。以G小姐為代表,她在智慧、演講、實干以及膽識方面的突出表現無不是“阿尼姆斯”特質的表達。
然而這種“原型形象的特征并不僅僅取決于它所代表的那個潛在性別的特質,同時還受到每個個體在人生歷程中與異性代表相處經驗的影響,同樣產生影響的還有女性個體心靈中的男性集體意象”。但由于英國教會寄宿學校的嚴格古板,學生們缺少對男性的了解、與異性相處的經歷,尤其是一生未離開過學校的G小姐,所以她們所表現出的異性化人格傾向必然是原始而局限的。因此,當G小姐脫離學校范圍而接觸真實社會時便會表現出不安和膽怯,當個體的權威受到威脅時便會制造矛盾、轉嫁外部,甚至采取極端措施。影片通過G小姐的造型變化和對費雅瑪的態度轉變、費雅瑪和跳水隊女孩們的關系變化、黛的心理矛盾等,逐漸將色厲內荏的G小姐形象刻畫完整。另外,三方的持續拉鋸反復激活著G小姐的“阿尼姆斯”特質,并將其轉變為消極的破壞力,從而使這一個體走向分裂。
而對于G小姐以外的跳水隊成員來說,導致其自身分裂的最大原因在于依附性人格。囿于空間局限、知識閉塞,以黛為首的忠于G小姐的紅絲帶團體對G小姐虛構的冒險經歷、制定的跳水規則、宣揚的生命主張深信不疑,因而形成對G小姐的極度崇拜和依賴,以至于使個體消失于集體中。而由于這種依附性人格的養成,弱小的羅西、法茜怯于表達自己的反抗,莉莉、波比等不齒于推波助瀾,對集體絕對服從,小團體的首領黛則尤其受此影響,害怕被人忽視,當與G小姐的親密度降低時便感到崩潰。
小說《裂縫》被譽為“女性版《蠅王》”,卻有著比《蠅王》更真實殘酷的故事、更錯綜復雜的人物,但也同樣探討了“宇宙生發、人類演化和彌久恒新的集體無意識本性,以及共同性、集體性為主體的人類性”。電影保留了小說的陰暗質感,聚焦黑暗的人性和邪惡的執念,使人們認識到自己本性的危險并加以有意識地控制。同時又通過結尾處G小姐的被拋棄和黛的主動離開給予影片一抹亮色,并以此打破封閉體系和封閉空間的圍困,換取分裂個體的再度彌合。
二、封閉體系的分裂
Crack意為“裂縫”,在《約伯記》中象征七宗罪之一——“嫉妒”的惡魔利維坦(Leviathan),其詞語本意即為“裂縫”,它是暴戾好殺,令周遭聞之色變的海怪,亦指人類內心無法填補的差距感而產生的裂縫。影片中,宣揚“欲望”“野心”的G小姐受到被教會學校的嚴肅刻板禁錮已久的女孩們的迷戀。在費雅瑪到來之前,G小姐用獨樹一幟的思想領導力使這些具有分裂潛質的個體緊密黏合在一起,從而構成了等級分明的封閉體系。影片開端處的幾個段落便將此勾勒得淋漓盡致,黛無時無刻不在搜尋G小姐而渴望獲得其關注,黛注視G小姐時的神情,唱詩時女孩們對姍姍來遲的G小姐的翹首期待,跳水訓練時G小姐雄健有力的演說,跳水隊女孩們對黛的服從、嫉妒或忍受,跳水隊女孩取笑、欺負其他女學生,由此構建了“G小姐——黛——跳水隊其他女孩——普通學生”這種由高到低的層級關系,展現出以集體性為主體、趨向穩定、群體分層的自然本性。
但隨著費雅瑪的強勢介入,封閉體系的平衡狀態則被打破。以G小姐為代表的教師階層(封閉體系的頂層)對這位西班牙貴族學生采取了與以往不同的接待態度,使其異于普通學生,G小姐對她的青睞有加、主動示好使其異于跳水隊員,費雅瑪拒絕G小姐的拉攏、抵制教會學校的陋習又使其遠離體系上層,因此,嚴格而穩定的線性等級秩序就變成以嫉妒為動力的體系重建運動。為嫉妒所俘卻又鼓吹欲望的G小姐所施展的思想領導術受到置疑,使得受此約束的個體分裂潛質被激活而強化,包括G小姐、黛、波比等,她們開啟各自不同的自我防御機制,以期達到體系的再度平衡。
在弗洛伊德看來,防御機制指的是“自我在解決可能導致精神疾病的沖突中所采用的全部手段”,包括否認、壓抑、文飾、投射、置換、退行、認同等,通過歪曲現實以降低或排除焦慮,從而維持心理平衡,因而“自我”才成為“本我”和“超我”之間的緩沖結構。但“自我總是被本我的欲求牽制著,因此,自我的行動在本質上不是以與主體意識相獨立的客觀理性為出發點,而是以滿足動機或緩解緊張的主觀要求為根本導向”,自我防御機制的無意識、非理性在G小姐和黛的身上獲得突出展現。
對從未離開過教會學校范疇的G小姐來說,其精神人格的成長并不健全,仍停留在嬰兒早期的自戀階段,以自我為中心,常輕易地抹殺事實,這樣的初級防御機制使得已經成年的G小姐脆弱且具有危險性。對于以黛為首、處于青春期的跳水隊員們來說,不成熟的防御機制使其在遇到挫折后退化到更幼稚原始的心理和行為來應對矛盾,因而也就暴露出最初級的群體性和動物性。“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由此,自戀需求與依附需求一拍即合,領袖的本我欲求、領導力、煽動性和“群體的沖動、易變、急躁、易受暗示與輕信”合謀殺死了“入侵者”費雅瑪,但在此過程中,原有體系內的成員們也發生了心理變化,從而使原有的封閉體系再難維系。
三、封閉空間的分裂
影片將故事背景由20世紀60年代的南非轉移到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是契合導演的文化底蘊又富有挑戰的做法,因為喬丹·斯科特選擇了耐人尋味的教會寄宿學校為具體的敘事空間。喬丹·斯科特曾解釋說:“教會學校是英國最正統、最刻板的代名詞,地處田園牧歌式的鄉村,卻發生這樣一件事情,因而更具有諷刺意味。并且,將故事設置于更容易產生極權和極端事件的時代,使教會寄宿學校更能發揮映射歐洲人心理的作用。”
英國的教育制度并不如它的先進地位一樣發展迅速,教育通常由私人負責,國家并不太插手這項事業。“在很長時間中,學校主要是由教會開辦的,不同教派都有自己的學校,為本教派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國家不存在教育政策,也不制定教學要求,各校水平因此參差不齊,沒有統一的標準。”富有階級色彩、與教會關系密切的教育體系造就了英國文化的孤傲、保守、文明、自律,而片中縮影式的教會寄宿學校則集中展現了這種文化底色偏執的一面,將在此文化氛圍下的人性養成、改造和抑制與潛藏于人性深處的本性相碰撞,從而凸顯這種循規蹈矩的封閉空間對人的異化的影響。
影片實質是封閉的單性別空間里個體成長到不同階段的群像呈現。從三位主角的個體發展狀態來看,便呈現出“費雅瑪—黛—G小姐”這樣由高到低的排序,個體的成熟度、完整度顯然與其在教會學校這一封閉空間停留的時長成反比,從未離開過學校的G小姐已然成為封閉空間孕育下的怪獸,可見長期封閉的環境對人的思想圈禁、模式灌輸。同時,這種無意識的控制又是根深蒂固的,從三位主角的結局來看,攜著新思想、閱歷豐富、心理成熟、具有獨立意識的費雅瑪必然首當其沖,成為刺破傳統的殉道者。處于青春期的黛則受此觸動主動離開桎梏眼界、扭曲思想的教會學校,而處于“嬰兒期”的G小姐也被迫離開而不得不接受繼續成長的現實。三位主角的相繼離去使得教會學校這一封閉空間出現分裂,影片借此批判了盤根錯節的教會體系和長期以來教會教育對健全人格的抑制,透射出社會性與自然性的天然矛盾。
影片通過呈現特殊環境下的群體和個體間的斗爭以及個體的最終勝利,從而完成了一次現代性寓言。并通過探索邪惡而幫助人們認識、理解其本性,由此人們才能控制和防范罪惡,最終實現自我救贖和社會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