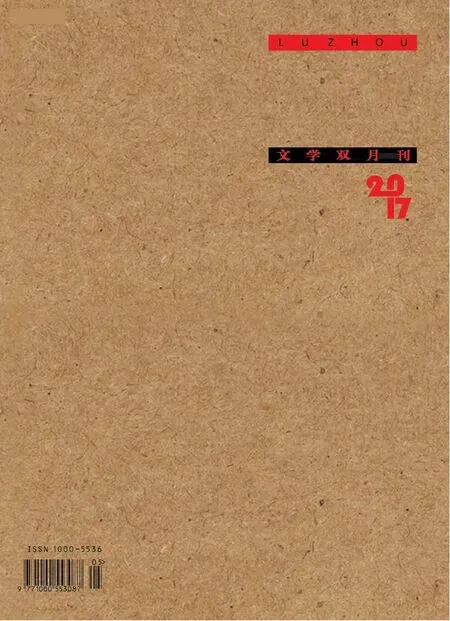原始的花朵
張靖
原始的花朵
張靖
胡楊花開
秋風吹拂處,成千上萬絨團般潔白的小花,瞬間一簇簇告別胡楊枝頭,在無邊無際的曠野上漫天飛舞。
胡楊竟然也開花?這個發現令我興奮不已。
光線透過玻璃溫暖地流淌進來,一片巨大的原始胡楊帶著勃勃的生機映入眼簾,它們有的高舉著蒼老的臂膀獨自向天;有的如同一把大傘,支撐著永恒的翠綠;有的如同情侶,在眾目睽睽下緊緊擁抱;有的如智慧的老人,在獨自思索生命的意義。不論以何種形式存在,它們都以獨立的姿態存在,在歷經了千百年歲月的滄桑后獨守著蒼涼的荒原。陽光下,它們安靜淡然,充滿了古老而又柔韌的力量。
發現,給我帶來了無限的歡愉。
一個人背負著沉重的行囊,從城市走向鄉村,從繁華走向荒原,在這個渺無人煙的地方,時間仿佛靜止。置身于一片茫茫戈壁,是無聊的懲罰也是惡意的妒忌,在原始的森林里,我體會了另一種繁華中的孤獨。煙雨間,那些辦公室里的追名逐利、爾虞我詐正一點點離我遠去,時間讓我陷入無邊無際的空寂之中。我開始安靜地思考,思考存在的意義和未來的方向,孤獨讓我第一次更加清晰地認識自己,在久久的思索中,為自己獲得一個更為遼闊的視野。
人類總是那樣的自相矛盾,很多時候,在人群中我們向往孤獨,在孤獨中我們又向往人群。然而,靈魂往往在孤獨中凈化與升華,同時帶來更多的是生命的啟迪,我相信孤獨使人智慧,此時,我的靈魂第一次真正地與自然、與神秘、與宇宙、與無限之謎相遇。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在交往中,人面對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獨處時,人面對的是整體和萬物之源……孤獨,讓我走進一方屬于自己的天空。
世界從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在這片胡楊林里,我發現了胡楊花,在無邊無際的孤寂中,它給了我另一種驚喜。
我立即打開門,興奮地朝著胡楊林奔跑過去。大片的胡楊花正在半空中隨風搖曳著,靜靜凝視,它們一個個色彩淡雅,花座呈淡黃色,一朵朵潔白的花毛茸茸的如同雪花,它們如孩童般頑皮地擠在一起,躲躲閃閃藏在葉片的后面,慌亂中卻閃爍著無法壓抑的快樂,它們低調而又美麗,在它們身體炸開的一瞬間,一朵朵潔白的花飛出身軀,向林間四處飛揚,搖曳在風中。我忍不住采下一束捧在手中。
闖進一眼望不到邊的原始胡楊林,我突然想起了輪臺那片胡楊森林。
那是金秋十月,辦公室的同事全體出動,一起跑到幾百公里以外的輪臺去看胡楊。那是一次多么難忘的旅行啊,交通不發達,于是七八個男男女女,背上各自的行囊、一路搭著汽車、毛驢車,興致勃勃地去看森林胡楊。
輪臺的胡楊,如同瀚海戈壁上一幅奇麗壯觀的油畫,一望無際,氣勢恢宏,它們棵棵莊嚴,在大漠孤煙下,如同千年的守望者。遠遠望去,胡楊千姿百態,有的舒展彎曲刺向天際,有的干枯赤裸站立,更多的如美麗的仙子翩翩起舞。深秋里,幾十公里的原始胡楊林,縱橫于一片沙漠戈壁之中,恍如一片巨大的金色海洋,在夕陽的余暉里,胡楊的葉片五彩斑斕,淺綠、米黃、桔黃、桔紅,那些瑰麗的色彩在霞光里,華美而又壯觀。
原始的胡楊公園,成了大家快樂的天堂,奔跑在胡楊林中,我們忘記了年齡,忘記了性別,男男女女相互手拉著手,盡情地追逐、嬉笑,一路上,幾個人擠在一輛維吾爾族大爺的馬車上大聲喊叫,一起唱著一首大家十分熟悉的兒歌《讓我們蕩起雙槳》。陽光下,我們的手指輕撫著頭頂上每一片從樹上落下的葉片,如同金色的小翅膀,劃過我們的肌膚在大地上飛舞。
徜徉在胡楊林里,我們相互擁抱合影,留下最美好的影像,偶爾一個人,更多時一群人。站著、坐著、半躺著,姿態不一,而每個人的笑容都同樣燦爛又明媚。陽光下,一張張鮮活的臉如同深秋的胡楊一樣璀璨奪目。
多么美好的時光啊,多么美好的胡楊,我獨自依偎在一棵樹下,不由得想起了席慕蓉的一首詩:如何讓我遇見你,在我最美的時刻……那個離去的詩人,早已在塵埃里,可她那種等愛的心卻剎那間感動了我。
時光一去不復返,曾經的歡樂隨歲月的流逝定格為永恒的記憶。長路無際,多年后,我離開了原來的同事,一個人久久地在人生的得與失中疲憊地奔跑。
再次邂逅胡楊林,讓我的心不由得一陣驚喜與感動。胡楊花開了,就在我的眼前,它們的花頭從一串串結著鵝黃的小葫蘆中抽出,悄然地分散著陽光的碎片,一瞬間,一簇簇黃色的花苞里驀然間飛出了雪白的花絮,猛然間觸動著我內心的柔軟。一陣狂風,它們翻飛舞動、左右搖擺。多么美麗的花束啊,樸素、淡雅,它們并不在意人類的關注,它們無拘無束地沿著屬于自己的枝枝蔓蔓跳著古老的舞蹈,在遠遠近近的原野上盡情綻放著。
那是一種怎樣的美,迎著晚風,成千上萬朵如雪花般隨風漫舞,它們共同沉浸在集體的歡樂里。
這是一種原始的花朵,素凈淡雅,它們由荒原的腹地孕育,接受著陽光、雨露的滋養,當秋季來臨時,它們用自己的方式打開身體,用美麗掀開了原始森林的一個夢想。與這片土地上的其他野花一樣,它們低調而不張揚,與其他植物共生共存、共同成長于這片土地上。
很多時候,它們常常用夢幻般的眼睛不解地打量人類、打量世界,它們自然而不矯揉造作,面對變幻無常的世界,它們常常隱藏在葉片后面,躲避世間的好奇與窺探。有誰比它們更愛自己的母親胡楊呢?在人類給予胡楊更多贊譽的時候,它們悄然躲在葉片后面,去仰望天空的高遠與空曠,來回避世人的目光與注視。
人類并沒有太多關注它們,提起它們,人們只會吃驚地睜大眼睛問:胡楊真的會開花嗎?是啊,胡楊真的會開花,它們盛開在初秋的光暈里。
大地是最慈愛的母親,只有它才會用心解讀它的每一個孩子,在每一個黎明與黃昏,它用愛給予萬物仁慈與溫暖。
大自然說:萬物平等、貧富不分,只要美的事物存在,心靈必將會伸向前方的坦途。
野麻花開
秋日的傍晚,白楊樹的濃蔭里藏著麻雀的蹤跡,村莊的紅辣椒掛滿了寂寥的秋光。
行走在曠野的田埂上,緲緲暮色中,我突然停住,一朵朵燈籠般的小花在風中起起伏伏,野麻花開了,我驚喜地叫道。
抬頭望去,大片大片的野麻花在戈壁灘上盛開著,在晚風的吹拂下,它們張開潔白的花瓣,在細長的葉片下翻飛舞動,如海面泛起的遼闊的浪花。在無盡的曠野中,它們如癡如醉,仿佛集體搖曳在夢里,展示的早已不僅僅只是美麗,而是一種植物群體生存的力量。
原野仿佛屬于野麻的領地,它們手拉著手,互相攙扶著生長在胡楊林、農渠溝、馬路邊,盡管個個腰肢纖細,卻有一種堅韌的力量,當微風拂動時,一種弱不禁風和惴惴不安的美,將野麻的生命推至一種溫柔、夢幻的境地。
八月的陽光依然熾熱,猶如戀人敞開的情懷。一個人行走在黃昏落日下,城市越來越遠。凝視空曠的荒原,大地已陷入沉沉的暮靄,獨自沉醉在清淺的野麻花香里,它們似乎才剛剛開放,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們便會鋪滿整個戈壁。
野麻花,學名叫羅布麻花,是新疆最普通的野生植物。幾十年前,它們曾是戈壁荒灘的主人,每到秋季,在一望無際的戈壁灘,它們常常一場接著一場上演著盛大的花會,肆意開放在原野與草地上,大地是它們的家,只要有陽光與土壤的地方,就有它們盛開的天地。它們花瓣嬌嫩、粉白相間,陽光下,它們常常仰著粉白的頭顱,一朵朵小燈籠般的花朵如同羞澀的少女,令人無限憐愛。只要有風的地方,它們會盡情地隨著纖細的枝條翩翩舞動。
與其它野花相比,野麻花過于羞澀靦腆,一片片花瓣單薄而又嬌嫩,在太陽的注視下,它們總是躲躲閃閃,如同少女般忐忑不安,面對荒原,也許它們懷揣著更多的期待與幻想,可它們始終羞澀地低垂著頭,柔軟的力量卻如同沾水的繩索,讓人類與它們緊緊纏繞。
野麻花的花語是“獻身”,盡管它本身并不十分艷麗,卻是極其珍貴的藥材,吸收了大西北的精華與靈氣,具備降壓、降血脂、抗癌抗衰老、潤腸通便等眾多藥用價值,別看它貌不出眾,卻是治療多種疾病的良藥。
當秋季剛剛來臨,野麻花便爭先恐后盛開在戈壁灘、胡楊林、沙漠中,柔弱的生命雖短暫易逝,卻醞釀著一個巨大的夢想,它們要犧牲自己去拯救人類。在人類忙著欣賞那些爭奇斗艷的名花時,很少人會記起為人類默默付出的野麻花。
我突然被感動了,還有什么比犧牲自己去拯救他人更加崇高呢?
七十年代,那個物質貧乏而又單調的年代,是一段令人難忘的歲月。在大片從未開發的荒原上,野麻花曾有過屬于自己的繁華。在連隊旁邊的戈壁灘上,生長著郁郁蔥蔥的野麻,它們不僅是這片土地生命力最旺盛的植物,也是家庭燒火做飯最好的木柴。每年秋季,父母總帶我和哥哥弟弟,一家人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舉著坎土曼、揮舞著鐮,瞬間,大片大片的野麻被砍倒。經過無數次綁扎、裝車、曬干,野麻成為家庭煮飯、取暖最好的燃料。
烈日炎炎的戈壁灘上,父母揮汗如雨,一捆捆野麻被哥哥和弟弟們捆綁得結結實實,只有我一人穿梭在花叢中快樂地奔跑著,采擷了一束又一束的野麻花,愛花、愛美的天性,那時才剛剛幾歲的我便已初露端倪。驕陽下,父母早已大汗淋漓,卻怎么也不肯休息一下,年幼的弟弟被曬得坐在地上大哭起來。整個原野上,只有我一人還在花叢中恣意穿梭,那繁星般的花朵讓我樂此不疲,清脆的笑聲回蕩在戈壁灘上……忙碌的親人們沒有一人來指責我的貪玩與任性,他們繼續一聲不響地埋著頭,用力揮動著手中的鐮。
荒原上的勞作是艱辛的,割野麻早已是連隊里家家戶戶所特有的一種原始的生活方式。烈日下的父母雖然滿身疲憊,可汗水卻隱藏不住他們內心的喜悅。那整整的一大車野麻啊,是一個冬季爐火最好的木柴,它們盡管還夾雜著綠葉的水分,卻讓家人們看到了寒冷的冬季里爐子竄動的火苗,尤其是母親,她仿佛看到了一家人正圍著火爐旁所擁有的溫暖。
夜晚,我把采擷的花束插在玻璃瓶中,那低垂的花頭令我無限癡迷,淡淡的花香讓我沉入一個個夢境,長大以后我才知道,那細小的花瓣里竟然藏著神奇的安眠功效。
十九歲那年,我在秋陽里遇見了辛,正是野麻花盛開的季節,害羞的我如花萼般死死地低垂著頭,內心也如野麻花般地充滿了掙扎、狂亂、喜悅與期待。我們常常在一家人忙忙碌碌時,手牽著手跑到沒人的地方躲起來,可沒有一個人來責備我。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他們眼里,我永遠就是那朵小麻花,稚嫩、嬌氣、羞澀,一朵由全家人精心呵護成長的小花。
時過境遷,世間的萬物始終處于不斷的變幻之中,再頑強的植物也抵不過歷史車輪的輾軋,野麻的生命力雖然頑強,可人類的強大與摧毀讓它們一點點在減少。
不論在田埂還是平地,我們幾乎找不到它們的蹤跡,人工的開墾與城市的擴建,早已讓那些曾經蓬勃旺盛的生命不知去向。
西部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土地不斷地被開發、被種植,人類不斷地進入,荒原一點點消失,原始的植被漸漸退出它們的舞臺。
未來是什么樣的,誰都無法預料,但世界永遠存在著兩股力量,一種是進攻,一種是后退。
鈴鐺刺花
每種植物都有一段屬于自己的美好的時光,譬如鈴鐺刺花。
在西北大地上,鈴鐺刺是一種再普通不過的植物,它們耐旱、耐寒、耐鹽堿,強大的生命力讓它們成為荒原上不可代替的主人,它們隨處生長著,不論沙漠、戈壁、荒灘還是排堿渠,只要有土壤,就能看到它們的身影,它們似乎不畏懼任何寒冷、干旱與鹽堿,用自己長滿利刺的身軀改良著新疆鹽堿的土地。
雖然,它們長的不是那么討人喜歡,卻有一個可愛的名字——鈴鐺刺,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它們敏感、尖銳、防范,比任何植物都懼怕侵略,它們的身軀長滿了無數只小小的利劍,注視著所有企圖想要接近它的人類與動物。它們始終是低調的,以一種從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生長在新疆的戈壁灘、荒原上、農渠邊、田間地頭上。它們一簇簇、一叢叢,蔥蔥籠籠地大片占據著荒原。
多么獨立的植物啊,永遠以一種自己的方式與世界保持著距離。鈴鐺刺,它的外表看起來像個稚氣十足的丑孩子,可它卻又是冷酷無情的,它一次次用尖銳觸角傷害著各種試圖接近它的肉體,它們仿佛用渾身的利刺向人類與動物發出警告。而它又是深情的,每到花季,它總會以驚艷的花朵呈獻給撫育它的母親——大地。
新疆的春天是風的世界,一場比一場更任性,一場比一場更狂野,鈴鐺刺卻迎著風旺盛地生長著,它們與風沙頑強地對抗著,成為荒原上一道防風固沙的綠色屏障。它們是那樣的不屈不撓,以不可阻擋的勇氣,對抗著鐵犁的進入與機器的摧毀,它們在現代機械的一次次失落里,不斷尋找到重生的機會。不管何時何地,只要有它們扎根的地方,它們便會讓風播下一顆希望的種子,在來年的春天生長出一株株新的生命。
一到五月,鈴鐺刺花便迎來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它們迎著陽光無拘無束地盛開著,它們密密麻麻地擠在一枝枝鈴鐺刺上,如同一輪明媚的太陽,撥動大地的心弦。
盛夏,是花的海洋,白色的花芯,粉色的花頭,那一串串綻放的花瓣滌蕩著世人的眼睛,它們有的像展翅欲飛的仙鶴,有的則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立在枝頭,花朵輕巧垂立,個個色澤艷麗,它們一個挨著一個整齊地排列在粗糙的鈴鐺刺上,一串串如蝴蝶飛上枝頭千姿百態、惹人憐愛。無數的蜜蜂小心地在它們的枝頭上飛來飛去。
當夕陽將連綿的群丘暈染時,像所有愛美的植物一樣,鈴鐺刺花迎著霞光,嬌羞地打開身體的寶藏,它竟是如此風情,依偎在粗陋的母體上燦爛地盛開出一朵朵嬌美的花朵,像自然界所有的愛一樣,它們悄悄與枝葉之間傳遞愛的密語,花與葉親吻,刺與花相擁,微風中,它們挺立在那里,始終手拉著手、心貼著心,不棄不離。
居住在大漠深處,沒有人能抵擋鈴鐺刺花驚艷的美。它們雖然身長只有兩厘米左右,但個個卻有著驚人的美貌,一個個整齊地垂立于一根根鈴鐺刺上,氣質如同一輪明亮的太陽。它們如此的美麗,或藏于水渠下、或躲在荒涼生僻的土地上靜靜綻放,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襲人的花香里隱隱散發出一種超凡脫俗的嬌貴氣質,那粉嫩嫩的花堆底下,一根根硬刺卻暗藏著無數殺機,隨時抵御外來的侵犯,仿佛用全身鋒利的尖刺警示所有妄想靠近它們的牛、羊等吃貨。
多么可愛的鈴鐺花啊,每當花期來臨時,它們集體上演著一個美麗的童話,它們打開身體隨風搖動著美麗的花枝,如同一只只燃燒的小火苗。像所有愛花的少女一樣,我曾經那么地著迷一種野花的美麗,我無法抗拒這種原始花朵所帶來的驚艷及誘惑。
在我還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時,我便愛極了這種花,那些看似粉嫩的花頭低垂著,多像嬌羞的少女,一個個親密無間地緊挨著,讓我想起了幾個從小一起長大天真爛漫的少女。紅、玲、雯、雪、平,五個再普通不過的名字,我們緊挨著,一起在荒原上度過了最美好的孩童時光。
七十年代,每當鈴鐺刺花盛開的季節,正是我們幾個女孩最快樂的日子。在盛夏的午后,趁著大人午睡,我們一個個偷偷從房間里溜出來,一起興奮地奔向連隊東面的戈壁灘上。那是五張生動而又陽光的臉,稚嫩的臉上滿滿的孩子氣,盡管驕陽如火,我們卻如同鈴鐺花似的拉著手,站成一排,在原野里拼命地奔跑著。
一束明媚的光線射在臉上,五張嬉笑的臉上如同含苞欲放的鈴鐺刺花,精巧而明麗,怯怯的笑里卻透著掩飾不住的喜悅。站在鈴鐺刺花面前,我們是那樣的迫不及待,一個個伸出細嫩的手指,企圖將一只只粉嫩的花朵占為己有。冷漠的鈴鐺刺早已看穿了我們的意圖,當我們正在樂此不疲地采花時,它便毫不猶豫地將刺扎進我們的手指,盡管如此,卻沒有人妥協,我們一次次將花朵采摘,甚至最后,不得不將它連枝折斷。
插野花,是那個時代女孩的一種別樣的愛好,杏花、沙棗花,大自然會在不同的季節給予我們各種驚喜,我們沉迷于花香中,盛開的花朵芬芳了整個小屋。
植物一定也有愛情,不然鈴鐺刺不會如此奮不顧身。
火熱的驕陽下,鈴鐺刺花攀援在刺刺椏椏的枝條上,如同一個個絕世美貌的少女,而鈴鐺刺在她嬌艷的面容襯托下,則顯得更加的粗暴與丑陋,我無法理解這種對比如此強烈的愛情。正當我用心想要將花朵摘下時,我的手指被狠狠地扎了一下。那一刻,鉆心的痛讓我突然明白了,原來最好的愛情是犧牲自己去精心呵護愛人,也許是花太美了,鈴鐺刺情愿化成一堆丑陋的利刺,去對付世間所有的圖謀不軌。
即便放棄容貌、放棄生命也要保護愛人,這是一種多么無私的愛啊,這種愛與被愛的植物讓我頓時心生羨慕,問世間,哪一個女子不渴望被情人用真心去愛,用生命去保護呢?
時光荏苒,到了九十年代,紅、玲、雯、雪、平五個女孩,她們在戈壁中也尋找到了屬于她們的美好時光。當年采花的女孩也如鈴鐺刺花般嬌艷地怒放著,她們有的找到了如同鈴鐺刺花般最好的愛情,得到了如鈴鐺刺般一生的呵護;也有的找到了愛情又失去,又重新尋找;還有的一個人孤獨一生。
曾經纖纖動人的華韻,早已消失在歲月的煙塵里,那些如花的容顏,終究敵不過似水的流年。一切美好,早已悄然褪色,暗自凋零,最后落入塵埃。
黃昏時分,大自然以它的方式安然注視著萬物。鈴鐺刺花的開放,點亮了寥落的原野,它們披著霞光自由自在地搖曳著,隨著微風衣袂飄飄,如同一群動人的仙子,向大地訴說著愛的密語。
它們一半向著天空,一半向著大地,愛與生命,植物與荒原,在時間無涯的荒野里中彼此消長。
責任編輯 翡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