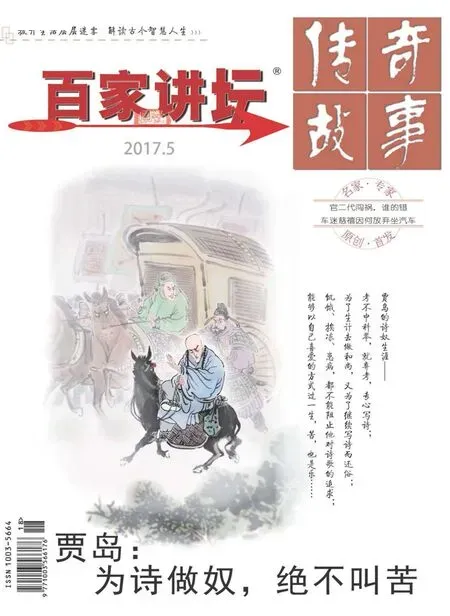潘玉良:長得不美,就努力活得豐盛
◎慕容素衣
潘玉良:長得不美,就努力活得豐盛
◎慕容素衣

鞏俐和李嘉欣都曾飾演過民國女畫家潘玉良,這形成了很多人對潘玉良的初步印象:一個長得很美卻命運多舛的女畫家。但從潘玉良的自畫像中可以看出,她身材壯碩、五官粗放,不僅不美,還有點兒丑。據當年熟識她的人說,潘玉良確實是個又矮又胖、長著獅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丑女人。
外貌是女人天生的通行證,長得不好看的人,人生相對來說要艱難一點兒。完全不漂亮的潘玉良卻憑著努力完成了從雛妓到侍妾、再到畫家的三級跳。
潘玉良本來姓陳,她自幼父母雙亡,只好跟著舅舅生活。舅舅有次賭輸了,于是把年僅14歲的她賣到了安徽蕪湖的一家妓院。由于長得不出挑,她一開始在妓院做燒火丫頭,干的是又臟又累的活。后來利欲熏心的鴇母逼她接客,她誓死不從,一次次逃跑出來,又一次次被捉回去毒打。她還試圖跳水、上吊來抵抗,均因看管過嚴而未遂。
17歲時,走投無路的她不得不在妓院里唱歌,歌聲如泣如訴,引起了蕪湖鹽督潘贊化的注意。潘贊化在日本名校留過洋,是個新派人物,他被眼前這個可憐而又剛烈的女子打動,決定為她贖身。
潘贊化本想將她送回親戚家,但她想留在他身旁,哪怕做一個小丫頭。善良的他自然不會讓她做個小丫頭,于是收了她做妾室。他待她是很珍重的,雖然是納妾,也辦了正式的結婚儀式,證婚人還是他的莫逆之交陳獨秀。
婚后,他竭盡全力地呵護她,不僅親自教她識字,還請老師教她畫畫。這份恩義與憐惜讓潘玉良始終感念不已,她毅然將自己的姓改成了“潘”——因為他給了她重生的機會。
如果按照舊式小說的發展,嫁給潘贊化的潘玉良應該溫良恭謹,夫唱婦隨。可是她偏偏不愿意只做個溫順的小妾,她要畫畫。她沒念過什么書,剛剛開始學畫畫,居然在老師的調教下展現出了驚人的繪畫天賦。于是她不滿足于在家里畫幾筆自娛,而是要跑出去到處求學,先是考上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后來索性跑到了巴黎。
畫畫也就罷了,潘玉良卻畫起了人體,還是裸體女子,這在當時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那年月,當局不允許人們畫裸體,她就趁去浴室洗澡時偷偷地畫,有次差點兒被一個胖女人打出來。回到家里,她對著鏡子忽然想到:“我自己不就是很好的模特嗎?”想到這里,她就脫掉衣服,對著鏡子開始畫自己。
除了畫人體,她在言行中也不拘小節。一次,大家討論起一個女詩人以狗為伴的八卦,潘玉良無所顧忌地發言:“狗比人好,至少狗不會泄露人的隱私。”
人一旦特立獨行,就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有人挖出潘玉良曾為雛妓的“艷史”,一名女同學甚至要求退學,理由是“誓不與妓女同校”。只有潘贊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包容她,在獲悉她的困境后資助她去法國留學。
潘玉良在法國考上了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與徐悲鴻同班,專攻油畫。留學近九年后,她回了國,在老師劉海粟及同學徐悲鴻辦的美院當過教授,并且出版畫冊,舉辦展覽。即便她已成名,人們并沒有停止對她的攻擊和詆毀。在她舉辦的一次畫展上,有一幅優秀的人體習作《人力壯士》。可某一天,畫上被人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妓女對嫖客的頌歌。”
對于曾經有過“污點”的人,人們表面上再尊敬,骨子里仍然是看不起的。可是潘玉良好像完全不把自己在妓院待過這件事當成“污點”,她理直氣壯地畫人體,理直氣壯地當教授,理直氣壯地辦畫展……一點兒也不畏縮,這就惹怒了當時的社會主流。
連潘贊化的正妻也看不過眼,跑到上海將她叫回家,無比威嚴地宣布:“不要以為你在外面當了教授,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在這個家里,我永遠是大的,你永遠是小的!”
潘玉良也是有脾氣的,既然險惡逼仄的環境容不下她,那她就走,去一個更遠、更大、沒有流言的地方。1937年,42歲的潘玉良再次去國離鄉。潘贊化依舊送她到黃浦江碼頭,并將蔡鍔送給自己的懷表送給她作為臨別紀念。
她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都沒有回過中國。
“遐路思難行,異域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這是多年后,潘玉良給潘贊化寫下的一首相思之詩。當時中法尚未建交,潘贊化過世兩年后,潘玉良才從大使館的人口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絕。
既然如此,她為何不回國呢?不是她不愛潘贊化—她終身都以潘贊化的妾室自居,而是她更愛繪畫。她是那種可以用生命去畫畫的女人。她堅持留在巴黎,是因為這里開放包容的環境更適合她創作。她情愿為此割舍自己的愛人。
在巴黎時,潘玉良不談戀愛,不加入外國國籍,不依附畫廊拍賣作品,終日待在一個窄小的閣樓里,全身心投入畫畫。由于不善經營,她日子過得很苦,身體又不好,以至于老年時靠著一點兒救濟金過日子。
在異鄉漂泊了40年后,潘玉良在貧病交加中死去,臨終前交代了三個遺言:第一,死后為她換上一套旗袍,因為她是中國人;第二,將她一直帶在身邊的、鑲有她跟潘贊化結婚照的項鏈和潘贊化送給她的那個懷表交給潘家后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帶回祖國。
以世俗的觀念來看,這位民國最知名的女畫家是個典型的失敗者,人生中透著凄涼和苦澀:沒有美貌,沒什么朋友,沒有錢,最后連健康都失去了,她的后半生大多是和貧病糾纏在一起的。而這一切只不過緣于她熱愛畫畫。如果可以重來,她還會這么選擇嗎?
會的。她會像英國小說家筆下的人物那樣,對“為何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得這樣折騰”的問題這樣回答:“我必須畫畫,就像溺水的人必須掙扎。”
被夢想擊中的人是沒有其他選擇的,她唯有迎著夢想一步步走上去,哪怕厄運與之相隨,哪怕通往的只是虛無。作為一個女人,潘玉良經歷了太多的不幸;作為一個藝術家,她卻是幸運的—她發掘了自己的天賦,并把這天賦發揮到了極致。任命運如何顛沛流離,貧病交加,那都是她甘愿承受的一部分,在一生追求的事業上,她始終走在一條向上的路上。
她身后留下了四千多張畫作,畫得最多的還是各種各樣的女性人體。這些人體豐碩、飽滿到了極致,宛如神話中的大地之母一樣健壯,和她本人一樣,談不上美,可滿身充沛的生命力仿佛要破紙而出。超越了風雨飄搖的俗世生活,她以這種姿態活出了雖然寂寞清冷卻又高蹈出塵的人生。
編輯/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