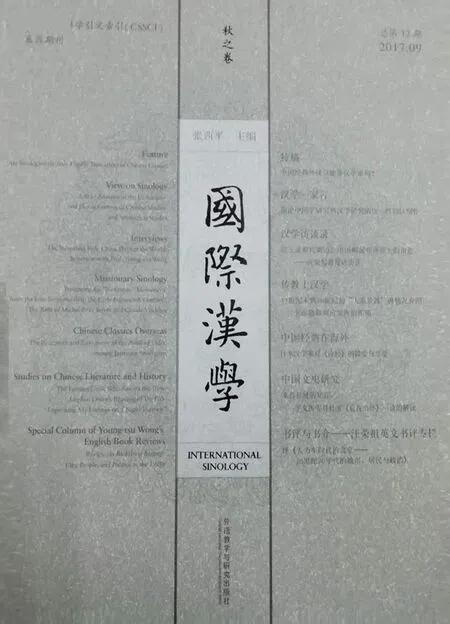霍克思《紅樓夢》英譯底本析論*
□
《紅樓夢》是部未完稿,迄今為止發現的早期抄本就有13種,而刻本系統也不少,現存僅程甲本就有10余種、程乙本30余種。①參看胡文彬:《歷史的光影》,香港:時代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20、21頁。展開《紅樓夢》英譯討論,譯者所用翻譯底本不容忽視,這一點已日益成為研究者的共識。
自早期林以亮的程高本、俞校本整合說②參看林以亮1973年6月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的《喜見紅樓夢新英譯》、1975年6—12月在臺灣《書評書目月刊》發表的霍譯評議系列論文《試評紅樓夢新英譯》及1976年結集出版的論著《紅樓夢西游記》。始,研究者發現了越來越多豐富的譯例共同佐證霍克思(David Hawks, 1923—2009)翻譯底本不拘一處的結論,有趣的是霍譯究竟參校了哪些本子,研究者卻從未達成一致之見。本文擬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引入霍克思藏書(即存于威爾士國家圖書館的《霍克思文庫》),比照霍克思《〈紅樓夢〉英譯筆記》、霍克思關于英譯底本的說明文字(譯本序、期刊論文、信函、訪談錄),厘清《紅樓夢》前八十回霍譯底本的具體版本信息,進而對霍譯底本這一基礎問題做出較為明確的回答。
一、尚無定論的霍譯底本
林以亮最早就《紅樓夢》霍譯卷一進行評論:“原文大體上根據程乙本”,③林以亮:《喜見紅樓夢新英譯》,《紅樓夢西游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臺北:聯經出版,1976年,第2頁。兩年后,他根據霍譯本卷一序言修正為“他根據的不僅是一種版本。除了第一回采取了程高本之外,他有時也采用鈔本(雖然并沒有指明哪一種鈔本),偶然則根據個人的臆斷而加以校訂”。④林以亮:《版本·雙關語·猴》,《紅樓夢西游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第21—22頁。此處,鈔本何指?林氏行文所舉各例均以俞校本為對照,并有“霍克思的譯文大體上根據俞校本”⑤同上,第22頁。一說。綜之,林以亮于20世紀70年代已指出霍克思英譯時參校的兩個本子即程乙本(程高本)和俞校本。
約三十年后,范圣宇發現了更多的本子,“他在翻譯過程中使用過的底本主要有《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俞平伯,1958年)、《王希廉評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北京:文學古籍出版社,1955年影印庚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己卯本)、《百廿回紅樓夢》(臺北:青石山莊出版社,1962年影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本)、《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影印有正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這幾種”。①范圣宇:《〈紅樓夢〉管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6頁。這里人民文學版《紅樓夢》即林以亮口中的程乙本(程高本),故除去林氏已然提到的兩本,范氏增加了王希廉評本、庚辰本、己卯本、青石山莊《百廿回紅樓夢》《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和《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等六個本子,并附上具體版本信息,從而明確界定了具體底本。在霍譯底本討論上此為不小的進步,但問題在于有些版本并非霍克思英譯中所使用的本子,上述部分結論仍有商榷余地。
近年,鮑德旺、劉洵從霍克思英譯筆記入手,指出“根據《筆記》,霍克思在翻譯過程主要參考了人民、俞本、王本、庚辰、甲戌、高抄、乾抄、刻本、程甲本等版本,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紅樓夢》則是其翻譯的主要參考底本”②鮑德旺、劉洵:《霍克思〈紅樓夢〉英譯底本分析》,《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第236頁。。鮑氏、劉氏此處列出的是英譯筆記中霍克思提到的版本,問題是這些簡稱有些是同指,如“高抄”與“乾抄”;另外“刻本”是泛稱,與《筆記》中同樣表示泛稱的脂評本或抄本系統相對,本不應計入。除去如上錯訛,將之與范圣宇所列諸本清單對照,可發現兩份清單仍出入頗多。即使《筆記》中的“王本”一稱即范氏清單中的“王希廉評本”,兩份參考版本明細除了最初三項相同外,其余皆難一一對應:筆記中的“甲戌”“刻本”“程甲本”在范氏清單中無對應項,而范氏口中的“己卯本”在鮑、劉清單中也付闕如;鮑氏清單最后剩下的“高抄”“乾抄”如與范氏清單中另四種版本之一對應,那剩下的三種版本如何認定?兩份清單孰是孰非?
次年,劉迎姣③按:劉文《〈紅樓夢〉霍譯本第一卷底本析疑》是目前在霍譯底本問題討論上最有價值的一篇,研究方法創新,全文立足文獻,以數據說話,頗受啟發,特此感謝。遺憾的是劉文只限霍譯本卷一底本,且列出的九種參考版本仍存在諸多問題,故有再討論的余地。也就此問題提供了一份清單。她首次將霍克思“人民文學本”清晰界定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第三版簡體直排本”,且以“全稱+簡稱”的方式列出了霍譯《紅樓夢》卷一參校的九大底本:
在《筆記》中,霍克思提及的版本除了主要底本‘人民本1964版’外,還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或脂京本)、《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高鈔本或戚序本)、《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俞校本)、《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甲戌本或脂殘本)、《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王本或王府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抄本或全抄本)、《紅樓夢》(作家本)、《紅樓夢索隱》(中華索隱本)、《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刻本)等9個本子。④劉迎姣:《〈紅樓夢〉霍譯本第一卷底本析疑》,《外語教學與研究》2013年第5期,第770頁。
仔細比校,這份清單與上述兩份清單亦非一致,其中《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是否為“高鈔本”?《蒙古王府本石頭記》是否為“王本”?前兩份清單中未出現的《紅樓夢索隱》是否是一參校本?“刻本”是否能納入統計?這些問題都亟待回答。
二、不應計入參校底本的版本泛稱
霍克思四百多頁的《〈紅樓夢〉英譯筆記》,提到版本不下三百次,是目前研究者探討霍譯參校底本最重要的依據。但筆記中使用的均是版本簡稱,其中有很多屬于寬泛指代,不能指向明確版本,如果研究者統計霍譯參校底本時簡單依筆記順序排列版本,不加剔除,則不可避免重復計入。
具體而言,筆記中霍克思使用了“抄本version”“MSS”“MS text”“MS version”來指代《紅樓夢》抄本系統。從1971年6月20日筆記可知,霍克思眼中的抄本系統大致包括高鶚手定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和脂評本;⑤霍克思:《〈紅樓夢〉英譯筆記》,香港: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2000年,第17頁。另霍克思以“脂本”“脂texts”“脂硯MSS”“舊鈔本”及“抄本”①按:在霍克思英譯筆記中,“抄本”多指《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指代“脂評本”的只有兩回,分別是筆記第177頁1975年8月13日條目和筆記第239頁1978年11月25日條目。言說脂評本;而筆記中的“刻本”“printed eds”“印本”和“印刻本”等則指代的是與抄本系統相對的刻本系統,包括程甲本、程乙本和后世據之翻刻、排印本。上述三類提法均為泛指,明確的信息只是霍克思在翻譯過程中參校了抄本系統與刻本系統,至于具體參考何版本則無從回答,故此類寬泛簡稱在底本討論中實不應計入。
三、霍克思所指“程本”即“人民本”
排除了上述寬泛指稱后,討論霍譯底本時,另尚有一常用簡稱即“程本”需要我們仔細辨析。筆者發現,在霍克思英譯筆記中,“程本”多為具體指代,作為寬泛指稱出現次數頗少,目前能確定的有筆記中第75頁“1972年12月4日”和第201頁“1976年8月5日”兩條目,其余大多數的“程本”何所指則是另一個需要厘清的問題。
1979年7月,霍克思受邀為中國《紅樓夢學刊》創刊號撰寫過一篇中文學術論文,題為《西人管窺〈紅樓夢〉》,文中集中討論翻譯中遇到的丫環紫綃、檀云、彩云、彩霞等名字的處理問題。由于各版《紅樓夢》原文存在異文,霍克思遂不厭其煩地列出了援引版本信息,居首的是程本。巧的是有關丫環“紫綃”應為“秋紋”一節內容,霍克思1975年撰寫霍譯《紅樓夢》卷二序言時曾予以陳述。討論內容相同,所用語言一中一英,正可比照,霍克思口中的“程本”面貌亦清晰了起來。相同段落對應“程本”,英文為Gao E’s printed edition、the printed text of Gao E’s edition或Gao E’s printed text。②David Hawkes, “Introductio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2.Tr.David Hawkes.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7, pp.18—19.而進一步查看其撰寫的譯本卷一和卷三序言,可以發現Gao E’s version③Hawkes, op.cit., Vol.I, p.45.、the Gao E-Cheng Weiyuan edition、the Cheng-Gao edition④Hawkes, op.cit., Vol.3, p.16.等指稱。可見,霍克思口中的“程本”即高鶚本、程高本。
再對照霍譯《紅樓夢》卷一長序與1980年(霍譯《紅樓夢》三卷本完成之際)發表的學術論文,該問題的探究能更進一層。霍譯《紅樓夢》卷一長序談及底本,常被征引:
在翻譯這部小說時,我發覺無法忠實遵照任何一個文本。翻譯第一章時,我主要依從的是高鶚本(Gao E’s version),因為它雖然沒有其他本子有趣味,但卻更為前后一致。在接下來的章回翻譯中,我經常遵從一個抄本,并且偶爾也會做點自己的修訂。⑤Hawkes, op.cit., Vol.1, pp.45—46.
1980年春,他在學術論文《譯者、寶鑒與夢—談對某一新理論的看法》(“The Translator,the Mirror and the Dream—Some Observations on a New Theory”)中,又一次談到翻譯底本,文字如下:“最初以一通行的現代版120回本(a convenient modern edition of the 120-chapter version)為底本,但當某脂本提供了更好的文字時就會不時偏離此120回本。”⑥David Hawkes, “The Translator, the Mirror and the Dream—Some Observations on a New Theory,”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Ed.John Minford and Siu-kit Wong.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59.相似的事實陳述,表明霍克思口中的“高鶚本”即“通行的現代版120回本”。至于通行的現代版120回本真面目,我們可在1998年霍克思75歲高齡接受的訪談中找到答案,那是他第三次提到《紅樓夢》翻譯底本,也是他談得最清楚的一次。他說:“我開始時沒有太考慮版本問題(editions),我想我是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四卷本《紅樓夢》(theRenmin wenxue人民文學 4-volume edition)著手翻譯的,但那時手中也有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⑦Connie Chan, “Appendix: Interview with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s Journey to the West: A Study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Conducted at 6 Addison Crescent, Oxford, Date: 7th December, 1998, p.327.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新中國成立伊始組建的國家級專業文學出版機構,符合“modern”的標準,其出版物具有權威性與通行性,符合“convenient”的標準。要之,上述三段霍克思在不同時期就同一話題所做的說明,讓研究者清晰認識到,霍克思翻譯中依從最多的底本人民文學四卷本(通行現代版120回本)即其所言的“高鶚本”“程高本”“程本”。
人民本與程本關系,人民文學四卷本《紅樓夢》“關于本書的整理情況”①按:人民文學版《紅樓夢》共有三版,1957年10月第一版,簡體橫排,120回,三冊,精裝、平裝兩種;1959年11月第二版,簡體直排,平裝四冊、精裝兩冊;1964年2月第三版,簡體直排,平裝四冊、精裝兩冊,1972年4月第9次印刷,1973年8月第10次印刷,均為簡體直排,1974年10月再印,改簡體橫排。各版“關于本書的整理情況”一節相同。參看胡文彬編著:《紅樓夢敘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7—48頁。一節實有明確說法,“本書整理,系以程偉元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活字本作底本(校記中簡稱‘乙本’)”;并在解釋選擇取舍原則時說:“附帶說明一句,所謂選擇取舍,有一個大致的原則,就是這個普及本既然屬于百二十回本系統,校改時自以百二十回本的異文為盡先選取的對象。至于八十回本的文字,差別較大,除非個別實有必要時,是不加采取的。”②曹雪芹、高鶚著,啟功注釋:《紅樓夢》(共四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第1—2頁。人民本為霍克思依據最多的底本,上引文字自稱“普及本”,這應該也是霍克思論述中會用“a convenient modern edition of the 120-chapter version”來指代的原因,而“人民本”大致即“程乙本”,霍克思亦默認,只不過他不用“程乙本”稱謂,而是用“the Gao E-Cheng Weiyuan edition”,或簡稱為“Cheng-Gao edition”“Gao E’s version”。英譯筆記中前半部分霍克思用“人民本”一說,后半部分則變換稱呼,用“程本version”“程本”“程”或“程高version”“程高本”“程高”“高本”等簡稱代指此“人民本”。試看以下幾例。
1979年1月18日筆記,首段文字如下:“程15/166/14‘原來這鏝頭庵和水月寺一勢,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諢號;離鐵檻寺不遠’。”③《〈紅樓夢〉英譯筆記》,第244頁。這段文字非常寶貴地記錄了其選用文字來自“程本”第15回第166頁第14行,從回數、頁碼和行數的排列格式來看,這是筆記中“人民本”摘引文字一貫的記錄方式,④按:筆記中參校俞校本時也有列出回數、頁碼、行數的時候,如此則筆記(第244頁)程引文字下即是,但俞本文字引用前都有“俞”的簡稱,不會與人民本摘引相混淆。其他版本的討論只在版本簡稱后列出摘引文字;另,仔細核對回數、頁碼、行數及文字,此處的“程”也無疑是“人民本”。再則,該筆記條目第二段列出的對比版本是“俞”,第一段的“程”為“人民本”亦符合霍克思筆記中一貫的“人民本”“俞本”對校習慣(具體參看圖1、圖2)。

圖1 霍克思1979年1月18日英譯筆記內容

圖2 人民本《紅樓夢》第15回相關文字
1973年5月17日筆記,霍克思寫到“第387頁‘襲人聽了……’……程本version‘又是……又是……’這一結構是對第385頁‘黛玉聽了又……又……又’的蹩腳模仿”。①《〈紅樓夢〉英譯筆記》,第109頁。基于上述討論,根據頁碼與摘引文字,可知霍克思心中“程本version”不是泛稱,而是專指“人民本”。
再看1978年7月15日筆記:
第70回第907頁,到底有多少丫環,拿出了多少風箏?等。程本這部分一團糟,而俞校本關于黛玉起初為什么去取美人風箏則交代得很清楚。也許第907頁第5行被誤讀了:寶琴的話實際是對黛玉說的,而寶釵錯回了。這樣可能引起了困惑。……第70回第908頁風箏段落也完全被程高本弄得一團糟。②同上,第232頁。
這則筆記中與“俞校本”相對的“程本”,根據回數、頁碼、行數與討論的文字也可以明確即“人民本”。筆記末句提到的“程高本”,從頁碼連續性推斷,與此段文字第二句提到的“程本”應該同指,即“程高本”就是“程本”,也就是“人民本”。
當然,從簡稱本身來看,“程”指“程偉元”,“高”指“高鶚”,“程高”并不僅指代程偉元、高鶚合作刊刻的“程本”一種可能,也可能指代最早出于程偉元之手后由高鶚手定的“夢稿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霍克思筆記中簡稱“乾抄本”)。霍克思1976年7月8日筆記③《〈紅樓夢〉英譯筆記》,第198頁。很好地排除了上述疑惑,該則筆記以表格形式明確了“程高”非“乾抄”,如圖3,首先,筆記中“程高”“乾抄”二者并列出現,不可能同指;其次,從排列來看,“程高”排在第一欄,下有符合“人民本”的回數與頁碼,后分別與“俞”“庚”“乾抄”“戚本”對比,顯然此“程高”即筆記前半部分霍克思參考最多、討論版本文字差異時排在首位的“人民本”。實際上,當年《紅樓夢》卷一譯稿問世,紅學專家林以亮判定霍譯底本時,“程乙本”與“程高本”也是同指:他在《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中說“原文大體上根據程乙本”,④林以亮:《喜見紅樓夢新英譯》,第2頁。后在《版本·雙關語·猴》中如此重述“我在《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中曾指出霍克思的譯文大體上根據程高本”。⑤同上,第21頁。

圖3 霍克思1976年7月8日英譯筆記內容
此外,霍克思筆記中還使用到“高本”(“高version”“高”)這一簡稱,應是承“高鶚本”一稱而省,亦應同指“程本”或者說“人民本”。如霍克思1977年1月19日筆記,該則筆記涉及《紅樓夢》第59回回首與回末文字討論,列的是“高本”與“俞校本”異文。按霍克思筆記中習慣,與“俞本”對校的應是“人民本”,查“人民本”文字,正與所引“高本”文字相同。在“高鶚本”即“人民本”的前提下,根據此例是不難推出“高本”亦即“人民本”的結論的。
綜上,作為翻譯的主要底本,“人民本”亦常被霍克思稱作“程本”,包括“程本version”“ 程 本 ”“ 程 ”“ 程 高 version”“ 程 高本”“程高”及“高(鶚)本”等復稱,在梳理霍克思《紅樓夢》英譯參考底本時應注意不可重復計入。
四、霍克思參考底本呈列
(一)《〈紅樓夢〉英譯筆記》中版本簡稱
剔除寬泛指稱,并列所有復稱,整本筆記有效的版本簡稱依其出現先后為序排列,共有以下13種:
1.人民本(程本、程本version、程、程高version、程高本、程高、高鶚本、高本、高、‘高’version);
2.庚辰(脂硯庚辰本、脂庚辰本、脂庚辰、庚辰本、庚、脂京本 );
3.乾抄(乾隆抄本、乾隆抄稿、乾鈔、乾原、乾改、乾、乾隆高鈔本、高鈔本、高抄本、高抄、全抄本、抄本、抄稿);
4.俞本(俞校本、俞、俞校、俞’s 八十回校本、Y);
5.王本;
6.甲戌(甲戌本、脂殘本、脂殘);
7.作家;
8.索引;
9.國初本(國初戚序本、戚序本、戚本、戚序、有正大字本、有正);
10.胡藏程乙本(胡程乙、胡程、胡、胡本);
11.藤本;
12.己卯(己);
13.程甲(甲本);
(二)《霍克思文庫》提供的詳細版本
霍克思自1983年退休始,用兩年時間陸續將自己珍藏多年的東方語文藏書(約4 400冊)悉數捐贈給位于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的威爾士國家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含《紅樓夢》文獻近百部。其中,我們發現霍克思購買、收藏的《紅樓夢》版本達14種,①參看威爾士國立圖書館收藏庫The David Hawkes Collection card catalogue (pdf)。https://www.llgc.org.uk/fileadmin/fileadmin/docs_gwefan/casgliadau/casgliadau_ethnig/can_david_hawkes_hung_lou_meng.pdf.最后訪問日期:2016年9月2日。文庫均有詳細版本信息記載,為我們進一步明確霍克思《紅樓夢》翻譯底本提供了可能。但問題在于,筆記中出現的13種版本并不能全部在文庫中一一落實版本信息,有些仍需甄別。現將文庫所提供的詳細版本信息(保留原格式)對應上述《〈紅樓夢〉英譯筆記》所列版本順序進行呈列,并附簡析:
1.人民本
紅樓夢 / 曹雪芹、高鶚著;啟功注釋
北京:人民文學,1964
4v.: ill (ed.); 21 cm.—(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
此為霍克思口中“人民本”的具體版本信息,末尾“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字樣亦符合霍克思“convenient”的描述。
2.庚辰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曹雪芹撰
北京:文學古籍,1955
2v.;21cm.
本書據庚辰本用朱墨兩色影印,原書缺第64、67兩回,本書用己卯本補充
此為霍克思反復參看的“庚辰本”之詳細版本信息。
3.乾抄本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高鶚手定);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北京:中華書局,1963
12 v.;32cm.
此版本亦即霍克思筆記中反復提到的“乾隆抄本”,在霍克思英譯《紅樓夢》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自翻譯初始即看重高鶚手定本,只不過早期是借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藏書,后在友人、漢學家杜德橋(Dr.Glen Dudbrige)的成全下幸獲此本。
4.俞本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 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
北京:人民文學,1958
4v.;21cm.
此本即霍克思英譯時另一重要參考底本“俞校本”。
5.王本
王希廉評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王希廉評
臺北:廣文書局,1977
8v.: ill.; 22 cm.—(紅樓夢叢書)據道光壬辰(1832)雙清仙館刊本百廿回影印
⑴ 王本,究竟是蒙古王府本?還是王希廉評本?范圣宇認為霍克思英譯筆記中的“王本”指代的是《王希廉評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臺北:廣文書局 1977年),②《〈紅樓夢〉管窺》,第26頁。而劉迎姣列出的參考底本中認為《蒙古王府本石頭記》才是“王本”,亦稱“王府本”。①《〈紅樓夢〉霍譯本第一卷底本析疑》,第770頁。究竟何本為準?霍克思《〈紅樓夢〉英譯筆記》為研究者留下了寶貴的線索,筆記第11頁鳳姐協理寧國府,給眾人立下規矩,其中人民本“……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諸本異文。霍克思參校了“俞本”“王本”“庚辰”“甲戌”“高抄”等另五個版本,關于“王本”,其筆記為“王本same as 人民”。②《〈紅樓夢〉英譯筆記》,第11頁。查“蒙古王府本”相關文字為“……只在午初刻戌初燒……”,③(清)曹雪芹撰,俞平伯題簽,周汝昌作序:《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凡六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影印原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485—486頁。與“人民本”文字有差異,而王希廉評本《繡像紅樓夢》“……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④(清)曹雪芹撰,王希廉評,《繡像紅樓夢》,京都隆福寺路南聚珍堂書坊發兌,光緒丙子年校印,四函24冊,第5冊,第14回,第3頁。,除無句讀外,文字正與“人民本”同。
霍克思筆記中另有一處提及“王本”,亦有文字引用,是又一份寶貴文獻:“Chap.18 p.202作家&人民both have香巾—so have索引,王本,else俞,高抄本,脂硯all have香珠。”⑤《〈紅樓夢〉英譯筆記》,第16頁。查“人民本”第202頁,原文為“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對照“蒙古王府本”,此處文字為“又有值事太監捧著香珠繡帕漱盂掃塵等類”,⑥《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第646—647頁。“香珠”與人民本“香巾”不同,再比照“王希廉評本”相關文字為“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⑦《繡像紅樓夢》第5冊,第18回,第3頁。,與“人民本”完全相同,再次說明霍克思口中的“王本”為“王希廉評本”,而不可能是“蒙古王府本”。實際上,霍克思英譯筆記中只有“王本”一稱,并沒有“王府本”一說。
⑵ 霍克思“王本”所指并非1977年本。范氏認為文庫中所收藏的1977年本就是霍克思當年所參考之本,實可商榷。因為,霍克思筆記中只有兩次提及參看“王本”,時間分別為1971年2月17日和1971年5月30日,顯然早于1977年。換句話說,1977年王希廉評本絕對不可能是霍克思英譯《紅樓夢》時參看的底本。王希廉評本共有1832年雙清仙館刊本《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1876年聚珍堂刊本《繡像紅樓夢》和1877年翰苑樓刊本、蕓居樓刊本《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四種,除正文前排印內容有些許差異外,四本正文內容相同,排版亦同,均為每面10行,行22字,回首題洞庭王希廉雪香評,回末有評。上述版本均有可能是霍克思參看的本子。另1930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王云五主編的《增評補圖石頭記》(萬有文庫本,繁體豎排,王希廉評批,總16冊),亦有可能。故“王本”是王希廉評本,但具體版本信息暫作闕疑。
另,劉迎姣文中將王希廉評《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歸為霍克思底本話語中的“刻本” 也不妥。以作為主要依據的英譯筆記為例,通覽全書,“刻本”一稱均為泛指,將其限定在王希廉評本,自然不當。
6.甲戌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脂銓本,共16回,即1—8回、13—16回、25—28回。霍克思自第14回首次參校,隨后15、16、18、27、28⑧按:甲戌本討論分別出現在《〈紅樓夢〉英譯筆記》第11、13、15、79、82、81頁。回均有涉及,時間跨度從1971年2月17日至1972年12月22日止。據查,此本原由胡適1927年收藏,胡適逝世后寄藏于美國康奈爾大學,1961年(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題《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962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影印,同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此翻印,1973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再次印刷,1975年出平裝本。⑨參看胡文彬編:《紅樓夢敘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頁。霍克思文庫中沒有收藏“甲戌本”,暫無法確認霍克思所參考底本的具體版本信息。
7.作家本
紅樓夢 / 曹雪芹著
北京:作家,1955
3v.;21cm.
上述即霍克思所言“作家本”的具體版本信息。
8.索引本
(1)紅樓夢索隱 / (曹霑,高鶚著);王夢阮,沈瓶庵索隱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4
4v.;21cm.
(2)紅樓夢索隱 / (曹霑,高鶚著);王夢阮,沈瓶庵索隱
上海:中華書局,1916
10v.in 1 case;23 cm.
文庫中收藏有兩個《索隱》本,霍克思英譯筆記第76頁在討論“紅麝香珠”時給出了其參閱的具體版本信息即1916年本,故索引本可以確定版本信息。需要注意的是,筆記中兩處關于參考該本的記載,霍克思均記作《紅樓夢索引》,“引”實為“隱”之誤,應注意。
9.國初本
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 / 曹霑撰;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4v.;22cm.
本書據民國九年上海有正書局印本影印
(1)“國初本”為“戚序本”,卻非“高抄本”。劉迎姣列出的參考版本中認為《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即高鈔本或戚序本,此判斷前部分有誤。
“國初本”全稱為《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脂硯齋評,八卷80回,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有民國元年(1912)大字本和民國9年小字本兩種,扉頁題:“原本紅樓夢”,封面題:“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中縫題:“石頭記”, 首戚蓼生“石頭記”序,次目錄,“簡稱戚本或有正本”①一栗編著:《紅樓夢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頁。。1973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據大字本,校勘小字本、脂蒙本及脂寧本整理影印,名戚蓼生序本《石頭記》,簡稱脂戚本。②參看《紅樓夢敘錄》,第16頁。故“國初本”即“戚序本”這一判斷是正確的,但認為“國初本”為“高抄本”則是誤斷。“國初本”只有80回,與“高鈔本”中“高”(即高鶚)沒有任何關系,高鶚參與整理校勘的是120本。
另霍克思筆記1977年10月3日條目“高抄”與“戚序本”并舉,亦是“戚序本”非“高抄本”的明證。該條筆記討論“人民本”探春一語“既這么著,就攆他出去”,筆記指出“庚辰”“俞本”和“人民本”此處不對,“高抄has the correct text here‘探春點了頭道這么著……’This is also the text of 戚序本”。③《〈紅樓夢〉英譯筆記》,第212頁。霍克思1998年12月7日接受香港理工大學在讀碩士陳靄心(Chan Oi-sum Connie)訪談時,曾詳談自己當年翻譯《紅樓夢》的情景。其中提到版本問題,他有一段這樣的話:“很遲的時候我才開始真正感興趣并卷入版本問題……譬如說乾隆鈔本,你知道的,高抄本,我就沒有看到,我得到它已為時晚矣。”④“Appendix: Interview with David Hawkes,” op.cit., p.227.這里,霍克思也明確了其“高抄本”即指“乾隆鈔本”。
(2)范圣宇認定1976年版國初本即霍克思英譯《紅樓夢》時參看的底本,也有待商榷。因為《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有1912年、1920年、1927年和1976年等四個版本,從英譯筆記顯示,霍克思最早參看“戚序本”是在第27回,時間為1972年12月22日,其時1976年本尚未問世,顯然無法成為霍克思翻譯中參看的底本。故之,國初本的具體版本信息尚需存闕。
10.胡藏程乙本
百廿回紅樓夢稿 / 曹霑撰;高鶚續
臺北:青石山莊出版社,1962
20v.in 4 cases: ill.;19cm
—(青石山莊叢書:子部小說類之七)影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本
霍克思最早參考“胡本”是在1973年4月7日,當時譯至《紅樓夢》第31回,湘云薔薇架下撿拾到一個更大更有文采的金麒麟,她擎在掌上心有所思,“人民本”提醒此處諸本有異,霍克思參閱了“庚辰”“乾抄”和“胡藏程乙本”。之后連續多回(多集中在第30至40回間),霍克思參看此本,英譯筆記中以“胡藏程乙本”“胡程乙”“胡程”“胡本”“胡”等稱呼之,具體何指,霍克思同時期致港臺學者潘重規的一函,為我們揭開了其真面目:“青石山莊影印胡氏藏程乙本紅樓夢”。①紅樓夢研究小組編:《霍克思教授致潘重規教授函(一)》,《紅樓夢研究專刊》(第12輯)附錄,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1976年,第1頁。該本由臺灣青石山莊出版社主編胡天獵(原名韓鏡塘,別號胡天老獵、遼寧布衣)舊藏,1962年5月15日影印發行,名《影印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排印本百廿回紅樓夢》,列《青石山莊影印古本小說叢書》第七種,全套線裝20冊,四函。胡適作短序,舉之為“程乙本原排本”。 故此處所列版本信息應即是霍克思參看的確切底本信息。
11.藤本
霍克思文庫中未收藏“藤本”,《紅樓夢英譯筆記》中也只有一次關于參校“滕本”的記載,具體時間是1977年12月1日。②《〈紅樓夢〉英譯筆記》,第218頁。“藤本”應指藤花榭藏板,藤花榭嘉慶庚辰鐫刻本《繡像紅樓夢》,屬程乙本系統。霍克思英譯時僅參校一回,具體版本信息尚無法確認。
12.己卯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曹雪芹著
上海:古籍,1980
5v.in 1 case;29 cm.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鈔本影印;馮其庸作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序
霍克思1978年3月7日譯到《紅樓夢》第67回時提到庚辰本中兩回(64、67回)據己卯本補錄,③同上,第223頁。但這不一定說明霍克思一定參閱了“己卯本”。到1978年6月23日,霍克思譯第69回時,則有明確提及己卯本文字,④同上,第230頁。故較為保守的說法是霍克思至少在1978年6月參閱了“己卯本”。從時間上判斷,文庫中收藏的1980年本無法成為霍克思當時參閱的底本,故而霍克思參校的“己卯本”具體版本信息在沒有新證據出現前亦暫不能確定。
13.程甲本
《霍克思文庫》中無“程甲本”的記錄,查閱其英譯筆記也只提及一次,參校時間為1979年1月26日。⑤同上,第246頁。“程甲本”應屬程偉元、高鶚1791年刊刻的《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系列,但具體版本信息目前尚無法確定。
(三)《霍克思文庫》中尚存版本辨析
通過謹慎比對霍克思《〈紅樓夢〉英譯筆記》,《霍克思文庫》14個《紅樓夢》收藏版本中有七個版本可以確定為霍克思當年英譯《紅樓夢》時所參考的底本,排除了1964年臺灣中華書局《紅樓夢索隱》、1976年臺灣學生書局《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1977年臺北廣文書局《王希廉評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和1980年上海古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四個本子,另余三種版本需要辨析: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曹雪芹著
香港:中華書局,1977
4v.;21cm.
該本為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8月第一版,影印的是“庚辰本”。⑥參看孔夫子舊書網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7510_438753512/。最后訪問日期:2016年9月2日。從時間上判斷, 霍克思英譯過程中參閱的底本更可能是1955年北京文學古籍出版社發行的“庚辰本”而不是此中華書局本,因為霍克思英譯筆記清晰表明早在1970年11月10日他撰寫筆記之始⑦《〈紅樓夢〉英譯筆記》,第3頁。已參看了“庚辰本”,故排除此本。
校定本紅樓夢/ 曹霑 高鶚著;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紅樓夢研究小組(編輯);潘重規主編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3
(32),34,1465 p.;22cm.—(紅樓夢叢書,1)
此本無法計入霍克思英譯底本,因為其問世之時霍克思早已完成《紅樓夢》前80回的英譯工作。
紅樓夢 / 曹雪芹,高鶚著;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
北京:人民文學,1982年
3v.;21cm.
同理,此本時間在霍克思完成《紅樓夢》英譯工作之后,無法計入。
結語
綜上,霍克思在《紅樓夢》翻譯過程中至少參考了13種底本,其中7種可確定具體版本信息,其他6種暫付闕如。具體而言,可確定版本信息的有《紅樓夢》(曹雪芹、高鶚著,啟功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四卷)、《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曹雪芹撰,北京:文學古籍出版社,1955年,二卷)、《蘭墅閱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高鶚手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2卷)、《紅樓夢八十回校本》(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四卷)、《百廿回紅樓夢稿》(據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本,胡天獵藏本,曹雪芹撰、高鶚續,臺北:青石山莊出版社,1962年,20卷)、《紅樓夢》(曹雪芹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三卷)和《紅樓夢索隱》(曹霑,高鶚著;王夢阮,沈瓶庵索隱,上海:中華書局,1916年,10卷),另有《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繡像紅樓夢》(藤花榭藏板)、《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程甲本)、《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王希廉評本)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六種無法確定具體版本信息的參考底本。
在13種底本中,人民本《紅樓夢》是霍克思翻譯的主要底本,英譯筆記中但凡討論到版本問題,首先引用的均是該本文字,如不存在版本文字歧異,霍氏亦是徑直依據人民文學本譯介。除了此本,霍克思參校較多的依次是《蘭墅閱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52次)、《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50次)、《紅樓夢八十回校本》(35次)、《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29次)和《百廿回紅樓夢稿》(胡天獵藏本)(13次)。其他諸本參考較少,分別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六次、《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王希廉評本)和《紅樓夢索隱》各兩次、《紅樓夢》(作家本)、《繡像紅樓夢》(藤花榭藏板)、《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和《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程甲本)均僅參考一次。有關霍譯本各回參校底本版本情況與各版本總參校次數等數據統計與趨勢圖,筆者另文具體探討。
《漢學家日文初級讀本》(2017)
由福格爾(Joshua A.Fogel)與文子(Fumiko Joo)編輯的《漢學家日文初級讀本》(Japanese for Sinologiests.A Reader Primer with Glossories and Translations)于201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長期以來,學術界都有種說法,即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者須了解日本學者對中國的研究。本著致力于幫助漢學家學習有關中國的日語文獻,為迄今正式出版并流通的首部教材。其內容涵蓋日本著名學者的論文、標注羅馬字母的詞匯表、英文譯文、語法講解等。讀完該著,讀者將會較全面地了解日本著名漢學家及其寫作風格,并具備獨立閱讀日本中國學的初始能力。導言部分介紹在日本文獻中提供關于中國研究基本信息的詞典、百科全書、人名錄、術語表及其他研究資源。正文部分涉及一系列主題與時代,并突出了所有中國學研究方面的著名日本學者。附錄里有所有文章的英文譯文。(秋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