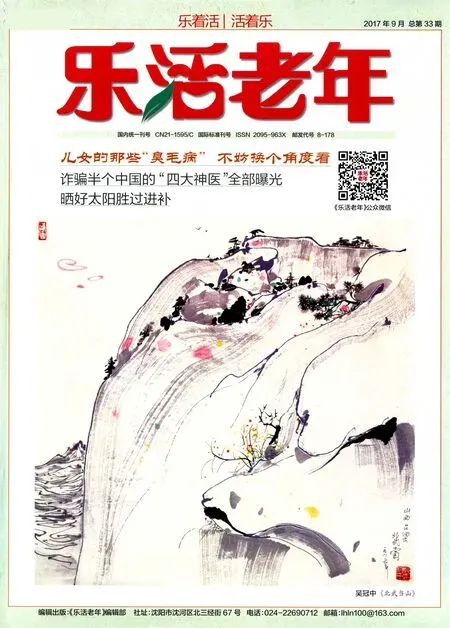消失的鄉(xiāng)村吆喝聲
文/劉明禮
消失的鄉(xiāng)村吆喝聲
文/劉明禮
小時(shí)候雖生活在窮鄉(xiāng)僻壤,卻也有些最真實(shí)的人間煙火令人難忘,尤其是那一聲聲獨(dú)具韻味的鄉(xiāng)村吆喝,不僅使冷寂的鄉(xiāng)村多了一些生機(jī),也給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一些情趣,更給我的童年帶來(lái)了許多歡樂(lè)。
在那物質(zhì)匱乏的年代,交通不方便,沒(méi)有現(xiàn)代化的交通工具,也沒(méi)有太多的產(chǎn)品,更見(jiàn)不到各種廣告。那些手藝人、買(mǎi)賣(mài)人,或騎車(chē)或挑擔(dān),奔走在坑洼不平的鄉(xiāng)村街巷,憑借響亮、悠長(zhǎng)、獨(dú)特的吆喝聲招徠著顧客,更吸引著我們這些頑皮的孩子。
“破鋪拆(破爛布)爛套子(爛棉絮)換鋼針”“爛頭發(fā)——換鋼針——”聽(tīng)到這吆喝,便知道村里來(lái)了推車(chē)的貨郎。那時(shí)候人們手頭緊巴,居家常用的零零碎碎,可以用破爛兒來(lái)?yè)Q。針頭線(xiàn)腦、鍋碗瓢盆、木梳、篦子、雪花膏、小鏡子、小胰子等日用品,幾乎應(yīng)有盡有。當(dāng)然,讓男孩子最感興趣的,還是彩色泥哨、泥模子、做彈弓用的氣門(mén)芯這類(lèi)物件,常會(huì)背著大人把家里的廢銅爛鐵等拿出來(lái)?yè)Q。有次,我看中了貨郎車(chē)上一對(duì)彩泥鴿,很想得到,便偷偷起掉了母親陪嫁的格子柜上的銅吊墜。后來(lái)被母親發(fā)現(xiàn),為此我屁股上飽嘗了父親一頓掌摑。
能直接換的東西,還有香油、豆腐等吃食。有道是“吃慣了的嘴,跑溜了的腿”,雖然賣(mài)香油的不止一個(gè),可我們村的人似乎只認(rèn)鄰村那個(gè)老胡,說(shuō)他賣(mài)的油沒(méi)摻假,不缺斤少兩。老胡約摸有五十來(lái)歲,短脖子,光腦袋,矮胖矮胖,叫賣(mài)的聲音卻很響亮。他騎著一輛“大水管”自行車(chē),車(chē)架上掛著一個(gè)鐵絲筐,裝著一只不大的油桶,上面搭條油乎乎的布口袋,進(jìn)村就是一嗓:“打香油吃來(lái)啵——,芝——麻——換香油——”把車(chē)子往街心大槐樹(shù)上一靠,又是一嗓,然后就叼起煙袋和人們聊開(kāi)了天。時(shí)間長(zhǎng)了,村里人便稱(chēng)他為“油胡”。他三天不來(lái),村里人就得念叨:“油胡這家伙怎么回事,這么多天沒(méi)來(lái)?”再來(lái)了難免要挨幾句數(shù)落。
村當(dāng)中的大槐樹(shù)下似乎成了買(mǎi)賣(mài)人的固定場(chǎng)所,磨刀的老頭來(lái)了也會(huì)奔那。那個(gè)磨刀老頭很有意思,他肩上扛著條長(zhǎng)板凳,悠悠閑閑地走進(jìn)村來(lái),走上幾步便拉著長(zhǎng)音吆喝一句:“磨剪子嘞——搶——菜——刀—— ”一吆喝,他脖子上的青筋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末尾的“刀”字,似乎能飄出去很遠(yuǎn)很遠(yuǎn),能在空中停留半天。他來(lái)到大槐樹(shù)下,不及放下板凳,就有村民拿著菜刀、剪子等著他來(lái)給拾掇。不管有多少人等著,他總是不慌不忙,把每把刀剪給磨得锃光瓦亮。
如今,好多傳統(tǒng)的營(yíng)生已成為過(guò)去,曾經(jīng)走村串巷的手藝人、買(mǎi)賣(mài)人不見(jiàn)了蹤影,那熱熱鬧鬧的場(chǎng)景也仿佛從這個(gè)世界消失了,鄉(xiāng)村再也難以聽(tīng)到各種吆喝聲。然而,那韻味悠長(zhǎng)的鄉(xiāng)村吆喝,那給我童年帶來(lái)無(wú)盡歡樂(lè)的鄉(xiāng)村元素,卻時(shí)常在我耳畔回蕩,在我腦海回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