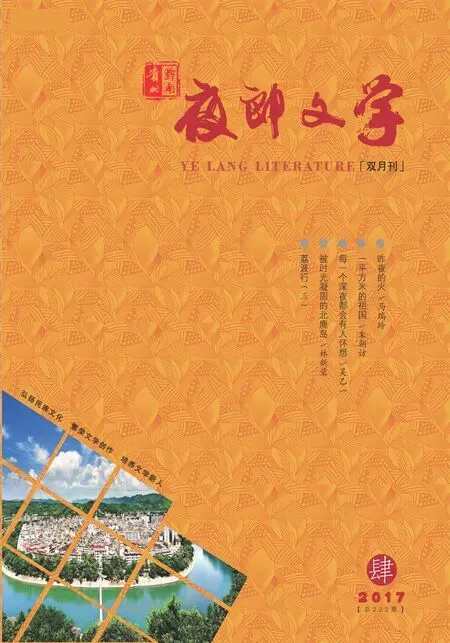挖礦的人
——朱朝訪詩歌淺析
伍亞霖
所謂“挖礦的人”,在這篇文章里至少有兩重以上的意義。
一是與生活直接發生的意義,也是現實的意義,如詩人在詩歌《挖礦的人》中寫到的:“數十年來/每一天都肩扛十字鎬/手拿放大鏡/奔波在這荒山野嶺上/尋根究底,挖山不止”,這樣一個勞動者的形象,這是直接意義;而現實意義是,詩人因為常年工作在磷礦企業,盡管詩人并不是真的每天背了十字鎬去干挖礦的活,但是他身臨其境感受和體會到作為曠工的悲喜生活,也正好切合了他現實的身份。
二是詩人通過詩歌這種文學形式,將自己所經歷的日常生活:其庸俗的、瑣碎的、卑賤的或者高貴的,或嬉笑、或怒罵、或呈現,賦予了最真實的表現和還原。如:“經理、設計師、工長/電工、木工、泥工/這一群素質參差不齊/各懷鬼胎的人們/熱情大方彬彬有禮的合謀/欺凌,蹂躪,折騰”《對一套房屋的裝修》這首詩中所呈現的,原汁原味的生活場景。
當然,既為“挖礦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意義遠遠不止以上兩種,而是詩人用以上兩種形式作為載體,挖掘出了生活中的殘酷、丑惡、人性的狹隘和卑劣;同時也彰顯了人性善良、美好的另一面。
關于這兩者中,誰重要或誰不重要,這是不可以選擇的;一方面從詩人朱朝訪先生習慣于選擇的多向性敘述維度,對一起事件全方位的記述,由外到內,再進入到深層的剖析或者反思;另一方面詩人作為敘述的對象或者敘述者本身,似乎并沒有要求一定要獲得某一種結果,其意義更多放在了呈現的現實上。
一、直接呈現與現實意義的抵達
中國新詩在經過100年的成長和探索之路,走到今天,呈現出一派從來未有過的繁茂與多元姿態,從偏愛意象的紛紜龐雜、到口語的簡單平實、從象征手法到超現實到后現代主義,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詩歌本身的發展需要而言,這理應是很好的發展態勢,因為藝術創作一直主張多元,唯有多元化才最能推動其進步,帶動大眾思考,并將之思考從單一式轉化為復雜,以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和趨同。
詩人朱朝訪的詩歌,介于傳統和口語之間,或者說是兼具了兩者的語言以及呈現形式,其間的詩意元素,如:比喻、借代、形容、象征等的運用依然存在,只是側重面多與少的區別。
對于直接呈現,說明白點,就是直接,不拐彎抹角,不晦澀,不作詞語間、意象間的糾集取舍,如“把血糖降下來/再修補好牙齒/你就成為了一個好人/一個精神強大的好人/一個思想健康的好人/這就是最近我在干的兩件事情/生活,其實就是這么簡單”《做一個好人》中這樣直白的內心呈現;有如:“在這一平方米的祖國里/安放著/母親溫暖的白骨,以及/我和她的魂靈”《一平方米的祖國》這之間的直抒情懷。
我愿意將直接呈現理解為心靈所追求的純粹,是一種樸質、誠實認真的生活態度,是一種大度、豁達的坦然姿態,是一泓懂得取舍、向低處自然流淌的清澈山泉,是一場能帶給閱讀者愉悅和輕松的對話。
當然,如果一味的只是直白呈現,只是將看到的一切賦予其文字的形式,那絕非詩歌寫作的目的,詩歌的意義之一,就是對我們生活的世界有所揭示。而要具備與之相關的,抵達詩歌寫作的目的和特性,這就引出直接呈現后的關于現實意義的抵達,如果說直接呈現的結果是作為對一首詩歌必要的過渡和鋪墊,好了,現在準備好了,我們總會抵達任何一處地址,那是必然也是必須的果實。“為了追問一只鳥的下落/我要在我的詩歌里/永不停歇的尋找下去”《追尋一只鳥的下落》,這首詩歌中的尋找和執著情懷,顯然就是為了抵達而進行的抵達;又如“不管怎么樣/我始終要抱著這樣一個信念/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以上是我選取的兩首詩歌的結尾,前面幾段是通過敘述進行的鋪墊,即呈現其抒懷或者言志的內容,在結尾部分,是一種抵達后的反思與和解,是對整首詩歌的交代,同時也是詩人對日常生活的認知所引發和挖掘內心礦藏而得來的感知與理性的升華。
二、從多維度的敘述到內心的思考
當我們將經歷的一切用詩歌的形式表達時,選擇什么樣的角度非常重要。雖然,關于詩歌的表達形式多種多樣,不論哪一種,都各有所長、各有千秋,“既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以,不管是閱讀者和詩寫者都應秉持了完全包容的心態。
“夜色中的太平洋百貨/風雨不動安如山。一對男女/踏上廣廈膝下的過街天橋/向春熙路走去/穿著深黑色套裝的中年男子/殷勤抽動的鼻翼上/兩粒綠光在幽幽的發藍……”《成都,今夜無人失眠》。在這首詩歌里,詩人可以說是站在一個四通八達的視覺點上,他看到的最先是太平洋百貨的一處商場,然后將視線轉移向下,很突然,他的眼光捕捉到一對走過天橋的男女。緊接著,鏡頭拉近,他看清了男人、女人的外衣顏色,甚至男人鼻翼上灑落的暗淡燈光。詩人的目光甚至是拐彎的,能穿街走巷,進入到最深的巷子里。我們都知道,寬窄巷是位于成都的一條中國的名巷,我去過,所以當我讀到這首詩歌時,熟悉的街巷立刻就涌向我的眼前;要知道,詩人的主題是成都,那是一片非常遼闊的地域,詩人選擇的視角點也正好契合了那樣的廣闊,從這里到哪里,從一個光點向無邊處擴散,甚至抵達了一大片成都平原……。
關于在《成都,今夜無人失眠》中,這樣的視角與維度選擇,詩人不光在大多數敘事性的詩歌都采用了這樣一種多維度敘述的形式,在其它關注個人體驗的詩歌寫作中,也大多如此,比如:“有人害怕你,憎恨你/說你是一簇鬼火/預示著死亡即將來臨/而我卻熱愛你這若即若離的個性”《致磷火》中反叛或者個性的磷火;又如:“平時一提起上班就頭痛/而這幾天卻很享受辦公室那略帶霉味的氣息/早出晚歸/行走在灑滿陽光的生活區/空曠的人行道微風習習/正好吻合我這顆寂靜的心”《沉醉于節前的寧靜》中對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的言和與矛盾對峙所達成的和解。

▲ 一池秋水鬧禽聲(國畫) 180x220cm /朱 瑞
“詩”即“思”,這里的“思”,我想應該是詩歌最終的意義和目的,是詩人在經歷世事后或者在發生過程中所引發的一次心靈“地震”,是詩人通過對外在事物的觀察、經歷、體會所對應的結果,也是詩人最后走向的內心思考,即詩人不論是對日常生活的描述、觀察,記錄、言志的終極結果跟目的。“最近沒什么大的動作/似乎比往昔安靜了許多/然而我并沒有沉默/身心每天都在狂野的奔突……/安靜,并不意味著已經死去”《安靜》,比如在這首名為安靜的詩歌里,大部分句子幾乎都是簡單表面的描述,其中“或許,按捺住心中的狂野/就是一個最大的動作”以及最后的一句“安靜,并不意味著已經死去”,留下了讓人思考的重量,帶給人思考的空間。這其中自然有許多作為閱讀者不得而知的東西,但詩歌所帶來的空間點,幾乎是共同的。
三、形式和語言的自由,以及對當今社會現象的揭示
在進人一首詩歌寫作開始之時,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會有這樣的體驗,往往第一句是最為重要和主要的。一方面,第一句確定了一首詩歌的主題,明確了整首詩歌的切入點和你對所要寫的事物的選擇角度;第二方面,第一句是帶領進入到整首詩歌的門,音節氣韻都在那一個點上開始,就像一首歌中的高音或者低音,當第一句完成,接下來的任務就是順著第一句確定的氣息一氣貫穿。由此,第一句可能會是最難寫的,也可能是最容易寫成的。
朱朝訪先生的詩歌第一句大多很輕松,讀得輕松,至于寫得輕不輕松,我們不得而知。這樣的輕松,理應是來自于詩人所選擇的形式和語言的自由,這也是其詩歌的最為重要特點之一,并表現在他的大部分詩歌里。比如“朝霞,落日/夜晚,或者清晨/一些與開頭和結局/有關的意象在我的眼前縈繞”,在這首名為《最后》的詩歌中這樣的開頭的輕松自然;又如:“其實就是幾個歪瓜裂棗/平庸得就像我的人生一樣平庸/討厭得就像我性格的缺陷一樣令人討厭”《關鍵詞》這首詩歌中帶著自嘲式的自由表達。
詩歌作為語言的藝術,其語言是用作為詩歌這種文學形式的載體,我認為,不論是煉字或者煉句,都是對于語言的練習,當然,這里的語言包含了太多東西,超越了我所指向的語言功效。我要說的是:一個詩人對于詩歌形式和語言的自由駕馭,是一種詩歌能力,一方面靠長期的練習獲得,一方面靠悟性。有一句老話這樣說:“寫詩如參禪,目下功夫二十年”,這里的 “目下”我理解為閱讀和學習的過程,也涵括寫作的練習,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這樣,對于我,在經歷了長達20年斷斷續續的詩歌學習和閱讀,我依然只是一個站在詩歌殿堂外的游人。我的意思說,要做到輕松自然的駕馭語言和形式的自由,那是詩歌寫作中最大的不自由和難題。因為,更多時候,語言是最難操縱的,相反,是語言在左右著我們的思想。
在這些輕松的背后,詩人應該是隱藏了無比多的“焦慮”,這樣的“焦慮”出現在詩歌里,是一種現代文明對于人類精神壓窒的掙扎和反抗,比如這樣的句子:“一番又一番粗野的搗鼓/一陣又一陣鉆心的疼痛/清純簡略的鄉村少女/搖身成為珠光寶氣的少婦《對一套房屋的裝修》;再如:“不管是明白還是糊涂/我也不能免俗/明天,將告別這節前的寧靜/攜帶著我的煩惱我的苦楚/去赴一場喧囂和騷動的盛宴”《沉醉于節前的寧靜》。一首詩歌總是要揭示一些什么,有所挖掘,詩歌才能稱其為詩歌。對于朱朝訪先生的詩歌,這一個特征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就其平時、客觀的語言和表現形式,無疑都是對這一切的鋪墊和承托,如果失去這些,所有的語言和句子終將淪為一場無意義的語言游戲。
朱朝訪先生是一位有著豐富詩歌寫作經驗的詩人,從閱讀他的詩歌中可以發現,他在保持著傳統的詩學理念同時也在不斷探索對詩歌寫作的新嘗試。他試圖拋棄繁復的事物,更多轉向對于內心的觀照,呈現其簡單、甚至童真的心靈世界。
但是,一方面,他的部分詩歌,如《安靜》《最后》《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等等,不管是表達形式或者語言,都表現了詩人消極的一面,這或許是因為詩人對時間流逝以及生活殘酷現實的無力感和退讓。
另一方面,因為過多追求語言的自由以及詩人天性不羈的性情所致,他的詩歌往往在其陳述、敘述過程中,顯示出語言上的累贅,欠缺精煉和含蓄。因為出現過多的敘述性事件的鋪墊,導致最終的出口偏于狹窄,與相比之的鋪墊失去了平衡和相持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