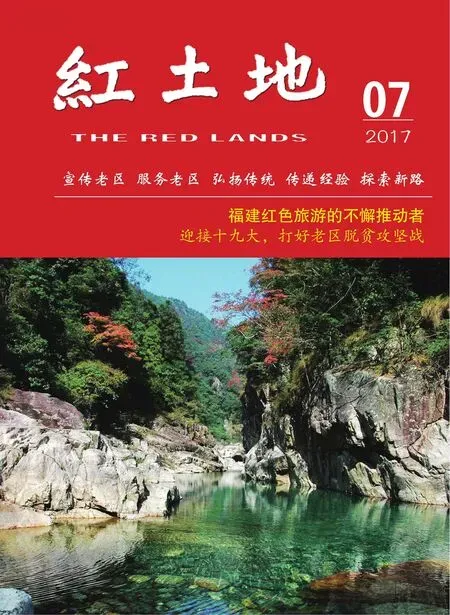張衛(wèi)龐:習(xí)近平曾來(lái)我家搭伙吃飯
張衛(wèi)龐:習(xí)近平曾來(lái)我家搭伙吃飯

習(xí)近平在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zhèn)梁家河村調(diào)研時(shí)同村民邊走邊聊(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1969年1月,15名北京知青來(lái)到陜西省延安市延川縣梁家河,其中包括習(xí)近平在內(nèi)的6名知青分在二隊(duì)。一開(kāi)始,隊(duì)里派人專門給知青們做飯,灶房設(shè)在張衛(wèi)龐家的窯洞里。后來(lái),北京知青只剩下習(xí)近平一人,他又在張衛(wèi)龐家搭了將近一年的伙。
這一組訪談,通過(guò)張衛(wèi)龐和房東呂侯生的講述,我們可以走進(jìn)當(dāng)年,看看習(xí)近平是如何與村民融合在一起的,他又是怎樣“滴水之恩涌泉相報(bào)”的。
采訪日期:第一次2016年2月27日,第二次2016年12月29日
采訪地點(diǎn):梁家河村委會(huì)接待室
“再糙的飯近平也吃得香,再窮的人近平也看得起”
采訪組:習(xí)近平到梁家河插隊(duì)的時(shí)候,您和他在一個(gè)生產(chǎn)隊(duì),平時(shí)吃飯、勞動(dòng)都在一起,請(qǐng)您講講您和習(xí)近平交往的事情。
張衛(wèi)龐:近平到梁家河來(lái),比我到梁家河還早一個(gè)多月。我之前是馬家河鄉(xiāng)龐家河村的,1969年2月,我成了梁家河的上門女婿,就到梁家河村來(lái)了,見(jiàn)到了已經(jīng)在梁家河下鄉(xiāng)一個(gè)多月的近平。
我當(dāng)時(shí)來(lái)的時(shí)候,近平他們二隊(duì)知青一共6個(gè)人,都住在劉金蓮家的一孔窯洞里;我也是二隊(duì)的,他們做飯的灶房設(shè)在我家一孔窯洞里,隊(duì)里派了人來(lái)專門給他們生火做飯,所以我們每天都一起吃飯,一起勞動(dòng),打交道挺多的。
我的老丈人叫張貴林,他是老共產(chǎn)黨員,也是梁家河的老書記,從1935年到1960年一直都是梁家河的村支書,經(jīng)過(guò)的事情多,在這個(gè)村里有威望。近平經(jīng)常來(lái)我們家,找我老丈人聊天。
后來(lái)時(shí)間長(zhǎng)了,慢慢接觸多了,我們就熟悉了,彼此交流也就多了,關(guān)系越來(lái)越好。我沒(méi)事就跑到近平的窯洞串門,找他拉話。
近平當(dāng)我們村的支書時(shí),村里的知青都走光了,就剩下他一個(gè)人了。他每天既要忙村里的事情,又要參加隊(duì)里的勞動(dòng),根本顧不過(guò)來(lái)做飯、刷碗,就對(duì)我說(shuō):“我到你家里去吃飯,你看咋樣?”我說(shuō):“行嘛!只要你不嫌棄我們家人口多嘛!”近平主動(dòng)提出到我家來(lái)吃飯,我當(dāng)然歡迎了,可心里又有些擔(dān)心,我家里當(dāng)時(shí)一共六口人:一個(gè)老人,我們夫妻兩人,還有三個(gè)娃娃,我怕家里人多吵鬧得厲害,怕近平吃不好飯。
近平把他每個(gè)月分的40斤糧都交到我家。在我們家吃飯的時(shí)候,我婆姨(妻子)做什么,他就跟我們一起吃什么。他這個(gè)人就是這樣——再糙的飯他也吃得香,再窮的人他也看得起。
就這樣,近平在我家里吃了將近一年的飯,一直到他上大學(xué)離開(kāi)梁家河。
采訪組:你們每天都吃什么飯?
張衛(wèi)龐:每天早上就是做團(tuán)子,團(tuán)子是用玉米面和糠做的。下午就是面,有時(shí)候是豆子面,有時(shí)候是高粱面。麥子面七八天才能吃一回,當(dāng)時(shí)就是缺少這東西嘛。
采訪組:吃飯的時(shí)候有菜嗎?
張衛(wèi)龐:有酸菜嘛,近平那次回來(lái)后就說(shuō),很久不吃梁家河的酸菜還很想吃呢。
采訪組:酸菜是用什么做的?
張衛(wèi)龐:就是白菜和黃蘿卜,切碎之后腌上它,酸的嘛。
采訪組:是一年到頭都能吃到酸菜嗎?還是有的時(shí)候才能吃上?
張衛(wèi)龐:酸菜基本能吃半年,從9月份開(kāi)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都沒(méi)有新鮮蔬菜,就吃酸菜嘛。等有新鮮蔬菜的時(shí)候就不吃酸菜了。
采訪組:當(dāng)時(shí)能吃到什么蔬菜啊?
張衛(wèi)龐:就是黃瓜呀,洋柿子(陜北方言,西紅柿),茄子,辣子……都是個(gè)人種的,不掏錢。
采訪組:當(dāng)時(shí)炒菜有油嗎?
張衛(wèi)龐:那時(shí)候油太少了,基本上就沒(méi)啥油,就把山上的杏摘下來(lái),把杏核砸開(kāi),再把里頭的杏仁壓碎,鍋燒熱后倒進(jìn)去炒一下,就算有點(diǎn)兒油,炒菜就用這東西。
采訪組:您后來(lái)和習(xí)近平還有聯(lián)系嗎?
張衛(wèi)龐:近平走的時(shí)候,送給我兩條棉被,兩件大衣,還有一個(gè)針線包。這個(gè)針線包是近平來(lái)插隊(duì)時(shí),他媽媽給他做的,上面繡著三個(gè)字“娘的心”。在那個(gè)年代,沒(méi)有錢買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縫補(bǔ)了一層又一層的,針線包可以裝一些針線用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不像現(xiàn)在,新衣服都穿不完,沒(méi)有誰(shuí)還穿有補(bǔ)丁的衣服。
近平給我的棉被和大衣,在那個(gè)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用舊了。唯獨(dú)那個(gè)針線包,我一直珍藏著。我是個(gè)莊稼漢,粗枝大葉,也不懂啥大道理,就覺(jué)得近平是我的親人,就想存著這個(gè)針線包,留個(gè)念想。這個(gè)針線
包,我保存了38年,直到2013年才捐給了縣里,交給國(guó)家保管。

習(xí)近平在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zhèn)梁家河村看望村民,同他們親切交談(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近平給我治腿病”
采訪組:習(xí)近平在梁家河插隊(duì)時(shí),曾在您家里住過(guò)很長(zhǎng)時(shí)間。請(qǐng)您講講,您最初認(rèn)識(shí)習(xí)近平的情形。
呂侯生:近平來(lái)我們村插隊(duì)的時(shí)候,分在二隊(duì)。我們這山溝溝非常閉塞,突然來(lái)了知青,大家都覺(jué)得新鮮,都過(guò)去看看。剛開(kāi)始,他們說(shuō)話,我們都聽(tīng)不太懂;我們說(shuō)話,他們也聽(tīng)不太懂。后來(lái),一起勞動(dòng),就慢慢熟悉起來(lái)了。
近平特別愛(ài)看書,他的炕上都是書,一得空閑,就捧著書看,干了一天活,累得不行,他還點(diǎn)著煤油燈看到半夜,經(jīng)常熏得臉上都是黑的。有一次,近平晚上看書到很晚,我就在旁邊一邊抽煙一邊陪著他。結(jié)果看到半夜,近平肚子餓了,當(dāng)時(shí)也沒(méi)啥吃的,我們倆就煮玉米吃,把一碗玉米倒進(jìn)鍋里,煮了半晌,以為熟了,其實(shí)還是夾生的,我們就把這碗半生不熟的玉米給吃了。
采訪組:習(xí)近平離開(kāi)梁家河以后,您和他還有什么聯(lián)系嗎?
呂侯生:1993年,近平已經(jīng)到福建工作多年了,他抽空回梁家河來(lái)看望鄉(xiāng)親們的時(shí)候,我與他見(jiàn)上面了,他還給我留了一張名片。

習(xí)近平在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zhèn)梁家河村察看自己當(dāng)年住過(guò)的知青窯洞 (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1994年,我修窯洞的時(shí)候,被窯洞頂上掉下來(lái)的一塊石頭砸了右腿,因?yàn)闆](méi)有及時(shí)治療,右腿后來(lái)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嚴(yán)重,我才到醫(yī)院去治療,花了好幾千塊錢,還是沒(méi)有治好。
那時(shí)我修窯洞,本來(lái)手頭就很不寬裕,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積蓄,還欠下很多外債。而且,因?yàn)椴](méi)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來(lái)到了嚴(yán)重的時(shí)候,走路已經(jīng)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當(dāng)時(shí),我真是走投無(wú)路,再不治療,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兒女可咋辦呀?實(shí)在沒(méi)辦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給他寫了一封信。讓我沒(méi)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給我寄來(lái)了500塊錢的路費(fèi),讓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這個(gè)匯款啊,心里特別感動(dòng),眼淚都快流下來(lái)了。
我是第一次離開(kāi)梁家河,第一次出這么遠(yuǎn)的門,從延安坐火車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見(jiàn)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說(shuō)不用擔(dān)心,我這心里頓時(shí)真是百感交集。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聯(lián)系醫(yī)院幫我治療。他平時(shí)工作很忙,經(jīng)常下基層,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會(huì)到醫(yī)院來(lái)看望我。
有時(shí)候,我心里覺(jué)得不安,我問(wèn)起他醫(yī)療費(fèi)的事,近平對(duì)我說(shuō):“侯生,給你治病,花多少我都愿意。”其實(shí)我心里清楚,九十年代初,咱們國(guó)家普遍工資都挺低,近平的工資也并不高,他沒(méi)有多少積蓄。給我看病花的這些醫(yī)療費(fèi),大多都是彭麗媛老師的錢。
我在福建治療,腿當(dāng)時(shí)恢復(fù)得不錯(cuò),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錢,大概有幾萬(wàn)塊吧,我當(dāng)時(shí)也無(wú)力還給他,即使給他,他也不會(huì)要的,我只有把這件事記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過(guò)了幾年,沒(méi)想到病情又復(fù)發(fā)了,這次更為嚴(yán)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術(shù),近平知道這個(gè)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醫(yī)藥費(fèi)。轉(zhuǎn)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達(dá)我對(duì)他的感謝,那時(shí)我已經(jīng)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體已經(jīng)恢復(fù)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見(jiàn)到我,非常關(guān)心地俯下身體,看我的假肢,還用手反復(fù)摸,好像是看看這假肢的質(zhì)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興地對(duì)我說(shuō):“侯生,你的大難過(guò)去了,咱們一起合影留個(gè)紀(jì)念吧!”
(摘自2017年2月17日~23日《南方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