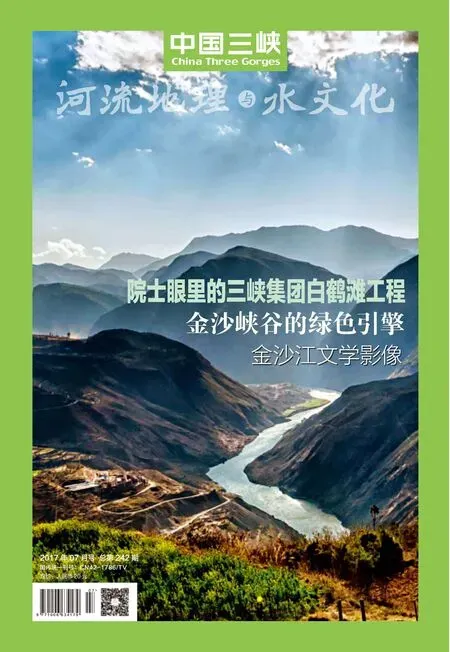白鶴灘的鄉土記憶
文 | 鄒長銘
白鶴灘的鄉土記憶
文 | 鄒長銘
金沙江浩浩蕩蕩地奔流在高山峽谷之間。在大江流經巧家縣白鶴灘處,一座裝機容量僅次于三峽電站、居世界第二的巨型電站正在建設中。待電站建成,“高峽出平湖”,煙波浩淼,靜影沉壁;沿湖百里,循曲徑得茅舍掩映,凌秋水見負廓煙霞,水岸家園,美不勝收。然而,世事滄桑,曾經的高山峽谷,曾經的急流險灘以及在高山峽谷、急流險灘的磨礪呵護之中生生不息,延續了千年的萬眾蒼生鄉土記憶又當到何處追尋?
驚濤駭浪中的“雙飛燕”
水流千轉,浪遏飛舟。
在金沙江的風浪里漂泊的小木船有一個美妙動聽的名字——“雙飛燕”。何以如此稱謂?或者因為其形體輕盈、行動敏捷;或者也因為整日出沒在風浪里的船工們,在漂泊無定的生涯中,更需要一種心靈的溫情的慰藉。如此而言,“雙飛燕”既是終日漂泊風浪里的船工們人生歲月的承載,也是船工們現實生存困境中的心靈寄托。
“雙飛燕”船體長約8米,寬不足1米,船幫稱“亮子”,深約80厘米,船頭、船尾微微上翹,形如弦月,飄逸、輕靈、精巧、別致,與上江“元跨革囊”時的羊皮筏,與下江平頭的“豬槽船”大不一樣,別是一種情趣。打造“雙飛燕”所用木料以樟木為最好,紅椿木次之;也有用攀枝花木,取其浮力大,價廉,但不耐腐蝕,新船下水,一般只能使用一年。船體由龍骨、桁木、艙板結構而成。船身成形后,要用桐油石灰涂刷船體,以防腐蝕。船上分隔成3個艙:船體中部1個艙,稱“大肚”,是載客、裝貨的地方;船頭、船尾各l艙,稱“小肚”,是掌艄、劃漿的操作臺;艙底板與“亮子”平,便于觀察水勢。
“雙飛燕”的操作系統僅有1櫓,稱大橈;2槳,稱“小橈”;系著于船頭、船尾的纖繩,稱“箍頭繩”。額定船工5人:1人搖櫓,是舵手,也稱“老大”;1人撐篙;3人劃槳,兼任拉纖的角色,故又有“背箍頭”的雅號。“背箍頭”又分一把纖、二把纖、三把纖。一把纖要非常熟悉沿江的纖道和江灘、礁石的分布情況,盤灘、吊灘時會指引水路。二把纖沒有特別的技術要求,但要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出力。三把纖要求有“絕活”,“絕活”稱“減腕”,就是在遭遇險灘、礁石時,能準確、適時地拋出纖繩找到系著點,以便調整船位、船速,在越險后又能及時地回收纖繩。
“雙飛燕”是一位柔弱的沖浪者。江流平緩處,一只櫓,兩葉槳,有浮漾的清波輕輕地推送,有無聲的浪涌悄悄地托舉,“雙飛燕”輕盈、自如地在波峰浪谷中躍動著滑過,兩岸青山如屏,村寨依稀,桃紅柳綠,移步換景。當其時,“雙飛燕”是金沙江的寵兒,是天地間自由飛翔的精靈。至狹谷險灘處,柔弱的沖浪者便無可掩飾地表現出力不從心的難堪:大江忽被兩岸絕壁緊束成一線,江流如飛瀑跌落,“虎豹磨牙伺客過,黿鼉吹浪窺人往”。當此時,“雙飛燕”便只能無奈而又無助地收束了翅膀,靠“盤灘”或“吊灘”走出困境。

金沙江銅運古纖道 攝影/袁志堅

所謂“盤灘”,是指船行上水時遇到險灘,要先將裝載的貨物(或乘客)盤駁上岸,“背箍頭”下水背纖,將卸載后的船拖拽上灘后,再裝貨(或載客)前行。所謂“吊灘”,是指船行下水時遇險灘,同樣要先將貨物(或乘客)卸載,“背箍頭”拽纖繩,按照“船老大”的指令,不時收、放、拖、抬纖繩,以調整船的方向,控制船的速度,將船“吊”過險灘,再裝貨(或載客)前行。也有例外,如果“船老大”藝高人膽大,且是個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冒失鬼,行下水遇險灘也不卸載,也不吊灘,看清水勢,暴喝一聲,任著柔弱的沖浪者往驚濤駭浪中闖,習稱“彪灘”。“彪灘”時可憐的“雙飛燕”如在狂風暴雨中掙扎,一忽兒被巨浪拋離水面,一忽兒又被巨浪兜頭蓋腦地砸向水底,船底在獠牙巨齒的礁盤上嘎嘎吱吱、顛顛搖搖地劃過,恍惚之際,又被推上了幾米高的浪尖。“彪灘”不是勇敢者的游戲,而是冒失鬼的惡作劇,船毀人亡的事故多在“彪灘”時發生。
“雙飛燕”上的船工終年不穿衣褲,雖數九隆冬亦赤身裸體。之所以這樣,既因為常要下水背纖、盤駁,也因為一旦遇險時利于脫身。行為雖不雅觀,但生存環境決定,岸上行人及船上乘客亦見怪不怪。船工隨船帶油米,饑餓時就在江灘上用石塊支個鍋樁,燃幾把從江中撈起的水柴,野炊、野餐。夜不宿店,系纜江邊,船工即在崖穴崖洞中棲身。行船有諸多避諱習俗。新船造成或每年首航前要祭船,燃香燭,宰殺公雞,用雞血繞船滴一周,據稱可避邪。載客時乘客只能從側面上船,不準跨船頭;上船后船家要交待政策,不準多言,以免犯忌。忌什么?忌諱可就太多了。諸如:吃飯要說“開粉子”,吃飯用的筷子不準叫“筷子”要稱“濠竿”,碗、碟、盅等餐飲用具不能倒扣,等等等等。
或問:金沙江灘險流急,何以選擇柔弱、嬌小的“雙飛燕”來承擔負重遠行的重擔?道理其實并不深奧。“元跨革囊”的皮筏,雖然能在孫髯翁著名的大觀樓長聯中附驥揚名,但可能像“雙飛燕”一般負重嗎?“漢習樓船”的艨艟巨艦固然威風,但在金沙江的狹谷險灘中又該怎樣施展?“雙飛燕”是金沙江養育的頑皮而又聰慧的兒子,“雙飛燕”是船工風雨人生中一方可供棲息的熱土,一脈可以獲取的溫情的慰藉。
懸掛在溜索上的人生
文人喜歡雅致。在后世追求雅致的文人的筆下,一股系著于兩岸絕壁之上的竹纜,一條凌空垂掛、橫越江河的溜索,便也有了一個雅致的稱謂——“笮橋”。不僅如此,如螻蟻般攀緣溜索過渡的履險者驚心動魄的經歷,在文人的筆下,便也有了幾分詩意的沉穩與自信。且看唐人獨孤氏的《笮橋贊》中的一段文字:
“笮橋絙空,相引一索。人綴其上,如猿之縛。轉貼入淵,如鳶之落,尋橦而上,如魚之躍。頃刻不成,隕無底壑。”
如之何?雅。一“雅”,便詩情畫意,“如魚之躍”,“如鳶之落”,何等美妙?雖有“隕無底壑”的警告,無妨“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妙趣天成的誘惑。打住!請保持應有的冷靜,切勿被文人的筆墨蠱惑,把萬眾蒼生生存的艱辛當作魚躍鳶落的娛樂的游戲。

金沙江溜索捕魚 攝影/袁志堅
據史料記載,最遲不晚于兩晉時期,溜渡(或曰笮橋)便是金沙江、牛欄江兩岸百姓實現彼此抵達的極為重要的工具。事實上,我們更有理由認為,自我們的祖先在關山絕塞、復水縱橫的滇東北定居那天起,溜渡便是他們走向明天的朝夕相伴的朋友。此后經歷了不知多少個世紀的變遷后,雖然溜渡使用的材料早已今非昔比一一諸如藤條換成竹纜、竹纜換成鋼纜——但基本的結構形式和過渡方法并沒有太大的改變:在深溝峽谷江河兩岸選擇一處巖基堅固的地方作為錨地,錨地上安置錨鏈。將藤條、竹纜或鋼纜固定在錨鏈上,繃緊,凌空橫懸于江河峽谷之上,稱為溜索。溜索上套一筒形木套(或竹套、鋼套),稱溜殼。溜殼上懸掛一長方形木肋座盤,即為載運客貨的容器。過溜時,人坐到木肋座盤上,雙手緊拽住懸吊座盤的繩索,守溜人松動拉繩,座盤迅速滑落到溜索的中心位置,守溜人再一把一把地收攏拉繩,座盤逐漸向對岸接近,并最終在彼岸的錨地上停住。
溜索的跨度差異甚大,跨度小的不過三四十米,跨度大的如金沙江上被稱為“亞州第一高溜”的鸚哥渡跨度達400余米,距江面空高達220余米。溜索的懸空高度主要由地形和跨度兩個因素決定。一般而言,在近岸處懸高約三四十米,至中心位置自然垂降成半弧形,與錨地高差約20米左右。跨越江河的溜渡,在汛期洪水暴漲時,溜索的中心一段距水面不過三四米。
過溜渡,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百姓而言,是艱難人生中一段無可逃避的歷程,別無選擇也就無所選擇。對于獵奇探險者而言,絕對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探險,即便是歷險后的愉悅,也只能在事后的很長一時間,才能忐忑不安地去回味過溜時的情景。那又是怎樣一種情景呢?爬上座盤、坐穩,緊緊地攥住座盤上的吊繩。左顧右盼,但見削壁如堵,淵藪百丈,此時心里早已是虛空空地找不到著落了,只能閉上眼,把未可預卜的前途隔絕在視野之外,僅存留一份不計生死的悲壯,勇往直前。待守溜人松動拉繩,座盤便無可自主地晃晃悠悠地向江心滑落。——“如鳶之落”?胡扯。哪里有那種矯健、輕捷、自如的快意,只有緊張、驚悸、恐怖的折磨。怯怯地睜開眼,高天一線,逝水千秋,人若螻蟻,棲身于凌空橫懸的溜索上,宛若天地間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在凜冽的江風與驚濤的雷吼中飄搖。繼之,“尋橦而上,如魚之躍”的過程極為漫長,無論你脫離深淵、抵達彼岸的愿望如何強烈,守溜人緊拽著的拉繩只能一寸一寸地收攏,載人的座盤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動。此時,置生死于度外的悲壯已被求生的欲望所代替,而生的現實卻總是在溜殼移動的吱吱嘎嘎的響聲中遲遲不肯兌現。等待,于驚恐中無助地等待。只有真實地站在了彼岸的土地上,情不自禁地喚一聲“阿彌陀佛!”才有可能在日后的某一天回味歷險時的感受時依稀感悟到幾分歷險后此生仍在的愉悅。事實上,或因溜索斷折、座盤脫落,或因過渡時因驚恐手足無措而“隕無底壑”的悲劇,總是與溜渡的存在而不斷地上演。
清同治二年(1863年)農歷正月,西進滇川的太平軍橫江決戰失利后,翼王石達開率殘部抵達牛欄江邊的竹林灣,欲取道巧家渡金沙江入川。牛欄江無舟渡,也無棧橋,上萬人馬只能靠溜渡過江。困頓在江岸的崖洞中,見沿江兩岸竹林森森,瑩瑩碧綠的竹叢中,有紅黃青紫的野花點綴,落魄的翼王怦然心動,隨口吟出一聯:“無事看花兼看柳,有時長嘯復長歌。”表面上的曠達、散淡掩蓋不了內心的焦灼、蒼涼。隨營有善書、擅刻者,把翼王的吟詠刊石摩崖于江岸,至今遺跡猶存。
進入21世紀,金沙江、牛欄江上所有的溜渡均已開始“溜改橋”工程,橫跨江河的橋梁將完全代替懸空垂吊的溜索。不久的將來,當悲劇的陰影不再永久地籠罩,巧家大地上跨谷飛澗、逾越江河的溜渡便只存在于記憶中,成為記憶中一道連結過去與未來、彌漫山野氣息與蒼古風韻的“橋梁”。

△ 金沙江邊的碉樓(紅外攝影) 攝影/袁志堅

▽ 紅外攝影中的金沙江 攝影/袁志堅
烏蒙馬傳奇
《滇南見聞錄》載:“滇中之馬善走山路,其力最健,烏蒙者尤佳。體質高大,精神力量分外出色,列于凡馬內,不啻鶴立雞群。”
烏蒙山區是烏蒙馬的原產地。當地出土的三趾馬、云南馬化石證明,早在距今100萬年以前的更新統時期,這里就是原始馬的棲息地。曾有報道說,在20世紀30年代初,金沙江、白水江流域仍有“野馬”活動。烏蒙馬是三趾馬,是云南馬和當地野馬在長期進化中經自然篩選,再由人工馴化培育獲得的優良品種。
烏蒙馬身材勻稱,骨骼清峻,性情溫順,四肢端正,關節強韌,筋腱發育良好,行動敏捷,是馱、乘兼用的優良品種。前清有一位大名田雯的巡撫寫過一篇《烏蒙馬說》,這位說“馬”的巡撫濃墨重彩地描述了著名的水西馬的體態及“逐云飆電”的神力后,筆峰一轉,為烏蒙馬寫下了一段極為精彩的文字:“然而未若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神駿過之。食蒼茛之根,飲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磨,齒背廣,以平途試之,夷然弗屑,反不喜走,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德貴養晦也。”——說的是馬?是人?是負重致遠的烏蒙馬啟迪了烏蒙人的心智,抑或是胸有丘壑、晦以養德的烏蒙人蘊化了烏蒙馬的性靈?
據昭通漢墓出土的“人逐馬圖”、“車馬畫像磚”考證,最遲不晚于兩漢時期,烏蒙馬已經被作為役畜使用。堂瑯銅、朱提銀、巴蜀鹽米閩浙絲,商旅貿易,貨物流轉,烏蒙馬是主要的運輸工具。元、明、清三朝,烏蒙馬是例定的向朝廷納貢的方物。明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于貢賦之外,規定用茶葉、布匹換烏蒙馬,“凡馬一匹,給布三十匹或茶一百斤,鹽如之。”烏蒙、烏蠻、芒部每年換馬四千匹,以為定例。明洪武十九年二月,詔令神策衛指揮同知許英領校卒七百余人,攜銀二萬六千六百余兩,到烏蒙、烏蠻、芒部、烏撒買馬,以滿足文治武功、軍需民用。五月,再令虎賁右衛百戶甘美率軍士千人,繼往烏蒙購馬,得二千三百八十匹。清乾嘉年間,為確保滇銅供應京師及各省錢局鑄幣需要,每年征用烏蒙馬承擔銅運常達二三萬匹。時人有詩記其事。詩云:“天府頻年鼓鑄多,銅鉛擁載歷關河。鈴聲鏜鎝攪清夢,恍聽燕山走駱駝。”
烏蒙馬中的佼佼者,能與“烏孫”、“汗血”等所謂“天馬”比肩而立。但要培養出優秀的烏蒙馬,需要的不僅是時間、耐心和精力,更需要大氣和一種非罪的殘酷。
《昭通志稿》記載烏蒙馬的培訓過程,頗有意味。馬駒出生,先要照顧好“產婦”,要確保充分的營養,隨時清潔“產婦臥室”,使產后的母馬能盡快恢復強健,使馬駒秉承的先天之氣能及時得到后天的培補。馬駒長到3月,就其體形、骨骼,關節、蹄掌、反應作綜合評價,“擇質之佳者而教之”。教的方法極為嚴格,近于殘酷。先把母馬系于懸崖之巔,馬駒系在崖下,不給飲食,讓其饑渴。饑渴難耐的馬駒渴望母乳而不得,始則焦躁,繼則萎靡。待饑渴難耐的馬駒確實無法忍受了,解開羈絆的繩索,馬駒初還有幾分膽怯,隨后便朝懸崖之巔的母馬奔去,“奮蹄奔踔而直上,不知其為峻也”。再把母馬和馬駒的位置交換,“系其母于千仞之下而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馳之,則狂奔沖逸而逕下,亦不知其為險也”。同樣的訓練要選擇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氣候條件反復多次,且不斷加大訓練強度、難度。在這個過程中,馬駒或畏葸、或傷殘,不堪造就,則自然淘汰。能經受住考驗的,“其膽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既成,猶復絆其踵而曳之,以齊全是,所投無不如意。而后馳驟之、盤旋之,上巉崖若培階,履羊腸若康莊,而軼類超群也。”如此培養、篩選出來的烏蒙馬豈有不“神”之理?

△ 烏蒙磅礴 攝影/王連生

▽ 火把節活動 攝影/王連生
“不求伯樂之顧,不假王良之工。”烏蒙馬晦以養德,馱載著烏蒙大地的盛衰興亡無怨無悔地走了幾千年,仍在無怨無悔地走著,烏蒙馬有屬于自己的歷史。
金沙江曾在這里斷流
自白鶴灘溯金沙江沿巧蒙公路南行50公里,有一去處現稱石膏地。蜿蜒北流的金沙江,到這里莫名其妙地拐了一個彎,江流進逼東岸,讓出西岸江灘上一片斷巖巨石堆疊而成的崗丘。東岸臨江處,絕壁如削,高千仞,長約百米,仿佛被巨斧將山體一劈兩半,絕壁凌空斷面上寸草不生,但依稀仍可見到挫裂的痕跡。江西岸屬四川會東縣小田壩村,那片巨石堆壘的崗丘卻與周圍環境極不協調,巖塊的色澤、紋理、質地卻與東岸絕壁毫無二致,當地人把這一多少有些奇怪的景象稱為“云南搬四川”。
這地方,舊時地名標記“黑巖子”,曾經是金沙江沿岸地區交通往來的重要通道,是著名的古渡口。史載: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五月渡瀘,深入不毛”,這里是大軍南渡的主要渡口。東晉末,寧州刺史王遜大敗成漢李驤的“堂瑯之戰”在這里落幕,“李驤軍赴瀘水死者千余人”。清同治二年春,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所部從這里渡江北上入川,船只不足,以篾纜橫牽系于兩岸,上鋪木板以為浮橋,“因人馬過多,秩序紊亂,過者僅及其半而浮橋遂斷,人馬溺死江中者不知凡幾。其后續部隊,有鑒于浮橋誤事,乃易于浮筏,失事溺斃者仍復不少。”又過了十余年,一場突發的地質災害徹底改變了黑巖子的面貌,“云南搬四川”,從此再也見不到曾經繁忙的古渡存在的痕跡。
民國《巧家縣志稿》援引《東川府志》記:光緒六年“三月初九日,巧家廳石膏地山崩。先是于更靜后忽吼聲如雷,夜半,山頂劈開,崩于對岸,四川界小田壩平地成丘,壓斃村民數十人。金沙江斷流,逆溢百余里,三日始行沖開,仍歸故道。”所幸,金沙江山高谷深,雖江流阻斷三日,逆溢百里,復又潰決,尚未造成上下游大的洪災。
四川小田壩村不幸而橫遭劫難,好端端一個村寨絕大部分被掩埋在亂石堆下。村中有易姓,是個大姓,30余口人亦無一幸免。災后30年,村民中有幸而未死者,集資捐工,在村寨舊址的亂石堆上清理出一方平地,修墓、建廟,以供祭奠。廟側立一碑,書刻《建修廟序》,序文說:“嘗聞,官清司吏瘦,神靈廟祝肥。如我小田壩……因光緒六年二月初六日,滇山崩倒過江,阻斷江水三天兩夜,壓絕數十家,易姓亦絕。……自此古墓下村一概被壓,慘不勝言……大清宣統庚戌年孟春中皖日立。”——碑序與志書所記有幾點差異:一是時間。據案冊記錄災情呈報文書,山崩發生在三月初九日,碑序記為二月初六日,或記憶有誤;二是傷亡。《縣志》記“壓斃村民數十人,”碑序言“壓絕數十家”。考慮建廟立碑者為死難者親屬、后裔,所言也許比志書所記更為準確。
“云南搬四川”遺址、碑序至今猶存,是長江災害史、地方災害史難得的實證資料。

△ 金沙江支流小江兩岸的農田 攝影/黃正平

△云南東川境內的小江,兩岸環境脆弱,每到夏季泥石流頻發。 攝影/黃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