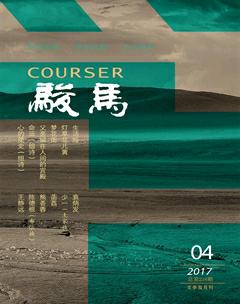燈草花兒黃
少一(土家族)
一
在老家當民辦教師頭一年,我第一次向女孩子求婚。陪我去求婚的伴郎是表弟康兒。
康兒是我大姑姑家的小兒子,小我兩歲。我那年二十歲,他十八歲。別看他年齡小,卻比我早懂事,尤其是在想女人方面比我厲害許多。每次遇到他,說不上三句半話,他就和我討論起女孩子的話題。他會說,某某家的大姑娘長得如何水靈聰惠,看一眼讓人過目不忘神魂顛倒;某某家的幺姑娘對他有那點意思,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等等等等。他甚至還要我?guī)退麑戇^求愛信,求愛信的內(nèi)容太文化了不行,他喜歡來點肉麻的詞句,搞得我都不好意思。而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他的臉皮簡直比牛皮還厚。
有件事情我一直揣心里,現(xiàn)在想起來都有些后怕。有段時間,康兒天天學唱《燈草花兒黃》,一學就學到深夜。那是一首表達土家兒女相思之情的民歌,開頭幾句我還記起來:
燈草(那個)花兒黃(哦),
聽我開言(啦)唱。
唱的(那個)情妹兒(呀),
想呀想情郎……
康兒睡在他家吊腳樓上,樓下關(guān)著家里那頭黑犍牛。白天干農(nóng)活很辛苦,可夜里洗完澡爬上床,他就急不可耐地把蚊帳撩開,就著煤油燈(那時候,我們老家還沒通電)閃爍不定的光亮開始哼唱情歌。他唱歌很走心,瞄一眼手抄本上的詞兒,然后閉著眼睛吟唱。唱兩句,覺得不踏實,又啟開疲憊的眼瞼,湊近本子對詞兒。這么唱歌,一是為了熟記歌詞,二是讓自己沉浸到歌聲的情調(diào)中去,半是練歌,半是享受,那情景真是受用——樓下牛欄里的犍牛在不停反芻,脖頸上的銅鈴激越地“丁當”個不停,像是在為夜歌者敲打著節(jié)奏。月光從木窗里漫進來,瀉在床邊木枕板上。有來歷不明的風時輕時重,把一盞如豆的燈光搖曳得醉漢似的。于是,歌聲里都似乎飄蕩出酒香,聽得出東倒西歪的節(jié)奏。有天深夜,康兒唱著唱著,瞌睡蟲把他拿下了。他腦袋一歪,手松開,手抄本掉到枕板上,同時打落那盞用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燈。煤油灑在蚊帳和棉絮上,燈捻子把煤油點燃,火苗“噗”一聲騰起來。睡夢中的表弟被“烤”醒后慌亂撲打,在付出滿手的燎泡之后,一場火災(zāi)被撲滅在萌芽狀態(tài)。雖說蚊帳和棉絮部分受損,但比起整棟木房子付之一炬的嚴重來,這個后果是值得慶幸的。第二天,他把手抄本轉(zhuǎn)給我,托我替他秘密收藏。大姑姑、大姑父最終追查失敗,手抄本得以幸存下來。
那時候,雖說我的身體已經(jīng)發(fā)育得完全成熟,來自生命本能的某些欲望偶爾會在心里像野草一樣瘋長,但我都能理性地抑制自己的情緒,不讓青春氣息洪水泛濫。現(xiàn)在想起來,原因無外乎兩個,一是因為家貧——一個貧窮家庭的男孩子哪來資格向人家姑娘求婚?二是因為害羞——讀書人對待男女婚事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好像非得玩出點“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的浪漫情調(diào)才行。表弟康兒呢?只讀過小學三年級,他不必顧忌那些只屬于讀書人的廉恥,加上家庭條件過得去,所以,雖說沒到弱冠之年,可他在娶媳婦的問題上已經(jīng)相當成年了。
說起來,我那次心血來潮膽敢去求婚,受他的負面影響不小。
二
我去求婚的女孩叫惠。她比我大歲數(shù),我喊她惠姐,到底大多少,至今也是個謎。不過,可以肯定,她不會大很多,應(yīng)該不超過三歲。我當時之所以愿意去求婚,是相信那句老得掉渣的話:女大三,抱金磚。我媽就比我爸大三歲,他們一輩子雖說連金磚的影子也沒見著,但日子還是油鹽醬醋地活過來了。
怎么說呢?惠姐也是我表姐,只是我們之間沒有血緣關(guān)系。我爸爸和惠姐的爸爸曾經(jīng)同在一所中學傳道授業(yè)解惑,惠姐的媽媽到學校探親,和我爸談得很投緣,后來他們義結(jié)金蘭。幾十年過去,我們兩家往來密切勝同血族。在我兒時的記憶里,惠姐每年都要到我家弄糧食,度過那些可怕的饑荒。可見,她的家境并不怎么好。
惠姐住在雁池鄉(xiāng),離我家將近二十公里路程,到她家去要翻過一座名叫西山埡的高山,走路得花小半天。那時候,雖說通了簡易公路,但每天只有一趟班車開往縣城,花錢還不一定能買到座位,坐車成了一件既奢侈又受罪的事情。所以,我每次去惠姐家都是坐兩條腿的“11”路車。
小時候,每逢放了暑假,我是要到惠姐家玩一些時間的。天剛麻麻亮動身,等太陽最毒辣的時候,我就到了。惠姐家有兩個表弟,是我最好的玩伴。尤其是她家屋門口那條竹溪河,水流不急,水溫不涼,是好季節(jié)里游泳的好場所。對我這個山里長大的旱鴨子來說,是求之不得了。惠姐丟書早,幫助家里做家務(wù),洗衣服、弄飯、喂豬、收拾屋子,有時還種菜、上山砍柴。我和兩表弟都貪水,像娃娃魚一樣成天泡在河里,不到吃飯的時候喊不回去。半午時,惠姐也會來到我們洗澡的河邊洗衣服。惠姐洗衣服洗累了,有時會伸腰朝我們這邊張望。等她把衣服洗完了,就揮舞著棒槌對我們喊:“把短褲脫下來,我給你們搓一把。”說起來不怕你笑話,那時候,我和表弟每人都只有一條短褲,一件汗背心。下河洗澡時,把汗背心脫在家里,光著上身只穿短褲子下水。我們這算好的,能有一套夏裝很不錯了。我記得表弟隔壁的張氏三兄弟只有一條短褲,誰出門誰穿,整個夏天基本上光屁股,窩在家里輕易不敢出門。惠姐讓我們脫褲子,我們就脫褲子。我和表弟狗刨到惠姐洗衣服的河邊,當她的面不知羞恥地把短褲脫下來裹著水撂過去,砸沒砸著她也不管,光著腚嘻嘻哈哈游跑了。我從水里遠遠地回頭看惠姐,卻不知她正好也在看我。我倆的目光撞在一起,短暫地糾纏了一下。我發(fā)現(xiàn)惠姐的腦袋馬上勾下去,一只手臂抬起來掩住大半邊臉,從臂彎里露出的嘴唇正抿著偷笑,也不知道她笑什么。笑完了,惠姐就把我們的短褲用茶枯擦擦,用手搓搓,然后用棒槌捶捶,再清洗擰干,曝曬在河卵石上。過不了一個時辰,我們又可以穿上干凈的短褲回家吃飯了。這時候,惠姐端起洗衣盆,長辮子往背后一甩,裊裊婷婷地立在河邊。她好像很累,一只手捶打著自己的腰,手搭涼棚,朝我們打望一眼,意思是提醒我們早點回家吃午飯,然后就上了河岸,領(lǐng)著自己的影子走了。
人的記憶真是個奇怪的東西!
關(guān)于惠姐,我記憶里恒定守一的印象永遠都是她蹲在河邊洗衣服和洗完衣服捶打腰身離開河岸的情景。去求婚之前是這樣,現(xiàn)在想起來還是這樣。
三
總的來說,我和惠姐的家都在山區(qū)。只不過,我老家的山比惠姐家的更大更高。相對而言,她家離坪區(qū)近一點。坪區(qū)水田多,產(chǎn)稻谷,可以吃上大米飯。而我們老家多山地,只出產(chǎn)雜糧,活兒苦,人很累,產(chǎn)量低。所以,一般的父母只把女兒往坪里嫁,很少有往山里嫁的,哪怕坪里的女婿人才差點也愿意。農(nóng)村人講個實在,過日子是一輩子的事情,人才好看又不能當飯吃,要那些高顏值干什么!于是,在我們老家就有了“寧嫁十里坪不嫁半步山”的說法。如此說來,我向惠姐求婚就有些自不量力了。坪區(qū)女孩子連山上望都不想望一眼,能指望惠姐遠嫁給三十公里外的我嗎?你如果這樣想就錯了。我自以為向惠姐求婚還是有蠻多優(yōu)勢的。首先我們是親戚,是親戚就都要給面子是不是?更何況我們從小一起玩耍彼此熟悉,愛情也是要講點感情基礎(chǔ)的,我們有底子。
還有,惠姐小學肄業(yè),算半個文盲。我高中畢業(yè)后,當了孩子王,當時正雄心勃勃地參加自考,對未來的前途充滿信心。可以這樣說,只要不出現(xiàn)太大的意外,我跳出農(nóng)門拿一份日不曬雨不淋的工資是沒問題的。而惠姐呢,注定只有當村婦的命。等我以后出息了,她跟著我算是夫榮妻貴。她一個農(nóng)村弱女子,能有這樣的歸宿夫復何求?另外,惠姐還有年齡上的硬傷。她比我大,大一天也是大,更何況她還大了幾歲。我不計較這點已經(jīng)夠?qū)掑读耍€有什么話說!
其實,在真正作出求婚決定前,我思想上很是斗爭了一番。我本想捱幾年,等自己條件好起來后,談一個吃商品糧的女孩子,這樣才門戶相對。可是,我父母年紀大了,家里急需要一個能當家頂事的人,以減輕二老的負擔,幫我撐持一把,助我事業(yè)有成。我在腦海里把周邊知根知底的女孩子都過濾了一遍,屬意的真還難找。有一天,母親突然提到惠姐,說成年后的惠姐嘴有一張,手有一雙,走路一陣風,身體強壯能打得死老虎,在農(nóng)村是把好手,誰家要是娶了她做媳婦,一定會有好福氣。成年后,我為自己的生活忙忙碌碌,好些年沒去惠姐家,對她的情況知之甚少。母親不提到惠姐,我還真把她給忘了。母親的話本是無意的,卻讓我眼前一亮,動了向惠姐求婚的念頭。我想,惠姐文化水平低一點無關(guān)緊要,只要她勤勞善良,善待父母,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就行了。男主外,女主內(nèi),農(nóng)村許多“半邊戶”的小日子過得都不錯,我們見得多。或許,對我來說,這樣的選擇是一個黃金組合。
決定向惠姐求婚的事,我在心里打定主意后并沒告訴父母。按說,這是大事,應(yīng)該征求大人的意見。可是,我不想讓父母親為難和失望。
這話怎么說呢?關(guān)于我的婚姻問題,父母心里早就各自打著如意算盤。母親有意要把舅舅的二女兒當兒媳婦娶過來,每次見到她和舅舅兄妹倆在一起嘰嘰咕咕地沒完沒了,我就疑心他們是在商量這件事。父親也已經(jīng)默許了大姑姑,準備把他的外甥女(也就是康兒的二姐)許配給我。當然,這主要是大姑姑的意思。父母親之所以一廂情愿地打這種歪主意,理由很簡單:親戚開親,親上加親。他們卻忽視了事情的另一個走向——弄不好就會親人變仇人,甚至比仇人還仇人。如果只是父母們這般瞎操心,我倒也沒什么,問題是兩位表妹都是人來瘋,表示愿意嫁給我這個表哥。這簡直要命!不談婚姻,我們表兄妹之間本來相處很好,關(guān)系融洽。可自從把話挑明之后,我心里總感覺別別扭扭疙疙瘩瘩的,就刻意和她倆保持距離,一直到現(xiàn)在,那種無形的隔膜似乎還未徹底消弭。《婚姻法》不允許近親結(jié)婚。從科學上講,有血緣關(guān)系的人結(jié)婚不能優(yōu)生,甚至影響幾代人。我們身邊就有這樣可怕的例子。我的父母親當然不希望他們的子嗣出現(xiàn)任何意外,所以,現(xiàn)實既然擊垮了他們心中那些虛妄的幻想,我也不想再去觸碰那根敏感的神經(jīng)。
我把求婚的事情想得很簡單,以為把話說出來就完了,同意不同意,就是一句話的事。我當時之所以躊躇滿志,完全出于對事情結(jié)果的幼稚預期,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盲目樂觀,認為這是件很有把握的事情,就跟到商店買牙膏買鹽差不多。可到了準備動身的時候,我心里卻空落落的,自己一個人去,連個傳話的人都沒有,萬一碰到尷尬怎么辦?不行,還得帶個人去。
帶誰呢?我就想到了康兒,我認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
四
沒想到,我找康兒,康兒也正要找我。
見了面,我還沒說出事由,他先開口:“表哥,你跟我做伴出一趟遠門好不好?”
我問他:“出好遠的門嗎?”
他說:“去惠姐家。”
我們這些山里長大的人活動的范圍是有限的,平時最遠的行程無非就是上街趕集,或者就近走親戚,超過十公里就算遠行了。所以,他說去惠姐家是出一趟遠門有點搞笑,但半點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他竟然也要去向惠姐求婚!
我的腦袋里像有人突然扔進一顆炸彈,“轟”地一聲,驚得頭發(fā)都倒豎起來。但我畢竟胸有城府,心里沉得住氣。我沒把自己內(nèi)心的慌亂表露出來,也沒把準備向惠姐求婚的想法告訴他。我說出的話是這樣的:“老表,你在發(fā)癲是不是?惠姐比我都大,比你要大好幾歲,她當我的媳婦還差不多,做你的美夢去吧。”
康兒說:“你有媳婦,我沒媳婦。你別跟我爭媳婦好不好?”
我比較愚蠢地說:“我哪來的媳婦?”
“我二姐就是你媳婦。”
聽他這話,我心里會煩死。我沒好氣:“誰答應(yīng)讓你二姐做我媳婦?”
他翻我一眼,銅銅鐵鐵地說:“她給你做的繡花鞋墊我都看見了,別以為我不知道。”
我不想和他爭論他二姐的事。我說:“我不會和你爭惠姐的,你不要誤會。”
“那你答應(yīng)給我做伴啦?”
我心里想,這不正好來個歪打正著?打死我都不相信,惠姐會答應(yīng)嫁給康兒。康兒除了有一身好力氣外別無所長,要文化沒文化,要人才沒人才,還比惠姐小四五歲,惠姐怎么會同意這種姐弟戀的婚姻呢?也好吧,等你康兒碰了一鼻子灰后,我再向惠姐提出求婚。我自信地認為,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對比之下,我的優(yōu)勢明顯,惠姐肯定會答應(yīng)我的。到時候,看誰給誰做伴,氣死你!
康兒是怎么打上惠姐主意的呢?后來我想明白了,禍根還是我自己惹出來的。有年秋天,惠姐到我家來撿野茶籽。所謂茶籽就是油茶果,山上樹林中那些沒有分到戶的油茶樹就算野茶樹,野茶樹上結(jié)的油茶果當然就是野茶籽。野茶籽撿回來可以榨油吃,榨出的茶油又香又環(huán)保,吃了不上火。惠姐那里不長茶樹,她家一年四季吃菜油,當然吃不到茶油。于是,寒露一過,惠姐就到我家撿野茶籽來了。惠姐對我們這地方不熟悉,山里有蛇蟲野物,她撿野茶籽需要人帶路才安全。那時候,我比較忙,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瞎忙些什么,沒時間給惠姐做伴,就把她交給表弟康兒。康兒自小跟他爹學打獵,對遠遠近近的山林了如指掌,加上他鉆山爬樹像猿猴一樣敏捷,又不怕蛇蝎和蟲子,這樣的差事交給他最合適不過了。那幾天,惠姐撿了很多野茶籽,每天早上出去,天黑前回來,收獲多多,歌兒不離口。她唱得最多的是《燈草花兒黃》,她好像就只會唱那一支歌。惠姐回家后,我發(fā)現(xiàn)康兒也就迷上了《燈草花兒黃》。看來,就是那幾天撿野茶籽把康兒的心撿野了。說不定,他那個手抄本就是根據(jù)惠姐的口述整理出來的孤本,怪不得他把手抄本看得跟命一樣寶貝。
后來有一次,康兒當著我的面提出過一個問題:“表哥,你認為惠姐人才怎么樣?”
我從來沒想過這問題,自然回答不上來。但我還是感到奇怪:“你問這話什么意思?”
康兒說:“沒什么意思,就隨便問問。”
看來,他早盯上惠姐了,他絕對不是隨便問問,他是有心的。
康兒見我答應(yīng)給他做伴去求婚,就征求我意見:“你認為這事有幾成把握?”
我陰險地說:“你想聽真話還是聽假話?”
他說:“當然聽真話,假話說出來卵用。”
我說:“不是表哥要打擊你,我認為你半點把握都沒有。”
“為什么啊?”
我想了半天,然后朝天上指指:“惠姐是一只天鵝……”我不忍心把后面的話說下去,讓他自己去想。
康兒一點都不覺得自卑和受辱。他對我說:“表哥,我邀你做伴,就是因為你有水平,到時候多給我打圓場,把好事促成了,你就當我們的媒人,我給你買牛皮鞋穿。”
我心里說:“呸,放你的狗屁!誰稀罕你的皮鞋,你還是留著自己穿吧。”
五
人逢喜事精神爽,走路的勁頭子也很足。不到上午十一點鐘,我和康兒就到了惠姐家。
我們土家人有規(guī)矩,第一次上門求婚,不能光腳甩手,多少是要帶點禮興的。康兒帶的進門禮是用酒瓶子灌的兩瓶茶油,他用一個半舊的網(wǎng)絲袋提著,網(wǎng)絲袋的一只角上還開了線。撿野茶籽可能是他對惠姐萌生感情的導火索,所以,康兒帶茶油對惠姐或許有一種暗示和寓意,希望能喚起她對某些往事的回憶。就憑這一點分析,我這個老表雖然文化不高,但情商還是不低的。為了和康兒顯出檔次上的區(qū)別,我在惠姐家對門的路邊經(jīng)銷店買了一條“洞庭”牌香煙和一瓶“德山大曲”酒拎著。惠姐的爸爸早幾年害肺病走了,這些東西他享用不上。但惠姐的媽媽是個女漢子,她是我們山區(qū)聞名遐邇的打鼓匠,長期在孝家坐夜打書,煙酒都不亞于男人。為了不引起康兒的懷疑,我的禮品是沖著未來的丈母娘買的,表面看起來和惠姐一毛錢關(guān)系都沒有。
不年不節(jié),對我們的突然造訪,惠姐一家人顯然莫名其妙,也準備不足。康兒心窩子太淺,人家還沒問起,他的屁股也剛剛坐熱,就結(jié)結(jié)巴巴地將來意和盤托出。聽說上門求婚,惠姐“噗嗤”一聲笑出來。她說:“康老表,你搞明白沒有,我和你大姐是老庚呢。”她這話等于是當眾摑康兒的耳光。
康兒還不知趣,傻逼說:“不要緊的,俗話說‘女大三抱金磚,大幾歲不要緊。”
惠姐說:“可是,我聽說‘寧可男大七,不可女大一,這樣的婚姻不會幸福。”
我和康兒都是頭一次聽到這說法,也不知是不是惠姐臨時瞎編的。她的話一出口,康兒就沒轍了。康兒朝我翻了一眼,意思是要我?guī)退鈬N页尚牡戎此暮脩颍斎徊粫退N壹傺b把頭扭向窗外,欣賞水井邊的那棵梨樹。高高的梨樹上正好有一對夫妻鳥在枝間跳躍啁啾,快活得很。它們恰到好處地配合著我的幸災(zāi)樂禍。
惠姐又說:“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我家豬娘生了一個一只眼睛的小狗,也不知道是禍是福,兩老表幫我解解吧?”
我想到的全是“瞎了你的狗眼、做你的美夢去吧、你就是個怪種”之類的咒語。
康兒附和著說:“這個夢是有點奇怪。”
見康兒腦殼有點受潮,惠姐又說:“康老表,真不好意思,你哥哥要是沒結(jié)婚就好了。”說完這句話,她不由自主地朝我脧了一眼,臉上紅了一下。然后,她就進廚房弄飯去了,再沒出來。
說實話,幾年不見,惠姐比以前長得更飽滿了。她的臉很光潔,皮膚細嫩,圓圓的鼻頭像一個半透明的小蘑菇長在正中,鼻下的人中連著薄薄的上唇,上面浮著一層茸毛。她的頭發(fā)黑油油,梳得根根直,一件水紅色的襯衣掐了腰,屁股和胸的輪廓顯得很突出。不知怎么,看見惠姐現(xiàn)在這副美貌,我開始氣短起來,感覺心里像遭遇針刺,有人放掉我不少的氣。尤其是康兒剛才遭當頭一棒,連我都好像頭上起了血腫,生疼。我不知道自己求婚的戲還能不能繼續(xù)演下去。
康兒肯定恨死我了。他一只腳在地上跐來跐去,跐出一地的土灰來。姑媽到底是見過世面的,她對擺放在桌面上的禮品掃去一眼,然后安慰康兒說:“賢侄啊,這個,婚姻呢,一家養(yǎng)女百家求嘛。不過,兒女不送請,婚姻要講自愿,這是政策。你不要急,慢慢來,等我在一邊好好跟你惠姐做做思想工作。其實呢,你這個孩子還是很不錯的,只是你們那里的自然條件……不過呢,條件也不是主要問題,事在人為嘛……”姑媽一分為二一番后,招呼我說:“賢侄,你跟我來,姑媽有話問你。”
我跟姑媽進了歇房。很顯然,姑媽是要避開康兒,單獨向我摸底。我起身的時候,康兒又朝我翻了一眼,他傳遞的信息我懂。
在一邊,姑媽完全是另外一副口氣。她對我說:“這是不可能的,惠兒能嫁給康兒,除非竹溪河的水倒流了。”
我馬上撇清說:“我知道這樁婚事不靠譜,我一不來二不來的,是他硬要拉我做伴。我也是礙于情面推不脫,老表關(guān)系嘛。”
姑媽表示理解:“這事當然不怪你,是康兒發(fā)神經(jīng)。”最后,姑媽要我給康兒委婉轉(zhuǎn)達,求婚的事免談,再不要提了。聽姑媽的意思,是在下逐客令。我說:“姑媽放心,吃了中飯,我就帶他回去。”這話一說完,我心里馬上后悔極了。我也是來求婚的,我居然忘記使命,把自己的后門堵上。我連求婚的意思都沒表達,就這么毫無成果地回去,太不值了。都怪康兒,他不應(yīng)該性急,如果熬到晚上,等氣氛稍微好些后再提求婚之事,或許不至于弄成這樣。至少,我們在時間上會充裕一些。現(xiàn)在,連回旋的余地都沒有了。他真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家伙。
姑媽果然說:“如果不太忙的話,還是住一夜再走。”
誰能不忙呢,我們不忙人家可忙啊。姑媽的話是在攆人。我“嗯”了一聲。
“你都好幾年沒來姑媽家了,現(xiàn)在當老師,工作還好吧?”見我情緒落寞,姑媽開始轉(zhuǎn)移話題。
我又“嗯”了一聲。
這時,姑媽上上下下地看了看我,慨嘆道:“哎,這世上有多少事陰差陽錯啊。”
幸好姑媽最后來這么一句語焉不詳?shù)脑挘蝗唬艺鏇]勇氣開口求婚。我說:“姑媽,我這次來,其實也是來向惠姐求婚的……”
姑媽瞪大眼睛看著我,然后說:“寶呀,你怎么先不說?”她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把一口痰利索地吐了出去。“是啊,賢侄也長大了,是該談婚事了。你看,怎么不早說呢?這事弄的……”
我知道,姑媽感到為難。我和康兒都是她的侄輩,手背手心都是肉,得罪哪個也不好。現(xiàn)在,我倆求婚像組團,當面鼓對面鑼的,叫她如何是好?
姑媽思忖片刻,拍著我的肩膀說:“賢侄啊,今天千萬別回去,這么遠來一趟不容易。有些事情,我單獨跟惠兒說說。你們兄妹從小就熟悉,我認為有感情基礎(chǔ)……”我發(fā)現(xiàn),姑媽說這些話的時候,盡量在使用書面語言,她是不是忽然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位民辦老師呢?
聽說留我們住一夜再回去,康兒興奮不已。他以為自己有戲,當即表示下午要幫姑媽家去山上背柴。他真是個大傻瓜!
那天去求婚,我特意買了一雙新涼鞋穿上。結(jié)果,走遠路倒腳,打出兩個血泡,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怎么干得動活?康兒提出幫姑媽家勞動,等于是給我出了道難題。
吃完午飯,姑媽對兩個表弟說:“你們和康老表去把山上的柴背回來,姐姐在家里準備夜飯,大表哥腳上打了血泡不能跑動,需要休息一下。”
對姑媽這種別有用心的安排我心知肚明,只有康兒蒙在鼓里。他樂呵呵地隨兩個表弟背柴去了,出門時還情不自禁地哼唱那首《燈草花兒黃》……
六
關(guān)于那天下午我和惠姐單獨相處的諸多細節(jié)我記不起來了。大致的情況是她弄飯,我?guī)蛷N。記得我們在一個盆子里擇洗蘿卜菜,盆子小,菜又多,兩雙手時不時撞到一起。那時候,我有賊心沒賊膽,本來有許多機會可以抓住她的手,渾水摸魚表達一下親昵,但我蠢得跟豬一樣,每次碰到她的手,就像碰到螞蟥立馬甩開。我那些做賊心虛的動作甚至讓惠姐暗自好笑。她笑起來的時候抿著嘴,兩邊的酒窩窩惹人喜愛。我從心底里承認,我是真心喜歡上惠姐了。
她炒菜的時候,我坐在灶門口添柴燒火。我沒話找話,提到《燈草花兒黃》那首情歌。我說:“惠姐,你唱《燈草花兒黃》真好聽,能不能唱幾句我聽聽?”
惠姐一點也不羞怯。她說:“好呀,那是女孩子唱給情哥聽的,你愿意聽嗎?”
我對著她點頭,并熱切地望著她。我想,我的目光里所傳遞出的溫柔和婉約足以化掉世界上任何一個女人。
惠姐說:“我有一個條件。”
“唱吧。”我回了句繞口令的話,“在我這里,你所有的條件都是無條件。”
“我只唱給一個人聽,誰聽了我的歌,他就要娶我。”
我假裝醋意說:“康兒聽過你的歌,他是不是應(yīng)該娶你?”
惠姐遲疑有頃,解釋道:“那時候不懂事,唱著玩,現(xiàn)在才當真。”
有一點毋庸置疑,姑媽肯定把我求婚的意思對惠姐說了。她能直截了當這么說,等于就是應(yīng)允了我的求婚。當時,我正用膝蓋頂住一段干木柴。它太長了,直接送進去,灶洞里裝不下,必須折成兩段。我使出一把暗力,只聽“啪”的一響,干柴斷成兩節(jié),塞進灶孔,馬上燃燒起來。
接下來,惠姐開了歌頭。她唱歌的時候,我也濫竽充數(shù)跟著唱,但記不住詞,一首好好的情歌被我唱得歪七扭八。幾個回合之后,我們之間的對話不再遮遮掩掩。我把心中的疑問說出來,尋求她的解答。我的第一個疑問是女孩子到了十七八歲,上門提親的都要踩破門檻,而像惠姐這樣能干又漂亮的人,難道就沒人上門求婚嗎?按照我們當?shù)氐牧曀祝粋€女孩子如果要想改變婚約的話,下家就要承擔退婚費用。我擔心自己會碰上那種扯皮事。惠姐告訴我,以前上門向她求婚的人很多,但都被姑媽一概拒之門外。姑媽說,二十五歲之前,她女兒不嫁人。人家男方一聽掉頭就走。人家等著娶媳婦才上門求婚,等惠姐年滿二十五歲,男方都小三十了,如果出現(xiàn)其他變故,豈不是讓你給耽誤青春了嗎?所以,你耗得起人家耗不起。姑媽的條件傳開后,媒人再不敢登惠姐家的門。惠姐也就剩下了。
“姑媽為什么要這樣呢?”
“她是嫌我在這個家的工還沒做夠,她要把我的油榨干了才肯放手。”惠姐幽幽地說著。她的目光投向虛空,就像是在講述一個和她并不相干的故事。她手里的鍋鏟停止炒動,鍋里“嗞嗞”冒出藍煙,直到聞出一股刺鼻的辣味,她才慌忙往鍋里淋一調(diào)羹清油。
姑媽家條件不好。姑父走了之后,兩個大點的女兒都嫁了出去,她要拉扯著惠姐和兩個表弟。惠姐勤勞能干,幫姑媽頂起半邊天,她自然不想讓身邊這么一個好幫手輕易出嫁。
“其實,一個女人,到娘家和婆家都一樣,在哪里都是做工,一輩子就是伺候人。”惠姐的話闡釋著一個客觀存在的哲理,一個女人對自己命運無法把握的虛妄與無奈的哲理。
我的心被刺痛了,就像一把鈍刀割裂著良心。我知道這種痛感來自于我求婚的初心。我不是因為想早日替父母減輕負擔而需要一個女人伸出肩膀嗎?我不是想能有一個女人替我遮風擋雨成就個人的所謂輝煌嗎?與惠姐比,我感到自己是那樣渺小,她的話讓我惴惴不安無地自容。
我從一種低迷的情緒里走出來。我需要知道如果我和惠姐能成的話,她能不能很快嫁給我。
我說:“惠姐,我正式向你求婚,你會同意嗎?”
惠姐點著頭:“問二姐。”
我說:“你答應(yīng)了,姑媽能讓我們很快結(jié)婚嗎?”
惠姐還是那句話:“我隨便,問二姐。”
我明白了。惠姐家的事情都由她二姐做主。二姐夫有彈匠手藝,常年帶三四個徒弟串鄉(xiāng)走戶招攬生意,一年收入不少。二姐家庭富裕,也就掌控著對娘家的影響力和話語權(quán)。可是,我對二表姐知根知底,她也沒讀幾天書,自小長大連縣城都沒進過,未必會有多大的見識。把一個家庭以及每個家庭成員的命運全交到這樣的女人手里,是不是有點滑稽可笑?
我半開玩笑說:“凡事問二姐,你們一家人都成提線木偶了。”
惠姐無奈地笑笑:“我媽只相信二姐和二姐夫。”可能怕我失望,打退堂鼓,她又補充說:“二姐和二姐夫都喜歡你。”說完,她像突然想起來似的,從歇房抽屜里拿出一雙塑封的絲光面料襪子要送給我。我客氣地推辭。惠姐緊著臉說:“快收起來,別讓康老表看見了。二姐給我兩雙,只剩這一雙了,沒多的。”她最后的解釋笨拙而多余。
我說了句總結(jié)性的話:“二姐和二姐夫喜歡我沒用,我喜歡的人是你。”
惠姐臉上頓時落滿煙霞,有笑從酒窩里往外飛。
七
這天的晚宴比中午豐盛多了,光葷菜就有三個。惠姐殺了一只正在生蛋的土雞,熬了一只臘豬蹄子,還燉了一缽黃骨魚,煎了韭菜雞蛋,小菜也炒了四五個。
吃飯的時候,我本來挨著姑媽坐,可不知怎么換來換去,后來身邊換成了惠姐。下午,康兒大顯身手,帶著兩個表弟把山上那些木柴全部背回了家,一家人很高興,豐盛的晚宴帶著隆重的犒勞意味。姑媽竟然開了一瓶酒,自己滿上一杯,給康兒也斟上。康兒樂呵著接受了姑媽的敬酒。姑媽也給我斟過酒,但被我拒絕了。惠姐把缽子里的雞肉用筷子翻了翻,招呼我和康兒搛菜吃。我發(fā)現(xiàn)她把帶著雞大腿的幾塊好肉扒拉到我面前的缽邊,然后在桌下用腿子碰碰我,說:“兩位老表,你們莫講客氣,吃菜。”我領(lǐng)會惠姐的心意后積極響應(yīng),伸出筷子象征性地把一只雞腿夾進碗里埋頭吃。坐我對面的康兒只顧著喝酒,對發(fā)生在眼皮底下的一切渾然不知。
我沒喝酒,其實,我心里醉了。
夜里,我沒和康兒一起睡。他和大表弟被安排到西廂房的舊床上休息,我和小表弟睡新床。種種跡象表明,我的求婚達到目的。這是我第一次求婚,對一個男人來說,這樣的成功令人欣喜,有著刻骨銘心的意義。秋夜深深,我激動得無法入眠,在腳頭表弟的鼾聲里,一遍遍陷入遐想,把屬于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喜悅無限放大。這時候,我聽到房門被輕輕推開的聲音,有一束手電筒的光亮移進來。這么晚,誰來干什么?我的心跳加快了,莫不是……
真不是惠姐。我從躲在手電光后面的暗影里辨識出姑媽的輪廓。她走近床邊,在一把搭放衣服的木椅上坐下,輕聲說:“賢侄啊,我知道你沒睡著。姑媽有話要對你說——”
我欠欠身子,準備坐起來。姑媽指指酣睡中的表弟,一只手按住我的被子,“噓”了一聲。她告訴我,惠姐已經(jīng)答應(yīng)我的求婚,她也表示同意。她說:“你明天先回去,等姑媽的好消息。這件事,我還要跟二姐他們商量一下。不過,你放心,二姐和二姐夫都會同意的,我會說服他們。”
姑媽的意思,商量二姐也就是走程序。
次日早飯后,我和康兒回家。康兒得到的承諾是姑媽掩耳盜鈴的謊言,而我吃下的是一顆定心丸。
回途中,康兒還在自作多情地回憶著在姑媽家受到特殊禮遇的每個細節(jié),當他感到那些熱情似是而非捉摸不定的時候,又不厭其煩地向我求證。他越是這樣,我心里越是糾結(jié)。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個自私卑鄙的小人,康兒是那樣的可憐和無辜。我想,將來我把惠姐娶進門,這一切怎么向他解釋清楚?他會不會在明白真相后鄙視我的為人?我們的親戚關(guān)系會不會從此走向破裂?
管不了那么多。我相信,在情感問題上,世上沒有大度的男人。康老表,我只能在心底里說一聲:“對不起!”
我沒有等來姑媽的好消息。一個月沒有,兩個月沒有,半年也沒有,一年還沒有。這么多“沒有”加在一起,就是一個生硬的不用置疑的結(jié)果,只有白癡還會心存僥幸,做自欺欺人的幻想。在那些漫長的等待里,我像一只面對洶涌河水無法泅渡的狗在岸邊無可奈何地竄來竄去。好多次,我都產(chǎn)生了再去姑媽家一趟的想法。我想當著惠姐的面把話問清楚,她為什么食言,我哪點配不上她?最終,我沒有為自己這個愚蠢的想法付諸行動,所有的原因就是為了守住一個男人那點可憐的虛榮和自尊,這是我最后唯一攥在手里的一張底牌,我不想把它打出去后讓自己落個滿盤皆輸?shù)南聢觥T僬f,我對自己未來的婚姻充滿希望。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這期間,康兒還在不厭其煩地往姑媽家跑。一開始,他邀我伴行,遭拒后就單干。我真為他的癡心不改而點贊,同時也為他的執(zhí)迷不悟而痛心。連我都等不來惠姐的回信,康兒的結(jié)果可想而知。我真想現(xiàn)身說法,讓康兒徹底死了那份心,不要把自己的婚事吊死在一棵樹上。可每次見他興興頭頭的樣子,我都不忍心傷害他,把拱到嘴邊的話咽回去。只在心里替他暗暗著急,回頭吧,兄弟,別瞎折騰把自己耽擱了。
第二年年底,我進了縣城,后來按部就班地結(jié)婚成家、生孩子。其間,我聽到一個天方夜譚的消息,惠姐和康兒結(jié)了婚!而且就是我調(diào)進縣城后第三年的事情。
怎么可能啊,惠姐昏頭了嗎?
可是,我的疑慮最終被一個堅如磐石的事實徹底打消。
有一天,我在縣城商業(yè)步行街逛街時遇到了惠姐的小兄弟,也就是我那小表弟。他買了火車票要去外地打工,時間還有幾個鐘點就散步到步行街,不期然遇上我。我請他到旁邊茶樓里喝茶,我虛與委蛇的熱情里暗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我想知道惠姐拒絕我求婚的真相。
小表弟揭秘說,是二姐和二姐夫最終投了我的反對票。他們的理由現(xiàn)實而荒唐:一對地位懸殊的夫妻沒有幸福可言。他們不忍心看到妹子一輩子低三下四地伺候一個教書匠。與其和我談婚論嫁,還不如讓惠姐嫁給康兒。支撐這種混賬邏輯的理據(jù)就是求婚當天,康兒能賣力地幫著姑媽家背柴,而我卻以腳上打泡為借口躲懶!窺斑見豹,婚前都放不下臭架子,還指望婚后把女人當人看嗎?
昏聵啊。
表弟還告訴我,惠姐開始堅決反對二姐和姑媽的決定,以絕食的方式等待我再次上門求婚,她堅信我對她的愛情,只要等不到消息,我就會義無反顧地再次登門。二姐和姑媽也都猜疑,我如果是真心想和惠姐結(jié)婚,就會執(zhí)著地追求下去。姑媽他們甚至和惠姐打賭,只要我再上門,哪怕就一次,他們就允下這樁頗有爭議的婚事。可我的自作聰明與他們的賭注正好逆向而行,這就更加坐實了二姐他們的斷言,我的求婚缺乏誠意,這樣的婚姻即使成了,也如水月鏡花經(jīng)不住時間的檢驗。與其悔不當初,不如迷途知返。無奈的惠姐被自己的輕信和無知擊得粉粹,對自己為我絕食的行為悔恨得咬牙切齒。恰恰相反,康兒的不懈努力贏得了惠姐家人的肯定,他雖然存在種種不足,但有一顆真誠的心——這種真誠勝過世界上任何海枯石爛的誓言。康兒用自己的笨蛋贏得了一樁美滿姻緣,我成了照亮他婚姻的鏡子。
有一天,我接到康兒的電話,說惠姐因患風濕性關(guān)節(jié)炎住進縣人民醫(yī)院,她的四肢關(guān)節(jié)均已紅腫變形,診斷結(jié)果可能是終身癱瘓。他希望我能去看看她。
走近對號的病房門口時,我聽到有女聲在輕哼那首熟悉的《燈草花兒黃》:
夜里(那個)睡不著(哦),
睡到夢又多;
夢見(那個)哥哥(呀),
調(diào)(呀)調(diào)戲我……
跨進病房,我看到了病懨懨的惠姐。要不是康兒在旁邊護理,我根本就認不出她來。病魔和勞累徹底擊垮了一個形象姣好的女人。惠姐也只五十來歲,可蒼老、憔悴和病態(tài)加在一起,構(gòu)成了一個人破敗不堪的現(xiàn)實。康兒說,惠姐的關(guān)節(jié)炎已到了無法治愈的程度,醫(yī)生明確告知,惠姐的下半輩子只能在輪椅上度過。康兒還說,惠姐的病根是在娘家落下的。從小到大,惠姐都在寒濕環(huán)境里生活,哪怕來了月事,她從來都無法禁忌生冷。一個女人,長期不顧自己的身體,哪能不生病?惠姐面色平靜,用那種很家常的語氣和表達方式與我交談,但我還是看出她竭力在裝,表面的平靜掩飾不住她內(nèi)心世界的荒涼。離開病房時,我把皮包內(nèi)所有的現(xiàn)金全掏出來塞給康兒,希望他能給惠姐買點營養(yǎng)品,補補她千瘡百孔的身體。惠姐吃勁地揮著那只變形的右手向我道別,我的眼眶濕潤了。
走到電梯口,我忽然想,如果惠姐下半輩子真的站不起來,我無論如何要送她一副輪椅才安心。我走轉(zhuǎn)身,想把這個想法告訴他們。我擔心遲一步,他們會另有安排,讓我的愿望落空。
躡腳走到門邊時,我聽到他們夫妻倆在對話。
康兒:“當初,你要是跟了表哥,可能就不會受這份罪,是二姐他們把你害了。”
(下轉(zhuǎn)31頁)(上接24頁)
惠姐:“別這樣說,一切都是命。”
康兒:“你心里肯定后悔。”
惠姐:“從我決定嫁給你那天起,我一天都沒后悔過。你把我照顧得很好,我知足。”
“真的?”
“真的!”
“為什么?”
“我想明白了,哪怕我成了一個癱子,你還會守在我身邊。這一點,只有你做得到,表哥他——做不到。”
……
我實在聽不下去,腦袋內(nèi)“嗡”地一聲,眼前升起一片黑霧。我趕緊伸手扶住電梯,努力定住飄忽的身子……
責任編輯 高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