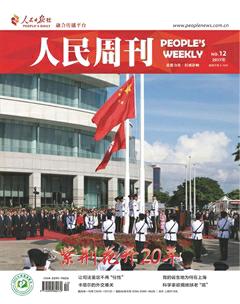廬山高
楊振雩
“廬山高”,實乃人性之高,人文之高。有形的高度,可以測定;無形的高度,則不可以丈量。太史公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廬山多高?似不難知,地理書籍均有標準答案,一千四百七十四米。茫茫九州,突兀高山比比皆是。眾山之中,廬山海拔實不算高。不說珠峰昆侖等西部諸峰,也不說泰山華山等五岳天尊,就連與之毗鄰的幕阜、九嶺山脈,主峰也超過廬山。
然而,古來詩文丹青卻屢屢稱頌“廬山高”,似乎情有獨鐘,是何原因?是因一山據江平地拔起,高入云端,相對高度較為突出?顯然也不是,因為同一緯度的黃山,也比廬山高出許多。
原來,此“高”非彼“高”,廬山高,乃賢者品格高尚之謂。
劉渙,字凝之,江西筠州人,與歐陽修為同榜進士,僅任太子中允和屯田員外郎等卑職,為潁上縣令。
然劉渙“居官有直氣,不屑輒棄去”(陳舜俞《廬山記》)。因事冒犯上司,自請歸田。甫過五十,以屯田員外郎致仕。
劉渙回籍時,途經南康軍星子縣,有感于此地山川秀美,且為隱士陶淵明的故土,遂心生愛樂,定居廬山南麓的落星灣,一住就是四十載,并終老于斯。
劉渙隱居第四年,歐陽修由潁州改知應天府,取道星子特意看望他。為作《廬山高贈劉中允歸南康》詩,以廬岳之高峻狀劉渙之高風: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峨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羨君買田筑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廬山高》一時震撼文壇。司馬光、梅堯臣、蘇軾和曾鞏等,對劉渙氣節都大為仰慕。曾鞏和蘇軾兄弟都親往拜謁。
黃庭堅作《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云:“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起居飲食于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
司馬光欣然為之月旦:“為潁上令,不能屈事上官,年五十棄官,人服其高。歐陽修作《廬山高》以美之。”
劉渙生有二子,劉恕和劉恪,均中進士。長子劉恕,為編史著作郎,秘書丞,協助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他為人正直,因觸怒權貴,以親老為由,放棄京官,“求監南康軍酒稅以就養”。劉恕兒子劉義仲、劉和仲,都是剛直勁節之士。劉渙夫婦之墓,原在星子縣城西郊少府嶺,朱熹任南康知軍時,在墓地附近建“壯節亭”。朱熹并寫有《壯節亭記》,中說:“清名高潔著于當時而聞于后世,暫而輯其遺風者,由是以激懦而律貪。”
明朝,王守仁慨然揮筆書寫歐陽修的《廬山高贈劉中允歸南康》。
七年后,戶部主事冠天輿和九江兵備副使何棐,將王陽明手書鐫刻于九十九盤古道石壁,并于詩壁旁建有一座石牌坊,橫額上刻著王陽明手跡“廬山高”三個大字。歐詩王書,珠聯璧合,嘆為雙絕。
劉渙得歐陽修之識,乃有《廬山高》為之旌表,否則,不過廬山寂寂一老翁。是劉渙之幸,也是廬山之幸。其實,此前此后,可譽為“廬山高”者,賢者輩出,代不乏人,何止劉渙?
三國神醫董奉,隱居廬山山南時,為人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治愈者,只需栽種五株杏樹,輕者植杏一株。如此者十年,郁郁成林,計萬余株。待到杏子成熟,若有買杏者,只需以同量大米交換即可。董奉則用大米來救濟貧苦。此后,人們用“杏林”稱頌醫生,用“杏林春暖”歌頌醫德。
陶淵明,曾祖陶侃為晉大司馬,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為人穎脫不羈,任真自得。胸懷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
陶淵明為彭澤令時,郡守派遣督郵前來督察,屬下提請他正衣束帶迎接,陶潛嘆道:“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遂解印去縣,賦《歸去來兮辭》。
陶潛義不仕宋,所著書文,但書甲子。與周續之、劉遺民世號潯陽三隱。蕭統評價陶淵明:“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
陶淵明真乃廬山高之范本,白居易詠之“常愛陶彭澤”“俯仰愧高山” ;龔自珍稱之“萬古潯陽松菊高”。
晉朝慧遠駐錫東林寺,撰寫《沙門不敬王者論》,闡述沙門與王者之間應有的關系。高尚其事,破妄求真。力主出家沙門不以世法為則,保持佛教的獨立性,大智大勇大無畏,對佛教中國化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
北宋周敦頤任南康軍知軍,于山南鑿池種蓮,作《愛蓮說》。獨愛芙蕖,“出污泥而不染”。
南宋朱熹知守南康軍,重修白鹿洞書院,修筑紫陽碼頭,為民生之疾苦是憂,大災之年,竟無一餓殍。
賢者因廬山更崔嵬,廬山因賢者更圣潔。廬山是多種文化薈萃、交流和碰撞之地,兼收并蓄,博大精深,同時廬山還是一座人格之美的富礦,一座氣節之山,其高標突出,特立不群,令人敬慕。
“廬山高”同“廬山真面目”一樣,幾乎成了一個文化符號,一種隱喻,被當作一則典故來應用,一種意義來指稱。
王陽明尤好歐陽修的《廬山高》,親自書寫,似嫌不足,主試山東時,還仿作《泰山高次網內翰司線韻》。有意思的是,其開篇正是從歐詩切入:“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 顯然,此作深受歐陽修感發。其立意之高,其氣勢之雄,兩者各有千秋。只是吟詠對象不同,王陽明所追慕的是至圣先師孔夫子,比之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及。”且欲瞻眺于孔門墻外,窺其堂奧。
明代著名畫家沈周,四十一歲時,為他的尊師陳寬七十歲生日,作巨幅山水立軸《廬山高》,是中國十大名畫之一,原屬北京故宮舊藏,現藏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
畫作借五老峰的萬古長青來祝師壽誕,以廬山的崇高來蘊含老師的道德文章。這完全憑借想象而創作的一幅精品,格高意深,氣勢恢弘。畫中題詩,頗得歐陽修《廬山高》真意,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沈周之后五百年來,諸多名家如陳師曾、傅抱石、黃秋園等,紛紛慕其雅致,追其清風,屢以《廬山高》為畫題,并樂此不疲。足見《廬山高》意蘊之美,品格之高,藝術生命力之強,宛如廬山亙古常新。因為人性人情之美,乃永恒的主題。
或許,廬山真不算高,但借重先賢往圣的精神品格,廬山有以贏得嘉名令譽,聲震寰宇,而成其為人文圣山。恰如劉禹錫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且賢者寄居廬山,大抵簡陋省凈。陶淵明“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劉凝之饘粥為食,結茅為廬。然而,他們游心塵外,陶然自得。孔子所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至此可言,“廬山高”,實乃人性之高,人文之高。有形的高度,可以測定;無形的高度,則不可以丈量。太史公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