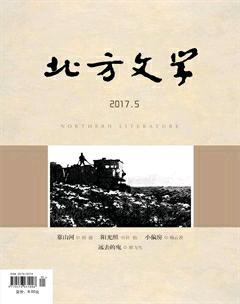泰斯比哈
石彥偉
泰斯比哈,阿拉伯語,意為念珠。
功課過后,沉靜的贊念開始了。為紀(jì)念冥冥中的九十九個(gè)尊名,并借以修身養(yǎng)德,回民安詳跪坐,逐一默念,每念一個(gè)尊名便撥動(dòng)一顆贊珠。故而泰斯比哈,常以九十九顆或三十三顆為計(jì),無論名貴的寶石、瑪瑙、琥珀,還是尋常的角骨、皮革、棗核,都由一根絲線穿為一串。
手指撥轉(zhuǎn)間,那長(zhǎng)長(zhǎng)的泰斯比哈也在微微轉(zhuǎn)動(dòng)了。
這一刻,光陰輾轉(zhuǎn),機(jī)密洞開。
西大橋
兒時(shí)的往事逝去得實(shí)在太久了。
每次去西大橋,都由祖父用自行車馱著,側(cè)坐在橫梁上。優(yōu)哉游哉四下望景,快到家才發(fā)現(xiàn)涼鞋被甩丟了。祖父便原路騎回,一街一巷地尋去。后來找沒找到,穿沒穿上,分明已忘卻了。
西大橋是姑奶奶的家。
在哈爾濱,祖父的姐姐只有這一位。八歲上,祖父隨曾祖父闖關(guān)東,由泊頭來到哈爾濱落腳。兄弟姊妹中,上有一位大姐出嫁于關(guān)里,不久因難產(chǎn)而亡;下有一小弟,幼年害天花,也沒活成。祖父生性寡淡,極少與鄰友交際,親戚也少,平素總是孤寂少語的。但只要到了西大橋,他就變了一個(gè)人,話多了許多,粗重的眉頭舒展開來,淤積良久的云團(tuán)終于散去。
姑奶奶家是個(gè)幾套間的老式平房,門外種著花木,一間一間跨進(jìn)去,光線暗下來,像是墜入一道深邃的迷宮。絳紅的地面,大概剛剛漆過,散發(fā)著油亮的光澤,跑起來當(dāng)當(dāng)響,弱小的影子在地板上晃來晃去。
姑奶奶個(gè)不高,有一些微胖,戴一頂白布帽,眉眼總是綻開的。她只管往外拿好吃的,然后便看著我們吃;若不吃,她便要催著快吃,直到看見我們吃下去她才放下心來。東北的回民女人喜歡張羅,男人卻話少,角落里的姑爺爺就比祖父還要安靜,極少言語,說起些什么總是平展展、慢悠悠的。他是瘦臉兒,眼睛不大,看上去總像在微瞑含笑,好像那就是他的話了。
是1996年吧,我大抵四年級(jí),家中做了一次事兒(紀(jì)念)。曾祖母無常四十年了。四十年是大年頭,回民講究四十年念著亡人,過了四十年,沒有條件的也可以不再做事兒了。猶記得永和街的祖父家中,擠得滿滿。西大橋的一大家人自然都到了,像是兩條支流的匯聚。老阿訇在炕上跪著,用關(guān)里腔朗聲誦念。白帽子密密跪了一屋子,連走廊也是白花花的一片。這般儀式并不多見,孩子的好奇中滿藏著珍惜,垂頭不敢張望,唯恐自己的無知破了那神圣的格調(diào),側(cè)耳聽著,只覺得阿訇念著念著便換了音色,換了一個(gè)人。悄悄瞥去,原是那姑爺爺閉了眼目,嘴唇節(jié)制地囁嚅著,泰然自若地接下去了。
姑爺爺名叫馬寶泉。
十八歲之前,我甚至不知他的名字。中考連著高考,兩點(diǎn)一線的學(xué)生怎會(huì)關(guān)心家族內(nèi)外的掌故?但一切因?yàn)橐环鈦碜躁P(guān)里家的信件被改寫了。信中說,我們泊頭石家可能是脫脫丞相的后裔。這個(gè)訊息忽然讓我感到,原來與我血脈相連的不只是祖父和那墳?zāi)怪械脑娓浮髡f中的高祖父,并不是到他們?yōu)橹贡阍僖矝]有可以溯尋下去的了——俯仰之間,一個(gè)家族竟與元朝、蒙古人搭上了關(guān)系,這可比中學(xué)的歷史課有趣多了。我開始纏著祖父問這問那,催著他給老家復(fù)信,想把一樁樁謎語漸次敲開。
祖父卻犯了難。他離鄉(xiāng)之際只是個(gè)垂髫少年,只身浪跡塞北,他又能講出幾句來呢?
“要不就去找找你姑爺爺,”就在這當(dāng)兒,祖父說,“他家是出過阿訇的,好像還與山東一位大阿訇有親。他興許懂得多!”
不久以后的一日,祖父終于要帶我去西大橋了,說是長(zhǎng)春來了貴客。
離群索居的心從此慌亂了起來。
秘密的大門就要?jiǎng)莶豢蓳醯爻ㄩ_了。
女阿訇
貴客便是姑爺爺?shù)耐馍饦滗俊?/p>
他管我的姑爺爺喊三舅,管姑奶奶喊三舅母,依此輩分,我也便管他喊大大了。
姑爺爺?shù)鸟R家也是從河北闖關(guān)東而來。他的姐姐馬淑琴是一位才學(xué)出眾的女阿訇,早年求學(xué)、設(shè)帳于哈爾濱,后經(jīng)人介紹,與濟(jì)南金家結(jié)了親。那金家,可是了不起的大戶,世代出阿訇,馬淑琴的公公便是民國(guó)享有盛譽(yù)的金子常大阿訇,曾赴埃及愛資哈爾大學(xué)留學(xué)。馬淑琴身懷六甲之際,丈夫病逝,留下苗裔金樹淇,母子相依,由山東回到東北,于長(zhǎng)春繼續(xù)做阿訇,直至天年。
可以想見,樹淇大大對(duì)母親的感情是何其深摯。
初次會(huì)面,他便將這位淑琴奶奶的事跡講給我聽。得知她七歲投師學(xué)經(jīng),受到楊素一、楊若君、韓鳳桐、海淑華等多位阿訇的啟蒙身教。1957年,曾參加第三次全國(guó)婦代會(huì),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首長(zhǎng)接見,也拜訪過馬堅(jiān)等教內(nèi)學(xué)儒,在省市政協(xié)、婦聯(lián)、青聯(lián)、伊協(xié)等部門都擔(dān)任過委員,是東北大地上難能可貴、備受尊敬的一位女阿訇。
此前,我對(duì)女阿訇的確缺乏常識(shí)的了解。走的地方多起來,才知在中原、西北多有女寺,自然也就有女阿訇的。即便東北三省,也較早地出現(xiàn)過一個(gè)功勞卓著的女阿訇群體。阿訇本就是學(xué)者,面對(duì)女性民眾授業(yè)解惑,女阿訇發(fā)揮的作用可能更為重要。
后聽人講起這樣一件事。馬淑琴阿訇曾有一條珍貴無比的泰斯比哈,不是金家就是馬家的,可稱傳家之寶。“破四舊”時(shí)被抄走了,落實(shí)政策時(shí),負(fù)責(zé)的同志到處尋訪,還是無法追還,然而此時(shí)的淑琴阿訇竟毫無怨艾,只淡泊一笑,說了一句:“泰斯比哈真是不好用錢衡量,就不必提了。”
我久久懷想。
那一刻的女阿訇或許已然徹悟,即便那串泰斯比哈用寶石穿成,遺失亦不必遺憾。因?yàn)樽钯F重的泰斯比哈,唯有經(jīng)霜后那顆堅(jiān)韌的心。
那次西大橋會(huì)面,樹淇大大不僅講他的母親、祖父,也講起了泊頭石家與金馬兩家的親密淵藪。實(shí)則他的出現(xiàn),是如絲線一般,把幾個(gè)家族貴如珍寶的記憶串聯(lián)了起來。那時(shí)正上高三,但心思全不在高考,卻極想到長(zhǎng)春去讀書,其中有一條,便是想和樹淇大大尋章問典。前定中撥轉(zhuǎn)的那根手指,或許感應(yīng)到了少年心底堅(jiān)如磐石的理想,縱然輟學(xué)半載,居然也如愿中榜,真考到長(zhǎng)春去了。
軍訓(xùn)后的第一周,樹淇大大便聯(lián)系了我。原來時(shí)值九月,正是吉林船廠的爾麥里(紀(jì)念活動(dòng))。我在高二便讀過《心靈史》,懂得船廠二字的分量。大大要帶我去趕人生中的第一個(gè)爾麥里,于我不知何等激動(dòng)!車來了,駕車送我們的是一位姓白的姐姐。樹淇大大介紹,白姐的母親也姓石,叫石景芝,也是泊鎮(zhèn)老家人,上世紀(jì)五十年代曾在長(zhǎng)春女寺追隨金母馬淑琴阿訇學(xué)過經(jīng)。二人情同母女,故而樹淇大大與這位景芝大姐全家早有誼切苔岑之交。
不久,景芝大姑過壽,樹淇大大約我同去赴席。那時(shí)我剛上大一,還是個(gè)混沌未開的蠢小子,不大懂得禮數(shù),只知叫我去吃席,竟未想到買上一份賀禮。事后父母知道了,還把我好頓批評(píng)。但其實(shí),那一晚生日宴上,不論景芝大姑、俊賢姑父,不論白姐還是兩大桌子家人,對(duì)我這一個(gè)“外人”是毫不外道的,陪我說話、給我夾菜,使我這樣一個(gè)骨子里和祖父一樣內(nèi)向拘謹(jǐn)?shù)娜藳]有感到絲毫的邊緣與尷尬,仿若融為一家。
回溯起來,依然陣陣感動(dòng)。大姑闔家或許早已忘卻十多年前的一幕聚會(huì),也從未在意過那個(gè)滿面羞紅的學(xué)生娃是提了些水果禮品還是兩手空空,只是本能而為地想給初到異鄉(xiāng)的我說一句:孩子,你到家了。
而今景芝大姑已經(jīng)離去,更多的背影都將飄逝。而我卻恍惚覺得她的恩師、我從未見過面的那位女阿訇淑琴奶奶正在向我走來,向我走近。
一個(gè)人在世上留存的功德終究是有限的,但其曾經(jīng)培育過的精神氣質(zhì),終歸會(huì)在更多靈魂的根部成其延續(xù),成其永遠(yuǎn),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shí)在。
大 大
在長(zhǎng)春讀書的時(shí)光,樹淇大大與我成了忘年交。
我們相隔三十余年,他的女兒比我還年長(zhǎng)幾歲,但大大與我談話,從未擺出長(zhǎng)輩的架子,或是因?yàn)樗囊姸嘧R(shí)廣而顯露絲毫的指點(diǎn)之意——以他的學(xué)養(yǎng)和閱歷,其實(shí)本可如此,我也一向把他當(dāng)作大家族中唯一鉆研歷史、能言擅寫的學(xué)者,總希望向他誠(chéng)意求教的。然而樹淇大大,他偏偏總把姿態(tài)放得很低,談起他所結(jié)識(shí)的列位名家來總是謙遜而仰觀,談起后學(xué),也總是竭力尋出閃光點(diǎn),哪怕如我這般僅僅喜歡寫幾筆東西,想為母族做些事,他就覺著欣喜、寬慰,似乎總可以在年輕人身上吸收新知,甚至永遠(yuǎn)對(duì)晚輩使用“您”這樣的敬辭。
在東北的大風(fēng)大雪中,如此儒風(fēng)仿似有些另類了。起初,我也不大習(xí)慣的,光陰久了,也就順應(yīng)了下來,明白了一切全出于自然。大大身上,確有一種民國(guó)知識(shí)分子遺留的謙謙之風(fēng),而那骨髓里的優(yōu)雅與謙恭,顯然是金馬兩家經(jīng)年教養(yǎng)的延伸和粹取。
長(zhǎng)春回族人數(shù)并不算眾,城關(guān)內(nèi)也并未形成像沈陽的回回營(yíng)、哈爾濱的道外十二道街那樣相對(duì)密集的社區(qū),但他們對(duì)本民族文化事業(yè)之熱衷、之踴躍,在東北可領(lǐng)一先,即便放之四海也未必遜色幾何。或許緣于我學(xué)習(xí)傳媒專業(yè)之故,有什么回民的大事,樹淇大大總拽上我,跟眾多叔叔輩、大姐輩的民族精英聚在一席。圍爐取暖中,我漸漸讀懂了一座城市的表情。
讀書四年,我四次擔(dān)任過開齋節(jié)文藝演出的主持人,除卻頭一年的2004年是大學(xué)生自?shī)首詷吠猓笕龑枚际怯墒忻裎⑹凶诮叹殖雒嬷鬓k,有時(shí)在清真寺廣場(chǎng),有時(shí)則選在禮堂。籌委會(huì)數(shù)月前即要策劃,那位大叔聯(lián)系京劇院、雜技團(tuán)的回民藝術(shù)家;這位大姐把武術(shù)隊(duì)的師兄弟們聚在一起,刀槍劍戟在冰雪嚴(yán)寒里重新操練起來;回民小學(xué)的女校長(zhǎng)領(lǐng)了任務(wù)回去,準(zhǔn)能排出最像樣的民族舞蹈;能唱男高音、女中音的,能朗誦的,能揮毫作畫的,都撇下手中的忙碌,一聲集結(jié)號(hào),全到場(chǎng)。
一顆寶石只是寶石,但穿成一串,就成了神奇的泰斯比哈。
那時(shí)的樹淇大大,雖說不是領(lǐng)導(dǎo),卻是一個(gè)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再大的場(chǎng)子,只要他一出面講幾句,大伙心里就有了底,有了奔頭。
記得2005年開齋節(jié),恰好在我母校東北師大演出。大大力薦才念大二的我與他一同登場(chǎng)主持。此前這類角色,一向都是他在擔(dān)綱。大大儀表體面,臺(tái)風(fēng)莊重,頗有學(xué)者氣象;脫口字正腔圓,聲如洪鐘,聽說年輕時(shí)差點(diǎn)考了播音員;穿針引線,妙語連珠,又善于臨場(chǎng)抓彩兒,救場(chǎng)補(bǔ)臺(tái),無怪乎被大家視為主心骨。
但我記得,那次大大主持過一節(jié)退到臺(tái)側(cè)來,每每總是摘掉眼鏡和頭上的圓氈帽不住地擦汗,臺(tái)上的精氣神頃刻間已注滿疲憊。我才猛然意識(shí)到,哦,原來我的大大不是當(dāng)年的小伙子了,他已是一個(gè)年屆花甲的老人!只是他不愿這樣承認(rèn),他仍在給肩頭壓著重?fù)?dān)罷了。
歡慶的筵席上,大大拉我到一邊,言深意長(zhǎng)地說:“大偉,有你這樣的接班人我就放心了,以后任務(wù)就交給年輕人了!”
這人聲鼎沸中孤寂的一聲托付,就是人們傳說中的“傳承”二字嗎?來得這樣早,這樣緊迫,這樣地沒有準(zhǔn)備。然而樹淇大大確乎抱定了舉意,此后兩年,便只力推我一人登臺(tái),他則卸下一身榮耀,退到追光之外,默默送上勉勵(lì)的雙掌。
長(zhǎng)通路
畢業(yè)后,我泊居京城,總能收到樹淇大大的來信。他有舊時(shí)文人的積習(xí),旅行感思、朝覲心得,或是發(fā)現(xiàn)了有價(jià)值的史料,都一一寄來。那一筆行楷俊秀剛毅,透著風(fēng)神,令我想起姑爺爺曾講過的:他曾看到山東金子常阿訇寄到哈爾濱親家的書信,信皮上寫著“永長(zhǎng)街”,那蠅頭小楷真是漂亮。
一個(gè)家族的精神密碼仍在暗暗撥轉(zhuǎn)。
但時(shí)代已經(jīng)斷裂了。
我一封封地收著大大的信,卻沒能親筆回過一封,多是打去電話。即便一個(gè)以寫作為生的人,親筆寫一封信,已太過奢侈。誰來完成對(duì)時(shí)代的寬恕?
但大大一如既往地寄著信。寄給我,也寄給異鄉(xiāng)親友。有一段時(shí)日,我的文字在一些刊物發(fā)得多了起來,特別是好些民刊多有轉(zhuǎn)載,有時(shí)我還不知消息,未見到樣刊,哈爾濱的祖父卻在電話里告知,看到我又寫了什么,發(fā)了什么。我自然訝異至極,因?yàn)樽娓甘菢O少能看到那些刊物的,追問下去,原來皆是那樹淇大大但見我的文章便復(fù)印下來寄給西大橋的姑爺爺,而姑爺爺看罷,又轉(zhuǎn)予我的祖父看。
我冒了一身冷汗!
我的那些自己都沒有下足功夫的淺薄文字,除卻受到辦刊人的器重外,原來也要在民間、甚至在我的家族、甚至跨越幾個(gè)地名之間如此傳遞嗎?我若不多寫一些,寫得再好一些,焉能對(duì)得起大大的心意,對(duì)得起幾位老人放大鏡下的夜讀呢!
終于算是有了一聲微薄的報(bào)答。
2009年開齋節(jié)前夕,時(shí)逢長(zhǎng)通路清真寺建寺185周年之紀(jì)念,金樹淇大大正受任為寺管會(huì)主任,桑榆晚景,初心不渝。一向注重文化積累的他向林松、李佩倫等大家約了專稿,囑我在京與之聯(lián)系請(qǐng)回,同時(shí)希望我也能寫上一篇,一并收入紀(jì)念文集中。
一介回回寫者,平生能為清真寺留一文,是至高無上的榮譽(yù)。我知道這是遠(yuǎn)在長(zhǎng)春的大大,對(duì)我為文生涯的又一次關(guān)照。縱然如芒在背,但想到與長(zhǎng)通路的朝夕往事、厚誼深情,想到那片土地對(duì)我的恩澤與哺育,我決意接下這神圣而艱巨的邀約,于是便有了一篇差強(qiáng)人意的《長(zhǎng)通賦》。
在結(jié)尾,我寫到一句:
弱冠而夜訪,廷巴巴乃賦經(jīng)名;四載乎日照,淇大大恩重岱岳。至若斯城、斯寺、斯眾,念甚至哉。
掩卷北望,關(guān)外的風(fēng)雪聲猶在耳際。那長(zhǎng)通路上的古寺故人,還在用余溫點(diǎn)亮萬家心燈。
金魚馬
十幾年間,隨著與樹淇大大交誼的增厚,我也成了一條行走的絲線。前定之中,更多的寶石等待著尋覓和串聯(lián):濟(jì)南金家、哈爾濱馬家、泊頭石家……幾大家族的交疊記憶在暗美中昭昭發(fā)光。
我去山東拜訪金子常阿訇的女兒、樹淇大大的姑母金衍蓮奶奶,并去尋訪業(yè)已消失的金家道堂。
我潛入濟(jì)南巷陌深處,找到曾為石家寫下家史的石景春老爺爺,從老人手中接過了他收藏一生的泛黃史料。
我找到祖父在泊頭的表弟戴忠文爺爺,竟意外發(fā)現(xiàn)他的老伴正是長(zhǎng)春石景芝大姑的親妹妹,而她們都與濟(jì)南石景春是堂兄妹!
……
輩分瞬間被打亂,一個(gè)人物產(chǎn)生了三種叫法。但我毫無畏難,滿胸的喜悅暗暗消受,無心向人訴說。
終于,在一幅龐雜無序的家族譜系中,摸清了樹淇大大經(jīng)常掛在口邊的一個(gè)“石六爺”是何許身世。其實(shí),我的曾祖父行六,按說也是石六爺,但金馬兩家念念不忘的這位“石六爺”與我的直系血緣無關(guān),而是泊鎮(zhèn)一位熱心的能人。我曾在《金石的顯跡》一文中寫過,據(jù)泊頭父老傳述,他先在沈陽落腳,照應(yīng)闖關(guān)東的眾多鄉(xiāng)鄰,其中便有一位滄縣鄉(xiāng)老馬書田,欲去哈爾濱謀生。偽滿光景,金魚行市看好,石六爺便建議馬書田從北京引進(jìn)魚苗,到哈爾濱去賣。于是,那馬書田在道外開了一家頗有規(guī)模的金魚鋪面,圓口如缸的魚池鱗次櫛比,獅頭、望天、鳳尾龍睛、熒鱗蝶尾……馬書田也得了一個(gè)“金魚馬”的綽號(hào)。
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我姑爺爺?shù)母赣H,金樹淇的姥爺!
金魚馬的金魚多到了什么份兒上呢?聽祖父講,當(dāng)年松花江發(fā)大水時(shí),道外一片汪洋,劃著船也可到處見到金魚馬家的大金魚;也曾拜訪我的高中校長(zhǎng)韓在山九旬高齡的老父親,我問韓老先生可曾聽說道外有金魚馬這一號(hào)嗎?老人家肯定地答說:有!知道!竟也講到發(fā)水年景,金魚遍流的情形。
這一細(xì)節(jié)深深吸引了我。
闖關(guān)東的貧苦回民,做牛羊行的、勤行的、手挑肩扛的很多,但做金魚生意的,這恐是唯一聽聞。無數(shù)次,我想象著金魚馬老人坐在陽光下的魚池之間,滿目金光燦爛,游弋生輝。有魚就有水,有水就有生存,就有盼頭,就有性靈中的一份潤(rùn)澤。倘若真有一日我能為闖關(guān)東的回回寫一部長(zhǎng)篇小說,一定要安排一位賣金魚的角色。因?yàn)椋娴脑诖髸r(shí)代中孤寂地存在過。
金魚馬的后人猶在,我便往西大橋跑得多了。每年春節(jié)回哈爾濱,大年初一都要去給幾戶長(zhǎng)輩賀年。因?yàn)橛袔准依先耍赣H和伯父?jìng)兺ǔ]啌Q,今年去這家,來年可能換去那家,但每年西大橋這一處,一定都是我與父親同去。
仍是那縱深的套間平房,與童年祖父帶我去時(shí)相比,它分明低矮了許多。那記憶中紅通通閃著亮光的地面,也早就暗淡無色了。老去的姑爺爺常坐在窗前的一條窄榻上,仍然微瞑雙目,像是永遠(yuǎn)在沉思。但他終于發(fā)現(xiàn)我來了,便吃力地站起身,蹣跚著拉住我的手。我們出起了在家鄉(xiāng)極少?gòu)埧诘馁悅z目,互相感受著經(jīng)年隔空的慰藉。我知他耳力不好,便坐得離他很近很近,傾聽著那顆衰微的喉嚨中所能發(fā)出的每一個(gè)字。
才知道這戶回民馬家初到哈爾濱時(shí),仍然在家里保留著過爾麥里的習(xí)慣,簡(jiǎn)樸的果碟,搖首誦念,那是根須的氣息,失落的鄉(xiāng)愁。后來,因人數(shù)甚少,便漸漸融入大坊,獨(dú)異的傳統(tǒng)成了一個(gè)深埋心底的念想。
那么,那金魚馬呢?
我還是想請(qǐng)姑爺爺多講講這位有故事的老人。
然而流年已去,往事斑駁。講到金魚馬晚年在兆麟公園一個(gè)干涸的水池中不慎跌倒,把腿摔壞,從此便隱于世外,直至終了。一代金魚大戶的傳奇,從此封存。姑爺爺?shù)淖窇洠材陱?fù)一年地稀薄了下去,最后只節(jié)制到了一詞半句。
“您能告訴我——”在姑爺爺行將遠(yuǎn)去的最后一個(gè)春節(jié),我拉著他的手,忍耐住靈魂深淵中的憂傷與惋惜,追問了這么一句,“金魚馬老人家有過什么掛在嘴邊的話嗎,他對(duì)您說的最多的一句是什么呢?”
沉吟半晌,姑爺爺緩緩思慮著說:“聽定然,順自然,歸本然……人生跟著泰斯比哈轉(zhuǎn)哪……”
又是泰斯比哈!
我脊背一冷,不再追問下去。
辭別老人,揮手老屋,天地間冰雪蒼茫。還需要怎樣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生的總結(jié),有此一句,已經(jīng)夠了。
霎時(shí)間,一群親切的背影隱隱疊化在面前:金魚馬、淑琴奶奶、樹淇大大、景芝大姑,還有長(zhǎng)通路上那些熱忱溫潤(rùn)的面孔……每一位都是一顆發(fā)光的寶石,被一條隱秘的前定串聯(lián)了起來。他們安詳跪坐,手指撥轉(zhuǎn)間,長(zhǎng)長(zhǎng)的泰斯比哈也在微微轉(zhuǎn)動(dòng)。在深懷參悟的人想來,這一刻,光陰之復(fù)蘇、天道之巡回、命運(yùn)之起落、福禍之消長(zhǎng)……唯在一泓靜水之中。
責(zé)任編輯 付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