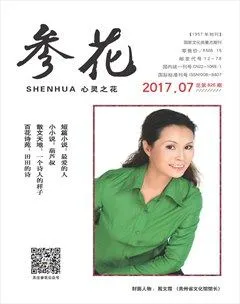馬維駒的詩
方言替你回鄉
當你老了,你會發現,所有的路
都會通向故鄉
所有的距離,都以那座老屋為起點
所有的疼,都像青銅箭頭,從四面八方
射向故鄉的心臟
你在他鄉交往的每一個人,都是
你的鄉親的化身
你學會了在商言商,學會了
用普通話、外語與各色人等交談
可是,在夜里,你無法收住回鄉的腳步
無法限制自己用鄉音做夢
在任何一張床上,你都會聞到
麥秸和牛糞燃燒的味道,都會
仔細掐算農歷、月相
都會記起每一位親人的忌日
清明雨
學者統計,清明雨的概率
低至百分之十五
杜牧一生只遇到七次,最后一次
才找到杏花村
我比杜牧幸運呢,還是更為不幸
母親離世的這十年,我的清明
年年都在雨中
那些雨啊,有時落在墳頭
有時,落在心頭
讀書
一千多年了,每當夜闌人靜
線裝書內部傳出輕微聲響
有些書,久不翻動
一些黑色的文字翻身坐起,變成
虔誠的讀書郎
它們互相指認,互相解讀,互相替代
陣營逐漸模糊起來
時光之水從書頁流過,漂洗著
當世的碎屑與前朝的塵埃
銀色小蟲有足夠的時間,緩慢地
閱讀著艱澀的句子
它們花去幾百年工夫,吃透了
厚重的人類史
寫信
想用全部所得,換回帶暗格子的稿紙
春日陽光溫暖,拭去輕薄灰塵
用寫信的方式返回過去
不在乎寫給誰,不在乎潦草的字跡
會不會謬傳了我的心境
寫信,是我多年的愿望
應該寫信的年代,沒有像樣的紙筆,和
可以讓人放心的消息
生活的窘迫,錯失了寫信的機會
室內有一只蒼蠅,像一個竊密者
偷偷摸摸地閱讀
我的文字,模仿它的觸須、肢體
也模仿它哭泣般的歌聲
寫信,要思前想后,是一件頭疼的事
折信,如同折疊僵硬的骨頭
封口,猶如蓋棺
我真想把信封反復拆開,一遍遍地修改
每刪一個字,都能感到身體的失重
有地址的,一一寄出
不等回音,不盼歸期
沒地址的,等一個不期而至的電話
母親,也許在天堂,也許在地獄
趁著天黑,把信燒給她
如果有嗶啵聲響,應該是
文字中的水分和血液遇火爆燃
如果火焰跳躍,那就是連接母子的筋骨
在寸寸成灰
我是多余的部分
熱帶魚在缸中構筑著階級和社會
王,統馭臣民
我的身影,是無名無姓的賤民
就像玻璃表面的一道污痕
蠶,專注于食桑、結繭
生命周期很短,留下的線索很長
我的目光,是柔軟之外的多余部分
無異于拋棄的蠶蛻
陽光濺起浮塵,揭示而又掩埋著事物的真相
此刻,它才是主人
而我,是它剝開的一只老玉米
肌肉,帶著骨頭的質感和音色
走進人間的樹
一棵被砌進房子的樹,使勁把頭探到高處
俯視時,它看到的不是自己的身子
而是平坦的屋頂
它的生命,不同于其他樹木
每年,可以更早一點發芽,更晚一點凋零
每天,既能享受陽光,又能享受燈光
它有機會見證滾燙的愛情,目睹小人物
躲在門后的嘆息和狹隘
它的根,牢牢抓著地下的泥土
身子,不敢有絲毫晃動
它似乎知道,只要略有松懈,房子里的幸福
就會跟著晃動起來
它也希望,房間始終是溫暖的,好讓
樹冠更大一些,枝葉更密一些
它習慣了穿透房頂的生活,很盡職地
為這逼仄的人間,撐著一把
遮風擋雨的傘
每一粒實都不多余
母親在晴好的下午曬谷子
方方正正一大片,用鋤把勾出壟溝
這些金色的谷粒,和長在地里的禾苗一樣
排著整齊的隊列
它們是一位舊式農婦精心寫成的古體詩
現在,我寫詩,七律或者五絕
雖然不長,可翻騰出不少溫熱的備選詞
千挑萬選。中意的,安放妥當
剩下的,暫時擱置
母親從谷粒中簸出的秕子,有時
成了雞鴨和麻雀的小點心
禽鳥們點頭稱謝
語文老師說,古人造的字,每一個
都有用處,要惜墨如金
母親說,土地供出來的籽實,每一粒
都不多余。吃饃,如同拜佛
只有這對膝蓋
族人發來掃墓照片,祖墳
是鄉村最熱鬧的去處
墳院里有一些閃光的東西,看不清楚是什么
也許是酒瓶和皮鞋,也許是靈魂
漂浮的青煙中,有沒有祖宗的臉龐
我不敢確定
從一堆人中,我認出了
當大官的遠方叔叔,經商的堂哥,還有
仍在和土地分不開的哥嫂
官員和老板,站著寒暄
雙膝深埋土里的,是愛惜土地的農民
他們身無長物,只有
這對膝蓋
還鄉
在這個山鄉,我學會了喊娘,也學會了罵娘
像村婦那樣,以各種惡毒的言語
咒罵窮窩子的丑陋
天不下雨,麥不拔節,豬不長膘
都是咒罵的理由
詞匯,黃土坷垃一樣,遍地都是
什么糜地灣的餓死鬼、瑪瑙溝的私生子
什么天不收的、地不養的
家鄉,欠我一段快樂,欠我十七年的飽飯
還欠我一個父親和哥哥
——他們被逼走他鄉,一去無回
離開山鄉幾十年,歲月,像濃烈的鹽酸
消解著鐵質的冰冷
深深淺淺的夢,背叛了所有的咒語
千里萬里的夜路,流放一樣
牽著我,一遍遍地
還鄉
飄
樓,是供人上的,也是供人下的
從樓上飄下來的,有時是鴿子,有時是云影
有時,只是一種想法
這一次,是一個絕望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