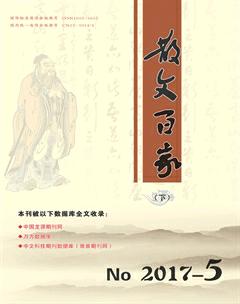談通俗文學的定位轉化
蔡健
通俗文學指除了歷史上的民間文學以外,還包括現實創作的通俗化、大眾化,具有較高的商業價值,以滿足一般讀者消遣娛樂為主要目的的文學作品。也可以說,所謂通俗文學就是一種大眾喜聞樂見的,在民間有著強大生命力的文學。自古以來,這類文字都被許多正統學者看作是“下里巴人”,登不得大雅之堂。但有時“下里巴人”比“陽春白雪”更有生命力,因為它有著社會最大比例人群的擁護與支持。明清時代,《三國演義》、《水滸傳》這類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文學名著的作品,當時就是“下里巴人”,就是通俗。即算是如今,我們也可認為它們可以歸屬到通俗文學范疇內。
能讀懂文學名著的人畢竟是少數,文學名著有其特定的閱讀群體和專家群體,而通俗文學就沒有,它適合各個階層。在人類群體中,“大眾”才是真正的絕對概念,而精英永遠只能是相對概念。正因為“大眾”是永恒的絕對多數,可以說,通俗文化將永遠存在。有的人甚至一輩子都沒讀過一本文學名著,卻可能看了不少通俗文學的作品。文學名著的影響力往往不是來自作品本身,而是得益于其他藝術形式對名著的通俗化演繹。譬如正是評書、曲藝、戲劇等通俗化的藝術形式讓《三國》、《水滸》、《紅樓夢》、《西游記》這樣的古典文學名名著走入千家萬戶,貼近尋常百姓。而大部分評書、曲藝、戲劇也是通俗文學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認為俗文化、俗文學是孕育催生高雅文化、高雅藝術的母體。雅與俗能相互轉化,也就有了相互制約的關系和彼此間的獨立性。
也許,有的人會贊同阿諾德?豪澤爾的說法:“民間文學使精英文學簡單化,通俗文學使精英文學庸俗化。”甚至就對通俗文學的概念來說,鄭振鐸先生在1938年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中說“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換一句話說,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于民間的,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漢語大詞典》說:“通俗,淺顯易懂,適合一般人水平和需要的。”“不登大雅之堂”和“適合一般人需要”兩句話,幾乎就給通俗文學判了死刑。
中國的通俗文學在今天是獲得了巨大的合法性和確定性,上接唐傳奇、宋話本、明清的章回小說,中承晚清之譴責與黑幕,到張恨水、程小青、李壽民等等再到金庸、古龍和瓊瑤,如果算到如今這個“網絡時代”,可能就有安妮寶貝之類的作者吧。“通俗文學”成了一個一脈相承的偉大傳統,在這個傳統中,形成了自己的古典,自己的過渡和自己的現代化進程。通俗文學只是在我們的周圍,只是更貼近我們的生活,只是能迎合大眾的口味,只是能反映普通民眾的喜怒哀樂,你不覺得它能展現人民的審美觀,也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嗎?雖然所有的通俗文學,不一定都能成為名著,但大多數的名著,在其誕生之初,都是通俗文學。
我們應該以人文精神的尺度來審視通俗文學的積極面。文學本身除了人們常說的陶冶情操功能、審美功能、教育功能等,還有娛樂功能。古代中國和西方的文學理論有“寓教于樂”的文學思想,即使是當代西方最先鋒的文藝理論家也將審美愉悅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上。
例如羅蘭·巴特著有《本文的愉悅》,姚斯著有《恢復愉悅》,至于巴赫金,在他的詩學理論中,“狂歡節”這一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后現代主義多理論的源頭。
通俗文學的寫作采取了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和內容,從而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閱讀快感。這種閱讀快感對置身于高強度、快節奏以及沉重工作壓力下的現代工業化社會的人來說,畢竟提供了一條可休息的途徑,人們因此可以大大緩解其心理緊張和內在焦慮,我們不能期待人人都是英雄,都能面對慘淡的現實人生,面對“無物之陣”的挑戰,因此,通俗文學作為某種程度的宗教替代物,不僅僅能夠提供巨大的心理支持,而且能夠強化個體對社會的認同,加深社會溝通。
其實,文學本沒有什么高雅和通俗之分,一個文學作品在其創作后,才形成了高雅和通俗之說,文學其始都是通俗的。譬如今天的四大古典名著,我們都習慣把它們定位為高雅文學,可是它們最初都是以通俗文學的身份出現的。
因此,通俗是文學的生命力,是文學的發展方向。通俗文學比文學名著影響大,這不僅是二者定位不同的必然,更為歷史和現實所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