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與時代:沉浮身不由己
文/趙健雄
去年秋天,浙江美術館閉關整休三個月后,首展傅山,雅評不斷;今年秋天,同樣的展期,又推出王鐸,尚未開展就一片叫好之聲。
展覽當然可以規劃,更得看因緣,尤其幾百年前古人的個展,不是說辦就能辦的。
此次王鐸作品展,觀者如云,不少外地乃至國外趕來的。
明末清初,倪元璐、黃道周、王鐸鼎足而立,時人并稱“書壇三株樹”,至于“晚明五大家”,則還要加上傅山與張瑞圖。
以上幾位,用當下說法,稱作大師當無疑義。
尤其王鐸,被吳昌碩贊為:文安健筆蟠蛟璃,有明書法推第一。這也是此次展覽名為“健筆蟠龍”的由來。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這樣評價王鐸:一生吃著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結果居然能得其正傳,矯正趙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
林散之認為:覺斯(王鐸)書法出于大王,而浸淫李北海,自唐懷素后第一人,然盡變右軍之書法,而獨辟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
啟功則言:覺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

馬一浮

梅貽琦

陳寅恪

胡適
能得近現代書法名家如此大贊何等不易。但幾百年來,王鐸名氣事實上不那么大,也并非沒有道理。與他個人遭際、命運相關,更有時代氣氛和主流意識形態在起作用。和其他幾位書家比較,由傳統道德觀之,王鐸可以說是最沒骨氣的。
就對舊朝的忠貞而言,倪元璐與黃道周最為堅執,本來倪已深知朝政不可為,絕意仕途。崇禎十五年(1642)聞清兵入至北京,當朝求救兵于天下,元璐毅然盡鬻家產以征兵,募得死士數百人,馳赴北京,被拜為戶部尚書。兩年后,李自成陷京城之日,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幾上曰:“以死謝國,乃分內之事。死后勿葬,必暴我尸于外,聊表內心之哀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
已然歸隱的黃道周也在隆武元年(1645)募眾數千人及糧草,出福建仙霞關,抗擊清兵。幾個月后在向婺源進發時遇伏,被送至南京獄中,清廷派洪承疇勸降,黃道周寫下這樣一副對聯:“史筆流芳,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將史可法與洪承疇對比。洪羞愧難當,上疏請求免黃死刑,清廷不準。
黃于隆武二年三月五日(1646年4月20日)就義,至東華門刑場,向南方再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書遺家人:“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臨刑前大呼:“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最后頭已斷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們從他的衣服里發現“大明孤臣黃道周”七個大字。
傅山在鼎革之后,堅持反清二十余年,曾因參與南明王朝派來山西的總兵宋謙密謀策劃起義,被清軍捕獲下獄,幾經嚴訊,備極拷掠,抗詞不屈,絕食9日,抱定必死決心,終于獲釋。
出獄后,反清之心不改。隱居于城郊僻壤,自謂僑公,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無國無家,只是到處做客罷了。康熙二年(1663),結識參加南明政權的顧炎武,兩人抗清志趣相投,結為同志,自此過從甚密。他們商定組織票號,作為反清的經濟機構。
晚年他主要從事著述,成為在野思想文化界的領袖和代表之一,并以73歲高齡,絕食七日,拒絕參加清廷為籠絡漢族知識分子所舉辦的博學鴻詞科考,又在皇帝恩準免試、授封“內閣中書”之職時凜然拒絕,毫不客氣,仍自稱為遺民,表現了“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
與這些同人的事跡相比,王鐸可謂乏善可陳。
早年(1622)即與倪元璐、黃道周同時通過殿試被賜進士的他,由于種種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在改朝換代之際,于人生道路上作出了不同的選擇。
1645年,清兵破了南京城,身兼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蔭中書舍人的王鐸在洪武門與禮部尚書錢謙益等在雨中跪迎來者,降了清。
順治三年(1646)正月,王鐸被命明史副總裁。三年后,授禮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又加太子太保。再過兩年,晉為少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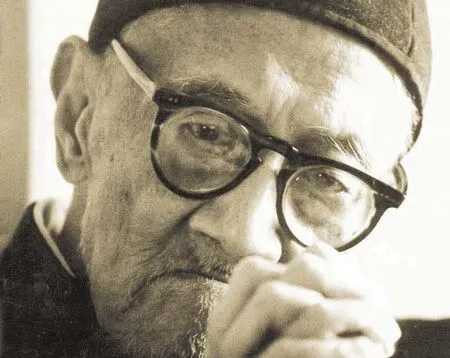
梁漱溟

潘天壽
他內心感受一定是復雜的。這才會有死時遺囑:用布素殮,壟上無得封樹。
此后兩三百年間,反清復明一直是漢族士人及民眾埋在心頭的夙愿,直至辛亥革命,仍成為黨人動員群眾的主要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其作用與力量有甚于國體改革的承諾。
這么一種時代背景下,不要說漢人看不起王鐸這樣的降臣,就是滿人也看不起。
乾隆稱帝后,朝廷借敕編《四庫全書》之際,查毀了王鐸的全部書刊,并將他列入《貳臣傳》。此種做法,也反映出他生前遭遇的某種處境。
書法與上面所說這些有什么關系?當然有關系,自內而言,心情變化會影響筆墨變化,從外來說,其時作品即便送人,恐怕也沒人要啊。這怎么可能不影響書法史上的地位?
如今辛亥革命也過去百年了,清朝統治被推翻后,滿人在大陸的影響不止日益淡薄,有時甚至讓人感覺幾近消失,(當然只是表象,其實滿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在為中華文化的建設出力與貢獻,但我們已然不會為譬如啟功的滿人身份有什么特別想法。)
或許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人們才能避開至少減弱種種其他因素而回到藝術本身上來,關注王鐸對書法的創造和取得的成就。
那么多人來看展覽是有道理的,浙江美術館的網上簡介中說:“王鐸(1592—1652),字覺斯,又字覺之,號嵩樵、石樵、十樵、癡樵、雪山。明萬歷二十年生于河南孟津雙槐里。順治九年病逝故里,謚文安。王鐸于詩文書畫皆有成就,尤以書法見長,有《擬山園帖》《瑯華館帖》及諸多詩文書畫傳世。
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他有‘神筆王鐸’之譽,他以其獨特的書風和書學成就,確立了在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他與黃道周、倪元璐、傅山等書家一道,提倡取法高古,開展復興書壇的活動,一掃明末書壇因循守舊之氣,開創了明末清初大寫意書風格局。”
這些簡略的文字里,看不出明清之際的血雨腥風,那段“留發不留頭”的歷史仿佛并不存在。而眼前展覽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個稱得上大師的書家,其種種特別努力。即便“鐸每日寫一萬字,自訂字課,一日臨貼,一日應請索,以此相間,終身不易,五十年終日而不綴止。”這一條,有幾人能做到?
說到大師與時代的關系,浮現與失落往往都身不由己。今天已沒什么人對滿漢關系還會予以格外關注,至于那些當年在清朝做官的漢人,譬如曾國潘,一般而言,也不再遭到特別的蔑視乃至仇恨了。
由此人們想起王鐸,覺得不妨以書法說書法,畢竟那是一位了不得的藝術家啊!
這個展覽,十年前很難期許;四十年前若癡人說夢;再早些日子如此作為既不可能更無疑把自己往斗鬼臺上送。如今居然也就開了,時代真是奇怪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