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步是看待大地的一種方式
[英]羅伯特·麥克法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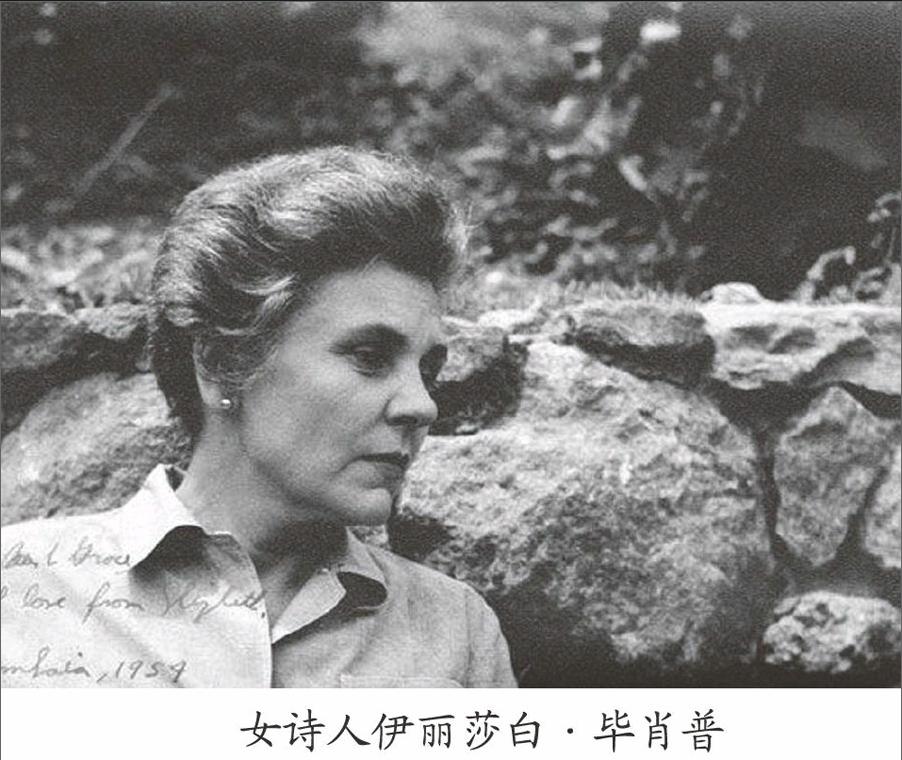
從我的腳跟到腳尖是二十九點七厘米,折合十一點七英寸。這是我步伐的單位,也是我思想的單位。“我只能邊走邊思考”,讓一雅克-盧梭在《懺悔錄》第四卷中寫道,“當(dāng)我停下時,我的思想也停了下來。我的大腦只和我的腿腳一起工作。”索倫·克爾凱郭爾推斷,心靈應(yīng)該按照每小時三英里的步速運行才發(fā)揮最佳效能,他在一則日記中記錄了自己一次漫游,并發(fā)現(xiàn)自己“被各種想法吞沒了”,以至于他“幾乎邁不動腳步”。克里斯托弗-莫利在論及華茲華斯時說,他“將自己的雙腳當(dāng)作哲思的工具”,而華茲華斯談及自己時則謂之自己的“感官領(lǐng)悟力”。在這個問題上,尼采是一貫的絕對——“只有那些來自徒步行走的思想才算有價值”——而華萊士-斯蒂文斯的觀點一貫是試探性的:“或許/真相依賴于一次環(huán)湖漫步。”在所有這些描述中,步行不是一種你可以通過它抵達(dá)知識的行動:它是我們認(rèn)知的手段。
提出認(rèn)識既是行動敏感型的,也是地點特定型的,在浪漫主義運動興起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是真正令它廣為人知的還是盧梭。這在今天是眾所周知的提法,但要把它定位一項規(guī)則,我們表示懷疑是合理的。有時,步行是心靈親密的伙伴,有時卻是殘忍的敵人。如果你曾經(jīng)日復(fù)一日地長距離步行,你就會知道,途中的極度疲憊會消滅除了最基本的功能外的大腦所有功能。走上二十英里,你就會頭暈?zāi)垦#荡舸舻乜粗s翰-希拉比所稱的“腦在非西方文化中,足跡作為知識,步行作為思維方式的想法廣為人知,特別是作為回憶的一種隱喻——歷史是人返身走人的一個地區(qū)。基思·巴索寫過,西貝丘阿帕奇印第安人是如何將過去比喻成一條小徑或一行腳印,祖先們踏過,但是對于生者卻大部分都不可見,必須要通過激活某些記憶中的道路間接地重溫。這些道路——包括地名、故事、歌曲以及遺存——有時被阿帕奇人稱為——“腳印”“行蹤”。對加拿大西北部的科林;中人來說,步行與知識是幾乎無法分別的:他們用于指稱“知識”和“腳印”的名詞可以互換使用。一部大約六百年前的西藏佛經(jīng)用shul表示“一種當(dāng)初留下印跡的東西已經(jīng)消失后所殘存的印跡”:腳印是shul,小徑是shul,這些印跡引得人回頭,通曉過去的事情。
乍一眼看上去,“步行就是思想”或者“腳可以知道”這些想法很陌生,令人困惑。我們并不將腳想象成一種表情達(dá)意或感官的附屬器官。腳缺少手那樣多才多藝的本領(lǐng)。大腳趾轉(zhuǎn)動不靈:它抓握方面的最大的本事,不過是和二腳趾一起做出剪刀一樣的笨拙動作。腳感覺上更像是假肢,帶著我們四處走,但不能為我們闡釋或組織世界。手肯定比腳更靈巧——我們說掌控,但從不說腳控。然而理查德·朗——他曾經(jīng)每天步行三十三英里,連續(xù)走了三十三天,從康沃爾的利澤德走到蘇格蘭北部的達(dá)尼特角——寫信時愛用一個紅圖章,上面是一雙腳的輪廓,腳底板上有雙眼睛,盯著你看。腳步是看待大地的一種方式;觸覺相當(dāng)于視覺——這就是我的所持的觀點。
對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而言,用腳和用腦子進(jìn)行探尋在他的哲學(xué)里是密不可分的整體。在劍橋跟隨伯特蘭·羅素學(xué)習(xí)期間,他會在羅素的房間里大踏步地來回,躁動不安、緘默不語,有時能走上好幾個鐘頭,在不過幾碼大小的房間里走上數(shù)英里。有一次,羅素半開玩笑地問這個在房間里踱著大步的學(xué)生:“你是在思考邏輯問題還是你身上的罪惡?”“兩個都是!”維特根斯坦不假思索地答道。1913年,維特根斯坦回到挪威一個偏遠(yuǎn)峽灣里的小村莊肖倫,在那里度過一個漆黑、漫長的冬季,一邊探索邏輯問題,一邊沿著村莊或通往山間的小徑散步。那土地貧瘠而堅定,與他所從事的思想工作非常般配,也就在那個冬季,他解決了關(guān)于象征主義探索真理作用的關(guān)鍵哲學(xué)問題。“我想象不出,我在別的地方也能像在這里一樣專心工作,”他在后來給妹妹的信中寫道,“在我看來,我已經(jīng)產(chǎn)下了自己體內(nèi)的新思想。”維特根斯坦用來表示思想的詞Denkbewgungen是生造的,大體可以譯作“思想行動”“思想路徑”或“思想之路”:思想,經(jīng)由沿著一條路而來人間。
在托馬斯·克拉克一首默默無聞的詩作中,一位行人沿著一段海濱來到一個地方,這里的石級“在巖石上雕刻而成/一直伸人水中”,旁邊是一片沼澤。詩歌接受了石級的邀請,那位行人想象著“下到海里/進(jìn)入另一種知識/荒涼而寒冷”。這里影射的是伊麗莎白·畢肖普的偉大詩作《在魚莊》。魚莊的房子慢慢探人紐芬蘭的某個港口那“灰暗、清澈、冰冷的水中”:那水“像我們想象中知識的模樣:/黑暗、咸澀、清澈、流動,完全自由自在”。而我想,畢肖普也是在模仿,模仿的是華茲華斯1815年那句人如何能接近“理性的深淵”:一個深奧的國度“心靈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下沉到那兒——而是必須踩著思想的階梯一步步下到那里”。這三首詩彼此互為應(yīng)和——是它們自己的一行腳印或一連串階梯。腳步、知識和記憶三者問最廣為人知的聯(lián)系是澳大利亞土著人的歌行觀。根據(jù)這種宇宙發(fā)生學(xué)觀點,世界是在一個叫夢幻時間紀(jì)里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時,先祖?zhèn)儼l(fā)現(xiàn)地球是個黑暗、平坦、毫無生機(jī)的地方。他們開始走出這個非地。他們一邊走,一邊開挖地球表面的硬殼,釋放地下沉睡的生命,于是大地隨著他們的步子開始煥發(fā)生機(jī)。布魯斯·查特文在他有瑕疵但影響很廣的描述中解釋道:“每個如圖騰般的祖先,在走過大地時,都認(rèn)為沿自己的腳步撒下一串文字與音符。”依據(jù)它們落腳的地方,這些步調(diào)就與特定大地的特征聯(lián)系起來。因而,世界就被“夢幻小路”覆蓋了,它們“覆蓋在大地上,成為交流的‘途徑”,每條小路有相應(yīng)的歌。澳洲大陸,照查特溫的說法,因此可以被視為“集合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如意大利通心面般扭動,每個‘篇章都是可以用地質(zhì)學(xué)術(shù)語讀懂的”。因此,唱出歌謠——到今天依然是讓它們勉強留存下來的方式,雖然每一代歌謠都在遺失——于是唱出歌謠也就是找到自己的路,講故事和步行是不可分割的。思想與步行的關(guān)系在語言史中浸染很深,也許演示了就我所知的最宏大的詞源學(xué)。這條軌跡從動詞to learn(學(xué)習(xí))開始,意為“獲取知識”。從語言史角度上溯,我們發(fā)現(xiàn)了古英語中的leornian,意為“獲得知識,教化”。從leornian開始,這條路徑進(jìn)一步向過去延伸,進(jìn)入原始日耳曼語滿是摩擦音的盤根錯節(jié)中,指向liznojan,該詞有個基本義項是“跟隨或找到一個痕跡”。因此,“學(xué)習(xí)”究其根本而言——究其發(fā)展路線而言——意思是“沿著一條路徑”。誰想得到呢?反正我之前不知道。要感謝那些詞源探究者,是他們揭示了那些消失了的路徑,將“學(xué)習(xí)”與“沿路徑而行”之意聯(lián)系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