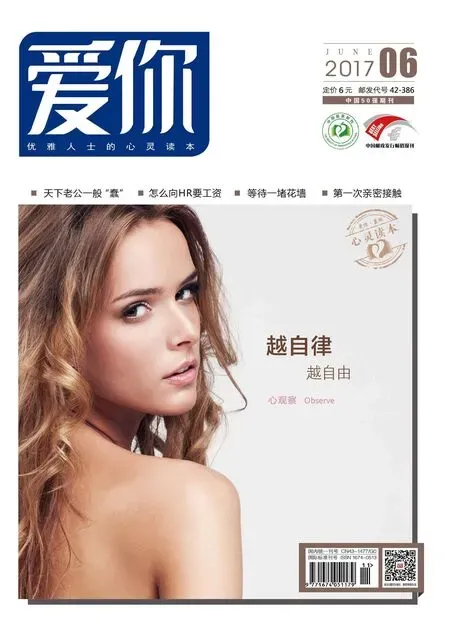我的美國爸爸
◎ 盛林
我的美國爸爸
◎ 盛林

菲里普第一次來中國看我前,他家里分成兩派——以他母親安妮為首的反對派和以他父親鮑伯為首的贊成派。反對派聽了太多有關中國的壞話,怕菲里普這一去,再也回不了家;贊成派則認為,為了真愛,哪怕赴湯蹈火也值。菲里普出發前,鮑伯只對他說了一句話:“兒子,祝你好運!”
菲里普從網上發給我一張鮑伯的照片,鮑伯英俊瀟灑,微笑地看著我。這是我最早認識的鮑伯,還沒見面,他的真情和微笑如和煦春風般輕輕吹動我的心。
來到美國,見面的第一天,鮑伯抱住我,說:“林,你終于來了,從此你就是我的女兒,希望你喜歡美國,喜歡你的新家。”
而這個時候,70歲的鮑伯身患癌癥和帕金森病5年了,他的癌細胞擴散到全身骨頭、腦部、血液。由于帕金森病,他行走需要拐杖,發音困難,口齒不清。醫生說他已無藥可治,只剩下兩年時間了。
但我每次看到他,他總是面帶微笑,輕柔地問我過得好不好,中國的父母好不好。家庭聚會時,大家搶著說話,一片熱鬧,但我一開口,大家一下就安靜了,一起看著菲里普,因為大家聽不懂我的中國英語,要請菲里普做翻譯。這時,鮑伯笑著對我說:“林,沒關系,我說話他們也聽不懂,我倆成立中美組合吧。”大家一聽都笑了。
我喜歡和鮑伯聊天,我聊我的家庭,聊杭州風景,他聊他的過去。他告訴我他當過9年炮兵,當過20年石油勘采工程師,當過10年農場主。他口齒不清,我只能聽懂兩三分,而我的話,他也只能聽懂兩三分。我們都不介意,聽不懂也會說yes。別人看我們說說笑笑,妒忌地問:“你們在聊什么呢,這么高興?”鮑伯把手指放在嘴上對我“噓”一下,說:“這是我和林的秘密。”
其實我知道,他怕我遠離家鄉,在新的家庭有孤單感,他要張開他的翅膀給我父親般的保護。他好幾次對我說:“林,我的女兒,只要我活著,我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我會像父親一樣愛你。不管發生什么,記住,我在你身邊。”聽了這話,我抱住他說:“謝謝您,爸爸。”
(摘自《嫁給美國》譯林出版社 圖/胡蟲蟲)但我就是覺得社會上也不都是陰暗面,網上說得太陰暗了,總宣傳陰暗面,把人都教壞了。多宣傳一些光明的事情有什么不好?宣傳光明才能促進積極的事。”
“媽,媒體不是宣傳,是報道真實。”我說,“光明或陰暗,存在就是存在。”
“那也要講光明才對嘛。”媽媽說,“總宣傳陰暗的東西,社會會越來越陰暗。”
我低下頭繼續剝毛豆。媽媽是會贊同關閉掉BBS或者禁止一些言論的,她那么認真地希望社會充滿光明,充滿積極向上的力量,哪怕是紙上或屏幕上的。可是這個時候我不想爭論這些,這是爭不出結果的,誰也不會改變自己的態度。這些爭論是我們的差異,但它們不再是決定性因素。我轉換了話題,跟媽媽談起她的健康,談起她的血糖和腿腳水腫,談起飲食和藥。
毛豆越來越少,露出了金屬盆光滑的底部。我有一點遺憾,如果毛豆能一直重復著剝到無窮,我們就一直這樣說話,也許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摘自《生于一九八四》電子工業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