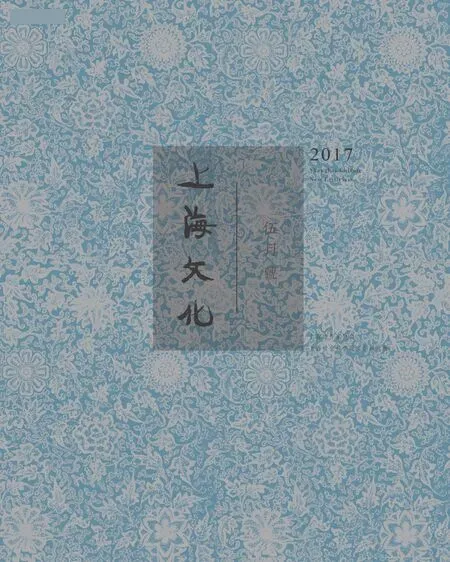蘇格拉底之凝神①
肖有志
蘇格拉底之凝神
肖有志
柏拉圖對話大多以蘇格拉底為主角,其主要形象是個對話者。而在《會飲》中我們發現了蘇格拉底或獨自或在大庭廣眾下沉思的形象。
據阿波羅多洛斯轉述阿里斯托得莫斯的敘說,蘇格拉底在從體育館前往阿伽通家的路上碰到阿里斯托得莫斯,蘇格拉底勸說阿里斯托得莫斯一塊去阿伽通家參加宴飲,隨后倆人一塊上路,路上發生了故事——蘇格拉底在路上發呆,就像是我們現在的表情包“我想靜靜”。
一
卻說,他們前行,蘇格拉底不知咋地乃凝神于己,落下了。于是,他等著,蘇格拉底催他先行前去。而當他出現在阿伽通的宅邸后,發現門敞開著。他說,真當場撞上可笑的事兒,因為里頭的男仆即刻迎上他,把他領至其他人躺臥的地方,發現他們已經就要進餐,而阿伽通于是即刻瞧見他。喲,他說,阿里斯托得莫斯,來得好,正好一塊兒用餐吧!而倘若你為了其他什么事而來,往后拖拖。說真的,昨天我還找你,以邀請你,確實沒能見著你。可你怎么沒把蘇格拉底給我們帶來?
而我,他說,轉身不見蘇格拉底跟著,因而我說,我自個兒和蘇格拉底一道來的,我被他邀請來這兒赴宴。真好耶!他說,可這人在哪兒呢?
他剛剛走在我后頭,而我自個兒也詫異于他會在哪兒。
不去瞅瞅嗎,他[阿伽通]說,小童,阿伽通說,甚而把蘇格拉底引進來。你呢,阿里斯托得莫斯,他[阿伽通]說,挨著厄里克希馬庫斯躺吧。接著他說,一個男童領他洗漱,而男童中的另一個來傳報,你的蘇格拉底在隔壁家,退進鄰居家的門廊,靜立不動,而我請他時,他不肯進來。

我們的內心有個特點——既封閉又開放。蘇格拉底凝神于己像似封閉自己,實則開放自己。蘇格拉底有兩個很著名的說法“認識你自己”和“關心你自己”(參《阿爾喀比亞德前篇》)。一個人要關心自己,先要認識自己。可以說,凝神于己就是認識自己,進而,凝神于己實質上亦包含關心自己——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
蘇格拉底走著走著,停下來,凝神于己。在柏拉圖大多數的作品中,很少有這樣的細節,但在這個關于愛欲的作品中出現了兩次。蘇格拉底私下干什么,柏拉圖一般不寫,主要寫他與別人對話。而蘇格拉底凝神于己跟隨后小童看到他靜立不動相關。蘇格拉底說自己害怕人群,但答應阿伽通去參加少數人的聚會,在人群與少數人中間蘇格拉底自個兒凝神于己。我們可以猜想,阿里斯托得莫斯天天跟著蘇格拉底,模仿他赤腳,聽蘇格拉底聊天,可他也凝神于己嗎?
顯然,蘇格拉底并不在乎自己要和誰一塊走,要為誰辯護,他不經意地凝神于己。
蘇格拉底催他先行前去:這時候阿里斯托得莫斯以為蘇格拉底還跟著。
宅邸:表明阿伽通的貴族身份。
發現門敞開著:在《普羅塔戈拉》這個作品中,也是很多人的聚會,但門是關著的。這里門開著,有人說阿伽通有意營造自由平等的氣氛,但是這并沒有打消阿里斯托得莫斯感受到的尷尬。之后,厄里克希馬庫斯提議把門關著;后來,門又被阿爾喀比亞德和一群夜游神敲打開;最后,又來了一大群夜游神,有人剛出門,他們涌進來了。劇終時,蘇格拉底把阿里斯托芬和阿伽通侃入睡后,蘇格拉底起身離開阿伽通家,阿里斯托得莫斯像慣常一樣跟著。蘇格拉底回到呂凱宮,又洗了個澡,消磨了一天,傍晚時分回家歇著。
而阿伽通于是即刻瞧見他:尷尬的是,不僅男仆領他進去了,可見男童知道可能阿里斯托得莫斯是誰;再來,也尷尬的是,阿伽通即刻看到他。阿里斯托得莫斯的尷尬,也可能是其自知。阿伽通說,有約過阿里斯托得莫斯,但其實并沒有。阿伽通說的是客套話。阿伽通看來并不把阿里斯托得莫斯放在眼里,如此阿里斯托得莫斯的出現似乎是個意外。
正好一塊用餐吧!而倘若你為了其他什么事而來,往后拖拖:來的目的是一塊吃飯、喝酒,阿伽通不知道阿里斯托得莫斯因何而來,事實上阿里斯托得莫斯也沒有別的目的。但是阿伽通這個人很有禮貌,他認識阿里斯托得莫斯,就邀請他進來,同時也消除了阿里斯托得莫斯的尷尬。阿伽通展現其禮儀、禮節上的賢人風范。
說真的,昨天我還找你,以邀請你,確實沒能見著你:這是句假話,詩人說假話駕輕就熟。在阿伽通眼里阿里斯托得莫斯不是個賢人。再者,阿里斯托得莫斯天天跟著蘇格拉底,但被阿伽通分開。而蘇格拉底又把自己和阿里斯托得莫斯連在一起,阿里斯托得莫斯是被蘇格拉底邀請來的。
可你怎么沒把蘇格拉底給我們帶來:此處是要害。阿伽通看到阿里斯托得莫斯就想到了蘇格拉底。在別人眼里,阿里斯托得莫斯是雅典最熱戀蘇格拉底的人。蘇格拉底雖然出身平平,但在雅典看來是個名人,好像也被視為賢人。在《云》中,阿里斯托芬嘲笑蘇格拉底,可見蘇格拉底和悲劇詩人、喜劇詩人都有關。阿伽通、阿里斯托芬、柏拉圖的出身都是比蘇格拉底高貴很多。蘇格拉底并沒有因為出身低,被人看不起,反之,阿里斯托得莫斯因為出身低,被人看不起。蘇格拉底沒被別人看不起可能與其智慧有關,而他的智慧恰恰也使他出問題。控告蘇格拉底的人中有詩人,如此蘇格拉底的身份相當尷尬。阿里斯托得莫斯并不真正地尷尬,蘇格拉底才是真正尷尬和可笑的人。蘇格拉底出身低,但是被出身或身份很高的人看重。出身很高的人要與蘇格拉底比智慧,蘇格拉底并且被出身很高的人控告、判死刑,其中有含混與矛盾之處。
而我,他說,轉身不見蘇格拉底跟著,因而我說,我自個兒和蘇格拉底一道來的,我被他邀請來這兒赴宴:這會兒阿里斯托得莫斯為自己辯護,之前蘇格拉底口頭上答應替他辯護。
真好耶!可這人在哪兒呢:阿伽通并不關心阿里斯托得莫斯被誰邀請來,關心的是蘇格拉底在哪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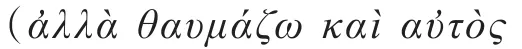
小童:是阿伽通家的男仆。阿伽通讓小童去找蘇格拉底,并且讓把蘇格拉底領進來。
挨著厄里克希馬庫斯躺:在這場會飲中,贊頌愛神是從左到右按順序來的,躺的順序至關重要的,再來阿伽通為什么安排阿里斯托得莫斯和厄里克希馬庫斯躺在一塊?這場會飲在贊頌愛神的過程中本來是阿里斯托芬先贊頌,但是他打嗝,厄里克希馬庫斯代替了他,所以,有人認為厄里克希馬庫斯和阿里斯托芬是可以互換的。因為喜劇詩人和醫生都很喜歡自然學,所以兩個人可以互換。而阿里斯托得莫斯為什么可以跟厄里克希馬庫斯躺在一起?為什么阿里斯托得莫斯沒有贊頌愛神?阿伽通則與蘇格拉底躺在一塊,最后阿爾喀比亞德進來,蘇格拉底、阿伽通和阿爾喀比亞德三個人擠在一張榻上,阿爾喀比亞德躺在中間。
阿里斯托得莫斯在此后的講述中漏掉了一些人,連自己也漏掉了。這場會飲看起來秩序井然,但背后其實有很多混亂的東西。《會飲》中有三場會飲,第一場是贊頌愛神;第二場是阿爾喀比亞德先贊頌蘇格拉底,但只開了個頭,就被蘇格拉底和夜游神打亂掉了;第三場會飲是蘇格拉底、阿伽通、阿里斯托芬三個人的會飲。第一場被阿里斯托芬打嗝的生理反應打亂,也有阿里斯托得莫斯記憶的問題,漏掉了很多。前兩場是不完整的,只有第三場是完整的。可是第三場的內容并不清楚。而第一場的主題是愛若斯,在其頂峰中蘇格拉底贊頌愛若斯,實質上他贊頌自己;第二場阿爾喀比亞德贊頌蘇格拉底;第三場是阿里斯托芬、阿伽通與蘇格拉底PK,最后蘇格拉底勝出。如此看來其中仍有其秩序。
領他洗漱:不僅是洗腳。平時阿里斯托得莫斯和蘇格拉底一樣赤腳,可這回蘇格拉底穿了便鞋。
來傳報,你的蘇格拉底在隔壁家:向阿里斯托得莫斯傳報,“你的蘇格拉底”,小童也把阿里斯托得莫斯和蘇格拉底聯系在一塊。

禪宗有“入定”之說,入于禪定。《金剛經》“如如不動”之說。基督教亦有“靈修”一說。
蘇格拉底靜立不動,可能在發呆,放空自己——無思無為。《論語》中顏淵“屢空”。阿伽通則把蘇格拉底靜立不動看成是獲得智慧的過程。
“退”,參老子《道德經》“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身體撤退,以退為進。蘇格拉底不著急去阿伽通家,飯吃到一半才到,而阿爾喀比亞德晚到的原因是繁忙和飲酒。
關于“凝神于己”和“靜立不動”,還出現在220c3-d5,阿爾喀比亞德贊頌蘇格拉底。他說蘇格拉底是個勇士,冬天不穿鞋在冰山走,夏天的時候靜立出神地想,持續一天一夜,出現五次“靜立不動”這個詞,并向太陽禱告。在柏拉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蘇格拉底三次禱告,兩次出現在《斐德若》的中間先向愛神、對話的尾聲向潘神禱告,一次是這里向太陽神禱告。此處蘇格拉底靜立不動,伊俄尼亞人很好奇,只有阿爾喀比亞德不好奇,阿爾喀比亞德把蘇格拉底看作是堅強的勇士,忍受和歷經的各種事情。蘇格拉底沉思,一群人在圍觀。而此時蘇格拉底獨自沉思,起先阿里斯托得莫斯打擾他,催他前行;后來小童打擾他,邀請他進阿伽通家。
阿伽通家有很多小童,他讓一個小童去叫蘇格拉底,沒叫得動。
忒出位嘛,他[阿伽通]說,你說呢,難道你不請他?可別讓他溜掉?
于是他[阿里斯托得莫斯]說,他說:別別……而聽之任之吧,因為他有這般習性。他出離,靜立于他碰巧在的地兒。他一會兒定會到,在我看來,所以別動他了,而聽任之吧。
他[阿伽通]說,那只好這樣做吧,倘若你這么認為。他說阿伽通這么說,孩兒們哦,那款待我們其余人吧!你們能想到的都擺上,無論何時誰都不曾指使你們,偶從不指使你們,今個兒還這樣,就以為連我以及在座的其余人都被你們邀請來赴宴,好好待客吧!以讓我們給你們點贊。

可別讓他溜掉:在《王制》第一卷開頭(327c)蘇格拉底正要從佩萊塢港回雅典,一伙人把他強行留下來,也是一個小童扯住蘇格拉底的大衣,不讓他溜掉。蘇格拉底在我們眼里是哲人,但在小童眼里不是。第五卷(449b)開頭蘇格拉底的同伴們強迫他討論關于婦女和兒童的共產制問題,不讓他溜掉。蘇格拉底時常受到別人強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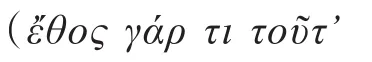
剛剛說了可以將這里的“習性”翻譯為“天性”,準確來說,蘇格拉底的習性就是他的天性。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的轉向就是要探究哲人蘇格拉底的習性,即其性情學或倫理學,而不是現代意義的普遍倫理學。后來,亞里士多德及其弟子區分習性、習慣與天性。我們一般認為習性是學習養成的,《大戴禮記·保父》中有句“少成若性,習貫之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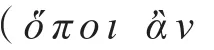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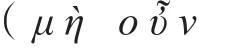
那只好這樣做吧:阿伽通聽從阿里斯托得莫斯的勸告,不讓小童去打擾蘇格拉底,但答應得有點勉強。蘇格拉底還沒有到阿伽通家,兩個人的緊張關系就已經存在,接下來倆人直接沖突。
偶從不指使你們:有人說這是阿伽通的民主做派,之后阿伽通讓小童作“主人”。但實際上阿伽通曾指使一個小童去叫蘇格拉底,且阿伽通的修辭帶有命令式語氣。阿伽通擺出民主做派,背后還有一層意思——阿伽通家的男童訓練有素,很會招待人,炫耀主人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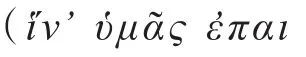
二
蘇格拉底還沒到,阿伽通和蘇格拉底的緊張關系已經存在。他們的關系繃得很緊,就像悲劇中的人物沖突,《俄狄浦斯王》第一場戲,先知不愿意來,因為他業已知曉,碰見俄狄浦斯必然與其沖突。他來了又不說話,俄狄浦斯被激怒了,罵先知,先知反過來也罵俄狄浦斯,并在倆人的咒罵聲中把真相吐露出來——俄狄浦斯弒父亂倫。俄狄浦斯懷疑先知之所以這么說是被克瑞翁收買了,倆人圖謀篡奪王權。此時,克瑞翁與俄狄浦斯的緊張關系已經潛藏著。第二場一開始,克瑞翁對俄狄浦斯氣憤不已,急沖沖地上場。人和人的關系有些不是直接的而是隱藏著,自然而然存在。而蘇格拉底與阿伽通的沖突,是這出戲的最重要的沖突——詩人和哲人的沖突,是人群中最高的兩類人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表面上看是生活方式的沖突,蘇格拉底靜立不動,而阿伽通搞悲劇演出,是個喜歡熱鬧的人;實質上是因天性和性情的差異而導致沖突。詩人和哲人還是社會學意義上人群的分類,兩種天性、性情則是靈魂學意義上的自然區分。蘇格拉底的生活方式是獨自沉思,阿伽通的生活方式是作秀,與高爾吉亞一樣——搞炫示性的演說。沉思的生活與榮譽沒有關系,哲人純粹地熱愛智慧和熱愛自己——無為名尸,圣人無名。
他說,此后他們進餐,而蘇格拉底還沒進來。于是,阿伽通幾次催人去召請蘇格拉底來,他則不許。接著,他不長時間,就同其慣常消磨生活時光一樣長,他到了。而他們差不多吃到一半了。接著,他說,阿伽通——因恰巧獨自斜躺在最邊上的[榻上]——喊道,這兒,這兒,蘇格拉底,躺我邊上來,好讓偶觸碰,以享用,在隔壁前院降臨你頭上的智慧,很明顯,你已發現且擁有它,不然你不會起身離開它。
于是,蘇格拉底入席,且答道:要是這樣就好啰,他[蘇格拉底]說,阿伽通噢,如果智慧是這般的,就如從盈滿者涌流向我們中較空虛者,假如我們互相觸碰,如同酒杯中的水經羊毛由較滿的涌流向較空的(杯子)。因為如果智慧也這樣的話,偶會高估躺在你邊上進餐,因為偶相信偶將被來自你的多而美的智慧注滿。因為我的智慧或許是某種低微的東東,甚或難以分辨,如同是夢(或夢幻泡影);而你的呢,耀眼奪目,而且能大展宏圖,你年紀輕輕,來自于你的智慧這般光芒四射,且前天它驚艷亮相于超過三萬希臘人的見證中。
你個肆心之徒,他[阿伽通]說,蘇格拉底哦,而待會兒,偶將與你斷斷這關于智慧(之案),待會兒再來,先吃飯,我們讓狄奧尼索斯當裁判官。這會兒呢,你先進餐。
蘇格拉底在飯吃到一半的時候才來,很明顯他并不是一個吃貨。我們可以猜想阿伽通家的晚餐肯定很精美。
他則不許:前面阿里斯托得莫斯已經阻止過一次了,阿伽通仍然多次催他的小童去請蘇格拉底,都被阿里斯托得莫斯阻止了。阿伽通表現出他與其小童們很民主很平等可是他對待蘇格拉底甚且不如他與小童們平等。當然,蘇格拉底靜立不動與阿伽通催促也可見他與倆人關系確實緊張,越是催促,愈發緊張。
他到了:蘇格拉底沒有早到,也不是等飯吃完了才到,飯吃到一半他到了。這說明蘇格拉底靜立不動,消磨時光,仍然懂得分寸和禮節,知道吃頓飯要多少時間。畢竟這是賢人們的聚會,有其禮儀和規矩,進餐、祭神、飲酒……
最邊上的[榻上]:阿伽通躺在最邊上的榻上,因為他是主人;后來我們看到實際上躺在最邊上的可能是蘇格拉底,因為蘇格拉底是最后一個贊頌愛神的人。看來蘇格拉底多多少少有點反客為主的意味,可這可能由于偶然——因阿伽通恰巧獨自斜躺在最邊上的榻上。后來,阿爾喀比亞德到來,三個人躺在一塊榻上。一開始阿爾喀比亞德躺在蘇格拉底和阿伽通之間,后來蘇格拉底提議讓阿伽通躺在中間。阿伽通正躺下,一大群醉醺醺的夜游神見門開著,一涌而進,到處亂躺,秩序全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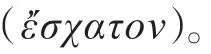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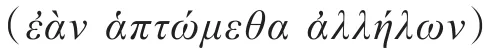
其中最重要的是“碰觸”一詞。“碰觸”表面的意思是阿伽通與蘇格拉底躺在一塊。
“碰觸”這個詞,在阿伽通的講辭中出現過三次(195e7、196c1、196e3)。
[195e7]既然愛神不僅用腳、而且簡直就是只碰觸柔軟得不能再軟的東西,他哪會不是最輕柔的呢。愛神是最輕柔的,阿伽通這里說的是愛神的品性,只碰最柔軟的東西。
[196c1]愛神的美德。最重要的是,愛神就不傷害神或人,也不受神或人傷害。即便愛神自己會遭受點什么,遭受的也不會是強制力——強制力觸碰不到愛神。
[196e3]這位神的正義、明智和勇敢都已經說過了,還剩下他的智慧要說。對這一點,我們得盡量不要有所遺憾。首先,像厄里克希馬庫斯崇敬自己的技藝一樣,我也要崇敬自己的技藝,說這位神是詩人,正是他太聰明才制作出詩人。“一個人即便以前對繆斯一竅不通”,一經愛神觸碰,馬上就會成為詩人。
第俄提瑪給蘇格拉底的教誨提到兩次:[209c2]、[211b7]
[209c2]依我看,這類人去觸動這位美人、與他親密相交,就是在讓自己孕育已久的靈魂受孕、分娩。
[211b7]也就是說,誰要是由那些感官現象出發,經正派的男童戀逐漸上升,開始瞥見那美,他就會美妙地觸及這最后境地。
觸及這最后境地,也就是可能碰觸到這最高目標。
阿爾喀比亞德提到兩次(221b5、221b8),他贊美蘇格拉底在戰場上撤退時,誰不敢碰他一下,不敢惹他、冒犯他。
“碰觸”在《斐德若》中也出現兩次(255b7、255e2)。
[255b7]當愛欲者繼續堅持[展示蜜意],通過在體育場和其他交往場合的身體接觸[相互]親近,最終,那股涌流之泉——宙斯愛欲伽尼墨得斯時叫它“情液”——澎湃地涌向愛欲者,一些沉入他自身,一些[在他身上]滿溢后流出來。就像一陣風或某個回音從一些平滑而堅硬的東西那里又蹦到原來促發的地方,美的涌流通過[有愛欲者的]眼睛再次走向美人,并自然而然走進他的靈魂,抵達[靈魂]時便振起[靈魂的]翅羽。[美的涌流]澆灌翅羽的通道,促發生出翅羽,被愛欲者的靈魂轉過來也充滿了愛欲。
此處的“接觸”、“涌流”與《會飲》的比喻相似。有情人愛情伴,然后智慧像涌流之泉,通過看他,涌流之泉進入被愛的人的靈魂,反過來被愛的人也充滿愛欲,變成有情人。這可能就是蘇格拉底式教育。不過,《會飲》中蘇格拉底面對阿伽通似乎否定此舉。在這里阿伽通興許嘲諷蘇格拉底應該教給他蘇格拉底靜立不動獲得的智慧;蘇格拉底則認為自己的智慧很低微,不值得傳授,也有可能認為阿伽通不值得教。他和阿伽通是兩類人,阿伽通是高爾吉亞的學生。
再者,人的智慧盈滿或虛空嗎?第俄提瑪對蘇格拉底說只有神有智慧,那么神盈滿,反之,人虛空嗎?
第俄提瑪說愛若斯的父親是波若斯[豐盈]、母親則是珀尼阿[貧乏],愛若斯居于豐盈與貧乏之間。如此,愛若斯就好像是碰觸或羊毛。
“盈滿”和“空虛”可能涉及教育的根本問題,即智慧或德性是否可傳授。
因為我的智慧或許是某種低微的東東,甚或難以分辨,如同是夢:蘇格拉底把自己的智慧看得很低,把阿伽通看作是自己的老師。《高爾吉亞》中有政治人看不起蘇格拉底,因他常常與人別人談論低微、低俗的東西(485e,486c,490c,490e-491a)。參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1.2.32-37與40-47比較;另參《會飲》221e-222a,阿爾喀比亞德對蘇格拉底的贊頌。
夢,如果蘇格拉底把自己的智慧看作是夢,那么跟接下來第俄提瑪的教誨可能相關,愛若斯恰如正確意見居于智慧與沒學識之間。柏拉圖的其他作品中蘇格拉底講自己做夢,比如《克力同》;再如《斐多》60e-61a,蘇格拉底對畢達哥拉斯派的年青人刻貝斯說:“事情是這樣的:在我走過的一生中,同一個夢不斷造訪我,情境顯得有時是這樣,有時那樣,但說的是相同的事情——‘蘇格拉底啊,’夢說,‘作樂吧,勞作吧。’我呢,從前一直以為,這是夢在不斷鼓勵我做已經做的那件事,鞭策我,就像人們激勵在跑的人,這夢不斷鞭策我做已經在做的事情,這就是作樂。因為熱愛智慧就是最了不起的樂,而我一直在做這個啊。”對蘇格拉底來說作夢、作樂、熱愛智慧相關聯。
你已發現且擁有它:蘇格拉底沒有說自己擁有智慧,只說自己愛智慧,只有神擁有智慧的人。參尼采《善惡的彼岸》294、295,諸神也熱愛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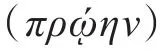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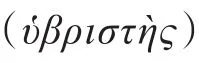
很明顯,阿伽通和蘇格拉底兩人正式見面后沖突得更厲害,并且隨后沖突不斷。
從荷馬到悲劇詩人,他們最高的主題是諸神,詩人智慧的象征、代表是諸神,誰理解的諸神最好、最完整,誰的智慧最高。可是哲人并不這樣認為,他們反思詩人的諸神——quid sit deus,把諸神變成一個標準的哲學問題。如此,諸神是詩人和哲人共同的最高的主題。當然,荷馬塑造的諸神是希臘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生活秩序;亦即詩人創造了諸神,也創造了希臘人的生活方式。諸神就是禮法,就是生活規矩,是共同體生活。可是哲人的意圖首先是明白自己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而不是共同體的生活。當然,哲人也探究共同體的生活,比如《王制》、《法義》等等。而詩人,特別是古典時代的詩人,對個人的探討比較少,他們似乎更關心共同體的生活。因而,詩人和哲人會有沖突和矛盾。反過來講,哲人思考自己的生活之正義,就要反思諸神的品性。按阿伽通來講這就是哲人的肆心、狂狷。
阿伽通這樣的悲劇詩人其實也是肆心之徒,但他先罵蘇格拉底肆心。顯然,肆心承接之前的智慧問題,其背后是諸神問題,從這個作品來看可能就是愛若斯問題。
我們讓狄奧尼索斯當裁判官:有人認為,這個裁判官就是后頭突然闖入阿伽通家的阿爾喀比亞德。阿爾喀比亞德給阿伽通系上飄帶,贊賞他最有智慧;后來他突然發現蘇格拉底,阿爾喀比亞德又從阿伽通身上分了一些飄帶給蘇格拉底,因為蘇格拉底更智慧。這說明這個政治人更靠近哲人,而不是詩人,他不是一般的政治人(參色諾芬《回憶蘇格拉底》1.2. 40-47),另外的一層意思是,這個作品的基本面貌是六個雅典人在一個悲劇詩人家依次贊頌愛神,某種意義上他們在進行類似于悲劇的競賽。最后阿爾喀比亞德的突然出現,又使得劇情像是喜劇。他贊頌蘇格拉底,把蘇格拉底比作薩圖爾,而薩圖爾劇恰恰是悲劇演出時作為喜劇最后演出的。
蘇格拉底和阿伽通的沖突暫時停歇,被吃飯取代。
結 語
這段故事主要的線索是蘇格拉底去阿伽通家赴宴的路上凝神于己、靜立不動。而阿伽通讓一個小童去叫蘇格拉底,沒叫得動,隨即多次叫喚小童試圖打擾蘇格拉底,被阿里斯托得莫斯攔住,他說這是蘇格拉底的習性。蘇格拉底到了后,阿伽通以為蘇格拉底靜立不動已經發現了智慧而且有了智慧,把蘇格拉底招呼至自己的榻上,兩人近距離相處以碰觸蘇格拉底獲得智慧。實則兩人拌起嘴來,關乎兩人智慧的品性問題。蘇格拉底一進場就暗中奚落了主人阿伽通的智慧一番,弄得阿伽通罵他是個肆心之徒,準備跟他就智慧打官司。
顯然,蘇格拉底之凝神與其習性、天性,進而與其智慧相關,最終似乎使得蘇格拉底在喜劇詩人(參阿里斯托芬的《云》)乃至悲劇詩人看來皆是肆心之人。在之后的這場關于智慧的官司中,通過贊頌愛若斯,蘇格拉底完全展露了自己的肆心。
正如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言:Ethos anthropoi daimon。蘇格拉底凝神、沉思之習性(Ethos)或天性,就是其愛欲(eros)其命神(daimon),亦是其肆心。
對蘇格拉底來說,被判死刑是俗世生命的終結;而在神面前,蘇格拉底遵從由神諭引發的探究凡人之智慧的使命;對于自己,他一生都在認識自己的命數,沒有改變,也不順從。蘇格拉底服刑、服從現世法律,可謂聽命;蘇格拉底虔敬地遵從神諭轉而探究人與人世,可謂改命;蘇格拉底認識自己則是其自然而然的生命歷程,可謂知命。
這或許是蘇格拉底之命運互相關聯的三層含義,其中最重要也最難理解的是認識自己,實質上是蘇格拉底之愛欲。蘇格拉底不斷檢驗自己的生命熱情、愛欲,以使之走上正道——思無邪,一輩子可能過得圓滿——吾道一以貫之。愛欲的圓成亦是命的圓成。所謂正位凝命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甚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 。
蘇格拉底之凝神有如孔夫子之好學——樂在其中且樂以忘憂。
① 本文譯文依據Sir Kenneth Dover注疏本,Plato, Sym posium,Cambridge,1980;參考Seth Benardete英譯文,Plato’s Symposium,Chicago,2001;劉小楓編修本《會飲章句》(未刊稿);劉小楓編/譯,《柏拉圖四書》,北京三聯書店,2015;講疏得益于施特勞斯講課稿,《論柏拉圖的<會飲>》,邱立波譯,華夏出版社,2012;伯納德特,《柏拉圖的<會飲>義疏》,何子健譯,收于劉小楓等譯《柏拉圖的<會飲>》,華夏出版社,2003;羅森,《柏拉圖的<會飲>》,楊俊杰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②參色諾芬《會飲》2.16-19,有人看到蘇格拉底在屋里獨自跳舞驚呆了。
編輯/黃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