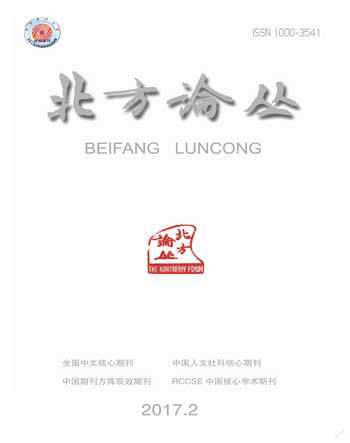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社會治理模式的困境與出路
吳瑩
[摘要]我國鄉村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發生了深刻變革,在社會結構上體現為開放性與流動性、在權力結構上體現為自主性與多元性、在農民身份角色上體現為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在鄉村社會治理層面,開放流動的鄉村社會現狀與“封閉排他”“城鄉二元”和“計劃行政”等傳統鄉村社會治理模式形成了明顯張力,需要以多元主體協商對話機制、農村經濟體制模式和“契約性整合理念”為進路,構建轉型期鄉村社會治理機制優化路徑。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社會基礎,鄉村社會治理是基層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參照,在推進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需要準確研判社會問題,并在國家治理層面推進社會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
[關鍵詞]社會轉型;鄉村社會治理 ;國家治理
[中圖分類號]D6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3541(2017)02-0130-05
Abstract: China's rural societ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t manifests openness and mobility in social structure, autonomy and diversity in power structur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lifestyle change in role of farmer's identity. I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open and flowing rural society forms a clear tension with traditional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such as “seclusion and exclusion”,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planning administration” and so on. It needs to construct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with multiple subject consultation and dialogue mechanism, rural economic system model and contractual integration as access.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the abi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ccurate judgment of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promotion of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multi subject 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re required in promoting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process.
Key words:Social Transformatio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一、引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偉戰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入了嶄新的歷史階段。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成為這一歷史階段的總體話語,市場經濟以其資源配置方式和價值觀念重塑為中國發展提供了經濟和思想上的不竭動力,以民主法治主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國政治建設提供了結構和觀念上的目標指引。
當代鄉村社會結構發生的系列變化導致傳統鄉村社會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呈現滯后性,鄉村社會自治在缺乏制度性供給保障下未能發揮應有功能。在社會轉型、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鄉村社會發生了哪些質性變革?傳統鄉村治理與上述變革形成的張力造成了哪些治理困境?如何以鄉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研究為視角考察國家治理與社會管理的相互關系?本文將對以上問題進行論述。
二、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社會的基礎變革
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推進,國家與社會正經歷整體轉型。鄉村社會正面臨結構性變革。表現為傳統鄉村社會結構變遷、權力結構演變和農民身份角色轉化。鄉村社會基礎的一系列變革導致城鄉二元分治逐漸合流,多元治理模式日漸生成,鄉土社會文化網絡日漸崩解。
(一)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遷
現代化發展正在削弱傳統鄉村社會的社會基礎,鄉村社會基礎的流變推動整體社會結構的變遷。開放性和流動性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這種開放性與流動性造成了鄉村社會的“去村落化”[1],傳統鄉村自然經濟解體,熟人社會網絡因市場化和工業化的沖擊日漸走向陌生化。鄉土本是一個以“差序格局”[2](p.25)為基礎的認同單位,在我國現代國家構建之前主要由鄉村精英進行治理,國家治權很難延伸到鄉土深處。但現代化進程打破了鄉村“堅硬”的自我治理機制,鄉村社會發生系列結構性變遷。新中國建立初期,社會架構穩固到略有僵化,排斥開放與穩定內向是這一時期鄉村社會主要特征。
改革開放后,國家對社會控制逐漸放松,市場經濟和政治領域放權加速了鄉村社會的轉型態勢。戶籍制度改革、工業化和城鎮化加快了鄉村社會的開放性,優良的基礎設施和快速發展的經濟吸引了鄉村居民大規模向城市流動,鄉村社會融合進現代化進程的大潮當中,但城鄉流動也同時造成了鄉村社會“空心化”等系列問題。在開放與流動社會中,城鄉邊界已經模糊淡化。當代鄉村既有本地農戶也有外地居民,村莊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以血緣為基礎的地理概念,逐漸形成現代意義上的“社區共同體”[3]( p.5)。市場經濟深入發展使鄉村組織中的經濟組織逐漸脫離集體社會組織,生產組織形式向多元化道路發展,組織間合作方式日趨多樣化。
(二)鄉村權力結構的演變
鄉村社區治理的提出與國家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尤其與國家權力在基層的配置結構高度關聯。從國家“強制權力”與“基礎權力”劃分視角[4]出發,探討國家權力在鄉村社會的延伸能夠清晰地看到兩種權力類型在鄉村政治中的運作態勢。同樣,鄉村社會權力格局配置轉換中創造的治理空間也會成為社會轉型變革的拓展場域。在國家“全能主義”[5]計劃經濟時期,國家依靠強制性權力對基層社會進行行政性整合,實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國家通過“行政下鄉”“政黨下鄉”[6]等方式,對鄉村公共事務進行干預,農民自治空間嚴重萎縮。
在權力結構和社會轉型關系視角中,社會轉型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以鄉村權力結構先行變遷為前提的。改革開放后,經濟體制改革帶動政治體制改革,鄉村權力結構開始解構調整。市場經濟逐漸瓦解機械的單方權力運行模式,開放流動賦予鄉村社會更多的自主性,國家權力對于資源的汲取也需要鄉村社會能夠擁有完善的經濟基礎。一元權力結構松動,鄉村社會進一步走向流動開放,農民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選擇權,多種經營和政策扶持豐富了鄉村經濟結構,同時奠定了多元主體參與國家治理的社會基礎,鄉村權力結構在開放社會中被賦予了更多靈活性和能動性。
(三)農民身份角色的轉化
社會轉型造成農民這一鄉村社會主體角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與環境在互動中彼此影響,社會環境的變化將農民從農耕中解放出來,職業身份發生轉變,繼而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自然也會發生相應變遷,農民群體逐漸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從農業轉移到其他非農產業,如從事經營性職業、外出打工、開展養殖業或者嵌入社會組織當中[7]。轉型期農民無論是在鄉村內部還是外出謀業,都已經不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范疇。
社會角色變化不僅僅停留在從業結構和生活質量這些表層現象上,農民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也在同步發生變化。城鄉兩地農民消費結構和消費方式逐漸由“緊衣縮食”,向“城市化消費”轉變,突出表現在更加注重通過商業交換的方式獲得物質上的提升,并且在精神消費上不斷向城市居民靠攏。農民在走向社會角色轉換的過程中,打破了傳統的血緣地緣、宗法鄉規等人際鏈條和傳統體制機制限制,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都在發生變化,自由平等、獨立自主、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觀逐步形成[8] 。 三、現代化進程中當代鄉村社會變遷造成的治理困境及挑戰 現代化的巨輪將鄉村社會卷入當中,社會轉型是社會結構和治理體系的全新變革。傳統鄉村社會正在轉型過程當中,鄉村社會基礎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遷。但是,作為國家治理基礎的鄉村治理仍然沿用傳統的治理模式,開放流動的鄉村社會現狀與封閉排他的治理形式形成了明顯的張力。
(一) “封閉排他”式治理困境
傳統鄉村結構是由國家運用強制性權力編織的封閉系統,鄉村內部和外部形成“圍城”,內外人員無法自由流通。傳統鄉村是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空間,村莊之間邊界明晰,個人成原子化分布于田間,農民有明確的身份,鄉村社會同質性很高[9]。在“行政性整合”[10 ]中,國家利用行政權力將自然村落打破,人為規劃合并出中國特色的行政村。行政村邊界由國家政策規劃文件劃定,這樣便形成了以行政村為治理單元的封閉性和排他性治理機制。
在鄉村社會發展中,鄉村與城市差異特征逐漸縮小。經社分離是當代村莊社會組織的總體演變趨勢,鄉村社會階層分布、利益構成、觀念體系和職業結構逐漸分化,身份認同逐漸降低,鄉村居住地人員開始內與外的雙向交流。但是,鄉村社會治理模式仍根據圈層社會結構,在橫向和縱向上進行分隔,以行政村為單位的治理場域將非本村身份居民排除在治理范疇之外。這樣就呈現出實踐中多元主體共存于鄉村社會的現狀,但目前治理模式下社會的分配正義得不到實現,居民仍根據身份在待遇上“內外有別”,造成群體間出現心理隔閡,各類社會矛盾和社會抗爭問題時有發生[11]。
(二)“城鄉二元”式治理困境
城市和鄉村是基層社會治理單元,二者的治理方式因承擔職能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城鄉關系在改革開放前由于工業化的需要,形成了鄉村支持城市,農業附屬工業的城鄉二元分制的治理格局,城鄉關系被基本割裂,沒有結成有機聯合體。20世紀90年代,國家開始支持城市開展自治活動,城市居民各項公民權利基本得到保障,政府在財政資金、政策待遇和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給予城市社區支持補助。
在鄉村治理實踐中,由于“汲取型”政權向“懸浮型”政權的轉化[12],鄉鎮政府對于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改革需求回應方式僅僅是合并村莊,用行政手段整合出“鄉村社區”,以鄉村管理區域的擴大換取管理單位的減少。但是,國家財政投入有限,嚴重影響鄉村服務設施建設和公共事務處理的財力保障,村干部由于承擔了大量行政事務也影響了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實。從鄉村社區和城市社區兩種基層社會治理單元的比較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城鄉二元分治的治理機制差異。在城鄉差別日益縮小的背景下,城鄉二元治理模式已經成為城鄉融合的主要障礙,鄉村社會已經陷入治理和發展的雙重困境。
(三)“計劃行政”式治理困境
“計劃行政”式治理模式困境在鄉村社會經濟組織和生產模式運行中表現尤為突出,學者分別從深化資本關系、提高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等治理進路出發探討治理行政化問題[13]。社會轉型必然造成社會組織形式的重構,為應對經濟體制變革和權力結構演化,改變農業生產組織方式,從自給自足的小農形式過渡到將各種形式組織“組織”起來[14] (p.4),可以提高利潤比重,節約交易成本,將資本要素融入農業生產當中[15]( p.48)。我國目前的鄉村經濟體制是以農村集體經濟為基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各種形式合作經濟為制度保障。但是,政經合一的傳統體制造成計劃經濟某些弊端不同程度呈現,政府在治理上趨于淡化合作,沿用傳統的單一“計劃行政”型治理模式,造成產權不清、財務不明、強制管理、責權不當、監管失靈等現象。所以,傳統集體經濟體制下的治理模式造成鄉鎮政府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關系沒有形成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合作關系,而是權力管控體制下的管制關系,致使出現一些鄉村負債過多,鄉村財務危機頻發,集體經濟組織發展遲滯等治理困境。
四、轉型期鄉村社會治理機制路徑優化
創新社會管理,優化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已經成為新時期社會治理重要內容,從社會轉型入手,以鄉村社會存在問題為導向,破解治理模式與社會轉型張力造成的治理困境,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治理機制,成為新時期改革發展的題中之義。
(一)建立鄉村基層治理中的多元主體協商對話機制
在快速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民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被動卷入進市場化、城鎮化和工業化當中,生活環境的急速變遷和公共生活空間中流動性和開放性要素參入必然造成熟人社會逐漸被陌生人社會取代,情感聯系也被利益考量所影響。在特殊時期,內外部力量共同塑造著社會基本面,利益導向、陌生社會、快速變遷和多元要素交織呼喚協商合作的治理模式,以適應治理的諸多困境。
現代社會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協作系統,單一主體已經遠遠不能完成治理任務,無論是浙江溫嶺民主懇談模式還是蘇州“政府+市場”模式,多元主體參與協同治理是化解矛盾、形成共識的重要手段。多元協商治理是鄉村社會治理的發展趨勢,也是在社會轉型發展中解決鄉村社會治理問題的重要方式之一,國家與基層社會關系重新調整,對于共同利益的達成和“善治”目標的實現都具有重要意義。鄉村社會治理問題也必須置于國家、市場、公民三維架構中去思考解決的辦法[16] 。
(二)放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打造集體層經營和多樣化經營相結合的經濟體制治理模式
對于鄉村面臨的諸多問題,經濟的發展是破解治理困局和累積合法性的鑰匙,而鄉村集體經濟是鄉村經濟體的基石,充分拉動內需,改善鄉村社會資本,就必須在治理中注重統分結合集體經營體制建設,平衡統分關系,立足壯大鄉村集體經濟,因地制宜采用聯合經營形式,增強集體經濟競爭力。
合作治理在鄉村經濟層面表現為多種合作經濟形式并存。目前,農村集體經濟還存在產權糾葛和行政干預等弊端,發展多種合作經濟有利于打破“計劃行政”式的傳統治理模式。農民應按照自愿原則組建經濟組織、法律明確產權剩余索取權歸農戶所有,市場依照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進行資源分配、圍繞人力資源和資本要素互聯統一架構體系,農戶可以通過市場競爭在商業交換中籌集資本,在零售和集體銷售價格差價上尋找機遇。靈活多樣的經營模式可以提高農戶生活水平,提升合作主體中農民地位,以適應社會轉型潮流,解決治理困境。這種被學者稱為“新型的統分結合的經營體制”[17]的經營模式和治理方式,對于轉型期鄉村社會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以“契約性整合理念”為進路,實現權力主體多元互動
社會轉型面臨的新問題預示鄉村基層社會對治理價值訴求發生了根本轉變。建國初期國家權力向鄉村社會全面滲透,國家全面壟斷鄉村資源,同時抑制甚至扼殺鄉村社會的其他權力,鄉村社會只有紙面上的民主,在實際政治過程中依舊是權力控制[18]( p.324) 。社會轉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重構鄉村權力結構體系,改變了鄉村社會在國家強制權力控制下運轉的單一軌道,遏制了行政權對鄉村社會的整合。多元化的權力主體互動必然與“統治”的控制型價值追求不同,轉型期社會結構和秩序的治理是以“契約型整合”[19]為目標追求。契約型治理以自治功能為強化點,依托村民自治和鄉村社會組織,已經成為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路徑。
在組織層面,通過對鄉村社會的再組織化來構造社會支撐要素,為契約型治理提供治理平臺和資源儲備。同時,組織化也是培養公民精神,提升農民在公共事務參與中的自主性和權利性的重要手段。基層民主最重要的實踐形式是農民參與社區事務治理,而契約型整合理念下的組織化恰恰為農民參與公共事務,訓練民主參與能力和培養公共精神提供了平臺。
在政府治理層面,契約型治理必然要求政府再造治理理念,更新管理方式手段,政府治理創新是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社會秩序根本變革的關鍵。契約型治理就是試圖跳出分析鄉村治理的“國家—社會”二元對立框架,探尋國家與社會彼此賦能、互動成長的“強國家—強社會”關系[20] 。在鄉鎮政府與基層社會治理格局構建中,政府效能提高是達至國家與社會“強強聯合”的實踐路徑。
在社會認同層面,傳統治理下農民社會認同不是出于自由意志和獨立判定,是在“生存依賴”的政治經濟控制下的被動承認[21]。在行政剛性的機械整合下,實現鄉村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必須理性分析轉型期社會需求,并在公共事務協商、鄉村經濟發展和治理主體關系等多維度下實現鄉村社會的制度性整合和認同性整合。余論:我國社會治理與國家治理體系的內在關聯 在我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戰略任務。國家治理是一個包容性概念,其中基層社會治理的體制性創新是國家治理體系的社會基礎,而鄉村社會治理正是基層社會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參照。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理論內涵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黨和國家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為應對國家與社會改革深化進程中重大問題所提出的戰略規劃,是價值判斷標準和政策實踐依據的統一體,具有規范價值和工具價值雙重屬性。國家治理現代化由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兩部分構成,國家治理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22]。國家治理范疇貫通政治、經濟、行政、社會和文化體制,需要運用國家權力整合社會利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化解社會沖突。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綜合體,社會轉型總括在國家治理體制當中。
社會治理現代化主要體現為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具體體現為治理方式改進、社會組織參與、矛盾化解體制和公民意識提升。社會治理以實現維護群眾切身利益為導向,注重民生建設,通過社會能動作用的發揮,激活多元主體共同治理,建構社會福利體制,推動社會有序發展。鄉村基層治理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社會基礎,分析鄉村基層治理同國家治理內在關系必須以社會問題為出發點,發掘鄉村社會基層治理在國家治理整體層面的特征顯現。
(二)研判社會問題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前提
現代化建設過程和制度構建中缺乏對社會問題的科學探討是造成這些尚待改進空間的底層原因之一,現階段國家治理過程中問題意識導向還未臻成熟。市場化、分權化、開放化、工業化是轉型期主要特征,在社會轉軌中,必然面臨利益格局的重組、文化觀念的重塑、公平正義的界量、發展體制的變革等難題。從鄉村治理角度觀察,科學合理診斷出鄉村基層社會中存在的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城鄉二元體制束縛、人口戶籍流動牽制,以及鄉土傳統文化與現代治理理念張力等社會問題既是構建國家治理體系的問題導向,也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前提。
(三)社會多元主體協同參與治理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顯現
國家管理與國家治理最大的區別在于“治理主體單中心向多中心的轉變,治理手段剛性管制向柔性服務的轉變,治理空間平面化向網絡化的轉變,治理目的工具化向價值化的轉變”[23] 。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框架下,表現為國家治理運行過程由單線向多維轉化。治理主體趨于多元化、平等化,政府雖然掌握行政權,但同時也是社會協作網絡中的一元,共同分擔治理責任,在協同治理機制基礎上共同完成治理任務,共享治理成果紅利。多元主體共同治理必須以合作協商為治理形式,社會必須構建一個多元統一、融合開放的治理結構,立法層面、行政層面、基層民主、多黨參政等領域發展出制度性協商機制。
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無論是建立國家與社會協商對話機制、集體經營與多樣化經營結合機制還是“契約型整合”機制,核心都是國家與社會合作共治,以解決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問題,真正形成黨的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民參與、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誠如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概念的經典概括:“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種方式的綜合,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行動的持續的過程。”[24]( p.4)
[參考文獻]
[1]李增元.基礎變革與融合治理:轉變社會中的鄉村社區治理現代化[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5(2).
[2]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3][德]費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林榮遠,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4]Mann,Michael.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ll):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5]鄒讜.中國廿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86(4).
[6]徐勇.“政黨下鄉”:現代國家對鄉土的整合[J].學術月刊,2007(8).
[7]侯麟科.鄉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背景下的中國鄉村社會分層分析[J].中國鄉村觀察,2010(1).
[8]林巖.分化與整合:社會轉型下農民價值觀變遷及當代重構[J].學術論壇,2014(11).
[9]李增元,葛云霞.集體產權與封閉鄉村社會結構:社會流動背景下的鄉村社區治理——基于溫州的調查分析[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4(3).
[10]曹海林.村莊治權合法性來源的嬗變進路及其現代化構造[J].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研究,2013(1).
[11]劉兵飛,郭臺輝.“區別對待的公民身份”與農民工的社會抗爭[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5(6).
[12]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J].社會學研究,2006(3).
[13]譚貴華.發展戰略與鄉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革[J].湖北社會科學,2011(8).
[14]賀雪峰.組織起來:取消農業稅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
[15][英]馬爾科姆·盧瑟福.經濟學中的制度:老制度主義和新制度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6]張成福.論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選擇[J].公共行政(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3(5).
[17]汪洪濤.新農村建設要重視農業生產組織方式創新[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3).
[18]于建嶸.岳村政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19]曹海林.從“行政性整合”到“契約性整合”:農村基層社會管理戰略的演進路徑[J].政治學研究,2008(5).
[20]唐士其.市民社會、現代國家以及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J].北京大學學報,1996(6).
[21]項繼權.鄉村社區建設:社會融合與治理轉型[J].社會主義研究,2008(2).
[22]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EB/OL].新華網,2013-12-31.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7463_2.htm.
[23]姜曉萍.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J].中國行政管理,2014(2).
[24]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作者系吉林大學博士研究生)[責任編輯冒潔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