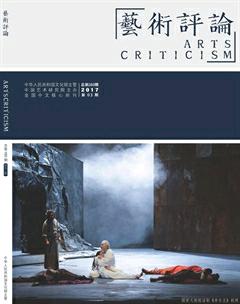夾縫中生存的美國當代繪畫
高中華
20世紀末以后的美國當代藝術,其最顯著特點就是多元的藝術形式共存。架上繪畫受到了裝置藝術、新媒體藝術等概念藝術的沖擊,似乎已經不再是藝術的主流。曾經代表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繪畫和波普藝術,也早已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淪為了拍賣場和富人的玩物。不過這一切恰巧說明,在當今的美國,沒有什么藝術形式能夠成為當代藝術的代表,事實上也不需要有何種藝術形式站出來代表美國。夾縫中生存的美國當代繪畫,以自己的方式對當代美國社會進行著有力的批判和諷刺。畫家們用個人的才華,讓繪畫始終占據著美國當代藝術的重要位置。
在美國藝術界、音樂界和戲劇界中,非洲裔美國人的貢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克里 ·詹姆斯 ·馬歇爾( Kerry James Marshall)和丹娜 ·舒茨(Dana Schutz)都是杰出的非洲裔美國畫家,他們為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爭取身份和文化認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克里 ·詹姆斯 ·馬歇爾的繪畫
馬歇爾于 1955年出生在美國東南部的阿拉巴馬州,但他成長在西海岸的洛杉磯。 14歲那年接受了正規的藝術教育,并自此對繪畫事業矢志不渝。在奧蒂斯學院學習期間,他看到了偉大的黑人藝術家查爾斯 ·懷特( Charles White)的作品。對藝術的熱愛和黑人的身份,讓青年時期的馬歇爾建立起對非裔美國人肖像這一題材的獨特偏好。
在查爾斯 ·懷特和個人生活經歷的影響之下,馬歇爾確定了他的目標:以黑人的角度重新修訂由白人寫成的藝術史。馬歇爾曾說:“我將引入理想化的黑人形象,用歐洲人建立藝術史一般的力量和創意精神介入藝術、重建歷史,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重新思考甚至顛覆歷史書上的藝術流派和那些載入史冊的作品,果真在馬歇爾后來的藝術道路上成為了他的座右銘。
馬歇爾創作的題材和藝術理念十分平常:重要但不出名的歷史事件或者日常的生活場景,通過藝術的方式介入美國長久以來存在的種族問題之爭。他在南芝加哥創作的《花園》(Garden)系列作品,就以巨大的幅面表現南芝加哥黑人聚集區的景象。那些街區治安環境較為惡劣,時常有暴力事件的發生,而馬歇爾認為即便在這樣的地區里,也總能找到很多歡樂。他還大膽地借用了那些在藝術史上的知名作品、或是經典電影場景中的視覺元素及構圖代入黑人的形象,表達自己的觀點。比如他在 1993年創作的《風格》(De Style),就是對黑人聚集區一家理發店的描繪。畫面中的黑人形象,以純黑的平涂而凸顯出來。同時,理發店的背景則以鮮艷的、甚至金碧輝煌般的色彩表現出來,非常符合在美非裔人士常有的“審美趣味”。在美國,黑人的這種夸張甚至艷俗的審美趣味,往往受到白人社會的詬病。但馬歇爾也正是通過畫面上人物和背景的夸張對比,來對抗美國主流社會存在的“品位上的歧視”。在這一點上,馬歇爾的藝術實踐和當今的一個熱點問題——“藝術全球化”的概念實際上不謀而合。當年從非洲或是南美遠渡重洋來到美國的黑人們,始終具有非洲原始藝術的氣息:喜歡鮮艷色彩、對紅色和黑色的崇拜、和對原始藝術中樸素而夸張的變形的喜好,這也自然遺傳至美國的非洲裔人士或藝術家們身上。對藝術創作而言,這正是非洲裔人士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藝術全球化過程中無可厚非的一步。令人欣喜的是,作品《風格》很早就被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收藏,馬歇爾也由此獲得了美國主流藝術界的承認。
馬歇爾作品中的黑人形象,往往以類似平涂的技法呈現。這種平涂的技法,在他的早期作品《自畫像》中就已經出現。如果不親眼看到馬歇爾的原作,這種看似簡單的平涂,似乎讓人想到波普藝術中常見的人物形象。但如果細細地觀看這些大面積的黑色塊,就會發現,馬歇爾的藝術對繪畫性的強調,遠遠超出了他對波普概念的借鑒。他賦予了平涂非凡的質感,表現出了絲網或水滴式的紋理,讓大面積的黑色呈現出細微的韻律和精妙的細節變化。這和他對作品中主題——黑人形象的情結相關聯:血緣式的聯系和文化上的承繼。馬歇爾用繪畫去擁抱更加寬廣的人類情感,比如愛和喜悅,正是馬歇爾作品中最為核心的藝術價值。
馬歇爾一直以來的愿望,是把他的作品掛到那些曾經忽視非洲裔藝術家的美術館中,而從美國當今最重要的美術館,如紐約現代美術館和大都會美術館的收藏列表來看,他的愿望早已實現。 2016年9月在華盛頓剛剛建成開放的美國非洲裔美國人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或許是對馬歇爾以及和他一樣的黑人藝術家的最直接的肯定。
二、丹娜 ·舒茨的繪畫
生于 1876年的丹娜 ·舒茨,同美國最知名的女畫家麗莎 ·優絲卡瓦潔( Lisa Yuskavage)和妮可 ·埃森曼( Nicole Eisenman)具有相似的才能:把流行文化的觀念和西方現代藝術史雜糅在一起,利用各種媒介在畫面上實現怪誕的敘事,實現藝術對社會的反諷。
丹娜 ·舒茨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郊區出生, 15歲那年起才接受正規的繪畫訓練,并先后在克利夫蘭藝術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美術學士和碩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求學過程中,她開始利用她天馬行空般的想象力,進行虛構人物和假想情節題材的繪畫創作。在創作了早期作品《觀察中的弗蘭克》之后,她在 2003年虛構出了成名之作《自食者》,描繪了一個自噬代謝的駭人生物,就像好萊塢科幻電影中的怪物一般。
《自食者》是舒茨創作過程的一個貼切的寫照,并涉及文化禁忌、繪畫語言和各種神秘自然現象。 “自食”的歷史根源十分深厚,從猶太人的民間傳說、瑪麗 ·雪萊的《科學怪人》和哥斯拉的傳說都有提及,它體現了人類恐懼和焦慮的心理,但同時也暗示了約束中的人性解放的可能。舒茨所描繪的人物和其他形象,是對人類所有倫理和邏輯的對抗。此后,舒茨把這種對抗延伸至了現實生活,她開始創作“反名人 ”的肖像。比如在 2005年,她創作了《邁克爾 ·杰克遜的尸檢》,以諷刺追星族的荒謬和無知。
在她的油畫《黨派》(Party)和《男人的撤退》(Men‘s Retreat)中,當年的小布什政府和資本主義任人唯親的傳統,也成為舒茨諷刺的對象。她以繪畫斥責美國政府濫用權力,以繪畫史上少有的激進語言展現出藝術和圖像的力量。在她 2005年作品《展示》(Presentation)之中,成功地抓住了美國人民在 “9·11”之后凝結的憤怒和無助心理,但也狠狠地諷刺 “9·11”之后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出兵。這幅 3米長的作品也被紐約現代美術館( MoMA)永久收藏。
舒茨的繪畫結合了幽默和憤怒、樂觀與絕望,這正是我們在新時期反思繪畫藝術的一種有效的策略。無論是從傳統的繪畫批評界的聲音,還是從舒茨展覽中得到的視覺感受,我們都能看到這一點。舒茨利用強大的視覺壓迫感,讓觀眾不得不選擇一個立場。她的成功來源于對倫理的探討,而她在繪畫藝術上的貢獻則來源于她對當代文化清晰的解析。
在今日的美國藝術界的確已經很少有人再把繪畫作為自己的主業。藝術家們更傾向于把藝術變成一個個事件。但堅持著繪畫創作的藝術家們,卻一刻也沒有停下他們的腳步。即使在裝置藝術和多媒體藝術大行其道的美國,懷疑繪畫的命運也是沒有意義的。繪畫的價值在于觀眾的欣賞,而非在“抽象—寫實關系”這樣的問題里糾纏不清,至少在馬歇爾和舒茨的繪畫之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1. http://www.metmuseum.org/press/exhibitions/2016/kerry-james-marshall.
2. Kerry James Marshall: Look See.David Zwirner,2015.P.112.
3. http://artistproject.metmuseum.org/4/dana-schutz/.
4. Dana Schutz: If the Face Had Wheels.Prestel,2011.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