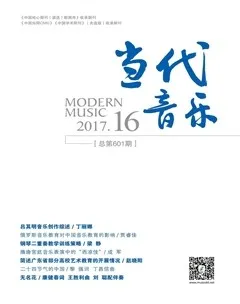隋唐宮廷音樂表演中的“西涼伎”


[摘要]根據史料與發掘文物相互參證,西涼伎當是中原、羌胡、龜茲甚至印度音樂長期交叉融合的產物。在孝文帝“漢化”運動中,中原傳統鐘磬之樂、羽衣歌舞大肆進入北魏宮廷。伴隨佛教東傳,處在絲綢之路交通要塞的西涼古國不斷吸收外來文明,印度佛樂、胡騰歌舞及其酒歌文化不盡東流于此。隋唐宮廷表演的西涼伎既有佛樂、胡騰歌舞,又有五行思想影響下的“方色”歌舞以及源于男根崇拜的羽衣歌舞。在一定意義上說,西涼伎既是漢族傳統音樂、胡樂、佛樂甚至波斯、伊朗、阿拉伯音樂交叉融合的產物,又是那個時代歷史與文化發展的縮影。
[關鍵詞]隋唐;宮廷音樂;宴樂表演;西涼伎
[中圖分類號]J6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233(2017)16-0012-03
西涼,又稱涼州、西涼國(今甘肅武威一帶),鮮卑人長期生活在這片水草豐美的廣大地區。處于絲綢之路以及東西方文化交流之樞紐地位的西涼國,便于不斷學習包括樂舞在內的外來文明。長此以往,西涼伎樂歌舞日趨成熟,朝野上下備受青睞。
伴隨佛教東傳,處于文化交流之要道上的洛陽、大同、武威等城市,佛教文化非常興盛。與印度佛教一道,佛教音樂及其龜茲樂大肆進入中原。東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1],京城貴戚競相仿效。孝文帝拓跋宏統一北方地區后,不僅遷都洛陽,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漢化“運動,漢族音樂大肆進入北朝宮廷。文帝楊堅掌權后,遂將西涼樂奉為“國伎”。
據《隋書·音樂下》記載,隋代宮廷“西涼伎”表演,所用樂器有鐘、磬、彈箏、搊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簫、大觱篥、長笛、小觱篥、橫笛、腰鼓、齊鼓、擔鼓、銅拔、貝等19種,參演樂工27人。其中,曲項琵琶、豎箜篌等樂器出自西域,《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的音樂本生于胡戎,時常表演的歌曲有《永世樂》、解曲《萬世豐》、舞曲《于闐佛曲》。[2]《樂府詩集》曾收錄北齊人魏收創作的西涼樂《永世樂》歌詩一首:“綺窗斜影入,上客酒須添。草羽方開美,鉛華汗不沾。關門今可下,落餌不相嫌。”[3]歌詩盡情描繪了良辰美景之日宴樂歌舞表演的恢宏場面:綺窗影射之下,高堂內賓朋滿座。觥斛交錯,美酒飄香。粉妝美人,羽衣歌舞。如此說來,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為大唐王朝敬獻的《霓裳羽衣曲》[4]乃與羽衣歌舞表演的《永世樂》應是有著某種淵源關系。
誠然,論及羽衣歌舞的文化淵源,學者秦序指出:“遠古時代的人們以為鳥羽具有神秘的力量,可以使人飛升,可以交通人神。……后成為道士的服飾及象征。”[5]筆者認同這一觀點。兩漢時期,尤其漢初黃老道學一度興盛。羽衣、羽人歌舞蔓延開來。關于這一論點,不僅有大量的文獻記載,而且還有很多羽衣、羽人歌舞的壁畫、帛畫為證。倘若沿著秦先生的思路繼續追問,我們還不得不逆向考察中國古代先民生殖崇拜祭儀表演的“羽舞”。其實,這也涉及中國文舞的源頭問題。印度佛教“珈琳顰伽”鳥神歌舞是否源于中國的男根崇拜?如此追問,也有待以后探之、考之。
關于西涼樂表演,還有一個重要事件不得不提及。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煬帝率大隊人馬巡查河西,“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在這次視察中,西涼古國的藝術家們盡情歌舞,一展風采。盡管我們不知其具體表演哪個節目,但從“金玉”“錦罽”以及“焚香奏樂”等具有西域風情的語匯來看,西涼樂一定帶有域外音樂的某些元素。如此艷麗的歌舞表演,煬帝還命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6]可見,來自西涼樂故鄉的歌舞表演,對于全面把握宮廷表演的西涼樂之風格特征,當是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新唐書·禮樂十二》曰:“周隋始于西涼樂雜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其余辭多可汗之稱,蓋燕魏之際鮮卑歌也。”[7]
北魏、北周等鮮卑血統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音樂歌舞自然不離歌頌自己可汗的佳作。大隋政權開創者楊堅也多少帶有鮮卑血統,其建立的“七部樂”宴樂表演體制中,西涼樂就被奉為“國伎”,位列“七部樂”之首。因此,隋唐宮廷表演的西涼樂當有不少歌頌可汗的先代作品。
有唐一代,西涼樂更是贏得眾人青睞。“立部伎”八部樂舞中,除《安樂》《太平樂》兩部樂舞乃為周隋遺音外,《慶善樂》獨用《西涼樂》,音聲嫻雅,頗受歡迎。[8]不僅如此,“西涼伎”在著裝、舞員人數以及樂隊編制等方面均是有著特殊的規定:其一,化妝表演方面:樂工頭冠平巾幘,身著緋褶。舞蹈演員,白舞一人,方舞四人,他們頭戴假發髻,冠玉支釵,著紫色絲布長裙,白色大口袴,五彩接袖,蹬烏皮靴。[9]其二,關于樂隊編制:鐘、磬各一架,彈箏、搊箏各一面,臥箜篌、豎箜篌各一面,琵琶、五弦琵琶各一面,笙簫各一支,大小觱篥各一支,笛、橫笛各一,腰鼓、齊鼓、檐鼓各一,銅鈸一對、貝一只。僅就八音樂器來說,鐘磬、笙簫等多為漢族傳統舊樂;箜篌、五弦琵琶、銅鈸、貝多出自西域,乃為羌胡、印度甚至波斯、伊朗等地的民族樂器。在隋唐多部樂中,如此規模龐大的樂隊,實屬罕見。
當然,論及西涼樂的風格特征,還必須考察西涼古國的歷史及其人文環境。首先,西涼樂中的鐘磬之樂應是伴隨中原文化的蔓延擴張而流傳到這一地區的。西漢時期,為抵御匈奴入侵,漢武帝曾派大將衛青、霍去病進行卓有成效的抗擊,并在打通西域古道(絲綢之路)之后又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魏晉時期,漢人一直統治黃河以西的大片地區。尤其西漢常山景王張耳第十七代孫張軌控制這一地區后,中原文化源源不斷西流于此。想必西涼樂中的鐘磬之樂乃與漢人建立的政權及其相關的文化交流大有關系。其次,關于西涼樂中的龜茲樂。“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魏太武旣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10]淝水之戰,前秦苻堅戰敗。一國無主,國將不國,其大將呂光索性攻破西涼,并一度占有涼州地區。其實,早在苻堅淝水戰敗之前,呂光曾奉命征討西域,降焉耆、破龜茲,遠近30多個小國來降。勸離龜茲時,呂光“以駝二千余頭,致外國珍寶及奇技、異戲”還國。[11] “奇技、異戲”,應是包括龜茲歌舞伎樂。攻占涼州之后,熟知龜茲樂舞的呂光“變龜茲聲為之”,遂改良為“秦漢伎”。
不僅如此,早在公元349年前涼王張重華在位時,天竺國(今印度)使者就為西涼國派送了一個由12位技術精湛的演員組成的歌舞團,并帶來了印度本土的《沙石疆》《天曲》等優秀作品。同時,還帶來了鳳首箜篌、銅鼓、毛圓鼓、都曇鼓以及四弦、五弦琵琶等珍貴樂器。[12]西晉永嘉之亂,太常樂工多避地河西走廊一帶,“(魏)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擇而存之”。[13]可見,“西涼伎”當是中原、羌胡、龜茲乃至印度音樂長期交叉融合的產物。
曾被隋文帝奉為“國伎”的西涼樂,今日是否能夠從塵封的歷史中尋覓到它的蹤跡?無獨有偶,敦煌壁畫第156窟彩繪的張議潮
張議潮,晚唐漢族人,出生于沙州敦煌。羅振玉補《唐書張議潮傳》曰:“張議潮者,沙州人。少習文史,長通韜略。雖生長虜中,而心系本朝。陰結豪俊,密謀歸唐,苦未有當。……懿宗咸通元年庚辰,議潮開窟為功德,畫壁多幅。為《莫高窟記》,書之窟壁。”“統軍出行游樂圖”和“宋氏夫人出行圖”,乃是反映河西風情的歷史畫卷,圖中樂舞更為我們研究這一地域古代樂舞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宋氏夫人出行圖局部圖畫(圖1)似有本地“方舞”表演的畫面。依字面理解,四人“方舞”表演大致有兩種情形:其一,四位舞蹈演員各立一方(東西南北)進行樂舞表演;其二,方整性樂舞。與一人表演的獨舞相對,集體性質的樂舞講究方整,動作整齊化一。但從舞者身著不同顏色的服裝來看,西涼“方舞”之冠名應和方位有關。畫中歌舞表演4人,各自獨占一方,每人服裝顏色也各不相同。她們發髻高聳,頭冠花釵,長巾逶迤,長裙飄逸,左手彎曲展袖,右手上揚飛舞,猶如下凡天仙正翩翩起舞。伴奏樂隊7人,能夠清楚辨認出的樂器有笙、拍板、橫笛、琵琶、篳篥、雞婁鼓等,所用樂器中西合璧,與《新唐書》相關記載基本吻合。可能因為出行不便,刪減了編鐘、編磬等大件樂器。可見,從畫面構圖及其樂舞元素來看,“宋氏夫人出行圖”局部4人樂舞大體反映了西涼古國“方舞”表演的原始風貌。
“統軍出行游樂圖”局部畫面(圖2)也有彩繪樂舞場面,其舞蹈演員 8人,每列4人,正對視表演。他們均身著不同顏色的套裝長裙,身披假發長辮,一手高舉,一手合腰,動作整齊劃一,從舞姿形態來看,可能是四人“方舞”的革新發展。其伴奏樂工12人,其中背大鼓者2人,鼓手2人,其他8人各執不同樂器。前排左起依次為拍板、橫笛、觱篥、琵琶,后排左起依次為箜篌、笙、擔鼓(一說雞婁鼓)、腰鼓。敦煌學研究專家陳明從晚唐河西地區的樂舞背景入手,全面分析了歸義軍時期的樂舞狀況,進而指出張議潮出行圖中的歌舞表演是西涼樂,舞蹈乃為《萬年豐》《永世樂》等。[14]
除“方舞”表演,《胡騰》獨舞更是風靡一時,深受中原達官貴族的賞識和喜愛。唐代李端《胡騰兒》歌詩曾對其舞姿舞容進行了著力刻畫:
“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后卷,葡萄長帶一邊垂。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安西舊牧收淚看,洛下詞人抄曲與。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絲桐忽奏一曲終,嗚嗚畫角城頭發。胡騰兒,胡騰兒,故鄉路斷知不知?”[15]
歌詩首先記寫了胡騰舞男的家世,然后對其容貌、裝扮、舞姿進行一一描繪。其舞蹈動作主要包括揚眉動目、環行急蹴、拾襟攪袖、反手叉腰、踢踏翻騰等,明顯具有馬背民族雄健、奔放的樂舞風格。
盛極一時的胡騰舞,也有相關文物予以佐證。1971年,安陽縣文物管理部門在漳河洹水附近的洪河屯村發掘了涼州刺史范粹古墓,上圖(圖3)黃褐色扁平樂舞瓷壺就是該墓出土的一件珍貴文物。[16]該壺最引人注目的是5人小組表演的歌舞圖畫,中間一人獨舞表演,“揚眉動目踏花氈”,雙腳踢踏舞于前。左手“叉腰如卻月”,右手高舉似揚鞭。左邊兩人,一人吹橫笛,一人似應節唱和;右面也兩人,一人橫彈琵琶,一人似擊鈸。唐代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歌詩“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遍頭促。亂騰新毯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槿花西見殘月”[17],正是對這一場面的高度“寫真”。其蕃帽頂尖、胡衫袖小、寶帶、錦靴等語匯,是對胡騰演員裝扮的特寫;跳轉帶鳴、弄腳靴軟、亂騰新毯、傍拂輕花,是對胡騰舞姿的描繪;“橫笛琵琶遍頭促”,指明了胡騰歌舞表演的主要伴奏樂器;酒喝干,歌舞竟,絲管聲絕,所謂“酒闌舞罷絲管絕”也!對于那些流落他鄉逢場作戲的胡騰兒來說,又有誰能知其難言心事?“西顧忽思鄉路遠”“木槿花西見殘月”,他們何時才能見到故鄉的明月?思鄉、念遠與懷歸之情油然而生。
在考量分析西域粟特人審美文化時,學者孫武軍指出,胡騰舞與酒文化關系甚密。[18]的確如此,《全唐詩》有不少描寫胡騰舞者借著酒勁騰踏起舞的場面。如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胡騰》“手中拋下葡萄蓋”,李端《胡騰兒》“附卻東傾又西倒”,元稹《西涼伎》“胡騰醉舞筋骨柔”等歌詩,均不同程度反映了這種酒筵歌舞的文化風貌。不僅如此,西安北郊安伽
安伽,姑臧昌松(今甘肅武威)人,應為昭武九姓之安國后裔。墓出土的圍屏石榻胡騰舞表演圖像中(組圖4),多有酒壇、酒壺、酒碗等酒器形象。
[參 考 文 獻]
[1] (南朝·宋)范 曄.后漢書·志第十三·五行一(卷103)[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272.
[2] (唐)魏 征等.隋書·志第十·音樂下(卷15)[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78.
[3]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雜曲歌詞十五(卷75)[M].北京:中華書局,2003: 1064.
[4][5] 秦 序.唐玄宗是《霓裳羽衣曲》的作者嗎?——《霓裳曲》新探之一[J].中國音樂學,1987(04).
[6] (唐)魏 征等.隋書·志第十九·食貨志(卷24)[M].北京:中華書局,1982: 687.
[7] (宋)歐陽修,宋 祁等.新唐書·志第十二·禮樂十二(卷22)[M].北京:中華書局,1975:479.
[8] (后晉)劉 煦,張昭遠等.舊唐書·志第九·音樂二(卷29)[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60.
[9] (后晉)劉 煦,張昭遠等.舊唐書·志第九·音樂二[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68.
[10] (唐)魏 征等.隋書·志第十·音樂下(卷15)[M].北京:中華書局,1982:378.
[11] (北齊)魏 收.魏書·列傳第八十三·呂光(卷95)[M].北京:中華書局,1974:2085.
[12] (唐)魏 征等.隋書·志第十·音樂下(卷15)[M].北京:中華書局,1982:379.
[13] (北齊)魏 收.魏書·樂志五第十四(卷109)[M].北京:中華書局,1974:2828.
[14] 陳 明.張議潮出行圖中的樂舞[J].敦煌研究,2003(05).
[15] (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284)[M].北京:中華書局,1979:3238.
[16] 河南省博物館集體小組.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J].文物,1972(01).
[17] (清)彭定求,沈三曾等.全唐詩(卷468)[M].北京:中華書局,1979:5323—5324.
[18] 孫武軍.北朝隋唐入華粟特人墓葬圖像的文化與審美研究[D].西北大學,2012.
(責任編輯:崔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