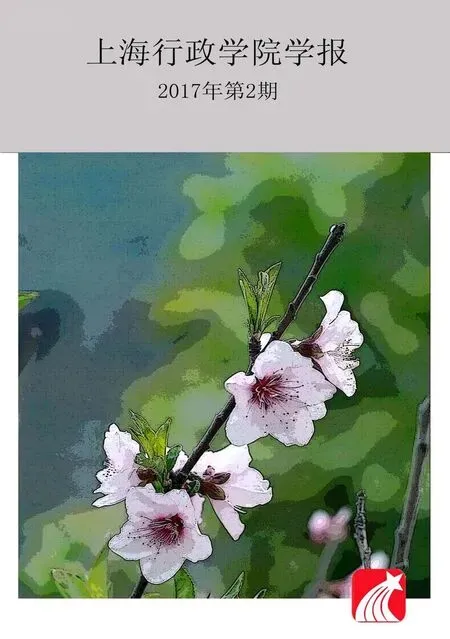網絡輿情的生態治理與政府職責
唐惠敏 范和生
摘 要: 網絡輿情在彰顯公民政治態度,保障公眾輿論話語權的同時,也導致了情緒輿論、負向輿論以及虛假輿論的滋生和蔓延。將網絡輿情沖突控制在政治秩序范圍內,防止公共輿論對政府權威的銷蝕,是構建網絡輿情生態的關鍵性議題。基于社會穩定大局的考量,要轉變政府網絡治理理念,以達到網絡輿情風險控制與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雙重目標。改善網絡輿論生態,政府既要充分保障網民網絡輿論自由的權利,又要適度干預網絡突發輿情,以規范網絡生態秩序。同時,在立法保障、制度設計、技術治理、文化建設等方面加強網絡輿情的生態治理,探索構建以“政府主導為前提,法律規范為基礎,行政監管為依托,行業自律為保障,技術支持為輔助,公眾監督為補充”的多元主體合作模式。
關鍵詞: 網絡輿情;生態治理;輿論自由;適度干預;政府職責
一、網絡輿情:政府治理不可小覷的領域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提出新聞輿論工作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輿情是廣大公民對社會事件、群體現象以及公共事務管理者所持有的基本認知、主觀看法、客觀評價以及現實態度的總和,是對政府施政和決策行為能夠形成重大影響的民意集合[1]。而網絡輿情是公民在網絡空間領域內對特定公共事項所表達出的社會政治態度、觀點和信念。當前,社會生活網絡化、日常生活政治化特征凸顯,網絡意識形態也隨之呈現“生活化”和“政治化”特質。當下中國正處于社會經濟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基層社會矛盾凸顯,利益群體間摩擦不斷增加,而整個社會缺乏有效的利益表達路徑,公民“話語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互聯網技術的蓬勃發展,使得個體在“脫域”空間中自由流動與平等交換,并逐步形塑“網絡社會”的現實性狀態,極大地壯大了民間輿論場,改變了傳統輿論場的格局。縱觀整個網絡輿論場,官方與民間的博弈仍在持續,與此同時,網絡輿論場中的混亂現象也引發了官方的持續介入,并引發了整個網絡輿論格局的再度調整。因此,網絡社會力量的崛起,彰顯了公民參政議政的優勢,有效地彌補了公權力不及和不足之處,對促進我國民主社會的建設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不容忽視的進步意義。
網絡輿論作為新時期民眾利益訴求表達的公共平臺,業已成為政府傾聽和捕獲真正民意、判斷和評價政策實施效果的重要渠道。由于互聯網獨特的開放性、匿名性與流動性特征,使得普通民眾樂于參與網絡互動與信息溝通,并逐步形成公民話語權實現的民間輿論場。“數字經濟之父”唐·泰普斯科特在《數字化成長:網絡時代的崛起》中指出,“在過去咨詢壟斷的權威時代里,人們無法找到真相,只要掌握及控制咨詢就可以輕易欺騙他們。但是,在網絡世界里,一切都會透明化,極權和欺騙將不容易存在”[2]。然而,網絡空間充斥各種謠言、謾罵、欺詐、暴力和色情等違法內容,造成信息失真和輿論失范,特別是一些負面輿論,過度放大社會不滿情緒,加劇社會裂痕,消解社會凝聚力,甚至誘發整個社會的信任危機。與此同時,大部分網民缺乏對網絡信息的甄別能力,往往被少數權勢者或不法分子所操縱,渲染有害社會穩定的消極言論,進一步加劇公民話語權的失衡。因此,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必須將網絡社會納入有效的社會協同治理體系之中,不斷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有效發揮網絡輿情的正面效應。
二、網絡輿情生態治理的關鍵議題
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6)》的數據顯示,2015年底我國網民凈增3951萬人,規模已達6.88億①。不可否認的是,網絡科技革命正悄然改變著我國民眾的生活與生產方式。互聯網發展的“狂飆突進”所形成的“網絡輿論場”在推進民主法治進程、倒逼社會制度創新以及加強社會監督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正向效應。但同時,網絡輿論由于缺乏立法規范和科學引導,網絡輿論生態也面臨著諸多新問題、新情況和新挑戰,網絡輿論治理成為社會治理的關鍵領域。
1.網絡輿論場官方話語與民間意見博弈的非理性傾向
網絡輿論場的成長,極大地壯大了民間輿論場,并逐步塑造新的輿論場格局,極大削弱了傳統媒體在整個輿論場發揮的主導作用。尼葛洛龐帝認為,“網絡真正的價值越來越和信息無關,而和社區相關……而且正創造著一個嶄新的、全球性的社會結構”[3]。而多元社會結構的不斷變遷和持續變動,催生了日新月異的網絡輿情環境。網絡輿論場將是近7億網民利益表達的重要載體,“直接成為民主政治的場域,成為公民參與政治的運行手段,以全新的作用方式改變著公民政治參與的理念”[4]。網民的意見能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決策提供強力支持,既有利于各級政府及時收集民意以制定相應政策,做到執政為民,又有利于對地方政府行政行為構成強有力的監督,確保依法行政。但是,應當看到由于網絡輿論場缺乏有效立法規范和政府監管,不法分子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網絡信息不對稱的弊端,妄圖混淆視聽,煽動網民的不滿情緒,制造社會不穩定性因素,以此來對抗政府,謀求自身的非法利益。網絡輿論場中的政府與民間博弈,并非傳統“政治力量的延續和呈現”[5],互聯網利益主體復雜,不同網絡行動者對政府的認知和與政府關系的想象具有多元性和模糊性。在網絡突發公共事件中政府往往被渲染為群體性抗爭事件的“靶子”,而由于民眾社會心理的失衡與錯位、執政者政治風險意識和輿論處置技能的薄弱,最終導致官方話語與民間意見的“互動”更偏向非理性的“博弈”與消極的政府回應。網絡輿論場對政府執政提出新的挑戰,對政府來說,網絡輿情治理的關鍵環節在于把握機會,主動積極地適應“網民力量持續壯大、社會利益結構深度解構”的“新常態”,使網民作為一個群體整體有序參與到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與利益格局的深度博弈中,一味地消極對待與放任自流只會引發新的政府信任危機。
2.網絡輿情甄別能力的弱化與政府監管的缺失
網絡空間儼然成為彰顯社會主義民主與自由的策源地,正深刻地改變著現有輿論權力的基本格局,并釋放出巨大的傳播影響力。事實上,我國網絡社會存在多重力量的博弈,存在不同的輿論場域。新華社南振中先生率先提出“兩個輿論場”的看法,指出我國網絡處在官方輿論和民間輿論不斷博弈和動態平衡的狀態。[6]在這之后,劉九洲[7]、童兵[8]等學者又提出了“三個輿論場”的主張,認為我國實際存在一個由政府輿論場、媒體輿論場和民眾輿論場構成的復合型多主體輿論場域。在后媒體時代,網絡輿情的甄別是網絡輿情分析與研判的關鍵環節。對網絡輿情的科學甄別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國網絡輿情治理的重要發力點。倘若政府對通過技術監測和收集到的網絡輿情信息嗤之以鼻,網絡輿情危機的處理機制和應對策略就缺乏堅實基礎與科學依據。當網絡空間場域中不同群體的話語表達與權益爭論激發起口角、謾罵、對立與爭斗,網絡輿情的發展態勢就難以判斷,甚至會延伸至現實空間中的各類集體行動。如果矛盾進一步激化,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控制,極易在短時間內醞釀成群體性事件,最終必然會削減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9]網絡輿情甄別能力的弱化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網絡輿情危機的蔓延空間。事實證明,離開了網絡輿情的常態化監測,就無法把握網絡輿情演化的深層次規律。離開了危機輿情的動態監管,就無法有效化解危機輿情的風險。因此,政府應當樹立善治理念,強化網絡治理的基礎,規范網絡生態秩序,進而將網絡空間塑造成民情甄別、共識凝聚和信任構建的輿論場域。
3.網絡立法滯后與實踐漏洞的雙重困境
正如埃瑟·戴森所言,“數字化世界是一片嶄新的疆土,可以釋放出難以形容的生產能量,但它也可以成為恐怖主義者和江湖巨騙的工具,或是彌天大謊和惡意中傷的大本營”[10]。網絡建構了新的社會形態,在催生新的社會結構的同時,“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性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11]。網絡已徹底削弱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生活與生產方式,有力地促進我國現代文明的進步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升。然而,互聯網在建立伊始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雙刃劍的烙印,迫切要求執政者制定和完善專門的法律法規來監督、制約和調整網絡社會的失范行為。而網絡社會具有的虛幻性、匿名性、開放性和互動性等特點,導致網絡欺詐、謠言、誹謗、人肉搜索、病毒攻擊等網絡越軌行為在種類和數量上呈逐年上升趨勢,已嚴重侵蝕了利益相關者的個人權利,威脅網絡社會安全。雖然早在1994年我國就頒布施行了由國務院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并不斷制訂和頒布了數十部網絡行政法規、司法解釋與部門規章,“初步構建起相對完整的網絡立法框架” [12]。但是,仍然存在網絡立法滯后、執法實踐漏洞的雙重困境。主要表現為:立法觀念與進程落后于網絡技術與違法犯罪行為的更新步伐;網絡法典的規范性、義務性條款過多,缺乏個人權利保障的禁止性規定;高層次、系統化的網絡法規相對欠缺,且部分法規的可操作性標準相當模糊;部門間的執法權限不明確,存在“多頭介入”與“管理有漏”的尷尬處境。整體而言,我國網絡立法的基本框架已基本確定,具備對網絡違法犯罪行為的基本管控能力,但需要進一步改進現有法規的層級,延伸法律監督的觸角,厘清執法部門的法定權限,增強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
4.網絡輿情的源頭治理與末端治理的脫節與失衡
政治學家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認為,政府最有效的危機管理職責是事前預防,而不是事后治療。政府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用少量錢預防,而不是花大量錢治療”[13]。而網絡輿情的發展與演化遵循著一定的內在規律。以網絡突發輿情事件為例,必然經歷“孕育——爆發——集聚——激化——升華——消減——轉化”的周期性過程。因此,缺乏對網絡輿情應對處置機制的頂層設計和通盤考慮,難以有效遏制網絡輿情演變為惡性網絡輿情危機和突發性群體性事件。傳統社會的管理方式傾向于嚴苛法規的緊急處置效應,注重對危機事件的末端治理,而忽視源頭治理。網絡輿情治理的根本之路是法治,而要實現網絡空間法治化,源頭治理必然是關鍵性環節。強化源頭治理,重點是落實主體責任。因而,在網絡輿情孕育、演化和發展的各個階段,應當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協同、行業推進和個人參與”的多主體協同共治的網絡輿情監管體系。仔細審視網絡輿情危機,其根源并不僅僅在于法律法規的缺失和監管體系的漏洞,忽視民眾話語權的保護、漠視民眾利益的合法表達,也是網絡負面輿情爆發的主要原因。政府應當及時甄別網民利益訴求的真實性,及時有效地為民排憂解難,以免不滿情緒堆積爆發。同時,積極引導網民通過合法、正當的渠道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壓縮謠言滋生的空間,妥善處置網絡負面輿情,從源頭遏制負面網絡輿情的發生。總之,政府在突發事件網絡輿情監控過程中始終要樹立源頭治理和動態管理的理念,不能只解決表面的輿情問題,要善于把握網絡輿情的傳播與演化規律,透視輿情背后社會治理領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困難,挖掘網絡輿情治理的有效之策。
三、保障自由與適度干預:網絡輿情治理的政府職責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反復強調新時期應“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因而,規范網絡空間行為,堅持正確輿論導向,成為國家社會治理的關鍵舉措。網絡空間扭轉了傳統社會話語權被壟斷的現實,民眾在網絡空間享有高度的自由權利。而網絡輿情的治理離開國家公權力的有效干預,任其自由發展,必然會導致網絡空間秩序走向混亂局面。著名法學教授凱斯·桑斯坦指出,“政府介入并提供一個多元的傳媒環境是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的”[14]。因而,“政府和立法者有責任保護、監督和指導網絡輿情朝著更利于公共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方向發展”[15]。正如前文所述,當下我國網絡輿情的生態治理并不樂觀,政府必須擔當起保障民眾網絡輿論自由和適度干預網絡治理的重要職責。
1.網絡輿論自由權的法理支撐與立法規制
著名法學家阿爾弗雷德·湯普森·丹寧提出“法律下的自由”的法律原理。他指出,自由是“每一個守法公民在合法的時候不受任何其他人干涉,想其所愿想,說其所愿說,去其所愿去”[16]。網絡輿論自由是傳統言論自由在權利空間領域的延伸。就言論自由的要素而言,網絡輿論自由擁有言論自由全部的價值屬性和本質特征。美國學者凱斯·R·孫斯坦指出,“一個運轉良好的自由表達制度應該是這樣一種制度,人們面對著跟自己的想法相競爭的想法,以至于他們能夠對自己的觀點進行檢驗,并且理解其他觀點,即使這些觀點他們并不贊同”[17]。網絡輿論自由權的實現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的必然選擇。我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2}。這是我國保護網絡輿論自由權立法的法理基礎和權威依據,不僅有助于削弱封建專制統治下精英階層與生俱來的話語優先權,而且從側面拓展了國家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體系,彰顯了社會主義國家人權保障的政治態度。當前,我國仍不存在專門性的法律條文或司法解釋對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的基本范疇、權限邊界、制度保障等問題作出明確而具體的規定,且“現有涉及網絡言論的相關立法,偏重于網絡管理和網絡信息安全,對網絡輿論權利加以法律保障的條款相當有限,只零星地見諸于網絡監管的行業性法規之中”[18]。從我國公權力對網絡輿論干預程度以及網民輿論監督能力薄弱和成效甚微的現實情況,即可窺見一斑。從世界各國網絡輿論權的保護現狀來看,尚不存在網絡輿論自由權立法規制的統一性框架和一般性原則。比如美國傾向于行業性立法加強網絡輿論權的保護,德國選擇對網絡輿論的保護進行專門性立法,而英國則采取立法管制和行業自律相結合的方式。應當明確的是,網絡輿論超越了傳統言論的表達方式,網絡輿論自由權已然成為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加強網絡輿論權保障的立法建設,已成為我國依法治網的重要舉措。
然而,網絡輿論自由權利也應當有所限制。任何權力缺乏監督就存在被濫用的風險,進而對現實社會的秩序和規范構成嚴重的威脅。網絡本身的“分散權力、全球化、追求和諧、以及賦予權力”[19]的特點,使得網絡輿情的治理更富有挑戰性。而“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手段,應該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實現社會和諧的工具。其規范功能,以及社會功能中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都應當受到特別重視”[20]。因此,通過立法,規范網絡輿論行為,將有害社會穩定良性運行的網絡輿情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是實現網絡輿論自由權的保障。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早就指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廢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21]當下,我國網絡輿論自由的管控相對欠缺,網絡輿論霸權主導負面新聞事件、境外敵對分子的網絡策反、民族分裂者的網絡暴力,以及非法分子肆意批評政府和攻擊司法機關等已經成為我國網絡輿情治理的當務之急。目前學術界和政府已形成對網絡輿論治理的統一認識,即遵照憲法精神,充分保障我國公民網絡言論自由權利的同時,依法防控和遏制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違法網絡言論行為。實踐證明,網絡輿論的善治就是要合理設定網絡言論自由和公權力介入的平衡機制,網絡言論自由的保障和公權力的有效介入,二者不可偏廢。[22]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對于言論自由權的限定性條款同樣適用于網絡輿論自由權的監督和制約。我國憲法第51條明確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權利。”{3}《民法通則》第101條和《刑法》第246條等部門法都有對言論自由禁止性行為的具體規定。《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19條甚至明確規定了言論自由權的特殊義務和責任:“(1)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2)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健康或社會道德。”{4}遺憾的是,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對網絡言論自由權的授權性和限制性條款相當分散,尚未有系統化的法律可循。
2.政府適度干預網絡輿情的邊界與模式
亨廷頓認為:“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不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后才談得上限制權威”[23]。事實上,公共輿論權力在網絡空間的極度擴張和肆意延伸,不僅無助于網絡民主權利的實現,甚至會破壞民主程序,消解法治作為公民基本權利保障的意識。網絡輿論的角色偏離,勢必會干擾公共事務制度化和規范化的進程。政府對網絡輿情的干預,就是要把網絡公共輿論的潛在性利益沖突控制在政治秩序穩定的合理范圍內,防止網絡輿情演化為群體性對抗事件。因此,網絡輿情的政府干預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輿論自由的保障與政府的干預二者是矛盾與統一的關系,其中保障輿論自由是目的,政府干預是達到保障目的的手段。從輿情學的角度來說,網絡輿情適度干預是指政府在法律的授權下,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對違背公序良俗原則、危及國家政權和社會穩定的網絡輿論表達行為進行監督、管理和約束的行為。其目標是維護和確保輿論秩序的形成和延續,以實現網絡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但政府干預又必須是適度的,政府干預的限度,即政府權力的邊界,是探討政府“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利性質和限度”[24]。政府對網絡輿論適度干預的邊界應當具備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兩大原則。
合理性原則暗涵兩層意思:一是政府干預網絡輿情是以承認和保護公民輿論自由權為前提。倘若公民基本的網絡輿論權都無法享有,自然也就不存在危害現實社會秩序的網絡強權力量。那么,設立政府網絡干預權的邊限也就毫無意義;二是網絡輿情適度干預的合理性標準是治理的有效性,也即公權力介入網絡輿論的治理應當區分“應管的”和“應放的”,以避免公權力對網絡空間的過度干預和無所作為,防止“一管就死”和“一放就亂”的尷尬局面[25]。合法性原則也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政府對公共輿論的干預是通過法律加以界定的;二是政府的任何干預行為都應當以法律準繩為前提。[26]任何以權代法或者超越法律規定界限進行的政府干預行為,都違背了政府干預與輿論自由二者間既對立又統一的邏輯關系。現代民主國家構筑輿論自由邊界的價值標準都應當遵循法治精神。踐踏法律的權威性就喪失了政府干預的合理性基礎,也就無法在有序的社會秩序內實現網絡輿情治理的善治目標。
我國學者就政府對網絡輿情的干預模式的研究尚處在探索階段,這是我國網絡輿情治理的嶄新課題。目前,對政府網絡輿情干預模式的研究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是按政府干預手段的形態,劃分為強制性和非強制性兩種干預模式。其中,強制性干預模式是指通過諸如反煽動叛亂法、信息安全法、謠言處理條例、色情管制法、誹謗罪法等法律法規對網絡負面輿情進行動態監視、強制管理和行政約束。非強制性干預模式則是指政府利用自身的政治、信息、人力、物力和技術等諸多優勢,按照政權統治和社會穩定的需要,影響媒體議程和輿論導向。主要手段包括新聞審查制、微博問政、新聞發言人制度、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等等。第二種是按政府干預方式的能動性,劃分為主動式和被動式兩種干預模式。在主動式干預模式中,政府主動收集和研判網絡輿情信息,充分發揮內部監督和運行機制的功能,掌控網絡輿情的演變和發展趨勢,坦誠接受民眾的監督,有效引導網絡輿論導向,并及時地反饋監測結果,通過政府權威平臺發布網絡輿情的發展動向和處理結果。而在被動式干預模式中,政府喪失了網絡輿情的主導權,被動地啟動輿情的管控和介入程序,并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觸發政策調整議程,落實傾向民意的處理辦法,以平息事態。以上兩種模式的劃分,只是為做學理分析而進行類型化處理。網絡輿情的生態治理,是一項系統而又復雜的工程,也是檢驗政府應對網絡突發公共輿論事件能力的試金石。在實際工作中,政府對網絡輿情的干預往往是多舉齊下,有的放矢。筆者試圖以干預主體為思考線索,認為改善網絡輿論生態,需要加快構建以“政府主導為前提,法律規范為基礎,行政監管為依托,行業自律為保障,技術支持為輔助,公眾監督為補充”的網絡輿情治理的多元主體合作模式。如是,電子政府、網絡組織、媒體行業、社會民眾四者才能形成網絡輿情治理的共同體意識,承擔起網絡社會治理的歷史使命。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網絡社會先天發育不足,加之市場制度不完善,協同合作的文化土壤缺乏,該合作治理模式能否在現實生活中發揮有效作用,還需要實踐的檢驗。
3.政府網絡輿論生態治理路徑選擇
政府在網絡輿論治理中承擔著主體責任,表現為既要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網絡輿論自由權利,又要采取適度干預措施,以規范網絡生態秩序的平穩運行。借鑒國外網絡輿情治理的先進經驗,并結合我國當下網絡輿情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趨勢,需要在立法保障、制度設計、技術治理、行業自律、文化建設等方面實現政府由“管網”向“治網”的角色轉變。
(1)立法保障:彌補政府網絡立法缺陷的不足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完善網絡信息服務、網絡安全保護、網絡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5}。前文已述,我國現行憲法明確規定保障公民言論自由權利不受侵犯,但對網絡言論自由權的立法保障存在嚴重缺陷。無論是英美等普通法系,還是德、法等歐洲大陸法系國家都認為,“言論的多元化是民主社會的根本,要求言論自由不僅應該保護主流意見和觀點,更應該保護少數的、邊緣的和非正統的意見”[27]。因此,將網絡言論自由納入言論自由的憲法保護范疇,并在部門法和單行法的立法規制中賦予網絡言論的權利屬性和民主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同時,我國有關網絡言論自由和輿情監管的部門法、單行法,或缺乏具體的明文規定,或條款的操作性不足,或權利與義務不對稱。因此,我國政府應當在規范網絡輿論的立法建設中彌補現有法律法規體系的不足之處:既要適度弱化網絡立法的處罰性措施,加強激勵性規范的制度設計,又要規范法律條文的規范化設置,增強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既要彰顯公民的網絡輿論權,平衡政府、網絡組織、媒體行業、新聞工作者、個人的網絡輿情責任,又要厘清不同行政部門的權力與責任邊限,防止執法重疊,堵住執法漏洞等現象。
(2)制度設計:探索合作式網絡輿情治理模式
政府的網絡治理是政府必須擔當起的重要職責。網絡輿情生態治理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政府網絡治理的“善治”,而“善治”的本質特征是“公民、社會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獨立管理或與政府的合作管理”[28]。網絡輿情的合作治理以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包括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的自我規范(自律)和制度約束(他律)為基礎,強調網絡治理主體間的彼此合作和權利共享,以達到網絡輿論治理的善治目標。作為網絡輿論的自律主體,網民、新聞工作者、自媒體組織應當在充分行使網絡輿論自由權的同時,承擔網絡輿論治理的應盡義務。由于網絡社會的“匿名性”“虛擬性”“面具化”等特性,無論是現實的或虛擬的政府,僅僅依靠公權力的強制干預,無法對網絡輿論的犯罪及異化現象進行有效的制約和規范。因此,網絡輿情的善治更多地應當依靠網民、自媒體、網絡社群組織等利益主體的自律行為,進而逐步建立以自律為核心、剛柔并濟的網絡道德系統。作為網絡治理的他律力量,政府的職責主要是通過法律授權的方式,“在行政許可、行業監管、注冊登記、業務審查等方面制定和落實法律的相關制度”[29],并加強技術監管,發揮社會輿論力量,拓展網民的權益表達途徑,依法追究侵權責任。同時,政府與網絡社群組織之間應當建立起有效的溝通和合作機制,鍛造有效的輿論表達平臺,引導網絡話題的均衡分布,以消解政府與社群組織之間的對抗與內耗,形成多元主體合作的格局。
(3)技術治理:增強政府輿情監管能力
網絡技術以某種方式重構了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現實,并深入影響著人類行為。“盡管技術具有其自身的力量,但是,它不獨立于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30]因此,網絡技術不僅是網絡輿論權利形成的源起,也是治理網絡輿論失范和防控網絡輿情安全的有力保障。國內學者對網絡輿情信息的監管主要存在“事前預防”和“事后追懲”兩種模式。從實踐來看,多數國家對“事前運用技術預防”持審慎態度,普遍傾向于采取“事后追懲”的模式,也即只有違法違規行為發生后并得到識別,才通過法律方式予以追究,一般不做普遍的預先審查。[31]鑒于網絡輿論廣泛而深刻的傳播影響力,如果缺乏普遍的預先審查環節,極易導致不法分子或別有用心者利用“單邊壟斷”和技術“獨霸”優勢,大規模收集敏感數據,威脅國家網絡空間安全。網絡輿情的技術治理應當采取普遍過濾的預審查與人工干預的后抽查相結合的方式。當務之急是加強對信息技術產品及其供應商開展網絡安全預先審查的制度設計。因此,既要建立起完善的、以技術為支撐的網絡輿情信息收集、挖掘、分析與研判的數據庫,為網絡輿情信息的預先審查提供依據,又要構建起網絡突發輿情事件的預警防控、協作組織與應急處置,及時遏制違法網絡輿論的傳播風險,并追究相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32]。
(4)文化建設:提升政府柔性治理能力
美國學者理查德·斯皮內洛指出:“社會和道德方面很難跟上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而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抓住信息時代機遇的同時,卻并不是總能意識到和密切關注各種風險,以及為迅猛的技術進步所付出的日漸增長的社會代價。”[33]筆者前文已述,網絡輿情的生態治理應當是剛柔并濟。既要以立法為依據,明確網絡輿論自由的權限,又要更多地借助柔性的治理方式,依靠網絡倫理道德和文化建設,發揮道德教化的引導作用。尤其在網絡立法欠缺的當下中國,網絡倫理文化的“軟”力量可以更有效地引導、規范和約束網民的不道德、不理性,乃至違法違規行為。一要充分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優秀的傳統文化理念滲透網絡虛擬空間。尤其是秉持“慎獨”的傳統道德理念,網民、媒體行業、網絡社群組織不僅要主動接受法律、制度和組織的監督,還要不斷加強自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二要建立健全互聯網文化市場體系。既要嚴厲查處損害國家利益,消磨干群意志和腐蝕人民靈魂的負面輿情信息,又要努力構建以法律法規為基礎、誠實信用為原則、市場監管為保障、行業自律為補充的網絡文化市場支撐體系,以彌補市場自身配置的不足。三要推進服務型“虛擬政府”建設,推動政務公開,增強政府執法透明度。同時,凝聚重點新聞網站、政務信息網站和各類文化和商業主流媒體的共識,加強網絡主流文化價值宣傳。
四、余論
網絡輿情的生態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個不斷探索、反復實踐、持續改進的動態過程。網絡輿情的治理儼然已成為我國網絡社會治理的關鍵領域。網絡輿情治理的核心問題是政府角色。作為網絡輿情治理的主要責任者,政府既要充分保障網民網絡輿論自由的權利,又要適度干預網絡突發輿情,以規范網絡生態秩序。
為實現政府網絡輿情治理角色的“善治”轉變,應努力學習國外網絡輿情治理的先進經驗,并結合我國網絡輿情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趨勢,探索和實踐我國網絡輿情治理的善治途徑。同時,加強網絡輿情治理的立法進程,合理界定網絡利益主體的權利與義務,提升網絡輿情防控的技術治理能力,并強化網絡行業的自律與監督機制,運用道德、倫理對網民、新聞工作者和社群組織的網絡行為進行引導和規勸。同時,改善網絡輿論生態,應當加快構建以“政府主導為前提,法律規范為基礎,行政監管為依托,行業自律為保障,技術支持為輔助,公眾監督為補充”的網絡輿情治理的多元主體合作模式。
注釋:
①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6年1月22日。
{2} 《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22頁。
{3} 《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31頁。
{4} 聯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第2200A(XXI)號決議《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13條)。
{5} 參見2014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參考文獻:
[1] 楊維東.構建網絡輿情應對長效機制[N].光明日報,2016-03-31(007).
[2] [美]唐·泰普斯科特.數字化成長:網絡時代的崛起(第1版)[M].陳曉開,哀世佩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McCraw-Hill出版公司,1999:3-4.
[3] [美]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13.
[4] 陸斗細,楊小云.近幾年來網絡圍觀議政現象研究的回顧與思考[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3):34-40.
[5] 何舟,陳先紅.雙重話語空間:公共危機傳播中的中國官方與非官方話語互動模式研究[J].國際新聞界,2010(8):21-27.
[6] 支庭榮.集合傳播權與謙抑性原則——解析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兩個輿論場”[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2):31-36.
[7] 童兵.官方民間輿論場異同剖析[J].人民論壇,2012(13):34-36.
[8] 劉九洲,付金華.以媒體為支點的三個輿論場整合探討[J].新聞界,2007(1):36-37.
[9] 張勤. 網絡輿情的生態治理與政府信任重塑[J].中國行政管理,2014(4):40-44.
[10][美]埃瑟·戴森.2.0版數字化時代的生活設計[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7.
[11] 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434.
[12] 蒙曉陽,李華.中國網絡立法的法理前瞻[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5(4):63-69.
[13] [美] 戴維·奧斯本,特德·蓋布勒 :改革政府[M].上海市政協編譯組,東方編譯所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218.
[14] 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M].黃維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7.
[15] 馬凌.風險社會語境下的新聞自由與政府責任[J].南京社會科學,2011(6):37-43.
[16] [英]丹寧勛爵.法律的訓誡[M].楊百揆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9.
[17] [美]凱斯·R·孫斯坦.自山市場與社會正義[M].金朝武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2002:252-253.
[18] 陳純柱,韓兵.我國網絡言論自由的規制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13(5):83-91.
[19] 劉文富.網絡政治:網絡社會與國家治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7.
[20] 卓澤淵.法政治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4.
[21] [英]洛克.政府論(下篇)[M].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5.
[22] 林凌.論依法引導網絡輿論——兼論網絡言論自由權保護[J].學海,2012(2):169-176.
[23] [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7.
[24] [英]約翰·密爾.論自由[M].程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1.
[25] 王魯捷.論政府適度干預[J].中國行政管理,1995(8):41-42.
[26] 王新華,房美玲.論政府網絡輿論干預的邊限[J].求索,2010(11):56-58.
[27] 邢璐.德國網絡言論自由保護與立法規制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德國研究,2006(3):34-38.
[28]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5):37-41.
[29] 汪玉凱.加強網絡治理是各國政府的重要職責[N].光明日報,2012-06-08(004).
[30] Priscilla Regan,:Legislating Priv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p.12.
[31] 顧理平.網絡輿論監督中的權利義務平衡[J].社會科學戰線,2016(3):152-151.
[32] 張佳慧.中國政府網絡輿情治理政策研究:態勢與走向[J].情報雜志,2015(5):123-127.
[33] [美]理查德·A.斯皮內洛.世紀道德——信息技術的倫理方面[M].劉鋼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