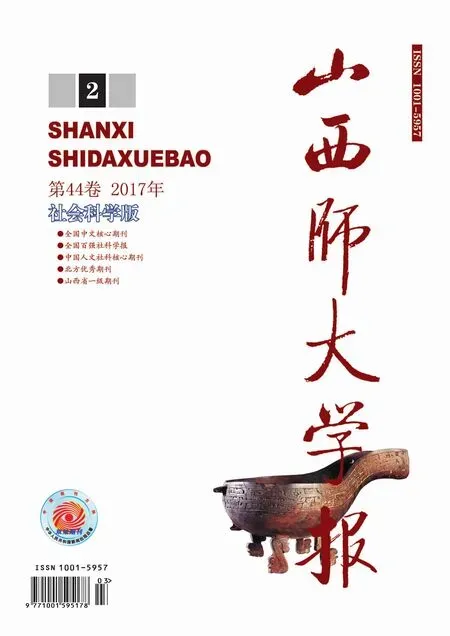從三晉方足布的分布情況看戰(zhàn)國(guó)中原人口的遷徙
段 穎 龍
(北京陽(yáng)光書(shū)苑,北京 100013)
三晉方足布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流通的一種布幣,其形制為平首,平肩,方足,方襠的片狀,因其面文多為三晉地名,故被定為三晉貨幣。研究三晉方足布,可以豐富我們對(duì)戰(zhàn)國(guó)地理地名的認(rèn)知。然而,三晉方足布是如何流通的?面文上的地名是否暗示其所流通的地域?如果我們需要結(jié)合古文獻(xiàn)與其出土分布來(lái)還原戰(zhàn)國(guó)貨幣的流通與人口遷徙的情況,以上問(wèn)題自然可解。
一、從都邑到邊塞的方足布分布
自春秋以降,諸侯大國(guó)的都城或一些都邑內(nèi)就已經(jīng)使用金屬錢(qián)幣了。如山西侯馬春秋晉國(guó)都城新田遺址[1]46,河南洛陽(yáng)東周王城遺址[2]124等都曾出土春秋空首布幣。至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一些都城沒(méi)落了,如侯馬晉都新田;還有一些都城繼續(xù)興盛,如新鄭鄭韓故城,在春秋時(shí)期為鄭國(guó)都城,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繼續(xù)作為韓國(guó)都城;另有一些新興的都城或都邑,如邯鄲趙王城、易縣燕下都等,在這些都城和都邑遺址內(nèi),都曾出土有三晉方足布。
在都城或都邑內(nèi)出土方足布幣,是當(dāng)時(shí)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以及集市貿(mào)易繁盛的體現(xiàn)。當(dāng)然,都邑也是錢(qián)幣發(fā)生與發(fā)展的原點(diǎn)。然而戰(zhàn)國(guó)錢(qián)幣出土分布卻不僅限于列國(guó)都城,很多已伸向了邊遠(yuǎn)地區(qū)。如山西陽(yáng)高、祁縣、原平,河北靈壽、鹿泉,內(nèi)蒙古包頭、涼城、和林格爾,遼寧鐵嶺等地都曾出土方足布(據(jù)《中國(guó)歷代貨幣大系·先秦卷·先秦鑄幣出土簡(jiǎn)況表》及其圖注資料,以下方足布出土地信息皆同)。以上地點(diǎn)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悉屬趙、燕兩國(guó)邊塞。
在一些諸侯國(guó)邊關(guān)要塞遺址附近出土的戰(zhàn)國(guó)窖藏的錢(qián)幣數(shù)量巨大,且有些甚至多于都邑出土的窖藏錢(qián)幣。這說(shuō)明,在出征或在邊境駐扎的軍隊(duì)中,必然存在著大量使用貨幣交易的情況。《商君書(shū)·墾令》即記載了在秦國(guó)軍隊(duì)的駐地附近,有供軍士購(gòu)買(mǎi)日用品的“軍市”,那么軍隊(duì)在軍市中可以使用錢(qián)幣,應(yīng)是與列國(guó)都邑內(nèi)的集市用錢(qián)如出一轍。
關(guān)于東周集市錢(qián)幣的使用方式,據(jù)拙文《東周錢(qián)幣起源“契券”考》對(duì)先秦金屬錢(qián)幣的起源問(wèn)題所作的綜合性研究,通過(guò)大量錢(qián)幣銘文考釋并結(jié)合古文獻(xiàn)、訓(xùn)詁學(xué)、貨幣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相關(guān)論證,我們得出所有先秦錢(qián)幣最早源于具有信用性質(zhì)的“質(zhì)劑”“傅別”這類(lèi)契券的結(jié)論。[3]根據(jù)《周禮·泉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待不時(shí)而買(mǎi)者”及貨幣經(jīng)濟(jì)學(xué)原理,推測(cè)周代泉府是將集市交易后的滯銷(xiāo)商品按平價(jià)以支付布匹的形式收購(gòu),以等待那些需要這些商品的人來(lái)購(gòu)買(mǎi)。再據(jù)《周禮·質(zhì)人》的記述,知周代質(zhì)人管理集市中的貨賄、珍異等商品,用質(zhì)劑作為買(mǎi)賣(mài)者交易的信用憑證。再據(jù)《周禮·泉府》描述周代泉府經(jīng)營(yíng)“凡賒者,祭祀無(wú)過(guò)旬日,喪紀(jì)無(wú)過(guò)三月”的記載,知泉府可賒買(mǎi)祭祀和喪葬用品。而《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亦載:“條侯子為父買(mǎi)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司馬貞《索隱》:“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可知漢代“尚方”是生產(chǎn)和銷(xiāo)售喪葬品和其他器物的官營(yíng)作坊。那么周代泉府恐怕也有生產(chǎn)和銷(xiāo)售各類(lèi)喪葬、生活物資的可能,出土的戰(zhàn)國(guó)和漢代墓葬中也不乏印有“某府”字樣的隨葬器物。綜合以上幾點(diǎn)考慮,我們認(rèn)為,泉府的經(jīng)營(yíng)模式是兼典當(dāng)、生產(chǎn)作坊和商鋪于一身的。據(jù)此所復(fù)原的東周集市貿(mào)易的基本形態(tài)為:普通商品交易是用布、谷作支付媒介或干脆用以物易物的形式進(jìn)行,而在購(gòu)買(mǎi)一些市場(chǎng)鮮有的祭祀、喪葬用的奢侈品時(shí),就需要到泉府中用實(shí)物來(lái)訂購(gòu)這類(lèi)商品以換取契券作為商品債務(wù)憑證。泉府在約定期限內(nèi)為訂購(gòu)者收購(gòu)或訂做所需奢侈品,比如絲綢錦緞。到約定期后,買(mǎi)家便攜券來(lái)泉府領(lǐng)取所訂做的物品。久而久之,泉府的這種經(jīng)營(yíng)模式就會(huì)轉(zhuǎn)變?yōu)榈洚?dāng)?shù)臋C(jī)制,而這種具有信用性質(zhì)的用于異時(shí)領(lǐng)取貨品的契券憑證也就演變?yōu)殄X(qián)幣了。[3]百姓用布匹從泉府中換來(lái)的錢(qián)幣可在集市中流通,錢(qián)幣幾經(jīng)易手,最終還會(huì)回流到泉府。[3]所以最初錢(qián)幣的流通范圍也僅限于泉府和集市。春秋時(shí)期的空首布就應(yīng)是都邑集市和泉府所運(yùn)作的錢(qián)幣。
到了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隨著戰(zhàn)爭(zhēng)規(guī)模的擴(kuò)大,各大諸侯國(guó)都出現(xiàn)了在邊境長(zhǎng)期駐扎軍隊(duì)的情況,戰(zhàn)國(guó)長(zhǎng)城的建置就是這一現(xiàn)象的具體體現(xiàn)。那么在邊關(guān)要塞附近設(shè)置“軍市”的原因,就是方便戍邊部隊(duì)日常生活。由于軍中不可能每名將士都攜帶大量布帛或谷物作為日常耗用,所以將泉府發(fā)行錢(qián)幣的經(jīng)營(yíng)機(jī)制移植到邊塞就顯得十分有必要了。因?yàn)殄X(qián)幣小而便于攜帶,且有契券的信用性,國(guó)家可以根據(jù)實(shí)際需要而任意賦予錢(qián)幣以購(gòu)買(mǎi)力,所以將士們只要攜帶少量的錢(qián)幣就可以供應(yīng)較長(zhǎng)時(shí)間的日常消耗了。戰(zhàn)國(guó)邊塞軍市錢(qián)幣的使用表明,春秋以來(lái)錢(qián)幣流通區(qū)域從大都邑的集市迅疾遠(yuǎn)播到邊疆地區(qū),使得錢(qián)幣的流通范圍驟然擴(kuò)張。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邊塞地區(qū)大量錢(qián)幣窖藏的出現(xiàn),既是錢(qián)幣走出大都邑而流通至邊遠(yuǎn)地區(qū)的重要標(biāo)志,又是漢代以后錢(qián)幣空前普及的關(guān)鍵性起點(diǎn),也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dòng)的明證。
戰(zhàn)國(guó)軍隊(duì)中普遍使用錢(qián)幣的現(xiàn)象,還能在出土的秦簡(jiǎn)文獻(xiàn)中找到相關(guān)情況的蛛絲馬跡。1975年湖北云夢(mèng)睡虎地4號(hào)秦墓出土了兩枚秦國(guó)士兵寫(xiě)給家里的木牘信件,信的內(nèi)容透露出秦軍使用錢(qián)幣的原因,其中一枚木牘文曰:
……黑夫寄益就書(shū)曰:“遺黑夫錢(qián),母操夏衣來(lái)……令與錢(qián)偕來(lái)。其絲布貴,徒[以]錢(qián)來(lái),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等直佐淮陽(yáng),攻反城久,傷未可知也,愿母遺黑夫用勿少……”[4]83
信是秦軍士兵黑夫?qū)懡o家中的老母,他希望母親能寄來(lái)錢(qián)幣與夏天的衣服。信中強(qiáng)調(diào)如果布昂貴,就寄來(lái)更多的錢(qián)幣,他自己買(mǎi)布做衣服。“直佐淮陽(yáng),攻反城久”即黑夫所屬的秦軍已經(jīng)駐兵于楚國(guó)的淮陽(yáng),并以此為據(jù)點(diǎn),進(jìn)攻楚國(guó)其他反叛的城池。這是秦將王翦發(fā)動(dòng)的第二次滅楚戰(zhàn)爭(zhēng)中發(fā)生的事。由此可見(jiàn),戰(zhàn)國(guó)時(shí)的軍中士兵很可能需要自備衣物。而除了衣服之外,仍需要家中供應(yīng)錢(qián)幣,這些錢(qián)幣應(yīng)是用于士兵們購(gòu)買(mǎi)軍糧的。當(dāng)然,軍隊(duì)的大量生活物資是需要通過(guò)后方補(bǔ)給線由陸路的輜重車(chē)或水路的運(yùn)輸船供應(yīng)的。但由這篇書(shū)信可知,這些軍用生活物資對(duì)將士來(lái)說(shuō)并非是免費(fèi)的。因?yàn)樵谲婈?duì)實(shí)行募兵制以前,軍需都是要靠士兵自備的。如果長(zhǎng)期在前線征戰(zhàn),士兵無(wú)法攜帶足夠的糧食,只能靠后勤糧草補(bǔ)給線維持,而軍糧是需要士兵出錢(qián)來(lái)購(gòu)買(mǎi)的。所以黑夫?qū)懠倚乓竽赣H寄衣外,似乎寄更多的錢(qián)幣是習(xí)以為常的事,這些錢(qián)幣正是維系士兵生存的口糧錢(qián)。
同樣,長(zhǎng)期在外服徭役,民夫們無(wú)暇種地,糧食供應(yīng)也需要靠家人或官府。服徭役離家較遠(yuǎn)的,則必須都由官府統(tǒng)一供應(yīng)糧食。這些糧食也需要民夫用錢(qián)幣來(lái)購(gòu)買(mǎi)。《云夢(mèng)秦簡(jiǎn)》中有關(guān)于服徭役的民夫飲食用餐制度的記載:
有罪以貲贖及有責(zé)(債)於公,以其令日問(wèn)之,其弗能入及賞(償),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錢(qián);公食者,日居六錢(qián)。(《云夢(mèng)秦簡(jiǎn)·司空》6)
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勞與垣等者,旦半夕參。(《云夢(mèng)秦簡(jiǎn)·倉(cāng)律》21)
《司空》中說(shuō),為贖罪和需要給官府償債的人可到官府干活,能帶飯的每日給八個(gè)工錢(qián),需要官府供應(yīng)餐飯的,每日可領(lǐng)到六個(gè)工錢(qián)。這些工錢(qián)都是為抵罪和還債之用,并非是為購(gòu)買(mǎi)日用品的。既然須由官府供給一日餐飯者要比帶飯者每日少二錢(qián),那也就是說(shuō),一日餐飯的費(fèi)用約值二錢(qián)。《倉(cāng)律》又說(shuō),給修筑城垣的徭役工人供應(yīng)的口糧是早飯半升(旦半),晚飯三分之一升(夕參),說(shuō)明工人每天吃兩餐飯。這樣算下來(lái),平均一餐飯大概價(jià)值就是一個(gè)錢(qián)。秦國(guó)當(dāng)時(shí)流行的錢(qián)幣是“秦半兩”,大概一枚“秦半兩”的購(gòu)買(mǎi)力在當(dāng)時(shí)就是一頓飯的費(fèi)用。這種推測(cè)得到了另一批秦簡(jiǎn)文獻(xiàn)的佐證:“受米一石,臧(贓)直(值)百卌,得。”(《里耶秦簡(jiǎn)》8-2015)這里明確說(shuō),一石米的市值是140錢(qián)。若參比《倉(cāng)律》,一個(gè)普通勞動(dòng)者一餐早飯食量為半升,晚飯為三分之一升,按一日早、晚兩餐花費(fèi)二錢(qián)來(lái)算,一石(100升為一石)米約花費(fèi)167錢(qián)。這與簡(jiǎn)文所記一石米140錢(qián)的價(jià)值極為相近。
依據(jù)以上結(jié)論,在軍事要塞和工程遺址附近出土的窖藏錢(qián)幣,也許就是駐扎于當(dāng)?shù)氐氖勘兔穹騻冊(cè)跔I(yíng)地里集體享用最后一餐飯的耗費(fèi)。所以文章認(rèn)為,窖藏錢(qián)幣的數(shù)量等于在此營(yíng)地駐扎的士兵或民夫的人數(shù)。那么在山西陽(yáng)高、原平,內(nèi)蒙古涼城、和林格爾等偏遠(yuǎn)地區(qū)集中出土的方足布幣窖藏和墓葬所陪葬的方足布就可以解釋為是軍隊(duì)在戍守邊疆時(shí)日常所用。士兵在邊疆死亡后,亦可將錢(qián)幣作為陪葬品下葬。
二、燕下都出土三晉方足布的歷史解釋
20世紀(jì)60—80年代初,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內(nèi)先后有25次出土窖藏燕刀幣,共計(jì)33315枚。[5]布幣共出土1100多枚,其中燕國(guó)安陽(yáng)布149枚,趙國(guó)尖足布和方足布400多枚,韓、魏布幣各數(shù)十枚。[6]
燕下都出土貨幣的情況比較復(fù)雜,不但燕、三晉、兩周貨幣共存,而且還發(fā)現(xiàn)過(guò)戎狄刀幣。一座都邑能同時(shí)發(fā)現(xiàn)多國(guó)錢(qián)幣,很多學(xué)者認(rèn)為這是國(guó)際貿(mào)易繁盛的結(jié)果,各國(guó)貨幣可以自由匯兌。但是,造成貨幣匯兌這一現(xiàn)象至少必須具備兩個(gè)條件中的一個(gè):一是兩國(guó)貨幣成色必須相當(dāng),大小必須一樣或成比例,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貨幣自身的實(shí)際價(jià)值;一是不必考慮兩國(guó)貨幣形制與成色,但須有對(duì)每種貨幣的購(gòu)買(mǎi)力所達(dá)成的國(guó)際共識(shí)。初看東周各國(guó)貨幣,其形制殊異,大小也不同,甚至不同窖藏出土的同種形制錢(qián)幣也存在大小及成色上的差異,故第一種條件在東周時(shí)期是不具備的。而在漢代以后,不同朝代和國(guó)家鑄造的錢(qián)幣往往可以混雜在一起使用,這正是由于錢(qián)幣的大小和形制的統(tǒng)一所決定的。前代成色好且制作精良的錢(qián)幣自然可以一直流通,其匯兌比率應(yīng)是1∶1。最典型的實(shí)例出現(xiàn)在宋代,1983年河南息縣鄭寨熊莊出土南宋錢(qián)幣窖藏,清理出的650余公斤銅錢(qián)中,年代最早的有西漢半兩,最晚的為南宋淳熙元寶,而從北宋太祖到南宋孝宗各朝的錢(qián)幣皆有。[2]3531981年內(nèi)蒙古林西縣新城子鎮(zhèn)發(fā)現(xiàn)的遼代錢(qián)幣窖藏出土古錢(qián)775.75公斤,計(jì)有20余萬(wàn)枚。這些錢(qián)幣有226個(gè)品種,以唐代和與窖藏同時(shí)期的宋代錢(qián)幣為最多,而遼錢(qián)計(jì)有10種,246枚。[7]這些窖藏錢(qián)幣雖然年代跨度較大,但錢(qián)型皆為圓形方孔,大小輕重也十分近似,故可混同使用。而東周時(shí)期諸侯之間關(guān)系錯(cuò)綜復(fù)雜,時(shí)戰(zhàn)時(shí)和。況且很多國(guó)家本國(guó)尚有若干種形制的錢(qián)幣,恐難有后世對(duì)某些錢(qián)幣形成的國(guó)際共識(shí)。所以推測(cè)東周不同類(lèi)別的錢(qián)幣根本無(wú)法實(shí)現(xiàn)匯兌。
既然東周錢(qián)幣無(wú)法實(shí)現(xiàn)兌換,那又如何解釋燕下都一座都邑會(huì)出現(xiàn)多國(guó)錢(qián)幣呢?據(jù)前文的考證,東周錢(qián)幣作為信用貨幣由泉府發(fā)行,流通范圍也僅在集市中,所以這個(gè)現(xiàn)象恐怕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每種錢(qián)幣在一個(gè)特有信用體系下獨(dú)自流通。事實(shí)上,《史記》《戰(zhàn)國(guó)策》《韓詩(shī)外傳》《說(shuō)苑》等“各書(shū)雖然都記載了燕昭王招賢納士這件事,但并未說(shuō)明燕昭王是在燕國(guó)的什么地方接待各國(guó)的賢士,只有《水經(jīng)注》中明確記載燕昭王接待各國(guó)賢士的地點(diǎn)是在燕下都,燕昭王為了接待‘諸侯之客’,因而‘修建下都,館之南垂’”[8]187。燕下都位于燕國(guó)南部,地近于中原,燕昭王為振興燕國(guó)而勵(lì)精圖治,營(yíng)建燕下都作為吸引中原諸侯之民的都邑,故燕下都同時(shí)出土燕刀幣、三晉兩周方足布、趙國(guó)刀幣及戎狄刀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些中原和北方國(guó)家的賢士在燕下都受到禮遇,更刺激了這些國(guó)家的底層平民成批涌向這里定居下來(lái),進(jìn)而在燕下都形成新的社區(qū)里坊,各自通行本族群的貨幣。在發(fā)現(xiàn)于燕下都的三晉方足布上的三晉古地名相對(duì)應(yīng)的如今所在地上,卻從未出土過(guò)三晉錢(qián)幣,所以推測(cè)徙居燕下都的三晉移民原本在故鄉(xiāng)不通行錢(qián)幣,但他們移居到燕下都后,可能為了標(biāo)明自己的來(lái)源及身份,才鑄造了面文為其祖居地名稱的方足布。
三、避難性戰(zhàn)爭(zhēng)移民對(duì)方足布流通擴(kuò)張的影響
秦錢(qián)的流通與分布呈東漸的態(tài)勢(shì),而中原諸國(guó)的錢(qián)幣發(fā)展則呈現(xiàn)出兩種現(xiàn)象:一是一地同出兩國(guó)甚至多國(guó)錢(qián)幣;二是列國(guó)在后期開(kāi)辟的新領(lǐng)地上,錢(qián)幣的發(fā)展與擴(kuò)張較迅速,分布也較為廣泛和密集。這些現(xiàn)象必然與廣大平民的活動(dòng)不無(wú)關(guān)系。燕下都出土的三晉布幣已經(jīng)證明是三晉之民為趨利而匯聚并定居在燕下都,從而在此通行方足布。那么,其他地方方足布的分布和擴(kuò)張又有著怎樣的原因呢?
(一)一地同出多國(guó)錢(qián)幣的原因
在一些大都邑遺址中,經(jīng)常會(huì)出現(xiàn)一處錢(qián)幣窖藏中有兩個(gè)分裝著不同國(guó)家錢(qián)幣的陶罐。典型的案例有:1957年北京市朝陽(yáng)門(mén)外呼家樓出土一坑戰(zhàn)國(guó)錢(qián)幣窖穴,其中有刀幣2884枚,布幣992枚。除燕、趙刀幣與趙國(guó)尖足布外,余皆為三晉方足布。面文有“大陰”“茲氏”“莆子”“皮氏”“北屈”“屯留”“長(zhǎng)子”等三晉地名[9];2006年7月,北京市宣武區(qū)廣義街出土窖藏兩陶罐,內(nèi)藏戰(zhàn)國(guó)中晚期燕、三晉、周等國(guó)錢(qián)幣約三萬(wàn)枚,其中一罐藏方足、尖足布幣,方足布中有鑄“屯留”“宅陽(yáng)”“奇氏”“皮氏”“莆子”“北屈”等三晉地名者。另一罐藏燕、趙刀幣。[10]這種不同地區(qū)的貨幣卻同藏于一處的現(xiàn)象該如何解釋呢?
一國(guó)都邑內(nèi)同時(shí)出土多國(guó)錢(qián)幣,一貫被學(xué)者看作是國(guó)際貿(mào)易的見(jiàn)證,在集市中進(jìn)行貨幣匯兌的結(jié)果。而前文已證,每種體系貨幣都由其所經(jīng)營(yíng)的泉府發(fā)行,它們只能各自在集市中流通,兩個(gè)不同國(guó)家的錢(qián)幣分別由各自國(guó)家的泉府機(jī)構(gòu)所掌握。在流通時(shí),二者并行不悖,似乎也并不能產(chǎn)生匯兌關(guān)系。前文還證明,燕下都出土三晉錢(qián)幣是移民的結(jié)果。那么北京市出土燕、三晉貨幣是否也是移民的結(jié)果呢?答案可以從東周墓葬考古中得到蛛絲馬跡。分布于山西侯馬及以南的萬(wàn)榮、聞喜、曲沃一帶的戰(zhàn)國(guó)早、中期平民墓葬明顯是晉文化的分支,當(dāng)是晉國(guó)魏氏家族所管轄的百姓及后來(lái)魏國(guó)的墓葬。[11]123—124據(jù)《史記·魏世家》載,由于魏國(guó)受到西面日益強(qiáng)大的秦國(guó)所逼,故于公元前361年“徙治大梁(今河南開(kāi)封西北)”;魏昭王六年(公元前290年),魏國(guó)更“予秦河?xùn)|地方四百里”。河?xùn)|地區(qū)正與此系魏人墓葬區(qū)地域相合,而其墓葬區(qū)衰落時(shí)間也大抵近于公元前290年。考古工作者將山西萬(wàn)榮廟前村,侯馬喬村、上馬墓地,聞喜邱家莊、上郭墓地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戰(zhàn)國(guó)早期的一系陶器墓葬(H2組)的類(lèi)型定為Ab亞類(lèi)型,即由晉文化分支出來(lái)的魏人統(tǒng)治下的晉遺民墓。[11]53,124而此系墓葬亞類(lèi)型在河?xùn)|衰落后,卻在中原的周都洛陽(yáng)、鄭韓以及魏國(guó)河內(nèi)地區(qū)獲得很大發(fā)展。[11]112在豫北古屬河內(nèi)地區(qū)的輝縣琉璃閣、固圍村、褚邱、趙固和新鄉(xiāng)楊崗等一組戰(zhàn)國(guó)早期延至戰(zhàn)國(guó)晚期早段的墓地(A2組)發(fā)現(xiàn)了同樣的Ab亞類(lèi)型[11]70,93,111。其時(shí)間跨度之所以大,是由于這里既有自戰(zhàn)國(guó)前期晚段“三家分晉”時(shí)就從河?xùn)|遷徙而來(lái)的魏人,又有戰(zhàn)國(guó)中期從安邑遷都大梁時(shí)東遷的魏人,更有戰(zhàn)國(guó)中期晚段魏國(guó)割讓河?xùn)|后東遷的魏人遺存。而分布于鄭州地區(qū)二里岡、崗杜兩地相對(duì)獨(dú)立墓區(qū)的一組戰(zhàn)國(guó)中晚期墓地(Z5組)及洛陽(yáng)燒溝、孫旗屯、中州路、澗東、玻璃廠及老城環(huán)衛(wèi)站的一組戰(zhàn)國(guó)中晚期墓(L2組)也發(fā)現(xiàn)了Ab亞類(lèi)型。[11]60,66故A2組、Z5組、L2組的墓葬年代上承H2組墓地[11]111,前三者與后者必然存在淵源關(guān)系,應(yīng)是河?xùn)|地區(qū)的魏人遷徙并滯留此三地而獲得特殊發(fā)展的文化遺存。[11]124這是先后因?qū)俚氐闹匦聞澐帧⑦w都和割地而導(dǎo)致的三次集體大移民。
由于受晉南中條山、豫西山地等地形的阻隔,河?xùn)|的遷徙之民不可能沿道路崎嶇的山脈而行,其所選擇的遷徙路徑應(yīng)是平坦易行的河道水路。據(jù)《史記·河渠書(shū)》記載,戰(zhàn)國(guó)時(shí)的魏國(guó)漕運(yùn)十分發(fā)達(dá),其境內(nèi)開(kāi)鑿鴻溝以連接黃河與淮河。而魏國(guó)對(duì)農(nóng)田水利建設(shè)也極為重視,“西門(mén)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nèi)”。1935年河南汲縣山彪鎮(zhèn)一號(hào)墓出土戰(zhàn)國(guó)早期魏國(guó)錯(cuò)紅銅水陸攻戰(zhàn)紋銅鑒,銅鑒上有戰(zhàn)船水戰(zhàn)場(chǎng)景,再次證明魏國(guó)在河內(nèi)地區(qū)的水上運(yùn)輸及水面作戰(zhàn)能力極強(qiáng)。故魏人的遷徙路徑大概是:自晉南黃河干流向東遷徙至洛陽(yáng);進(jìn)而通過(guò)黃河支流及運(yùn)河漕運(yùn)遷至鄭州;再一部分通過(guò)古黃河水道向北遷至河內(nèi)地區(qū)及今開(kāi)封一帶的大梁。輝縣、新鄉(xiāng)是戰(zhàn)國(guó)中晚期魏國(guó)在中原的統(tǒng)治中心河內(nèi)地區(qū)之所在,洛陽(yáng)時(shí)為周王城所在地,鄭州及南部的新鄭則為韓國(guó)屬地和都城所在地。魏人的集體遷徙,正可以解釋在輝縣、洛陽(yáng)、新鄭和鄭州地區(qū)出土的許多典型魏國(guó)橋襠布幣。如河南輝縣固圍墓地M1和M2均出土魏國(guó)的“梁正尚百當(dāng)寽”橋襠布[12]圖版肆捌,新鄭鄭韓故城遺址內(nèi)亦出土“梁正尚百當(dāng)寽”橋襠布幣范及鑄有魏國(guó)河?xùn)|地名的方足布幣范[13]81—85,圖5—圖9。況且洛陽(yáng)、新鄭還同時(shí)出土各國(guó)鑄幣的錢(qián)范,進(jìn)一步證明這些外國(guó)移民已長(zhǎng)期定居此兩地,在新居地鑄造本族群的錢(qián)幣以通行。
如果是集體移民,而且到了新的移居點(diǎn)仍然不易俗,連墓葬風(fēng)格及隨葬品都保持不變的話,就只能說(shuō)明這些為避難而遷居的魏人到新居地仍聚居一處,而且生活方式保持高度獨(dú)立性,連陶器等生活用品都只在族群內(nèi)部交易,那錢(qián)幣就更不可能在異族之間交易匯兌了。這就是說(shuō),客居的移民雖與土著居民同處一城,但卻各自保持自身傳統(tǒng)習(xí)俗,至少不會(huì)很快交融到一起的。那么同理,北京市區(qū)同時(shí)出土燕刀幣和三晉方足布幣,只能證明三晉之民曾大批移居燕都。史書(shū)中雖無(wú)直接證據(jù),但結(jié)合歷史史實(shí)便可大致推測(cè):秦國(guó)發(fā)動(dòng)的滅六國(guó)之戰(zhàn),三晉首當(dāng)其沖。尤其是秦滅趙戰(zhàn)爭(zhēng),秦國(guó)打得趙國(guó)喪失了太行山以西的所有土地。趙民必然與其他東方國(guó)家一樣,不愿歸秦,很可能逃難到燕國(guó)。趙民在燕都建立獨(dú)立的社區(qū)里坊,他們?cè)趩为?dú)一個(gè)時(shí)間進(jìn)入集市中使用趙幣交易趙族群內(nèi)部間生產(chǎn)的商品是很自然的事。這種小范圍內(nèi)的商業(yè)貿(mào)易應(yīng)是先秦乃至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的主要貿(mào)易形式和特征。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富商大賈跨國(guó)遠(yuǎn)程貿(mào)易固然有,但他們絕不會(huì)使用錢(qián)幣作為交易媒介。《管子·山至數(shù)》云:“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幣、萬(wàn)物輕重皆在賈人……人君操谷、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刀”應(yīng)指齊國(guó)錢(qián)幣刀幣,“布”即實(shí)物貨幣麻、葛布,而“幣”也指絲綢布帛,“谷”是同樣可作為實(shí)物貨幣的糧食,而“金”即指貴金屬。后面“谷、幣、金”三者并稱,證明“幣”只能指布帛而不是金屬刀幣。國(guó)家控制的府庫(kù)壟斷了大部分布帛和所有錢(qián)幣的供應(yīng),而商賈手里掌握的是私人制作的布帛及各類(lèi)商品,他們并不能操控錢(qián)幣。
(二)燕國(guó)新辟土地上方足布的擴(kuò)張
三晉方足布除了在華北地區(qū)有大面積分布外,在遼寧一帶也都有發(fā)現(xiàn)。其中,“平陰”方足布曾在遼寧鐵嶺出土[14],從其名稱和形制上看,顯系三晉風(fēng)格。然而遼河流域?qū)傺啵谘嗾淹踅y(tǒng)治時(shí)期,“燕將秦開(kāi),為質(zhì)于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余里,燕筑長(zhǎng)城,自造陽(yáng)至襄平,置上谷、漁陽(yáng)、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史記·匈奴列傳》),這才占據(jù)了遼東。另?yè)?jù)遼寧朝陽(yáng)袁臺(tái)子墓地的第二期戰(zhàn)國(guó)墓葬的形制、遺物的特征與河北邯鄲百家村戰(zhàn)國(guó)墓極為相似[15]231,而百家村墓地的族屬顯系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趙人。所以從這個(gè)角度也可判定,在燕國(guó)設(shè)置遼東郡之后,曾有趙人遠(yuǎn)徙于此。
結(jié)合史實(shí)推測(cè),既然方足布大量出現(xiàn)在燕都薊城,那么出土于遼寧鐵嶺的方足布就有可能是由燕都的方足布使用者攜帶過(guò)去的。之所以從燕都移居到偏僻的遼東,其最大的可能就是避戰(zhàn)亂。《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喜)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很顯然,薊城被秦軍攻破后,薊城居民只能與燕王一道逃往遼東。而鐵嶺位于遼寧省東北部,境內(nèi)的后山屯就曾發(fā)現(xiàn)有戰(zhàn)國(guó)燕長(zhǎng)城遺跡。此外,在鐵嶺新臺(tái)子遺址等地也發(fā)現(xiàn)有戰(zhàn)國(guó)至秦漢長(zhǎng)城的蹤跡。在燕國(guó)東北邊境長(zhǎng)城沿線出土方足布,說(shuō)明三晉之民徙居燕國(guó)后,有不少加入燕軍或服徭役,為燕國(guó)戍守邊疆。為避戰(zhàn)爭(zhēng)之難而遷徙的三晉移民,在不斷的戰(zhàn)爭(zhēng)中,將本族群使用的錢(qián)幣播撒到蠻荒之地,從而為錢(qián)幣的擴(kuò)張與普及做出了貢獻(xiàn)。
四、方足布所昭示的三晉人口遷徙歷程
三晉方足布的分布面積甚廣,北至遼寧、內(nèi)蒙古中部,南達(dá)流經(jīng)河南到山東西南部的黃河兩岸。欲求這個(gè)現(xiàn)象的解釋,我們可先以“皮氏”方足布為主,其他方足布為輔,來(lái)探究方足布的流通狀況,進(jìn)而描述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三晉人口的遷徙歷程。“皮氏”布在山西陽(yáng)高、靈石、河南洛陽(yáng)及北京市等地出土,而皮氏之地則在今山西河津,位于汾河與黃河的交匯處,戰(zhàn)國(guó)時(shí)屬魏國(guó)之河?xùn)|(今山西侯馬以南至黃河一帶)。《史記》多處記載秦、魏兩國(guó)爭(zhēng)奪皮氏。皮氏屬秦后,這里成為秦國(guó)進(jìn)入魏國(guó)河?xùn)|地區(qū)的一個(gè)跳板。由此向南可直逼魏都安邑,向東、向北則可進(jìn)入汾河谷地,插入三晉腹地,可見(jiàn)其戰(zhàn)略位置的重要。山西河津東辛封村曾發(fā)現(xiàn)窖藏秦半兩13公斤,總數(shù)約至少2000余枚。[16]按前文所證,邊關(guān)錢(qián)幣窖藏中的錢(qián)幣數(shù)量應(yīng)為營(yíng)壘駐軍人數(shù),秦軍在這處營(yíng)壘駐屯2000多人是完全有可能的。1963年山西陽(yáng)高天橋村出土平首布幣13000枚,其中僅方足布的面文種類(lèi)就有36種之多[17],這里面就有“皮氏”方足布。陽(yáng)高縣在山西省北部,境內(nèi)有戰(zhàn)國(guó)長(zhǎng)城遺址,應(yīng)是趙國(guó)北長(zhǎng)城的一處重要關(guān)塞。在趙國(guó)的北疆居然出土了帶有魏國(guó)河?xùn)|地區(qū)地名的方足布,這不得不讓我們回到歷史中,去找尋魏國(guó)河?xùn)|與趙國(guó)北疆之間可能存在的淵源。
趙國(guó)在北長(zhǎng)城沿線抵御匈奴的趙軍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一支勁旅,“于是乃具選車(chē)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wàn)三千匹,白金之士五萬(wàn)人,彀者十萬(wàn)人,悉勒習(xí)戰(zhàn)……大破殺匈奴十余萬(wàn)騎。滅檐襤,破東胡,單于奔走。其后十余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史記·趙奢李牧列傳》)可見(jiàn)趙長(zhǎng)城邊防部隊(duì)人數(shù)之眾,軍力之強(qiáng)。陽(yáng)高縣出土的13000枚布幣表明,趙國(guó)在其北長(zhǎng)城關(guān)塞一處營(yíng)地駐扎13000人的部隊(duì),也是可以想見(jiàn)的。在陽(yáng)高縣出土的36種方足布面文內(nèi)容均為地名,如“平陶”“彘”“土勻”“襄垣”等皆為趙國(guó)地名,而另有“皮氏”“奇(猗)氏”等位于魏國(guó)的河?xùn)|地區(qū);“馬雍”“長(zhǎng)子”則皆位于山西省南部,戰(zhàn)國(guó)時(shí)屬韓國(guó)的上黨郡。[18]108,140,215,225,230,232這或許說(shuō)明,在這個(gè)長(zhǎng)城關(guān)塞戍守的趙國(guó)部隊(duì)中,有來(lái)自趙國(guó)內(nèi)地、魏國(guó)河?xùn)|以及韓國(guó)上黨郡的人。而今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地區(qū)亦為趙國(guó)邊塞,該縣土城子遺址出土戰(zhàn)國(guó)墓葬的人骨經(jīng)過(guò)體質(zhì)人類(lèi)學(xué)研究,為“古中原類(lèi)型”。他們很可能是趙國(guó)移民,在趙武靈王時(shí)移民戍邊,他們是長(zhǎng)期屯駐邊塞的軍事移民。通過(guò)葬俗,我們又可斷定,這些戍卒的來(lái)源地可能是趙國(guó)都城邯鄲及邯鄲以南的趙國(guó)屬地。[19]101,109這說(shuō)明,趙邊塞軍事移民都來(lái)自趙國(guó)內(nèi)地。趙邊塞出土帶有三晉地名的方足布,證明逃難來(lái)的韓、魏移民移居趙都及附近地區(qū),后又與本土趙人共同加入戍邊隊(duì)伍,并來(lái)到趙北疆戍邊。由于強(qiáng)秦的威逼,魏國(guó)割讓了河?xùn)|四百里,河?xùn)|之民很可能大量逃往其他國(guó)家和地區(qū)。河?xùn)|之地南接黃河,可聯(lián)通魏國(guó)的河內(nèi)地區(qū)和韓國(guó)都城所在的河南地區(qū);北接汾河谷地,可直接進(jìn)入趙國(guó)的太原之地。故帶有河?xùn)|諸地名的方足布可能是逃難于趙國(guó)的魏人為標(biāo)明祖籍地而鑄。公元前262年,秦軍攻占了韓國(guó)的野王,從沁河下游切斷了韓國(guó)南北水路交通,使韓國(guó)北方領(lǐng)土上黨郡孤懸于本土之外。上黨郡守馮亭不愿歸順秦國(guó),便將上黨郡委命于趙。所以韓國(guó)上黨郡諸屬縣之民遂投靠趙國(guó),鑄有韓國(guó)上黨郡諸縣地名的方足布即是他們?cè)诩尤脍w國(guó)軍隊(duì)后出現(xiàn)的。
前文已經(jīng)根據(jù)東周墓葬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河?xùn)|地區(qū)與河南洛陽(yáng)、鄭州一帶的部分平民墓存在淵源關(guān)系,證明了包括皮氏在內(nèi)的河?xùn)|之民曾遷徙到中原地區(qū)。而我們另從時(shí)間與歷史背景來(lái)看,魏獻(xiàn)河?xùn)|四百里后的河?xùn)|之民大遷徙也是十分合理的。《商君書(shū)·徠民》是一篇由三個(gè)不同時(shí)期上奏給秦王的奏章所組成的策論,文中記述秦國(guó)四代君主連續(xù)對(duì)三晉用兵,都取得完勝。然而由于秦法嚴(yán)苛,三晉之民便大量逃亡,使得秦國(guó)占領(lǐng)下的大片三晉故地地廣人稀,無(wú)人耕種。作者建議秦王通過(guò)獎(jiǎng)勵(lì)措施,吸引三晉之民回歸故土務(wù)農(nóng),為秦國(guó)增加糧食生產(chǎn)。文中提到秦對(duì)三晉的“華軍之勝”、“周軍之勝”和“長(zhǎng)平之勝”三大軍事勝利,它們分別指華陽(yáng)之戰(zhàn)、伊闕之戰(zhàn)、長(zhǎng)平之戰(zhàn)。其中長(zhǎng)平之戰(zhàn)發(fā)生最晚,結(jié)束于公元前260年,說(shuō)明《徠民》完成于公元前260年之后。而此前秦國(guó)占領(lǐng)三晉故地的狀況誠(chéng)如《徠民》所言,“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那么“魏獻(xiàn)河?xùn)|四百里予秦”發(fā)生在公元前290年,早于長(zhǎng)平之戰(zhàn)30年,顯然河?xùn)|之民的狀況也只能如《徠民》所述,逃亡他地。
根據(jù)“皮氏”布的出土分布分析,秦國(guó)占領(lǐng)皮氏城后,皮氏族群之一部沿著黃河向南遷往洛陽(yáng)周王城,另一部則沿汾河谷地向北遷往趙國(guó),靈石即位于河?xùn)|地區(qū)北部汾河沿岸的趙國(guó)境內(nèi);在趙國(guó)的皮氏人有可能被征兵派往趙國(guó)北疆戍邊,所以至今尚留存戰(zhàn)國(guó)長(zhǎng)城遺址的陽(yáng)高縣境內(nèi)會(huì)出土“皮氏”方足布;秦滅趙后,居住在趙國(guó)的皮氏人還可能隨眾逃往燕國(guó)都城薊,即今北京市。北京出土的“皮氏”方足布恐怕就是在那時(shí)出現(xiàn)的。
根據(jù)上文分析的結(jié)論,方足布上的地名文字很可能是遷徙族群的祖居地,他們移民到新的土地上,勿忘先祖,在錢(qián)幣上鑄祖居地名以紀(jì)念,為本族群(河?xùn)|之民)內(nèi)部流通。除“皮氏”方足布外,魏國(guó)的“北屈”“莆子”“奇氏”方足布上的這些地名也都處在魏國(guó)河?xùn)|地區(qū)*“北屈”在今山西吉縣東北;“莆子”在今山西隰縣或蒲縣;“奇氏”即“猗氏”,在今山西臨猗縣南。這些地方都位于山西西南部,即古代的河?xùn)|地區(qū),戰(zhàn)國(guó)時(shí)屬魏國(guó)。,而這些方足布的出土地也不在其面文所指地,而是分布于中原和北方地區(qū)。如“北屈”“莆子”方足布發(fā)現(xiàn)于河南新鄭鄭韓故城;“奇氏”方足布在山西靈石、祁縣、陽(yáng)高,河北靈壽及北京市都曾出土過(guò)。[18]176—177,256,232在河北靈壽出土的“奇氏”布,也能證明魏國(guó)一部分猗氏人早先曾移居趙國(guó)。靈壽縣在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屬趙國(guó)的番吾,《史記·趙世家》記載:“番吾君自代來(lái)。”裴骃《集解》引徐廣曰:“常山有番吾縣。”張守節(jié)《正義》引《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20]1797—1798隋始置房山縣,即今河北平山縣,其東北部毗鄰靈壽縣,與《括地志》所云在“房山縣東二十里”完全吻合。《趙世家》又云,“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說(shuō)明番吾是趙國(guó)的軍事重鎮(zhèn)。今河北靈壽故城村戰(zhàn)國(guó)古城遺址當(dāng)即趙國(guó)的番吾城。靈壽西鄰井陘關(guān),是阻遏太行山以西的秦軍進(jìn)入冀中平原,進(jìn)而從北面威脅趙都邯鄲的重要防線。趙國(guó)在番吾部署的大量軍隊(duì),很可能也吸納了原先移居趙地的魏國(guó)河?xùn)|之民。另外,靈壽故城村古城遺址只在西面有烽燧遺跡,也說(shuō)明這座具有軍事意義的城市是專門(mén)防御來(lái)自西面井陘關(guān)外的秦軍的。
五、方足布使用者的歸屬
三晉方足布因面文分別有韓、趙、魏、東周四國(guó)地名,所以其使用者即三晉、兩周之民無(wú)疑。但前已論述,鑄銘地名的方足布,皆為該地三晉移民遷徙到新址后所鑄,那么可以推知,他們?cè)谶w徙之前可能并不使用青銅錢(qián)幣。以魏國(guó)的河?xùn)|地區(qū)為例,帶有河?xùn)|地區(qū)地名的方足布甚多,但這個(gè)地區(qū)卻幾乎無(wú)方足布出土。如山西夏縣處古代河?xùn)|地區(qū),戰(zhàn)國(guó)中期以前是魏都安邑的所在地,這里恰恰被“安邑一釿”“安邑二釿”“安邑半釿”等魏國(guó)大型釿布所覆蓋。“安邑”釿布的出土地不但分布于河?xùn)|,還在河南洛陽(yáng)、新鄭有出土[18]236—237;“陰晉半釿”“虞一釿”(或謂“陜一釿”)布幣上的地名“陰晉”“虞”“陜”皆屬魏地,這幾類(lèi)錢(qián)幣也曾在洛陽(yáng)、新鄭出土。[18]198—199“陰晉”位于今陜西華陰,而“陜”位于今河南三門(mén)峽一帶,雖皆不屬河?xùn)|,但也先后被秦軍攻取,如“秦侵陰晉”[20]713、“相張儀將兵取陜”[20]730,說(shuō)明釿布才是河?xùn)|地區(qū)原本通行的錢(qián)幣,而且主要流通于都城安邑及附近地區(qū),邊緣地帶可能仍只使用布帛作為貨幣。應(yīng)該說(shuō),方足布的通行僅在原本不使用錢(qián)幣的三晉遷徙族群中。
綜上所述,三晉方足布與其他類(lèi)型錢(qián)幣共出的窖藏,不能解釋為不同貨幣之間可以匯兌,而是每種錢(qián)幣在各自族群內(nèi)部流通。方足布上多鑄有地名,應(yīng)是原居該地的戰(zhàn)爭(zhēng)移民在新居地上使用新款錢(qián)幣時(shí)加鑄的故鄉(xiāng)名,并非該地通行的錢(qián)幣。此外,結(jié)合歷史文獻(xiàn)研究以及方足布的廣泛分布可證,戰(zhàn)國(guó)錢(qián)幣的流通過(guò)程實(shí)際上是由普遍使用實(shí)物轉(zhuǎn)變到大規(guī)模使用金屬錢(qián)幣,由都邑平民享用到影響鄉(xiāng)鄙、邊塞軍民的錢(qián)幣普及化的歷程。同時(shí),戰(zhàn)國(guó)錢(qián)幣的普及化也為秦漢統(tǒng)一形制的錢(qián)幣在全國(guó)的推廣和流通奠定了普遍而深厚的心理基礎(chǔ)。
[1] 吳良寶.中國(guó)東周時(shí)期金屬貨幣研究[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5.
[2] 朱活.古錢(qián)新典(上冊(c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3] 段穎龍.東周錢(qián)幣起源“契券”考[J].中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研究,2015,(1).
[4]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jiàn)簡(jiǎn)牘合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 石永士,王素芳.試論“ ”字刀化的幾個(gè)問(wèn)題[J].考古與文物,1983,(6).
[6] 高婉瑜.布幣流通的歷史解釋[J].中國(guó)錢(qián)幣,2003,(2).
[7] 吳宗信.三道營(yíng)子窖藏古錢(qián)清理簡(jiǎn)報(bào)[J].中國(guó)錢(qián)幣,1986,(2).
[8] 王彩梅.燕國(guó)簡(jiǎn)史[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9]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duì).朝陽(yáng)門(mén)外出土的戰(zhàn)國(guó)貨幣[J].考古,1962,(5).
[10] 程紀(jì)中,梁學(xué)義.北京廣安門(mén)內(nèi)燕薊古城遺址出土數(shù)萬(wàn)枚戰(zhàn)國(guó)刀幣布幣[J].中國(guó)錢(qián)幣,2009,(2).
[11] 張辛.中原地區(qū)東周陶器墓葬研究[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2.
[12] 中國(guó)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fā)掘報(bào)告[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56.
[13] 馬俊才.新鄭“鄭韓故城”新出土東周錢(qián)范[A].中國(guó)錢(qián)幣論文集(第四輯)[C].北京:中國(guó)金融出版社,2002.
[14] 吳良寶.三晉方足小布的種類(lèi)統(tǒng)計(jì)與國(guó)別考辨[J].文物世界,2002,(1).
[15]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yáng)市博物館.朝陽(yáng)袁臺(tái)子.戰(zhàn)國(guó)西漢遺址和西周至十六國(guó)時(shí)期墓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6] 胡振祺.山西河津縣發(fā)現(xiàn)秦半兩錢(qián)[J].中國(guó)錢(qián)幣,1986,(1).
[17]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huì).山西陽(yáng)高天橋出土的戰(zhàn)國(guó)貨幣[J].考古,1965,(4).
[18] 馬保春.晉國(guó)地名考[M].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2010.
[19] 顧玉才.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遺址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人骨研究[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0.
[20] (漢)司馬遷.史記(全十冊(cè))[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