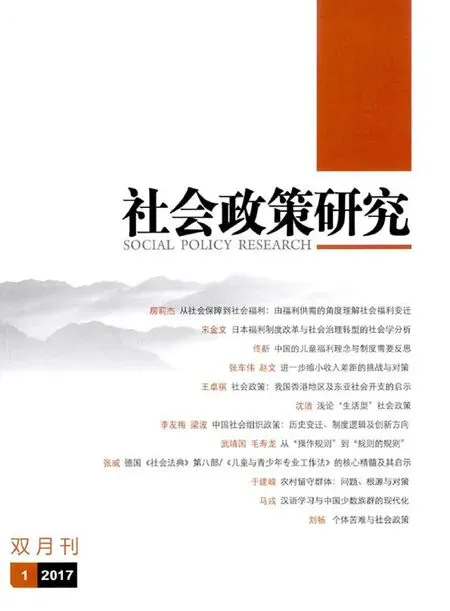個(gè)體苦難與社會政策
——基于對“打工文學(xué)”的考察
劉 暢
★劉暢:武漢大學(xué)社會學(xué)系副教授
“打工文學(xué)”①圍繞“打工文學(xué)”、“打工詩歌”、“打工作家”、“打工詩人”以及“農(nóng)民工”等稱呼方式有諸多爭議,本文為行文上的方便易懂起見,仍舊沿用這些一般稱謂,但對其中可能產(chǎn)生的歧視性含義抱有充分的認(rèn)識和批判。自20世紀(jì)90年代開始在農(nóng)民工大規(guī)模涌入的珠三角地區(qū)興起,一般意義上指外出農(nóng)民工自身進(jìn)行的文學(xué)寫作,被視為底層打工者自身的一種話語表達(dá)。沉默的大多數(shù)缺乏自我表述的能力(馬克思,2001;斯皮瓦克,2007),打工文學(xué)因而在農(nóng)民工群體話語權(quán)的提高和群體生活的呈現(xiàn)方面受到關(guān)注。打工文學(xué)很多作品中呈現(xiàn)了打工者生活中的種種苦難,本文探討這一苦難敘事的社會政策意義。著重分析以下問題:底層的“訴苦”如何成立、如何被傾聽?在這兩個(gè)過程中政府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打工文學(xué)中的苦難敘事是否實(shí)現(xiàn)以及如何能夠?qū)崿F(xiàn)其社會政策方面的可能價(jià)值?
一、個(gè)體苦難的政策意義
“苦難是經(jīng)驗(yàn)匯總發(fā)生的殞亡喪失、孤獨(dú)無助,以及個(gè)體性異化……由沮喪、焦慮、內(nèi)疚、恥辱、厭倦以及悲痛等情感組成”(Wilkinson,2005:16-17;孫飛宇,2007)。社會學(xué)視角將個(gè)體苦難視為社會問題的表征。米爾斯(2001:1-24)指出了個(gè)體苦難的社會性,認(rèn)為個(gè)人生活世界中無法解決的苦惱,是由他們無法控制的社會結(jié)構(gòu)變遷所造成的。布迪厄(Bourdieu,1999)進(jìn)一步探討了個(gè)人苦難的原因,將其分為社會不平等結(jié)構(gòu)帶來的位置性痛苦和社會關(guān)系紐帶弱化導(dǎo)致的解體性痛苦,并指出苦難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背景下國家的運(yùn)作方式。凱博文(2008:168-171)揭示了社會結(jié)構(gòu)變遷影響個(gè)體生活的方式,是以地方性場景中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變化為中介,帶來個(gè)體在其中結(jié)構(gòu)位置和生活機(jī)遇的變化,其風(fēng)險(xiǎn)和壓力造成了個(gè)體痛苦。這些研究指出個(gè)體苦難的社會根源,提示我們認(rèn)識、理解以及消除個(gè)體苦難具有公共意義和政策意義。
在中國的社會學(xué)研究中,表述苦難的目的和作用更受到關(guān)注。“訴苦”曾是中國革命中重塑普通民眾國家觀念的一種重要機(jī)制(郭于華,2008a),也是實(shí)現(xiàn)國家建設(shè)和鄉(xiāng)村治理目標(biāo)的一種群眾動員技術(shù)(李里峰,2007)。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訴苦是其生存遭遇某種苦難或陷入某種困境時(shí)進(jìn)行利益表達(dá)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抗?fàn)幖夹g(shù)(劉氚、何紹輝,2014)。底層苦難的表述與記錄本身也在口述史等研究領(lǐng)域被賦予了政治意義與倫理意義,成為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構(gòu)建歷史的重要方式(郭于華,2008b)。由此來看,苦難的表述具有豐富的政治涵義和社會意義,在向市場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以后,苦難的表述意味著弱勢群體主體性的形成。
苦難研究也是農(nóng)民工群體研究的主旋律,講述他們的苦難被視為社會學(xué)學(xué)者的倫理關(guān)懷與學(xué)科使命(江立華、谷玉良,2016)。研究者對進(jìn)城務(wù)工群體進(jìn)行田野調(diào)查時(shí)經(jīng)常遭遇打工者對“苦”的訴說,許多打工者以“能吃苦”建立積極的社會認(rèn)同,以苦的訴說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責(zé)任和自我依賴(朱敏、何瀟,2015);女性打工者的訴苦有情緒發(fā)泄功能,給予訴說者賦權(quán)意識,但也表達(dá)出她們對于改善自己處境的無能為力(杰華,2006);女性打工者還通過訴苦試圖將她們破碎的經(jīng)驗(yàn)縫合成一個(gè)關(guān)于自我發(fā)展的連貫話語,苦難經(jīng)歷被認(rèn)為是個(gè)體自我轉(zhuǎn)化的基礎(chǔ)和條件(Yan Hairong,2008)。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與農(nóng)民工接觸過程中獲得的來自底層自身的口頭苦難表述,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群體訴苦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對于打工者個(gè)體的作用和意義,對它們的公共價(jià)值和社會意義挖掘較少。
本文認(rèn)為,在農(nóng)民工缺少參與公共生活的制度化途徑,也缺少話語權(quán)的現(xiàn)狀之下,打工者“訴苦”的意義不應(yīng)僅僅局限于個(gè)人的心理釋放和自我建構(gòu),其對于社會政策的意義潛能應(yīng)受到更多關(guān)注。為此,在重視個(gè)人苦難的社會根源的前提之上,除了“何以講述苦難”之外,還需要考察和探討“誰來傾聽以及如何傾聽苦難?”很多學(xué)者提出重視傾聽,但多集中于知識分子對底層的理解與把握,如探討或倡導(dǎo)社會學(xué)、口述史在田野調(diào)查、訪談?wù){(diào)查中對苦難講述的捕捉方法(郭于華,2008b;江立華、谷玉良,2016)。作為造成個(gè)體苦難的重要根源以及能夠?qū)鉀Q苦難提出重要政策方案的主體,國家與政府作為傾聽者的角色沒有被充分重視。對于社會政策來說,政府是否傾聽以及如何傾聽底層的聲音是實(shí)現(xiàn)具有前瞻性、“托底性”社會政策的重要方面。
“訴苦”也被認(rèn)為是打工文學(xué)的主要特點(diǎn),本文以打工文學(xué)尤其是打工詩歌中的苦難講述為主要考察對象①本文的考察基于2014年至今對珠三角地區(qū)打工文學(xué)的資料收集、訪談?wù){(diào)查以及作品內(nèi)容分析。。農(nóng)民工的日常社會交往多具有封閉性,主要集中于血緣和地緣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之中,因此研究者們收集到的口頭訴苦難以為更廣泛的群體接觸到。而作為相對固定的文字文本,打工文學(xué)具有將打工者的苦難表述進(jìn)行廣泛傳播的可能性。此外,近年來有關(guān)進(jìn)城打工者的社會政策主要致力于農(nóng)民工物質(zhì)生活的改善與保障,對此一些研究指出應(yīng)該更加重視農(nóng)民工的精神健康(王思斌,2003;何雪松等,2010;張宏如等,2015)。文學(xué)話語擅長表達(dá)個(gè)體內(nèi)心情感與體驗(yàn),其中往往有田野調(diào)查、訪談?wù){(diào)查的口述資料中難以捕捉到的內(nèi)容。因此打工文學(xué)中的“文字訴苦”可以與口頭訴苦的研究形成補(bǔ)充和對照,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農(nóng)民工群體的內(nèi)心世界,進(jìn)而推動社會政策的發(fā)展。
二、底層何以能夠講述自己?——打工文學(xué)的發(fā)展與政府的作用
在一般意義上,打工文學(xué)主要指由下層打工者自己創(chuàng)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文學(xué)作品。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以珠三角為代表的東南沿海地區(qū)出現(xiàn)了眾多以底層打工者為主要對象的文藝刊物,主要發(fā)表打工者自身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作品。在網(wǎng)絡(luò)興起以前這些刊物一度以極高的發(fā)行量盛況空前,擁有數(shù)量龐大的作者群與讀者群,促成了“打工文學(xué)”作為文化現(xiàn)象的興起。
打工文學(xué)自90年代初進(jìn)入繁榮發(fā)展的時(shí)期,產(chǎn)生了第一代打工作家和一批引起強(qiáng)烈反響的代表性作品,某些打工文學(xué)刊物在1995年發(fā)行量達(dá)到每期50萬份。90年代中后期,打工詩歌成為打工文學(xué)中的亮點(diǎn),一批“打工詩人”在廣東省形成了“活躍崛起的打工詩群”。其詩歌以描寫打工現(xiàn)場、鮮活、感情真摯為特點(diǎn),表現(xiàn)農(nóng)民工艱辛的生存狀態(tài)。21世紀(jì)以來,2005年國家設(shè)立了面向打工群體文學(xué)愛好者的“鯤鵬文學(xué)獎”,以其獲獎?wù)邽榇淼牡诙蚬ぷ骷壹捌渥髌分忍嵘渲袛?shù)人獲得主流文學(xué)界的權(quán)威獎項(xiàng)。此外,2008年“打工文學(xué)論壇”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舉行,這些被視作打工文學(xué)走向全國、獲得主流文壇認(rèn)可的標(biāo)志性事件。目前,受到網(wǎng)絡(luò)的沖擊,很多打工文學(xué)刊物已經(jīng)停刊,但打工詩歌在各類文學(xué)期刊都有發(fā)表機(jī)會,與打工文學(xué)相關(guān)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論壇、文學(xué)活動、評獎活動十分活躍,并持續(xù)受到媒體的報(bào)道,打工文學(xué)群體的創(chuàng)作活動在繼續(xù)發(fā)展。2015年,紀(jì)錄片《我的詩篇》介紹了包括底層打工者詩歌創(chuàng)作在內(nèi)的“新工人詩歌現(xiàn)象”,該片以獨(dú)特的制作方式、具有沖擊力的內(nèi)容、廣泛的網(wǎng)絡(luò)宣傳以及電影節(jié)獲獎記錄,再次引起社會對打工詩歌的關(guān)注。
福柯認(rèn)為,無名者的面目得以呈現(xiàn)只有在被權(quán)力之光照亮的時(shí)刻(福柯,2001)。這個(gè)觀點(diǎn)未必準(zhǔn)確,但他與其他學(xué)者都指出了底層在公共領(lǐng)域發(fā)出聲音、表達(dá)自身的困難。改革開放以后的社會變遷中,農(nóng)民和農(nóng)民工在政治生活、經(jīng)濟(jì)生活中被迅速邊緣化并缺少話語權(quán)。那么打工文學(xué)這一底層話語是如何得以呈現(xiàn)的?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看,其中政府發(fā)揮了什么樣的作用?打工文學(xué)的興起與發(fā)展過程顯示,除打工者群體自身的創(chuàng)作與閱讀之外,政府部門的扶持、市場的文化生產(chǎn)機(jī)制、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專家學(xué)者、媒體報(bào)道以及民間社會組織的資助是推動與建構(gòu)這一文化現(xiàn)象的重要力量。以下在概述市場、學(xué)術(shù)等因素的基礎(chǔ)上,著重考察政府的作用。
(一)市場、文學(xué)權(quán)威與打工文學(xué)
市場是打工文學(xué)的培育者、推動者,為底層話語的表達(dá)提供了重要的平臺。打工文學(xué)的繁榮是在市場化的文化生產(chǎn)機(jī)制之下產(chǎn)生的。《佛山文藝》、《江門文藝》等打工文學(xué)刊物大部分以市場化運(yùn)作為主,把讀者定位于中下層打工者。它們在市場空間萎縮以前,均采用“自下而上”的平民立場和生產(chǎn)方式,努力把握打工群體的閱讀需求,欄目風(fēng)格與作品內(nèi)容緊貼打工生活的現(xiàn)實(shí);培養(yǎng)打工群體中的創(chuàng)作者以及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注重獲得打工群體的信賴和認(rèn)同,不斷吸引和擴(kuò)大讀者群(賀芒,2009;郁勤,2015)。也由于這樣的市場意識和生產(chǎn)機(jī)制,打工文學(xué)刊物內(nèi)容品味和審美層次多元駁雜,既包括民間性、娛樂性較強(qiáng)的通俗文學(xué)作品,也刊登具有現(xiàn)實(shí)性、審美性、技巧性的純文學(xué)作品。這些市場化運(yùn)作的文學(xué)刊物雖然此后相繼停刊,但它們?yōu)榈讓哟蚬ふ邉?chuàng)造了一定的話語權(quán)和公共空間,提供了經(jīng)濟(jì)支持以及相互聯(lián)系的渠道,推動打工群體形成歸屬感與文化認(rèn)同。
打工文學(xué)發(fā)展的另一個(gè)重要的支持者是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專家學(xué)者。在由政府文化部門以及打工文學(xué)刊物主辦的與打工文學(xué)相關(guān)的研討會和文學(xué)獎項(xiàng)評選活動中,在不斷增加的關(guān)于打工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中,在各種媒體對打工文學(xué)的報(bào)道和討論中,知識分子作為評判者、闡釋者和引導(dǎo)者參與了打工文學(xué)文化現(xiàn)象的建構(gòu)。作為文化生產(chǎn)過程中的守門人,專家、學(xué)者、評論家是打工文學(xué)獲得主流社會認(rèn)可進(jìn)而獲得關(guān)注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他們的參與主要出于倫理關(guān)懷與文學(xué)理念。
此外,民間組織也給予打工文學(xué)不同程度的支持。如一些優(yōu)秀打工詩人的評選活動來自于民間資金的資助,年度優(yōu)秀打工詩歌精選的選編與出版也是在公益組織的資金支持下得以進(jìn)行。這些組織對打工文學(xué)的資助有的偏重社會關(guān)懷,有的偏重推動文學(xué),但通常兩種宗旨同時(shí)存在。
(二)政府與打工文學(xué)
政府是打工文學(xué)的扶持者、組織者、宣傳者。研究界一般認(rèn)為在20世紀(jì)80年代最初對打工文學(xué)進(jìn)行發(fā)現(xiàn)與命名的是楊宏海,他當(dāng)時(shí)是深圳市文化局的一名干部兼文化研究者,試圖為被稱為“文化沙漠”的深圳找到自己的文化品牌,并在深圳大量打工者中發(fā)現(xiàn)了打工文學(xué)的發(fā)展?jié)摿ΑK趫?bào)紙上提出了“打工文學(xué)”這個(gè)詞語,陸續(xù)發(fā)表和主編了一系列關(guān)于打工文學(xué)發(fā)展的文章、著作,召集文學(xué)界的專家、學(xué)者組織打工文學(xué)論壇、研討會、座談會。以楊宏海為代表的地方政府文化部門對打工文學(xué)進(jìn)行的這些定義、闡釋、宣傳工作,將打工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組織在一起,并擴(kuò)大了其作品的社會影響力,是建構(gòu)“打工文學(xué)”這一話語范疇的重要力量。他們的支持和組織主要出于建設(shè)文化政績的需要,但也包含著對打工群體的倫理關(guān)懷。打工文學(xué)的成立與發(fā)展得益于政府的扶持,但這一幫助并非單向的,它們成為深圳市的文化亮點(diǎn),以及廣東省作為打工大省的文化特色,對打工文學(xué)的宣傳同時(shí)成為珠三角地區(qū)在全國范圍內(nèi)擴(kuò)大文化影響力的一種形式(吳繼磊等,2013)。
廣東省許多地方都實(shí)行了打工文學(xué)的扶持政策。如被視為打工文學(xué)的搖籃與重鎮(zhèn)的東莞、佛山及深圳市寶安區(qū)等地,政府每年提供資金資助打工文學(xué)作品的出版,舉辦各種類型的打工文學(xué)大獎賽,對于成果優(yōu)秀的打工作家給予城市落戶等優(yōu)惠政策。廣東省成立了青年產(chǎn)業(yè)工人作家協(xié)會吸收與組織打工作家,設(shè)立了面向打工文學(xué)的“全國青年產(chǎn)業(yè)工人文學(xué)獎”。共青團(tuán)廣東省委主辦的《黃金時(shí)代》雜志也曾大量刊發(fā)打工文學(xué)作品。在訪談?wù){(diào)查中,很多打工作家都提及并肯定這一官方雜志對打工文學(xué)發(fā)揮了重要的支持和宣傳作用。在近年來打工者群體性事件增加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這些扶持政策主要是出于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的目的。打工作者是進(jìn)城務(wù)工者中教育程度相對較高、思想活躍、有能力進(jìn)行公共表達(dá)的群體,政府部門認(rèn)為有必要對他們進(jìn)行了解和組織;政府也希望打工文學(xué)對農(nóng)民工群體以及社會讀者的影響是積極、正面的,力圖通過各類組織活動對打工文學(xué)的表達(dá)內(nèi)容起到引導(dǎo)的作用。在客觀效果上,各種創(chuàng)作與出版資助、作家身份和城市戶口的給予、作品發(fā)表與獲獎為打工作家提供了“靠文學(xué)改變命運(yùn)”的機(jī)會,但只要打工群體普遍的社會處境和生活狀態(tài)沒有改變,這些政策對打工文學(xué)內(nèi)容與風(fēng)格的影響就是有限的。
此外,在打工文學(xué)發(fā)展早期,有代表性的打工文學(xué)刊物原本多由政府文化部門設(shè)立。如被譽(yù)為中國第一打工文學(xué)大刊的《佛山文藝》是由佛山市委宣傳部主辦的文學(xué)期刊,同樣著名的打工文學(xué)暢銷刊物《江門文藝》由廣東省江門市文聯(lián)主辦,“很多打工者枕頭邊、身邊放的”《大鵬灣》雜志(施澤會,2016)是由深圳市寶安區(qū)文化藝術(shù)館主辦的。在改革開放以后不久形成的官方主導(dǎo)的文學(xué)體制對于打工文學(xué)市場的形成和繁榮是極其重要的基礎(chǔ)。
由上述內(nèi)容來看,打工文學(xué)這一底層聲音的公共表達(dá)得以實(shí)現(xiàn),在于市場機(jī)制、政府運(yùn)作、文學(xué)理念、社會倫理共同支撐而形成了一定的話語空間。政府機(jī)構(gòu)對打工文學(xué)的推動政策主要出于文化政績、社會穩(wěn)定及一定的市場營利的需要,前兩者是主導(dǎo)性、持續(xù)性的出發(fā)點(diǎn)。
三、底層話語被如何傾聽?——打工文學(xué)的社會反響與政府作用
打工文學(xué)這一在政治需要、市場機(jī)制、社會倫理與文學(xué)審美支持下形成的話語傳播,是否使其中的苦難敘事得到充分的傾聽?從底層話語的公共價(jià)值與政策意義來看,其社會反響有何特點(diǎn)?作為政策制定主體的政府是否成為傾聽者?
(一)打工群體的“社會支持式傾聽”
打工文學(xué)話語的主要傾聽者是打工群體自身,其受眾主要是在珠三角工業(yè)區(qū)地帶的打工群體內(nèi)部,即打工者寫、打工者讀。關(guān)于打工群體內(nèi)部讀者的數(shù)量,沒有準(zhǔn)確的統(tǒng)計(jì)數(shù)字。打工詩人群體的重要代表人物、十分了解打工文學(xué)發(fā)展情況的XQ認(rèn)為,一百個(gè)農(nóng)民工中至少有一個(gè)文學(xué)愛好者,全國近三億農(nóng)民工便會有近三百萬文學(xué)人口。著名打工詩人ZXQ,通過自己的調(diào)查認(rèn)為,雖然文學(xué)期刊式微,但通過手機(jī)、電腦在網(wǎng)上進(jìn)行文學(xué)閱讀的打工者大有人在。但也有一些研究指出,普通打工者對打工文學(xué)沒有太強(qiáng)的閱讀興趣,尤其對于純文學(xué)色彩較濃的打工詩歌知之甚少甚至抱有反感(Wanning Sun,2014:185-216)。因此,打工文學(xué)以打工群體為主要受眾,但這些讀者占整個(gè)打工群體多大比重很難進(jìn)行準(zhǔn)確的統(tǒng)計(jì)或估算,更為嚴(yán)謹(jǐn)?shù)恼f法應(yīng)該是,打工群體中的文學(xué)愛好者是打工文學(xué)話語的首要傾聽者。
打工群體內(nèi)部對打工文學(xué)是一種旨在獲得社會支持的傾聽。從閱讀感受來看,主要是引起了對共同的經(jīng)歷與感受尤其是生活苦難的共鳴,在此基礎(chǔ)上還經(jīng)常促成讀者與作者之間建立友情而形成新的社會交往。很多打工群體的讀者在看到打工詩歌后,感到自己的經(jīng)歷和體驗(yàn)?zāi)軌虮焕斫猓惺艿搅巳后w的歸屬感和文化認(rèn)同,能夠?qū)ψ约旱纳钪匦沦x予意義進(jìn)而獲得自我確認(rèn)和價(jià)值充實(shí)感。很多讀者會根據(jù)文學(xué)期刊上刊登的作者聯(lián)系方式或網(wǎng)絡(luò)上的溝通方式與作者直接見面交流,把自己的經(jīng)歷、故事甚至是情感糾葛向作者傾訴,還有一些讀者希望在介紹工作、解決勞動糾紛方面獲得幫助等。可以看出,底層之間苦難敘事的相互傾聽以及伴隨而來的互動基于對深層的精神與情感交流的渴望以及對社會資本的尋求,是一種建立以情感支持為核心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luò)的嘗試。其中體現(xiàn)了當(dāng)代中國中下層打工者在面對新的環(huán)境與新的生活問題時(shí),在傳統(tǒng)的血緣、地緣關(guān)系之外的社會交往需求。
(二)知識分子的“文學(xué)式傾聽”
打工文學(xué)第二個(gè)重要的傾聽者是主流文學(xué)界的評論者和研究者。從整體來看,對打工文學(xué)進(jìn)行細(xì)致與深入的閱讀,公開表達(dá)感受、進(jìn)行闡釋、給予評論的主要是作家、文藝評論家、文學(xué)編輯、文學(xué)研究者。他們的閱讀經(jīng)常進(jìn)而發(fā)展為推介、引薦、擴(kuò)大傳播范圍、提高知名度的過程。典型的個(gè)案如打工詩人群體的代表人物ZXQ,外出打工后同幾位著名詩人的書信往來對于其文學(xué)理念、閱讀積累、詩歌風(fēng)格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ZXQ的一些知名作品也是由于與他們進(jìn)行傾心相談而產(chǎn)生的。另一位著名打工詩人GJN在參與網(wǎng)上文學(xué)論壇時(shí),得到一位擁有國際威望的詩人YL的關(guān)注,在YL的推薦和幫助下,GJN的詩歌作品獲得重要文學(xué)獎項(xiàng),詩歌作品集得以出版,并有機(jī)會赴歐洲參加了國際性的大型詩歌活動。由此可見,在打工群體的整體發(fā)展中,文學(xué)界的專業(yè)人士的閱讀和評價(jià)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無論這些專家學(xué)者對于打工文學(xué)的立場是推崇還是批判,圍繞著打工文學(xué)的討論和爭議都擴(kuò)大了打工文學(xué)的社會知名度和讀者范圍,使其超越中下層打工者群體的內(nèi)部共鳴而引起更廣泛的關(guān)注和反響。總之,在文學(xué)領(lǐng)域已經(jīng)擁有較為成熟的理念、風(fēng)格與文學(xué)聲譽(yù),也擁有較高社會地位和社會資源的人士,成為打工詩歌的重要傾聽者,進(jìn)而作為文學(xué)先輩甚至精神導(dǎo)師給予打工詩人鼓勵(lì)、批評以及發(fā)展的指導(dǎo)和建議,幫助打工詩人擴(kuò)大了文學(xué)視野、社會資本以及生活機(jī)遇。
但是作為傾聽者,關(guān)注打工文學(xué)的文化精英集中于文學(xué)領(lǐng)域而非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因此打工文學(xué)更多是作為文學(xué)現(xiàn)象引起討論和爭議而非社會現(xiàn)象。在文學(xué)界關(guān)于底層話語的理論關(guān)懷之下,打工文學(xué)受到關(guān)注,爭論的焦點(diǎn)在于其文學(xué)品質(zhì)的高低。認(rèn)可打工文學(xué)的立場普遍從人文精神、寫作倫理的角度,強(qiáng)調(diào)其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和社會關(guān)懷打破了90年代以后中國文學(xué)日益脫離社會生活的趨勢,促進(jìn)了“非虛構(gòu)寫作”、“生存寫作”等新的寫作觀念的興起,是對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的有益補(bǔ)充,可以被視為一種獨(dú)具一格的文學(xué)流派。批判打工文學(xué)的觀點(diǎn)則基于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認(rèn)為其文學(xué)審美性較弱,同時(shí)也從題材、思想方面批評打工詩歌表現(xiàn)主題較為單一、風(fēng)格雷同、視野局限、鋪陳苦難而沒有超越苦難等。無論承認(rèn)還是批評,無論偏重社會意義還是文學(xué)意義,學(xué)者們對于打工文學(xué)的傾聽方式均較為集中于其文學(xué)價(jià)值。即使對其社會意義的涉及也是視為包括在文學(xué)品質(zhì)判斷標(biāo)準(zhǔn)之內(nèi)的一項(xiàng)要素,爭論的是從文學(xué)角度來看應(yīng)該如何描述苦難而并無意對苦難的社會根源及其解決方式進(jìn)行深入探討。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知識分子的缺席,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來自文化精英的“文學(xué)式傾聽”特點(diǎn)的凸顯,這一傾聽方式協(xié)助擴(kuò)大了打工文學(xué)話語的社會影響力,但是無法充分實(shí)現(xiàn)它們的公共意義和對于社會政策的參考價(jià)值。
(三)社會政策制定者應(yīng)該傾聽苦難
政府部門的扶持和組織是打工文學(xué)得以發(fā)展的重要因素,然而作為社會政策的制定主體,政府部門的主動傾聽顯得不足。一是因?yàn)閷Υ蚬の膶W(xué)的社會政策意義意識薄弱。社會政策的宗旨之一是滿足社會成員的基本需求。如前所述,政府對打工文學(xué)的各種促進(jìn)性政策出發(fā)點(diǎn)主要在于文化政績和社會穩(wěn)定,對于通過打工文學(xué)理解農(nóng)民工群體的基本需求以及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缺乏充分的關(guān)注。而理解基本需求并把握相應(yīng)的問題所在,是社會政策制定的第一步——“議程設(shè)置”的關(guān)鍵。近年來出臺了多種社會政策用以加強(qiáng)對農(nóng)民工生活的物質(zhì)保障以及促進(jìn)農(nóng)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社會融合,但與此同時(shí)許多研究指出社會政策缺乏對農(nóng)民工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支持。打工文學(xué)群體雖然在打工群體整體中所占的比例難以把握,但打工詩歌表達(dá)了打工者由鄉(xiāng)到城、由傳統(tǒng)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到面對現(xiàn)代城市匿名社會以及工廠管理的規(guī)訓(xùn)等過程中,他們共同的經(jīng)歷、體驗(yàn)、情感,呈現(xiàn)的是經(jīng)歷巨大生活轉(zhuǎn)型時(shí)具有共性的精神歷程。這些內(nèi)心價(jià)值、感受、心理,并非一般的社會調(diào)查便可以輕易捕捉到的,但在詩歌、散文等文學(xué)作品中卻可以獲得細(xì)膩而豐富的表述,正是政策制定者了解打工群體精神需求的重要媒介。關(guān)注政績與社會穩(wěn)定而對農(nóng)民工社會需求的把握與重視不足,這一點(diǎn)并非僅限于政府對打工文學(xué)的態(tài)度。我國要向積極型、托底型社會政策轉(zhuǎn)變(關(guān)信平,2016),首先社會政策制定者應(yīng)該具備積極了解社會需求的意識,傾聽弱勢群體和來自底層的話語并通過進(jìn)一步的實(shí)際調(diào)查將其反映在社會政策的議程設(shè)置之中。
綜上所述,不論打工詩人主觀上的期待還是客觀上打工詩歌的社會反響,傾聽者主要來自于打工群體的文學(xué)愛好者和文學(xué)專業(yè)人士,即使打工詩歌通過媒體擴(kuò)大社會影響以后,對農(nóng)民工群體的社會倫理關(guān)懷和作為文學(xué)現(xiàn)象的探討并未提升或?qū)蚱涔埠x和政策價(jià)值。因?yàn)樯鐣茖W(xué)領(lǐng)域知識分子和政府在這一底層話語的傾聽中是缺位的,未能通過這一話語表達(dá)把握社會需求。
四、打工文學(xué)中的個(gè)體苦難與社會政策
(一)打工文學(xué)中苦難敘事的真實(shí)與虛幻
要探討打工文學(xué)的政策意義,首先需要厘清應(yīng)該如何看待打工文學(xué)。很多研究指出打工作家是打工群體社會經(jīng)歷的見證者和書寫者,他們?yōu)榻?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中被忽視、被遮蔽的失語者發(fā)出了聲音,打工文學(xué)是底層的自我表述。同時(shí)也有反對觀點(diǎn)認(rèn)為,打工作家是介于普通打工者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群體,而且打工文學(xué)受到政府扶持、市場生產(chǎn)、精英文化等各種機(jī)制的影響,這些導(dǎo)致打工文學(xué)并不能真正表達(dá)底層的聲音(李新、劉雨,2009;施瑞婷,2014)。那么,打工文學(xué)是否能代表底層的自我表述呢?
首先,很多打工詩人在工作和生活境遇改變以后仍舊保持著對農(nóng)民工群體的身份認(rèn)同并具有較強(qiáng)的群體代言意識。對于打工詩人來說,既有通過文學(xué)增加文化資本改變命運(yùn)的目的,也有較為明確的記錄底層現(xiàn)實(shí)、喚起社會關(guān)注、爭取群體境遇獲得改善的意識。如湯普森(2001)、裴宜理(2001)所分析的,工人階級的形成并不意味著群體內(nèi)部完全同質(zhì)化,技術(shù)工人與非技術(shù)工人之間的分化是明顯的,但并不影響他們共同群體認(rèn)同的形成和共同利益的表達(dá)。其次,任何社會群體要表達(dá)自我、爭取權(quán)益,都必然通過獲得社會主流話語認(rèn)可的方式。打工文學(xué)的確受到來自政府、市場、文化精英的影響,但它們同樣是表達(dá)機(jī)會得以實(shí)現(xiàn)的基本條件;而且受到來自社會各種力量的支撐與影響,是所有進(jìn)入公共領(lǐng)域的話語文本的共性。忽略話語表達(dá)的“互文性”本質(zhì)而追求純粹的“底層話語”,從社會政策的層面來看,是徒勞無益的,對于推動社會公正并無建設(shè)性。
此外,也有觀點(diǎn)認(rèn)為包括打工詩歌在內(nèi)的打工文學(xué)有過度夸大、渲染底層苦難之嫌,是否如此?首先,筆者對同一題材的三部文本中的苦難描述進(jìn)行了比較。流水線出身的打工詩人ZXQ、勞工社會學(xué)研究者PY、美國著名媒體的華裔記者ZTH,均基于自身的長期實(shí)地調(diào)查對廣東省的工廠女工進(jìn)行了記述。美國記者的紀(jì)實(shí)作品呈現(xiàn)了由于打工收入而使家庭地位有所上升,并且利用各種機(jī)會不斷學(xué)習(xí)和向上流動的打工妹形象;打工詩人的詩集描述了女工生活各個(gè)側(cè)面的苦難,不僅有流水線的異化勞動和工傷,還有家庭生活、婚姻戀愛、社會交往、生活機(jī)會等各方面的“疼與痛”,但這位以偏重苦難敘事而聞名的打工詩人對打工妹的描寫側(cè)重于白描手法而呈現(xiàn)出“記錄、見證”的立場和較為冷靜、抑制的情感表達(dá);學(xué)者學(xué)術(shù)作品集中于考察和分析工廠勞作為女工帶來的身體損害和精神摧殘,在三部作品中,學(xué)者PY的研究對苦難的描述篇幅最長、最細(xì)致入微,呈現(xiàn)的痛苦程度和所用詞語的情感強(qiáng)度也是最高的,也正因其社會批判力度之深,這部學(xué)術(shù)作品引起廣泛的學(xué)術(shù)反響和社會反響。這一比較雖然簡單粗糙,結(jié)論不能輕易普遍化,但可以看出打工詩歌會過度渲染苦難的說法也是輕率而難以一概而論的。
另一方面,苦難如果在打工文學(xué)中被夸大和渲染,除了是寫作上的某種策略這一解釋之外,從現(xiàn)象學(xué)的角度來看也有可能是精神痛苦甚至心理創(chuàng)傷的表征。國內(nèi)對農(nóng)民工精神健康的實(shí)證研究結(jié)果可以成為參考。大多數(shù)研究都指出,農(nóng)民工在心理健康方面的不良癥狀較全國平均水平嚴(yán)重,常見問題有焦慮、人際關(guān)系敏感、抑郁、偏執(zhí)、敵意等,其精神健康狀況需要得到更多關(guān)注(何雪松等,2010:124;胡蓉、陳斯詩,2012:137)。因此,無論打工文學(xué)出于何種原因以及是否對生活苦難過度渲染,重要的是對苦難的感受在這一群體中是真實(shí)存在的,它們表明某些問題的存在,在社會政策的議題設(shè)置中值得進(jìn)一步調(diào)查和探討。
(二)傾聽底層苦難的政策意義
打工文學(xué)作為底層話語能夠進(jìn)入公共空間得以表達(dá)并獲得傾聽,體現(xiàn)出中國社會市場化轉(zhuǎn)型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以后,對于“農(nóng)民工”這一弱勢群體仍舊存在著一定的政治的、倫理的保護(hù)空間。但社會群體平等權(quán)益的獲取不應(yīng)僅靠外力的保護(hù)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擁有表達(dá)自身訴求的渠道。目前農(nóng)民工群體尚難以通過制度規(guī)定的渠道參與政治、維護(hù)自身利益(徐志達(dá)、莊錫福,2011;左珂、何紹輝,2011),他們在傳媒表達(dá)方面也缺少話語權(quán),處于集體失語的狀態(tài)。在這樣背景之下,以政府為主體的社會政策制定者更應(yīng)該重視和傾聽打工文學(xué)這一代表弱勢群體話語的文化表達(dá)形式,以把握這一群體的社會需求。
打工文學(xué)中既描述了打工群體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中的底層位置帶來的痛苦,也呈現(xiàn)了社會紐帶解體帶來的解體性痛苦。從話語文本中表述的內(nèi)容來看,打工群體的需求包括社會政策所重視的物質(zhì)生活的提高、勞動與生活權(quán)益的保障以及免遭歧視而受到尊重,除此之外,精神上的孤獨(dú)、空虛和價(jià)值取向的迷茫也是深刻而難以獲得解脫的痛苦。從寫作實(shí)踐來看,打工文學(xué)體現(xiàn)出打工群體自我表達(dá)與精神交流的需求,從作品的寫作、發(fā)表到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聯(lián)系往來,都是在血緣、地緣等傳統(tǒng)社會關(guān)系紐帶之外,渴望實(shí)現(xiàn)情感與價(jià)值領(lǐng)域的社會支持。很多研究呼吁社會政策重視農(nóng)民工群體的精神層面,打工文學(xué)中的確豐富地呈現(xiàn)了他們巨大而饑渴的精神需求,其中既有對社會交往的需求,也有對生活意義的尋求和自我價(jià)值感的需要。
社會政策要滿足社會需求,其制定不僅以社會理念為基礎(chǔ),還以對人的需求的認(rèn)識方式為基礎(chǔ)。關(guān)于個(gè)體需求的認(rèn)識影響最大的莫過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但打工文學(xué)的表達(dá)內(nèi)容和表達(dá)實(shí)踐都提示,打工群體的拮據(jù)和失語并不意味著精神需求的遲鈍,即便收入較低,他們對自身的處境也有著豐富而敏銳的感受,并且十分重視精神生活的充實(shí)。他們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滿足的條件下,也同時(shí)具有強(qiáng)烈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shí)現(xiàn)需求。如果完全依照馬斯洛的理論看待個(gè)體,便容易產(chǎn)生打工群體缺乏精神追求的偏見,也容易導(dǎo)致社會政策集中于這一群體的物質(zhì)性權(quán)益保障。
此外,繼續(xù)推動和傾聽打工文學(xué)這一底層話語的表達(dá)渠道,不僅有助于社會政策的議程設(shè)置,還有助于推動農(nóng)民工群體的精神健康和城市融合。對于打工群體的寫作愛好者來說,通過文學(xué)書寫,他們的苦難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精神上獲得自我調(diào)整。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寫作相當(dāng)于一種精神創(chuàng)傷的自助療法。而文學(xué)作品的閱讀也可以促進(jìn)對陌生群體的理解與同情,這是實(shí)現(xiàn)社會正義的情感基礎(chǔ)(努斯鮑姆,2009)。打工文學(xué)能夠增加城市居民對農(nóng)民工群體的了解,有助于消除偏見和歧視,進(jìn)而促進(jìn)社會的整合與穩(wěn)定。因此,“訴苦”、“抱怨”不是負(fù)能量,它們敦促理解與解決,而偏見、冷漠、隔絕、敵視才是真正的負(fù)能量,它們阻礙相互的理解和互動。政府不應(yīng)為了“正能量”限制苦難的公共表達(dá),苦難的真實(shí)呈現(xiàn)有助于社會政策制定者在弱勢群體缺乏制度性表達(dá)渠道的條件下把握社會問題,也有助于提高農(nóng)民工群體的適應(yīng)能力、消除城鄉(xiāng)隔膜與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