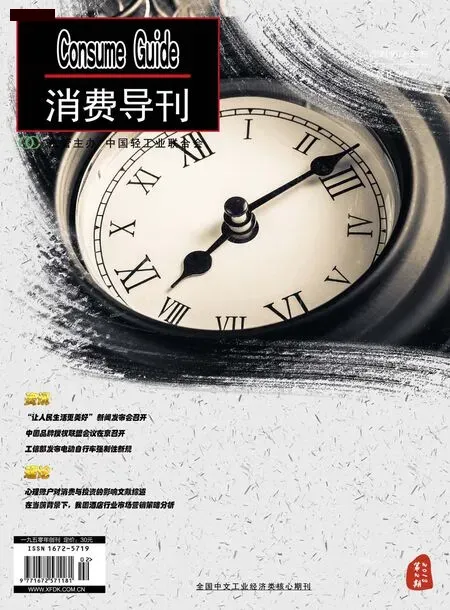威爾第《安魂曲》的音樂史學分析
趙艷辰
摘 要:達爾豪斯認為, 音樂史的重點并非在于文獻的反復重建, 而是基于理解作品。圍繞作品的作曲家生平、演出機制、社會審美等等一起形成了音樂的史實,本文根據達爾豪斯的結構史觀,通過分析威爾第《安魂曲》的音樂文本、作者生平以及當時的社會審美和演出概況等來闡釋威爾第的創作意圖和當時宗教音樂創作的一種情況。
關鍵詞:達爾豪斯 結構史 安魂曲 19世紀宗教音樂
什么是音樂史的事實?“音樂的作品以及其演出,寫作這些作品的作曲家的生平事實,作品運作于其中的建制,時代的美學觀念和維持音樂體裁興盛的社會階層”這些都是事實,并組成了一部音樂史。然而歷史的文獻與事實是確實存在差距的,盡管它的編撰者力圖獲得歷史的真相,但嚴格來說,文獻史料由于作者這樣那樣的主觀原因無法還原歷史真相。對于音樂史來說,“音樂作品……屬于史學家手中的‘當今, 是史學家能接觸到關于音樂史過去的直接殘余。它們作為屬于當今的美學對象, 與文獻、證據一起構成能與過去對話的第二手‘史料。”
既然如此,那么對于作曲家的創作本意分析也應該基于作品,從作品的題材、體裁、結構及更一步的寫作手法來了解作品的真意。
一、安魂曲的角色轉變
安魂彌撒曲簡稱安魂曲,又稱“追思曲”、“慰靈曲”,是天主教在悼念死者的祭奠儀式中演唱的一種合唱套曲。因唱詞首句以“Requiem aeternam”開頭(第一句是“主啊,請賜予他們永恒的安息”),故稱為安魂曲。我國天主教會一般將其翻譯為追思曲。
安魂曲作為教堂彌撒的一部分,可以說是天主教以音樂體現信仰的象征之一,然而隨著西方社會對宗教態度的轉變,作為宗教儀式而存在的安魂曲也勢必受到影響。張己任在《安魂曲綜論》中將安魂曲的創作分為為神而作、為(別)人而作和為自己而作三大類,分別對應音樂史的四個階段:中世紀時期、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時期至浪漫主義時期和 20 世紀以后。 尤其是19世紀之后,西方音樂的專業創作進入了“個人化”創作的時代,諸多社會思潮對宗教的沖擊使人的宗教信仰也進一步衰落,宗教儀式的約束逐步放開,作曲家對于“個人化”的追求就不斷地體現在宗教作品中——如歌詞的選用,對既有結構的刪減等等,社會化生產和市民音樂生活的轉變使得不少宗教作品開始由教堂轉移至音樂廳演出,從嚴肅的不可侵犯的宗教象征轉變為藝術化的商品。
二、威爾第《安魂曲》的音樂分析
1.結構與風格
傳統的安魂曲結構一般由8段經文組成,分別是安息經(Requiem)、慈悲經(Kyrie Eleison)、繼敘詠或末日經(Dies Irae)、奉獻經(Offertorio)、圣哉經(Sanctus)、降福經(Benedictus)、羔羊經(Agnus Dei)、圣餐經(Lux Aeterna)。其中末日經分成9個部分。威爾第在自己的《安魂曲》中將《降福經》刪去,安息經與慈悲經合并為一個樂章,又在《圣餐經》之后加入了一段賦格曲《拯救我》。然而《末日經》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不僅如此,威爾第將《末日經》的九個分曲通過一段“末日審判”音調統一成一個整體,篇幅占據整部作品近四成。
這段重要的“末日審判”音調在第一分曲《最后的審判》開始時用空拍隔開的全奏,合唱的凄厲的半音下行和暴風雨呼嘯般的樂隊將末日審判,天神震怒眾生驚恐的場面表現出來。
譜例1 《最后的審判》合唱部分的“末日審判”音調
之后的用相對安靜的風格持續描述人類恐懼,直到第三分曲《書已寫成》,這是《安魂曲》中第一個結構完整的獨唱曲。風格類似于歌劇中的詠嘆調。女高音演唱宣敘性音調時,樂隊不時地以“末日審判“音樂的動機片段對她進行烘托,隨后“末日審判”音調第一次完整重復。
譜例2 《書已寫成》中“末日審判”動機
在“末日審判”音調的狂風暴雨后,四至七分曲又開始出現時而祈求寬恕時而歌頌上帝的情緒,而第八分曲《從被詛咒者》“末日審判”音調再次在A段的重復中出現,這一分曲的結構是ABACBCode,區別于A呈示時樂隊的簡短急速的音型在長音處予以襯托的動機片段,當A再現時,樂隊發展得更為完整,配合著歌詞所唱“該下地獄者都被驅逐,并被趕入烈焰中”,定音鼓猛烈的敲擊,弦樂和木管極速地級進流動,描繪出《最后審判日》黑暗恐怖的景象,之后“末日審判”音調再一次插入,完整重復,貫穿了整個第二樂章。
譜例3 《從被詛咒者》A段呈示中的“末日音調”動機片段
譜例4 《從被詛咒者》A段再現時樂隊中的“末日音調”
傳統安魂曲的一大弱點就是樂章之間的結構力較弱,章節之間的聯系較少,而威爾第運用“末日審判”音調將龐大的第二樂章整合成了一個整體,更讓人驚異的是在整部作品的最后一部分《拯救我》中“末日審判”音調第三次重復,顯然“末日審判”音調已經作為了一種類似于“主導動機”一樣的樂思為威爾第所使用。
不僅如此,“末日審判”音調中營造的狂風暴雨般的災難場面與《奧賽羅》的暴風雨場面頗為類似。獨唱和合唱時而扮演惶恐的人類時而成為威嚴的上帝,用大量的重唱作為音樂的推動力,可見威爾第在創作《安魂曲》時使用的仍是自己得心應手的歌劇處理方法,沒有了劇情發展的需要反而更加靈活。
在《安魂曲》整部作品的風格安排上威爾第還是在盡量平衡著宗教性與戲劇性的關系的,威爾第依舊采用了拉丁文歌詞,在第一章《永恒安息》中遵循禮拜儀式文本的ABA結構;第五章《羔羊經》是由固定旋律變奏構成的變奏曲結構,固定旋律具有圣詠式的風格,發展手法頗具定旋律經文歌的特點。但是“末日審判”音調的線索性和對作品的結構力使得整個作品與其他宗教作品安詳寧靜的風格大相徑庭,以至于首演后得到了這樣的評論:“威爾第的上帝是個兇惡殘忍的上帝”,“這首安魂曲不能使我們集中精神祈禱,而是完全相反——在它里面是一片呼號哭叫,充滿內心的風暴和恐懼。”
《末日經》和《拯救我》是在為羅西尼寫安魂曲時就已經完成了的,那么“末日審判”音調這一樂思就是早已有之,在一部宗教音樂作品中使用如此戲劇化悲劇化色彩極強的素材作為整部作品的線索威爾第確有更深一層的創作意圖并且隨之的作品風格的改變也是他的有意安排。
2.復調技法與復調思維
作為一部宗教作品,《安魂曲》無法像歌劇一樣以腳本為依托,有既定的劇情發展線索和人物形象,作品中的音樂形象和內涵的豐富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復調的語言表述方式。為了建立和鞏固作品的音樂形象,威爾第在《安魂曲》中應用了大量的復調技法和高難度的復調曲式,比如在《安魂曲》的非格律形式的樂章中,一種音型化復調,即“贗品復調”的形式大量存在。
威爾第在《安魂曲》中安排了一些具有指向性意義的動機或音型,各自代表了某些特定的意象。在音樂進程中,這些動機和音型或以原型、變體形式各自獨立呈現,或被作為與某一樂段的主要旋律相對比的材料,與之進行對位結合,從而形成性格、形象的對峙。
譜例5 《最后的審判》第九分曲《哀悼》635-638小節
譜例是一段對比復調織體,很明顯地看出次女高音聲部是宣敘式、音型化的旋律。次女高音的音樂素材其實來自《安息經》中女高音聲部的抽泣音調,在這里威爾第把它縮短了,而男低音聲部則是流暢的分曲主題旋律,二者出現了明顯的音樂形象的對立。
譜例6 《安息經》女高音的抽泣音調格的程序,但卻根據音樂的內容和發展邏輯選擇性地采用了傳統賦格的部分格律原則與發展技巧,尤其是對題的寫法,他的對題來源于主題,兩者不具有對比性,對題與答題經常是三度的平行進行,實質上就相當于答題的平行附加聲部,這樣就構成了帶有輕微對位因素的主調化織體。
作品中大量的模仿復調也采用了音型化的處理,比如威爾第在各聲部主題動機的原型或變形在緊接模仿進入后很快便放棄模仿,或是休止,或是長音持續,或是進行自由對位。等待聲部全部進入后又立刻變為整齊的主調織體。
譜例7 《最后的審判》第九分曲《哀悼》657-660小節
威爾第的這種主調思維與復調技法的結合受到了當時浪漫主義作曲家對于復調寫作傾向的影響:即舍棄格律的形式,采用重唱式的對位以及裝飾性的隱形化的復調手段,將其作為主調音樂的補充、裝飾、潤滑。威爾第雖然仍保持著賦格的格律形式卻根據作品的需要對音型化復調進行了精心
主題被壓縮為五個音的動機,從男低音聲部逐漸爬升至高音區,而這時樂隊和合唱的低音部分出現了下行的對位線條,在音響和音色逐漸豐富和厚實并達到高潮后轉入了主調織體。
這種“贗品復調”其實是威爾第主調思維和復調技法的結合的體現,這種特殊的復調思維還出現了結構復雜的賦格曲中。
威爾第在《安魂曲》中共創作了三段賦格曲:《圣哉經》、《拯救我》的一部分和第一樂章的《慈悲經》。威爾第在創作中遵循了賦的安排,這不僅是大師作曲技術與技法的天才創造也是威爾第對這部作品內在理解,不恪守音樂寫作的宗教常規,用宗教的外殼來表達自己的創作意圖,這就是我們之前所說的“個人化”。
三、創作意圖
威爾第曾自嘲自己來創作安魂曲是個諷刺,跟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威爾第認為自己是個自然主義者,他的第二任妻子朱塞平娜說他是個“沒有信仰的人”,威爾第在歌劇作品中還明顯地表達了自己對宗教人士的厭惡,《唐卡洛》中陰險的主教和《阿依達》的大祭司都是徹頭徹尾的反派人物,那為什么威爾第這樣對宗教沒什么敬仰的人會起意創作一部宗教作品?
威爾第出身于農民,一般來講應該是個天然的天主教徒,但是威爾第童年對于教士打罵的陰影與成年后到米蘭闖蕩的坎坷經歷影響到了他對于上帝救贖的信念,這也能解釋為什么在旁人看來威爾第在《安魂曲》中描述了一個“兇惡的上帝”,這個作品中的“上帝”對人類的祈求和歌頌沒有任何回饋,只有在“末日審判”的音調中露出真實的面目,降下懲罰才是“上帝”職責,人類只有不斷的抗爭才能獲得重生,這似乎符合威爾第對宗教的一貫態度;而威爾第創作《安魂曲》時已經是一個年過六旬的老人,他身邊的親人、朋友也在不斷地有人病倒、逝世(包括曼佐尼),面對死亡和疾病,威爾第自然地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以及試圖在宗教中尋找一些能緩解他對于死亡的焦慮的東西,《安魂曲》中最后一章《拯救我》里面熱烈的情感可以說是威爾第對于尋找生命答案急切的表現。在這兩種矛盾的心理下的創作成的《安魂曲》既在作曲技法上吸收了宗教作品創作的手段,保持部分章節的宗教音樂氛圍,如《圣哉經》、《羔羊經》等,又保留自己的創作風格加強戲劇化表現,不斷地用“末日審判”提示人們和自己,“上帝”并非慈悲。
達爾豪斯認為作品的接受史是作品“真正的自我”,在時代的精神共鳴中尋找到作品的意義,威爾第這部有著特殊的情懷的《安魂曲》為何如此順利地被當時的大眾接受(當然也有些反對聲音)也能一窺當時人們甚至包括教會對于宗教和宗教作品的態度。
威爾第《安魂曲》除了紀念曼佐尼的宗教意味外也與當時的浪漫主義思潮對于“死亡”這一主題癡迷關聯甚密。“浪漫哲學的旨趣始終在于:在白天朗照、黑夜慢慢的世界中,終有一死的人就講從何而來,有要去往何處,為何去往?有限的生命究竟如何尋得超越,又在哪里尋得靈魂的皈依。”浪漫主義時期創作的安魂曲大抵都要面臨這種追問,這也是浪漫主義時期安魂曲創作爆發的原因之一。既然要尋得“靈魂的皈依”,按西方文化的慣性思考,必然是天堂或地獄,受神恩眷顧安詳平靜還是墮下地獄受盡苦難全憑上帝判斷,但威爾第在《安魂曲》中“人類”的表現卻是雖然祈求寬恕但不一味屈從,甚至奮起反抗,可以說這種對“上帝”的態度也是當時人們對于“上帝”的一種態度。
“首演”對于一部作品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即使首演不一定揭示一部作品的命運,也在這部作品的接受史中大有文章可做。涉及威爾第的《安魂曲》之前要先提一下這部《安魂曲》中的第二章《最后的審判》和最后一章《拯救我》。這倆部分最開始是為羅西尼的安魂曲所做,在羅西尼逝世后威爾第提出與當時知名的作曲家共同創作安魂曲并將這倆部分寫好,但這個主意并未實行,威爾第后將這倆部分放入《安魂曲》中。這個在我們看來有點天真的主意對于當時的人們恐怕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意大利南北統一戰爭時,教會暗中勾結法國人準備將意大利北部劃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但在1870年法蘭西第三帝國失勢,教會陰謀敗露,意大利共和國通過法律將教皇和教會的職權限制在了梵蒂岡內部。教會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教會采取了“曲線救國”的方針,將影響力轉向了文化領域。正值意大利國家統一民族解放之際,意大利民族主義意識空前高漲,教會將既能代表意大利文化又是教會中的知名人物,如帕萊斯特里那,作為代表大肆進行紀念活動。這種風氣從而影響到了意大利的文化界,紀念活動不再限于是否是教會名人,像羅西尼和曼佐尼這種文化名人的紀念活動自然會受到意大利文化界的支持,威爾第的《安魂曲》之所以能順利上演也是得益于此。
解決了受眾心理,演出場所和演員、服裝等等都是需要注意的。《安魂曲》首演于米蘭圣馬爾科教堂,之后由于觀眾過多,又在斯卡拉劇院上演了三場。這時的觀眾對于《安魂曲》這種宗教作品是否在教堂上演已經完全不在乎了,他們在乎的是大師的名望和音樂的藝術感染力。威爾第選擇在圣馬爾科上演的原因是——音響好,可見威爾第并不顧慮曼佐尼的天主教徒身份。但在教堂演出還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的是:女性要在教堂中保持沉默。威爾第的前輩羅西尼也同樣面臨過這個問題,結果是羅西尼不得不在私人小教堂演出。在經過與教會的拉鋸戰后,威爾第與教會相互妥協,女高音和次女高音帶著面紗躲在祭壇的柵欄后面演唱。其實,觀眾并不在乎女性在教堂中是否沉默,而教會也因時代的變化和大師的聲望變得通融了許多。
四、總結
威爾第的《安魂曲》之所以被認為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是因為深刻的文化象征和極高的藝術水準,其高超的個人創作水平在其中得以完美體現并與藝術表達高度結合。這部作品從技術層面上看,是威爾第個人創作技巧的濃縮;從精神層面上,這部作品也是在威爾第之后停筆的十三年沉寂之前向命運做出的最后的抗爭和吶喊。而對于當時社會而言,這部作品背后蘊含的文化象征意義正是當時意大利甚至整個歐洲的宗教與世俗社會的常態。這部安魂曲是當時人對宗教的態度——帶有復雜的情感但并不篤信,“上帝”是個幻想的化身,對于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上帝”從一種固定形象轉化為“個人的上帝”。
參考文獻:
[1]朱塞佩·塔羅齊(1992).命運的力量:威爾第傳. 北京:三聯書店.
[2]張己任(2003).安魂曲綜論. 臺灣:大呂出版社
[3]達爾豪斯著. 楊燕迪譯(2006). 音樂史學原理. 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
[4]劉經樹(2007). “作品”、結構史、人的歷史——達爾豪斯的音樂史編纂學. 音樂研究. 第二期
[5]李靜思(2014)“死亡”主題在浪漫主義時期音樂作品中的表現(碩士學位論文)西安音樂學院. 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