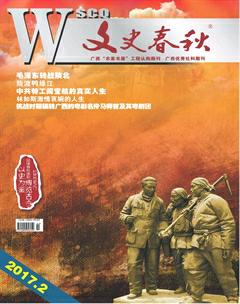險(xiǎn)渡鴨綠江
周民震
1951年初春,廣西緊急組建的廣西首個(gè)志愿軍團(tuán)——中南軍區(qū)補(bǔ)訓(xùn)二十八團(tuán)的3000多名廣西各族子弟兵,從祖國南疆奔赴抗美援朝戰(zhàn)場(chǎng)。
部隊(duì)乘坐的一列長長的悶罐(鐵皮貨車廂)火車,經(jīng)過一個(gè)多月的旅途勞頓,來到了抗美援朝的前沿地——安東市(今丹東市)。進(jìn)入安東時(shí),已是傍晚時(shí)分了,市區(qū)卻是一片漆黑。原來,這里實(shí)行嚴(yán)密的燈火管制。靜靜地傾聽,不時(shí)有一陣陣美國飛機(jī)的馬達(dá)聲從朝鮮方向飄來,還夾著隱隱的轟炸聲。3000多名首批出征的廣西各族人民的優(yōu)秀子弟。懷著對(duì)朝鮮人民的無限熱愛和對(duì)美國侵略者的無比仇恨,戎裝煥發(fā)地來到碧波蕩漾的鴨綠江邊。他們都是從廣西各地正在剿匪戰(zhàn)場(chǎng)上抽調(diào)來的。
當(dāng)時(shí)只有19歲的我,是該團(tuán)第十六連的政治指導(dǎo)員。我們連原是柳北游擊總隊(duì)十二中隊(duì),戰(zhàn)斗在大苗山一帶,解放后編為融縣縣大隊(duì)二連。由于在廣西剿匪中表現(xiàn)出勇猛的戰(zhàn)斗力,屢傳捷報(bào),被廣西軍區(qū)從剿匪前線全建制調(diào)集而來,光榮地參加到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的行列。在柳州附近的洛埠鎮(zhèn)集中動(dòng)員時(shí),戰(zhàn)士們個(gè)個(gè)情緒高昂,斗志堅(jiān)定,誓以滿腔熱血與侵略者拼搏!
許多戰(zhàn)士從山區(qū)來的,沒見過火車,出了不少意料不到的麻煩,見這龐大的鐵龍轟隆隆地奔跑。覺得又好玩又恐懼;坐的是貨車。沒窗戶沒廁所,睡在墊著稻草的鐵板上搖晃著,興奮得睡不著覺,整夜唱山歌,還用新編的事來對(duì)歌呢。有位小戰(zhàn)士問,抓到美國俘虜,叫他舉手投降,他聽得懂壯話嗎?引得大家哄笑。當(dāng)時(shí)交通不暢,火車走走停停,待著無事,于是我想到教他們一點(diǎn)實(shí)用英語,如:“Hands up!”(舉起手來!)“Dron your weapon!”(繳槍不殺!)“Surrender!”(快投降!)“What i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還有幾旬日常用語。僅憑我在中學(xué)時(shí)那點(diǎn)點(diǎn)英文水平當(dāng)然不夠,這還是出發(fā)前我那讀過大學(xué)的三哥民雷專從柳州來送行時(shí)教我的。戰(zhàn)士們興致濃濃的用漢字音譯了寫在本子上,還演繹著如何抓美國俘虜時(shí)的狀況。又熱鬧又能鼓舞士氣呢。
沒想到過了長江進(jìn)入河南省時(shí),思想工作最難做的竟是吃飯問題。閉塞的廣西山區(qū),農(nóng)村從未見過饅頭,而北方當(dāng)時(shí)根本見不著大米,沿途三餐都是供應(yīng)饅頭,每次到了吃飯時(shí)間,都要費(fèi)老大的勁來動(dòng)員戰(zhàn)士吃饅頭,好多戰(zhàn)士咬了一大口饅頭臉漲得通紅,對(duì)我怨訴:“指導(dǎo)員,卡在喉嚨吞不下去啊。”我說,小口慢咽,再喝點(diǎn)水就行了,哪有吃家鄉(xiāng)米粉那么順溜呀。大家都笑了,于是創(chuàng)造了“饅頭粥”,泡在口盅里吃。也有些戰(zhàn)士說:這個(gè)家伙比在家天天吃稀撈撈的玉米粥飽肚子。于是我提出了“吃下一個(gè)饅頭就是消滅一個(gè)敵人”的口號(hào)。還真起作用,有位胃口大的戰(zhàn)士競(jìng)一餐吃了6個(gè)饅頭。大家叫他“饅頭司令”“殺敵英雄”,現(xiàn)在聽起來一定覺得很可笑。
到安東的第二天,召開了排以上干部大會(huì),由前線來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三十八軍政治部朱主任做動(dòng)員。他首先代表軍長梁興初歡迎我們,并如實(shí)地介紹了前線艱苦殘酷的戰(zhàn)爭(zhēng)現(xiàn)實(shí),號(hào)召大家要充分做好戰(zhàn)勝困難甚至流血犧牲的思想準(zhǔn)備。原來,被稱為“萬歲軍”的第三十八軍,剛打完著名的“漢江南岸阻擊戰(zhàn)”,雖予敵重創(chuàng)。但自己也要大量補(bǔ)員。正在休整。他們向中央軍委提出指名要廣西戰(zhàn)士。因他們?cè)鴧⒓舆^解放廣西戰(zhàn)役。又與廣西游擊隊(duì)并肩剿過匪,知道廣西兵能打能拼能吃苦,光著腳丫子爬山比猴子還快。說得我們都笑了起來,更添了幾分自豪和勇氣。朱主任還要我們動(dòng)員戰(zhàn)士把多余的衣服毛巾牙刷等物品(都是部隊(duì)定期發(fā)的,常用不完)都寄回家去。輕裝上前線。大家聽了都心里明白他的含意。會(huì)后,我和孫珊副指導(dǎo)員去照了一張快相,寄回家去,別到時(shí)連張遺像都沒有。晚餐時(shí),朱主任特別在一家酒樓邀請(qǐng)我們排以上干部聚餐。聽說東北的宴會(huì)講究“小四四”和“大四四”,我們吃的是“小四四”,就是四盤涼菜四盤熱菜。“大四四”就是十六道菜。部隊(duì)?wèi)?zhàn)士殺豬加菜。廣西人叫做“打牙祭”。后來到了朝鮮分到各師團(tuán)時(shí),又有一次迎新會(huì)餐。雖幾個(gè)罐頭,一大盆豆腐,尤其是專給廣西戰(zhàn)士準(zhǔn)備大米飯。讓大家好高興,說三十八軍領(lǐng)導(dǎo)真好!
當(dāng)晚深夜,部隊(duì)在無聲中從安東市出發(fā)了。由于鴨綠江上的大鐵橋早已被敵機(jī)炸毀,我們只能行軍到上游的一座臨時(shí)搭起的浮橋過江。春寒料峭,來自西伯利亞的朔風(fēng),呼嘯怒號(hào),刮得沿路老樹、枯藤獵獵作響。但大家知道今夜就要過江,進(jìn)入抗美援朝前線,每個(gè)人心里就像燃燒著一團(tuán)火。通訊員小程一邊走一邊沒完沒了地問我,朝鮮人長什么樣子?朝鮮妹仔會(huì)唱山歌嗎?朝鮮人吃大米嗎?我說,明天早上你就會(huì)看見了。其實(shí)我也是一問三不知,那時(shí)誰也沒有出過國呀!
摸黑行軍十幾公里。3000多名戰(zhàn)士來到了浮橋頭,傳來了就地休息的命令。原來,浮橋在白天被敵機(jī)炸毀了一大節(jié),工兵正在搶修呢。
夜越深,風(fēng)越肆虐,還夾著一些凍雨。戰(zhàn)士們坐靠在地上休息。時(shí)間久了,個(gè)個(gè)冷得瑟縮著。宋瀛洲副團(tuán)長(后任廣西軍區(qū)副司令員)巡視各連。走過來關(guān)切地問我:“小周,冷不冷?”我說實(shí)話:“這風(fēng)像刀子割肉一樣。哪有不冷的!”他笑了笑說:“告訴你一個(gè)好辦法,這樣的氣候越歇越冷。站起來,原地跑步!”
咦!這辦法真靈!戰(zhàn)士們?cè)嘏懿?0分鐘,個(gè)個(gè)熱氣騰騰,額上滲出了微微的汗液。部隊(duì)又活躍起來了。
東方出現(xiàn)了些許曙色。敵機(jī)的馬達(dá)聲開始在空中嗡嗡作響了。連長喻振華悄聲對(duì)我說,糟了!天亮才過江,就會(huì)把目標(biāo)暴露給敵機(jī)。我說團(tuán)部會(huì)考慮的,也許要等到今晚才過江吧?話還未落音,團(tuán)部通訊員傳來了命令:橋已修好,部隊(duì)立即過江,時(shí)間就是勝利!
迎著朦朧的晨霧,3000多名戰(zhàn)士依次魚貫地踏上浮橋。宋副團(tuán)長焦急地站在橋頭指揮,口里不斷地喊著:“快!快!”在部隊(duì)秩序井然地快速過江中,敵機(jī)的馬達(dá)聲老在高空中環(huán)繞,大家不顧它的威懾,趁著迷漫的霧氣。鎮(zhèn)定地過江。
一個(gè)鐘頭過去了,天已大亮,云開霧散。正輪到我們連過橋,大家昂首前進(jìn)。興奮地望著對(duì)岸漸漸近了的異國山地田疇和身穿白衣白裙的朝鮮人的身影,誰還不加快自己的腳步?通訊員小程看著對(duì)岸看得著迷了,踏空了一腳,險(xiǎn)些掉進(jìn)江水中,我連忙把他拉起來。
恰在這時(shí),一架敵機(jī)突然破云而出,俯沖下來,發(fā)出震耳欲聾的呼嘯聲。正走在橋上的戰(zhàn)士一時(shí)不知所措,有的戰(zhàn)士伏在橋上不敢亂動(dòng),怕暴露了目標(biāo)。這時(shí)首長傳來命令:不管敵機(jī),只管前進(jìn)!我們立即帶領(lǐng)部隊(duì)繼續(xù)過江。
敵機(jī)飛過頭頂后。繞了一圈又轉(zhuǎn)頭回來。開始向橋上的部隊(duì)掃射。子彈在橋上橋下爆響,把水花激起老高。連長告訴我們,這是一架火力偵察機(jī),不必害怕。于是部隊(duì)加快了腳步,繼續(xù)勇往直前。
這時(shí)敵機(jī)好似無奈地盤旋一周。然后拖著無力的嚎叫,漸漸遠(yuǎn)去。戰(zhàn)士們見敵機(jī)遁去,興奮難抑,有名戰(zhàn)士自發(fā)地唱起了剛學(xué)會(huì)的《志愿軍戰(zhàn)歌》:“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歌聲一唱,立刻群起應(yīng)和。歌聲可以壯膽。歌聲可以揚(yáng)威。歌聲藐視敵人,歌聲長自己志氣!一時(shí)間。整條浮橋上的隊(duì)伍都以各自的調(diào)門唱了起來:“保和平,衛(wèi)祖國,就是保家鄉(xiāng)。中國好兒女,齊心團(tuán)結(jié)緊,抗美援朝,打敗美帝野心狼!”反正敵機(jī)走了,不走也聽不見歌聲。大家放開嗓子邊跑邊唱。
這時(shí),團(tuán)部傳令:“加快跑步前進(jìn)!敵人的火力偵察機(jī)發(fā)現(xiàn)了目標(biāo)后,只需15分鐘,大批轟炸機(jī)就會(huì)趕到。”
啊!15分鐘!時(shí)間就是生命!
當(dāng)我們連隊(duì)順利跑過了江,再回頭眺望時(shí),最后兩個(gè)連隊(duì)的戰(zhàn)士還正在飛快地過江,像一條矯健的蒼龍,呼嘯著向江這邊飛騰而來。他們昂起頭,揚(yáng)起戰(zhàn)歌,甩開膀子,與時(shí)間賽跑!我禁不住淚眼蒙嚨起來,暗暗祈愿:快呀!15分鐘快過了!每一秒鐘都連著親愛的兄弟們的生命啊!我們這些來自遙遠(yuǎn)邊疆的各族同胞,肩負(fù)著父老兄弟的重托,是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來捍衛(wèi)神圣祖國的尊嚴(yán)的!
15分鐘剛過。敵軍的轟炸機(jī)群果然隆隆地飛來了。幸運(yùn)的是,3000多名戰(zhàn)士已安全地過了江,隱蔽在森林里了。敵機(jī)撲了空,只好向一座空橋胡亂投擲炸彈。然后夾著尾巴逃跑了。
早上的太陽升了起來,鮮亮而帶有血色,我們披著偽裝行進(jìn)在苦難的朝鮮土地上。向著前沿陣地日夜兼程地前進(jìn)!
朝鮮北部多山,公路少而狹窄,擠滿了補(bǔ)給糧彈的車馬。部隊(duì)只能沿山路而行。即使這樣,也因美國飛機(jī)的威脅,改為了夜行軍,每天傍晚出發(fā),在黑夜中通宵行軍直奔向南,快步走了約50公里左右,天便拂曉了,于是在樹林中或山溝里隱蔽休息。當(dāng)時(shí)敵機(jī)猖獗至極。低飛偵察時(shí)。甚至可以看見飛行員的面孔一閃而過。有戰(zhàn)士想對(duì)敵機(jī)射擊,但被制止,因飛機(jī)速度太快,很難擊中,卻又會(huì)暴露我們的目標(biāo)。
由于制空權(quán)在敵人手里,為了不暴露自己,常不能埋鍋造飯,只能吃干糧。這些所謂干糧,還是過武漢時(shí)發(fā)給每人幾塊像書本大的玉米粉壓成的餅干和一罐咸菜。哪算是餅干,簡(jiǎn)直就是石頭片,用槍托砸碎了才能一點(diǎn)點(diǎn)啃。由于沿路村莊大多被炸毀,老百姓都在山里林中建了許多茅草棚臨時(shí)棲身,常常熱情地拉戰(zhàn)士們住在他們狹小的窩棚里。能燒一壺開水溶化那石頭般硬的玉米餅,喝上一碗熱乎乎的開水,就是最大的享受了。有次遇到一位朝鮮老大媽懂得些中國話,我向她學(xué)了幾句朝鮮話,在小本子上用漢字標(biāo)音,現(xiàn)在還記得的只兩句:“唐心瓜屋里娃,卡騰消里米約”(中國人朝鮮人都是一家人),“由幾索平洋嘎幾,明里騰里卡?”(由這里去平壤還有多少里路?)我都教會(huì)了戰(zhàn)士。怕掉隊(duì)時(shí)好問路。當(dāng)時(shí)只知平壤,別的什么地名也不知道。
我們晝伏夜行,走了七八個(gè)通宵,才到了第三十八軍的休整駐地——君子里一帶。全軍駐得很分散而且隱秘。我們3000多名戰(zhàn)士無聲無息的瞬間就各自分散到師團(tuán)營連去了,大家連告別的時(shí)間都沒有。我?guī)У倪B隊(duì)有一部分到了軍后勤部警衛(wèi)連(因?yàn)樵凇皾h江南岸阻擊戰(zhàn)”中,連警衛(wèi)連都補(bǔ)充到第一線去作戰(zhàn),而且傷亡很大,可見戰(zhàn)役多么慘烈),我仍任政治指導(dǎo)員。其余戰(zhàn)友們不知分到何處,戰(zhàn)地間是不能隨意來往的,當(dāng)然更沒有通信可能。大家都懷著掛念的情懷度過著緊張?bào)@險(xiǎn)的戰(zhàn)爭(zhēng)日月。
志愿軍部隊(duì)經(jīng)常輪回調(diào)換回國。我所在的第三十八軍也不例外。朝鮮停戰(zhàn)后,志愿軍陸續(xù)都回到東北各地。我是1954轉(zhuǎn)業(yè)到廣西文化局的。
大約1965年吧,有一位軍人輾轉(zhuǎn)找到我家。見了面先嚴(yán)正地向我敬軍禮,自我報(bào)告說“指導(dǎo)員,我是二排五班戰(zhàn)士覃某某。”我想了很久才記起來。他說回國后被送進(jìn)軍事院校學(xué)習(xí)。畢業(yè)后分配到新疆邊防軍,現(xiàn)回家探親,路過南寧特來看望領(lǐng)導(dǎo)。我笑說,你現(xiàn)在成了我的領(lǐng)導(dǎo)了吧?他靦腆地說:剛提了副師級(jí)。哇!你在朝鮮一定立了大戰(zhàn)功是吧!他點(diǎn)了點(diǎn)頭。遺憾的是幾十年后,現(xiàn)在我竟忘了他的名字。又隔了幾年。有次我去大苗山香粉鄉(xiāng)寫劇本體驗(yàn)生活,竟在一個(gè)山寨無意中見到了當(dāng)時(shí)的連代理文化教員林玉,他正忙農(nóng)活,他告訴我他所在的團(tuán)的一些戰(zhàn)士情況,誰犧牲了,誰負(fù)傷了,誰轉(zhuǎn)業(yè),誰復(fù)員。可惜,現(xiàn)在與當(dāng)時(shí)又很久遠(yuǎn),名字都記不起來了。只記得他在東北時(shí)找了位農(nóng)村姑娘結(jié)婚,比他高半個(gè)頭,回家鄉(xiāng)跟他一起干活,那次我也見到了他愛人,已會(huì)說當(dāng)?shù)赝猎捔四亍N业耐ㄓ崋T小程回南寧當(dāng)了貨車司機(jī),無意中在南寧解放路碰見的,還是他先喊我,長得又高又大,我哪里認(rèn)得出來?還有我們連的三排長韋宗輝。是融水人吧?打過游擊。后來不知怎么轉(zhuǎn)到了昆明鋼鐵廠工作,曾通過兩封信,“文革”時(shí)斷了聯(lián)系。聽說還有戰(zhàn)士提拔為干部。留在第三十八軍了。也有一些分配回廣西的縣人民武裝部工作。我們連的戰(zhàn)士至少有一半以上比我年長,即使比我小的,現(xiàn)在都是耄耋之年。健在的同志,我很渴望再見見面或通信聯(lián)系。
總之,這一批廣西首赴抗美援朝的戰(zhàn)士。到底有多少犧牲負(fù)傷,有多少留在部隊(duì),又有多少回廣西轉(zhuǎn)業(yè)和復(fù)員,我無法精確了解。但可以肯定的說,這3000多廣西子弟都是好樣的,為保家衛(wèi)國和祖國建設(shè)做出了貢獻(xiàn),為廣西人民爭(zhēng)了光爭(zhēng)了氣,是我們的驕傲。特別是那些為國犧牲的同志,永遠(yuǎn)值得我們敬仰懷念和紀(jì)念。也許他們的英靈有的留在了朝鮮的土地上,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相信有關(guān)部門會(huì)調(diào)查了解清楚,為他們立上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