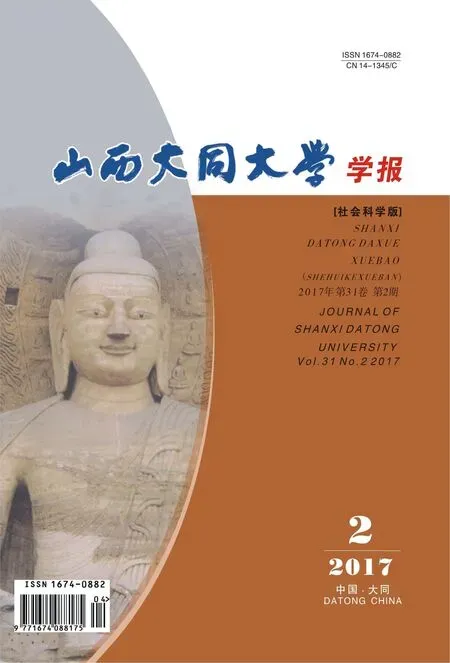“紅色的五月”與瞿秋白的“革命”敘事
梁化奎
(徐州工程學(xué)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江蘇 徐州 221111)
“紅色的五月”與瞿秋白的“革命”敘事
梁化奎
(徐州工程學(xué)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江蘇 徐州 221111)
在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成長發(fā)展史上,由“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卅”構(gòu)成的系列紀(jì)念活動,大革命時期即被冠之以稱為“紅色的五月”。瞿秋白此間寫作的系列紀(jì)念文本通過對紀(jì)念日所指稱的歷史事件的重新解讀,建構(gòu)起一套“革命”敘事話語體系。這一敘事話語體系傳播了馬克思主義,起到整合思想、表達(dá)訴求、展示力量、呼應(yīng)指導(dǎo)實踐之亟需的重要作用,彰顯出瞿秋白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萌芽。
“紅色的五月”;瞿秋白;紀(jì)念文本;“革命”敘事
在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成長發(fā)展史上,由“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卅”構(gòu)成的系列紀(jì)念活動,大革命時期即被稱為“紅色的五月”。此間,中共早期領(lǐng)導(dǎo)群體中的個體,如陳獨(dú)秀、李大釗、瞿秋白等,紛紛借此發(fā)表紀(jì)念文章,以為宣傳鼓動。認(rèn)真研讀這些紀(jì)念文本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顯著特征是其皆提取了“革命”一詞,以此作為分析言說的路徑,在初步習(xí)得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dǎo)下,通過對紀(jì)念日所指稱的歷史事件的重新解讀,建構(gòu)起一套“革命”敘事話語體系。瞿秋白此間寫作的系列紀(jì)念文本即典型體現(xiàn)了這一征象特點(diǎn)。
一、“紅色的五月”與瞿秋白的“革命”情結(jié)
歷史地看,自辛亥革命以降,“革命”一詞就已是國內(nèi)多家黨派集體想象中的一個魅詞。以國民黨、共產(chǎn)黨和青年黨為例,20世紀(jì)20年代,三家在革命目標(biāo)和對象的設(shè)定上雖不盡相同,但皆以“革命黨”自居,以“革命”相呼號。[1](P67)所以,大革命時期“革命”話語體系在中共黨內(nèi)的建立,也自有其來自和基礎(chǔ)。
在中共早期紀(jì)念活動史上,黨明確提出于五月各紀(jì)念日開展紀(jì)念與宣傳活動,始于1924年。這年4月19日,陳獨(dú)秀和毛澤東聯(lián)名簽署的中共中央第13號“通告”中,提出“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jì)念日各地“都須有相當(dāng)?shù)幕顒优c宣傳”,[2](P29)并對每個紀(jì)念日如何開展紀(jì)念與宣傳活動提出具體要求。1926年4月五卅運(yùn)動周年紀(jì)念前夕,中共中央就五月各紀(jì)念日之宣傳工作再次下發(fā)“通告”,指出在“紅色的五月”里,“沒有一個紀(jì)念日不值得我們作廣大的宣傳,警醒民眾,檢閱自己的力量,向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示威”。“通告”還為各紀(jì)念日圈定了宣傳主題和口號,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堅持“前松后緊”,“集中力量于‘五卅’的宣傳”的宣傳策略。[2](P100-102)大革命時期黨在宣傳資源相當(dāng)匱乏的情形下,突出強(qiáng)調(diào)要做好五月各紀(jì)念日之宣傳工作,顯示出黨對借助這些紀(jì)念活動擴(kuò)大宣傳影響的高度重視。
瞿秋白的“革命”情結(jié),發(fā)軔于“五四”前后,形成于赴俄考察期間(1921-1922年)。1923年初瞿秋白從蘇俄回到國內(nèi),其“革命”情結(jié)在呼號、禮贊中得到爆發(fā)釋放。這在其發(fā)表于同年6月《新青年》季刊創(chuàng)刊號上的《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chǎn)國際》《〈新青年〉之新宣言》兩文中有著極為鮮明的反映和體現(xiàn)。前文借助恩格斯對“革命”的經(jīng)典論述為“革命”定義說:“革命是天下最有權(quán)威的事,是歷史的大事,簡而言之,就是一部分的平民以刀劍或槍炮強(qiáng)制別一部分的人服從其意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概念如此。”文中強(qiáng)調(diào)指出:“并不是無產(chǎn)階級格外的喜歡革命,格外的喜歡‘殺人流血’,格外的歡喜‘強(qiáng)力’,而是為資產(chǎn)階級固執(zhí)的強(qiáng)力的手段所逼迫,不得不如此。”后文則直白表示說,“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機(jī)關(guān)”作為“中國社會思想的先進(jìn)代表”、“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羅針”,應(yīng)有堅定的“革命性”,“突現(xiàn)極鮮明的革命色彩”。[3]大革命時期,瞿秋白為“紅色的五月”寫作的系列紀(jì)念文本,不但貫穿了這一“革命”理念,并由此建構(gòu)起一套“革命”敘事話語體系。
二、瞿秋白的“五一”“五卅”革命敘事
瞿秋白“五一”紀(jì)念文本中的“革命”敘事,集中體現(xiàn)在大革命前后其發(fā)表的《五一節(jié)之四十年》《五一紀(jì)念與國際勞動運(yùn)動》《五一紀(jì)念與共產(chǎn)國際》三個文本之中。在《五一節(jié)之四十年》一文中,瞿秋白指出,“歐戰(zhàn)”前工人階級通過“五一”運(yùn)動雖然增進(jìn)了團(tuán)結(jié),提高了組織力和戰(zhàn)斗力,但其并非“就是世界革命”,亦非是對資產(chǎn)階級的“正式宣戰(zhàn)(革命)”。“歐戰(zhàn)”之后,以“革命”為職志的第三國際把工人運(yùn)動引向世界革命,指出要爭得八小時工作制“非革命不能達(dá)到”,非無產(chǎn)階級組織“革命的政黨”不能實現(xiàn)。[4]
在另外兩個“五一”紀(jì)念文本中,瞿秋白揭露了流播于第二國際中的“改良主義”主張,闡揚(yáng)了五一紀(jì)念的“真精神”。他指出:“五一”是國際無產(chǎn)階級進(jìn)行“階級斗爭的象征”。改良派認(rèn)為可以“不必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去爭得八小時制,表明其已拋棄“五一”紀(jì)念的“革命精神”,即“階級斗爭的精神”與“無產(chǎn)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當(dāng)前的任務(wù)就是要建立統(tǒng)一的職工國際,“如此方能實現(xiàn)五一紀(jì)念的真正的國際意義”。[5]瞿秋白還深入揭露指出,“歐戰(zhàn)”前各國社會黨即不肯在實際上推進(jìn)革命運(yùn)動,“只想用和平方法,懇求資本家實行八小時制”;“歐戰(zhàn)”爆發(fā)后又提出“工人應(yīng)當(dāng)保衛(wèi)祖國”的錯誤口號,從而宣告了第二國際的破產(chǎn)。與此相反,共產(chǎn)國際里的各國共產(chǎn)黨“都認(rèn)定革命的方法”,“都指示出革命的道路”,“所以五一國際紀(jì)念的精神,只有共產(chǎn)國際能代表”。[6]
“五卅”運(yùn)動是表征大革命進(jìn)入高潮的標(biāo)志性事件。瞿秋白為此寫作的紀(jì)念文本主要有:《五卅周年大示威之上海問題》《五卅周年中的中國政局》《五卅二周年紀(jì)念與國民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等。在《五卅周年大示威之上海問題》一文中,瞿秋白指出,值此“五卅”周年紀(jì)念之日,必須“認(rèn)清革命的方法”,“提出徹底的革命要求”。[7]在《五卅周年中的中國政局》一文中,瞿秋白指出,要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獨(dú)立和人民的解放,“便須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反赤統(tǒng)治”,“決然以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國主義的代理政權(quán)”,包括“武裝一般的革命民眾”,從抗稅抗貨的運(yùn)動,一直到武裝暴動和革命戰(zhàn)爭”。[8]
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國民革命后,作為對危局的一種回應(yīng),瞿秋白發(fā)表了《五卅二周年紀(jì)念與國民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一文,揭露了國民黨新軍閥的屠殺政策。他指出: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軍閥已經(jīng)“變成中國的白黨了”。對于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在革命中的表現(xiàn),瞿秋白指出,在反帝運(yùn)動初期民族資產(chǎn)階級尚能留在聯(lián)合戰(zhàn)線內(nèi);當(dāng)民眾要求實行革命戰(zhàn)爭之時,他們用軍事獨(dú)裁的方法來搶奪革命領(lǐng)導(dǎo)權(quán);當(dāng)無產(chǎn)階級領(lǐng)導(dǎo)民眾要求解決勞動和土地問題,他們即公開破壞聯(lián)合戰(zhàn)線“而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關(guān)于小資產(chǎn)階級,瞿秋白分析指出,他們客觀上要求革命,但其在聯(lián)合戰(zhàn)線內(nèi)“必須和無產(chǎn)階級、農(nóng)民建立革命的聯(lián)盟,方才能夠保障自己的利益和解放”。瞿秋白還指出,在以“貧農(nóng)為中樞”的國民革命的第三階段,土地問題將“成為反帝國主義斗爭的根本問題”,“必須用猛烈的攻擊”摧毀買辦封建制度,“例如逮捕豪紳,使之游街示眾,罰款罰米等等,其實都是封建制度摧毀的風(fēng)暴時期所不能免的。”[9]
三、瞿秋白的“五四”“五七”革命敘事
關(guān)于“五四”紀(jì)念,1924年4月,中共中央在第13號“通告”中最早提出過三點(diǎn)要求。即“以學(xué)生為中心”;闡明五四運(yùn)動在“恢復(fù)國權(quán)運(yùn)動”與“新文化運(yùn)動”上的意義;說明“五四運(yùn)動之精神仍有發(fā)揮之必要”。[2](P30)1926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關(guān)于五月各紀(jì)念日之宣傳工作的“通告”,再次強(qiáng)調(diào)了上述宣傳工作精神要求。指出:“‘五四’是中國民眾第一次自覺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紀(jì)念日,領(lǐng)導(dǎo)這個運(yùn)動的是青年學(xué)生。這天的宣傳,應(yīng)以學(xué)生為中心,在這革命潮流低落、學(xué)生群眾亦隨之分化的時期,我們應(yīng)提出學(xué)生會統(tǒng)一和回復(fù)‘五四’精神的口號。”[2](P101)
依照上述要求,瞿秋白發(fā)表了《自民族主義至國際主義》《五四紀(jì)念與民族革命運(yùn)動》等紀(jì)念文本。從敘事模式和內(nèi)容看,瞿秋白堅持了他慣用的“革命”敘事模式,并且深化了中央對五四運(yùn)動意義與“五四”精神的認(rèn)識。這是其“五四”紀(jì)念文本的不同凡響之處。他在《自民族主義至國際主義》一文中指出,五四運(yùn)動不同于以往反抗運(yùn)動的地方有兩個點(diǎn):一是它反映出當(dāng)時社會上兩種強(qiáng)烈要求的合二為一,即“平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本能感覺”與“第三階級進(jìn)步的民主要求”;二是它“傾向于接近民眾”,使用了“耶各賓式的革命手段”。即學(xué)生“不以上書運(yùn)動自限”,“第一次發(fā)露要求民權(quán)的革命方式”,“確有幾分革命的獨(dú)裁制的意義”。瞿秋白還力求把五四運(yùn)動納入到“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運(yùn)動”的范疇來加以論述。他指出:“五四運(yùn)動的發(fā)展,摧殘一切舊宗法的禮教,急轉(zhuǎn)直下,以至于社會主義,自然決不限于民族主義了。”所以,“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運(yùn)動,不但對于中國工人是當(dāng)然的同盟軍,就是對于全中國都是民族解放唯一的最好的友軍。”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根本上是國際主義。”[10]這樣,五四運(yùn)動在瞿秋白的筆下便實現(xiàn)了其與“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運(yùn)動”對接,并通過這種對接凸顯出五四運(yùn)動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的劃時代意義。
針對當(dāng)時具有代表性兩種“五四”觀,即認(rèn)為它“只是一個學(xué)生運(yùn)動”,或是將其簡單地看做是新文化運(yùn)動“思想革命”的高潮期,瞿秋白在《五四紀(jì)念與民族革命運(yùn)動》一文中指出:“單認(rèn)五四是學(xué)生愛國運(yùn)動及思想革命的紀(jì)念,未免減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義。”在瞿秋白看來,與脫離群眾的辛亥革命相比,五四運(yùn)動是“第一次”、“帶著群眾性質(zhì)”的民族革命運(yùn)動,因此,“切不可只看見學(xué)生,學(xué)生不過是運(yùn)動的先鋒”。[11]
瞿秋白闡述指出,辛亥革命既不敢反抗列強(qiáng),又沒有群眾的參與;五四運(yùn)動則以直接的革命行動襲擊軍閥和政客,提出廢除“二十一條”,這便打破了義和團(tuán)失敗后“‘尊洋主義’的天經(jīng)地義”,“這是五四在中國民族運(yùn)動史上最值得紀(jì)念的一點(diǎn)”。再者,辛亥革命領(lǐng)導(dǎo)層中有人先是“力主妥協(xié)緩進(jìn)”,后又迷戀“法律手續(xù),和平解決”,“民權(quán)主義只用以爭一個臨時約法”;五四運(yùn)動卻“直接以革命手段行使平民的政權(quán)”。尤其在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之后,“從此發(fā)現(xiàn)真正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以及工會的組織”。針對五四運(yùn)動存在“偏于排日”的問題,瞿秋白指出,現(xiàn)在一般平民已經(jīng)覺悟到:“不是對付某一帝國主義的強(qiáng)國,而是對付一切帝國主義的列強(qiáng)”。更重要的,中國無產(chǎn)階級“已經(jīng)自覺的來參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這革命中之領(lǐng)袖階級”。在南方,中國農(nóng)民“已經(jīng)開始做有組織的斗爭,而且贊助民族革命”。工農(nóng)群眾要“創(chuàng)造革命的平民共和國”,“真正平民的獨(dú)立的中華共和國”。中國民族革命“如今有了這工人階級及農(nóng)民的參加,當(dāng)然和五四運(yùn)動那年大不同了”。不但如此,瞿秋白還提醒人們說,五四運(yùn)動爆發(fā)時,中國人民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的”聽到俄國無產(chǎn)階級要聯(lián)合東方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列強(qiáng)的呼聲了,所以,五四運(yùn)動“在世界史上實在是分劃中國之政治經(jīng)濟(jì)思想等為前后兩時期的運(yùn)動”。[11]瞿秋白基于此重新定位五四運(yùn)動說,它是繼辛亥革命之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11]這個新提法在當(dāng)時還是很有睿見和思想深度的。對于蓬勃發(fā)展中的大革命運(yùn)動同時具有重要現(xiàn)實指導(dǎo)意義。
“五七”是為聲討袁世凱同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勿忘國恥而發(fā)起的紀(jì)念活動。大革命時期瞿秋白為此曾撰寫了《五七國恥與日本帝國主義》一文。文中瞿秋白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蠶食侵略,指出日本作為亞洲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以軍閥主義為后盾”發(fā)展起來的。針對以往以“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為主要斗爭形式的“五七”紀(jì)念活動,瞿秋白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但憑借著實力及其在中國攫取的各種特權(quán)在“得步進(jìn)步的侵略中國”,還在“利用中國的軍閥政客”,“造成中國國內(nèi)的某種政治勢力,時時擾亂中國,挑撥內(nèi)戰(zhàn),而且力能指揮中國的官廳警察,隨時隨地?fù)錅缗湃者\(yùn)動”。因此單純的經(jīng)濟(jì)抵制不能戰(zhàn)勝日本,“和平的消極的排貨運(yùn)動,只問外交不問內(nèi)政的愛國運(yùn)動,是絕無效果的”;“中國要根本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必須實行國民革命,打倒他們利用的一切政客及軍閥。”[12]顯而易見,這些言論帶有極強(qiáng)的政治動員意味。
四、瞿秋白的“五五”革命敘事
關(guān)于“五五”紀(jì)念,1926年4月,中共中央在其下發(fā)的“通告”中提出,在“五五”馬克思誕辰紀(jì)念日,應(yīng)著力說明和回答三個問題。即:“須借此機(jī)會說明馬克思主義是否能解決中國問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運(yùn)動的關(guān)系,并答復(fù)各方面對于馬克思主義之曲解和誤會。”[2](P101)同年5月,瞿秋白發(fā)表了《中國之革命的五月與馬克思主義》一文,該文實際上是對中央提出的三個問題的一種回應(yīng)。瞿秋白說:“中國的五月有許多革命運(yùn)動的紀(jì)念日”,這使五月因此成了“革命的五月”;“中國革命運(yùn)動紀(jì)念日的歷史上的意義,處處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經(jīng)濟(jì)、哲學(xué)及政治學(xué)說,證明馬克思主義正在指導(dǎo)著中國革命行向勝利的道路。”帝國主義在中國最怕的“是中國的革命的無產(chǎn)階級斗爭和他所領(lǐng)導(dǎo)的國民革命運(yùn)動”。這是因為,“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不但能分析出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并且能運(yùn)用這些客觀的規(guī)律和力量,發(fā)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國運(yùn)動。”[13]
瞿秋白深入論述指出,蓬勃發(fā)展的中國革命已經(jīng)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確能夠解釋中國革命發(fā)展的形勢,并指示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斗爭領(lǐng)導(dǎo)著一般民眾的民族解放運(yùn)動,加入世界無產(chǎn)階級國際革命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但中國無產(chǎn)階級的最終解放,必然要實行世界社會革命,就是中國民族的國民革命,都必須聯(lián)合國際無產(chǎn)階級,然后才能得到最后的勝利。”[13]這樣,瞿秋白不但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聯(lián)系在了一起,并表明它是已為實踐證明能夠指導(dǎo)中國革命的客觀真理。
綜上所述,在“紅色的五月”里,瞿秋白將中國革命同世界革命聯(lián)系在一起,其“革命”敘事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并起到了整合思想、表達(dá)訴求、展示力量、呼應(yīng)指導(dǎo)實踐之亟需等重要作用,彰顯出其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萌芽。
[1]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M].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0.
[2]共青團(tuán)中央青運(yùn)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青年運(yùn)動文件選編[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
[3]瞿秋白.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chǎn)國際[J].新青年(季刊),1923(01).
[4]瞿秋白.五一節(jié)之四十年[N].民國日報(上海),1924-05-01.
[5]雙 林.五一紀(jì)念與國際勞動運(yùn)動[J].向?qū)?1925(112).
[6]秋 白.五一紀(jì)念與共產(chǎn)國際[J].中國工人,1925(5).
[7]秋 白.五卅周年大示威之上海問題[J].向?qū)?1926(154).
[8]秋 白.五卅周年中的中國政局[J].向?qū)?1926(155).
[9]秋 白.五卅二周年紀(jì)念與國民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J].向?qū)?1927(196).
[10]瞿秋白.自民族主義至國際主義[J].上海大學(xué)周刊,1924(01).
[11]雙 林.五四紀(jì)念與民族革命運(yùn)動[J].向?qū)?1925(113).
[12]雙 林.五七國恥與日本帝國主義[J].向?qū)?1925(114).
[13]秋 白.中國之革命的五月與馬克思主義[J].向?qū)?1926(151).
“Red May”and Qu Qiubai’s“Revolution”Narrative
LIANG Hua-kui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Xuzhou Jiangsu,221111)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re were a series of memorable activities such as“May Day”,“May 4th”,“May 5th”,“May 7th”,“May 30th”.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was known as“Red May”.Qu Qiubai’s series of memorable texts reinterpreted the historical events on the related anniversaries,which constructed a set of consistent“revolution”narrative systems.These narrative systems spread the Marxism-Leninism and played a role in integrating thoughts,expressing the demands,showing strength and appealing to practice demands,which demonstrated the bu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Red May”;Qu Qiubai;memorable texts;“revolution”narrative
K262
A
〔責(zé)任編輯 馬志強(qiáng)〕
1674-0882(2017)02-0053-04
2016-12-1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專項任務(wù)資助項目“紅色文化資源育人功能研究”(15JD710053)
梁化奎(1965-),男,江蘇銅山人,碩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共黨史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