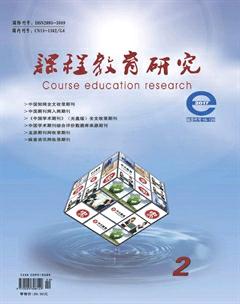還鄉
張志強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7)02-0083-01
東漢永平十年,佛教傳入中國,和強調倫常的儒家不同,佛教講無常。對無常的感受,導致文人的自覺,文人的自覺表現在他們的創作不再僅關注生活,而是有了對生命本身的關照。《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當一個文人攬鏡自照,發現“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而自憐和自戀之時,便有了對生命本身的凝視。而到了魏晉六朝三百多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動亂,文人士大夫朝不保夕、難以自處的人生境遇,更是加深了他們對人生無常、生命短暫的感受。那么,在無常的人生,短暫的生命中,人該怎樣自處,該怎樣處理精神和肉體的關系,便成了每個人必須追問的一個哲學問題。
中國文學史上,陶淵明是最早的將文學和哲學結合,在作品中集中進行哲學思考、體現出思想性的詩人。他的《形影神贈答詩》便是對這一哲學問題的嘗試性追問,而《雜詩》中“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的及時作樂的消極即是他對這一問題的嘗試性回答。但直到《歸去來兮辭》,陶淵明才終于對精神和肉體的關系,對在無常的生命中何以自處有了一個終極性的回答。
公元405年,因“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的貧困和無奈,“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向了官場,在離家百里的彭澤縣當了縣令。但在官僅八十余日,便因“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而毅然決然地踏上了還鄉之路,留下了這篇精神獨白——《歸去來兮辭》。
詩人一開篇便開始自責自己“心為形役”。并在自責中開始反省:“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這是中國文人精神史上關于獨立人格的最深遠的一次追問和反省。陶淵明對“心為形役”的深切體察和對“今是昨非”的明確判斷,直接提出了在封建一元專制體制下,在普遍奴化的現實中怎樣保持自我獨立人格不缺失的問題,提出了作為一個想保持精神獨立的文人該“怎樣活”的命題。正是帶著這一問題,陶淵明踏上了自己的還鄉之路,并在還鄉之旅中打開了自己的心靈,揭開了精神的蒙蔽,獲得了發現美的機遇,展開了對美的全面感受,感受到了被忽視的天地大美,感受到了生命的大愉悅、大歡暢。但是,不進入臨界狀態,我們也就無法看清存在的真實處境,也就無法發現“在”的本質。陶淵明在感受到生命的愉悅歡暢的同時,也認識到了“在”的本質,因此樂極生悲,不由發出了生命短暫,“吾生之行休”的感嘆。
但可貴的是陶淵明在感嘆生命的短暫和好景的難常的同時時,呈現出“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的曠達,并接下來發出了自己的人生宣言:“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陶淵明正是在對富貴和生死的超越中徹底擺脫了外在之物對自己生命的羈絆,也揭開了蒙蔽心靈紗,讓自我完全呈現在大地敞亮的澄明之境,從而維護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完成了自我的救贖,讓自己的生命在“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天天命復奚疑!”的樂天安命中與天地同化。從而成了蒼穹之下,大地之上,沐浴著神的光芒而詩意地棲居的一個詩人。
斯賓諾莎在《倫理學》第五部分命題第42中說:“懵懂無知的人不僅由于外界的各種因素而焦躁不安,以致永不得享受心靈的寧靜;他還對神和萬物懵懂無知,若不痛苦,便無法生活,真正不痛苦時,也就不存在了。有智慧的人,在他被認為有智慧的范圍內,心神泰然,還由于意識到神、萬物和自我,因具有某種永遠的必然性而時刻存在,由此得以安享心靈的寧靜。”
陶淵明正是在摒棄了外在之物對自己的羈絆之后,讓本來懵懂無知的自我完全呈現出來,并和自然之美完全契合,達到天人合一的化境,而心神泰然,享受到了心靈的寧靜。
海德格爾說:“接近故鄉就是接近萬樂之源(接近極樂)。故鄉最玄奧、最美麗之處恰恰在于這種對本源的接近,決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鄉才可親近本源……那些被迫舍棄與本源的接近而離開故鄉的人,總是感到那么惆悵和悔恨。既然故鄉的本質在于他接近極樂,那么,還鄉又意味著什么呢?還鄉就是返回與本源的親近。但是,唯有這樣的人方可還鄉,他早已而且許久以來一直在他鄉流浪,備嘗漫游的艱辛,現在又歸根反本。因為他在異鄉異地已經領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還鄉時得以有足夠豐富的閱歷……詩人的天職是還鄉,還鄉使故土成為親近本源之處。”
因此,陶淵明的這次還鄉行動,不僅是從官場回到了家、由世俗逃亡到山林,而是從物質的此岸泅渡到了精神的彼岸,從“心為形役”的奴化狀態進入了“無所待”的逍遙游狀態,從自我被外在之物蒙蔽的懵懂走向了大地敞亮的澄明之境,從世俗的焦慮回歸到生命的本源,接近了極樂。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陶淵明為士大夫精神潰敗提供了一道防線,也為他們的自我回歸提供了一條道路。所以,陶淵明不只是中國士大夫精神的一個歸宿,更應該是焦慮的現代人最后的一個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