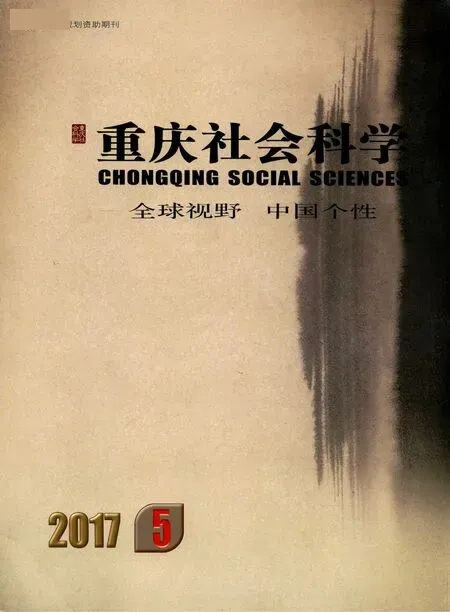空間結構、時間敘事與鄉村生活變遷
房靜靜 袁同凱
空間結構、時間敘事與鄉村生活變遷
房靜靜 袁同凱
空間與時間作為民眾生活的基礎,記錄、規約、承載、驅動著人的活動。以古村落的空間演變為例,從不同的空間格局中去描述時間敘事在空間中的排列。一方面意在確定空間結構要素對行為產生影響而發生改變;另一方面試圖表明在不同的空間演變狀況下,時間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構想。“時間焦慮”、“時間慌”、“鄉村記憶”、“鄉愁情結”并不僅僅是因為社會的快速變革所引起的文化恐慌,而是面臨社會轉型所引起的群體心理失衡。
新型城鎮化 社會變革 社會治理創新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天津 300350
20世紀80年代,空間與時間被納入社會分析的中心。關于空間的研究理路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空間與社會關系、空間與社會結構、空間與社會意義。社會結構與社會意義在“空間”中互動,確立了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并使之具體化。由此,空間性將社會生活置于一個活躍的競技場中。然而,時間是多維的,這種多維的深刻性在于勾連各種觀念或文化的時間共存在同一時空場合中,從而造成了現實表達與呈現的復雜化。“空間”與“時間”的關系問題驟然“升溫”,并成為構建和評判社會的重要維度。如在現象學中,“空間性”與“時間性”的概念意指空間與時間對主體來說何以成為空間或時間。我國傳統社會的基礎是鄉土社會,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村莊的自然空間有著明確的邊界及較強的封閉性和排他性,多以農為生,聚族而居,在這一空間中生活的人們的時間建構多與主體日常生活體驗不可分離。當時代的變遷在不經意間將傳統社會鏈條打斷時,社會就會發生深刻的空間轉換,改變的政治—經濟實踐和文化實踐決定了時空領域內人們社會互動模式的性質。因此,我們在了解社會如何建構其空間時,實際上也在了解其如何建構其時間觀。
一、空間結構與時間:理論譜系
(一)關于“空間結構”的理論闡釋
空間要素在古典社會學家的分析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分析中,土地作為一種具體的空間形態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工具和結果,并且憑借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開拓了世界市場,讓整個世界卷入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中。[1]涂爾干則認為:“圖騰崇拜和宗教儀式中的空間安排折射出主導性的社會組織模式。”[2]這種關于空間實質是“物質”的觀點,深刻影響了后來學者對空間結構的分析。如現代社會學中,戈夫曼使用“前臺”、“后臺”、“局外區域”等一系列概念,來探討空間區域的制度化特征,并開啟了研究行動者與社會結構互動關系的先河。[3]關于行動者與社會結構互動關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布迪厄的 “場域—慣習”理論、吉登斯的“時空壓縮理論”、愛德華·索賈的 “社會空間辯證理論”。布迪厄的“場域—慣習”理論,將整個世界劃分為無數的小世界,每一個小世界即場域中均有自己獨特的實踐邏輯,場域中的社會成員秉持著與之相適應的慣習。[4]吉登斯在解讀結構以及結構和行動之間的辯證關系時,實現了對時間與空間的社會學融入,并把時間和空間放在社會結構的終極性要素的位置上。[5]而愛德華·索賈的“社會空間辯證理論”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人們創造和改變著社會空間,二是他們也被自己所生活和工作的空間以不同的方式所支配。但是空間結構不僅僅是社會行動表現自身的競技場,且是帶有各種目的或所謂的“計劃”的目的性存在。
在此基礎上,這里將空間結構劃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以“再生產”為目的的空間結構,以列斐伏爾為代表。他認為:“社會生產關系僅就其在空間中存在而言才具有社會存在;社會生產關系在生產空間的同時將自身投射到空間中,將自身銘刻進空間。否則,社會生產關系就仍然停留在‘純粹的’抽象中,也就是在表象和意識形態中。”[6]索賈則提出:“空間是由社會生產的,而且如同社會本身一樣,既以各種具有實質性內容的形式存在,也以個體與群體兩者之間的一套關系,即社會生活本身的一種具體化與媒質而存在。”[7]因此,空間結構和空間關系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物質形式,整個社會生產出了一個空間,在空間中,生產關系的維持變得具有決定性,而技術和生產力則達到了令人難以理解的水平。空間性、社會再生產、生產關系的相互關聯成為“空間結構”建構的核心。
二是以秩序、紀律等權力分配為目的的空間結構,以福柯為代表。他認為:“一種完整的歷史,需要描述諸種空間,因為各種空間同時又是各種權力的歷史。”福柯從空間中發現了權力與知識的關系,提出了一種關于“權力運作基礎的空間”,即“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8]。他在緊抱歷史的同時,給歷史增添了關鍵性的聯結,即空間、權力和知識之間的聯系,由此,它們一起構成了空間結構的具體方面。
三是從個體角度討論空間結構,以梅洛·龐蒂和海德格爾的思想為哲學基礎的戰后現象學場所論,針對工業化和都市化所造成的空間異化進行了批判,它所關注的是日常生活空間形式的一部分。在現象學派的視野里,現代主義空間觀把空間當作社會變革的手段,而人被當成被動的存在者。如梅洛·龐蒂構想了一個關于身體、世界、知覺、時間、空間的相當復雜的協同構造進程,即“身體圖型”,并將其解釋為一種管理、協調和支配身體與空間交互構造的運作機制。[9]這可看作一種對空間異化的回應,但他采用“隱喻的身體”來探索日益復雜和分化的世界。
總之,空間結構既產生于空間的再生產,同時又是權力、知識、日常實踐活動等諸種結合體的具體表達,且是具有交互作用的各種因素和影響的一種歷史整體,即“有組織的空間結構,并不是一種獨立結構,有其自身自主的構建和轉型法則,它表征了各種一般生產關系的一種業已得到辯證解釋的成分”[10]。
(二)關于“時間”的理論闡釋
直到20世紀70年代,社會學文獻中仍然缺少對時間的關注,原因就在于社會學所強調的是秩序、穩定和狀態問題,而忽視了沖突、變遷和過程的問題。關于“時間”的研究可歸納為三個方面:時間內涵、時間意義、時間分類。
一是時間內涵。古典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最先強調“時間”是一種集體現象,并把它看作集體意識的產物,是集體表征的主題。[11]而埃利亞斯將“時間”定義為表示某種關系的符號,由人群,亦即一群具有記憶和綜合的現成生物性能力的生物,在兩個或數個事件過程之間所成立的關系,而其中一個過程則標準化成另一個事件過程的參考框架或基準。[12]休伯特則把“時間”界定為一種象征結構,這種結構通過時間的節奏來再現社會組織。[13]可見,對時間概念的表達無論是持續時間,還是對時間的標記,都是關于社會活動或者集體的成就。在此基礎上,現代社會學轉向從社會意義上對時間進行劃分,并在反思中提出了諸如 “社會時間”、“時間觀”等相關意涵。
二是時間意義。愛德華·索賈指出:“個體能理解自己的經驗,而且只有通過對自己所處歷史時期的定位來判定自己的命運,即只有通過對自己環境中所有其他個體的認識,他才能把握自己在人生中的各種機遇。”[14]劉易斯·科塞則提出時間研究旨趣在于:“當我們在社交聚會上講述過去的事情時,會把那些事件置于社會背景中。因為相關事件只有被置于社會時間而不是純粹的歷法時間之中才能獲得意義。”[15]其實,對時間意義的表達無法與社會活動發生的空間相分離,而將現象或事件放置于一種時間序列,對每一位理論家來說變得更具有意味和更能說明問題。然而,“時間意義”本身可能微不足道,各種時間在社會中的劃分則構成了一組刺激物,推動我們在時間中前行。
三是時間分類。古爾維奇將個體的、群體的和文化的層次當作社會結構理論的最普遍區分,并把這種區分作為社會時間類型學的出發點,由此區分了社會時間的三種形態:自我時間、互動時間和循環時間。[16]對社會時間多重性的劃分表明了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中諸要素之間的因果聯系。史坦利·柯恩則將時間分為“私人時間”和“社會時間”。如在前工業時代,幾乎所有工匠都自己經營生意,在他們自己家里,用自己的工具,根據自己的時間,可以選擇合適的時間完成自己的工作;工業化的到來,則造成了工作時間的剛性化。時間由松散而多變的模式開始轉向時間安排緊湊。[17]因此,時間開始變成有價值的東西,并獲得了一種商品的意向。時間的商品化意向則又進一步促使人們從“時間觀”方面來反思時間,如羅斯·科塞認為時間觀是一個社會中各種價值觀的整合部分,個體要根據與其共享價值觀的群體來確定現在和未來的行動方向。
概而言之,時間以社會學的建構將自己表征為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具體化存在,并被置于社會互動過程中,作為建構人社會意義的另一種形式和每一社會中制度和組織的組成部分。但我們從中獲得的啟示在于社會學的時間研究所強調的是社會事件、社會變遷、社會進程與時間的復雜動態關系,以及社會生活在時間的演進過程中,以什么樣的生產方式來表現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
(三)“空間”與“時間”的關系
通過對空間結構和時間的解讀可以發現,空間與時間在社會中一起運作,并與社會再生產的過程相關聯,然而任何過程都可以視為一種歷史性過程,都是在時間流中展開的社會呈現,即社會是由時間、空間和社會行動三個基本向度組成的復合體。涂爾干指出,“空間和時間都是社會構造”;在此基礎上,不同的社會產生性質不同的時空觀。而時空獨特的表現形式會引導時空實踐,時空實踐反過來又會維護社會秩序。[18]如在再生產意義的空間結構里,生產關系和生產時間變得具有決定性,并以生產時間體制的形式映射到空間形式和空間戰略中,成為資本積累的積極要素;而在權力分配的空間結構里,時間是以一種使人的行動和計劃的合理性成為可能的機制而發揮作用,并與社會制度的理性化相結合,成為植根于社會的一種同質的、連續的時空觀。當從個體意義上來理解時空觀時,我們意在通過個體對日常生活的重要時刻、微觀層面個體生命歷程的時間表達,來探討空間結構所傳達的社會、文化價值。總之,一個社會空間結構的分配,表明了不同的角色、行為的范圍和這個社會秩序下的權力路徑;而作出不同的社會行為和不同的關聯方式的時間和地點,則傳達了清晰的社會信息。可見,每個社會結構都根據自身的需要和社會再生產的目標,來建構關于時空的客觀概念,并根據那些概念來組織物質實踐。下面以山東雄崖所村為例,分析其空間結構與時間秩序的再造方式。
二、空間演變與時間敘事:以雄崖所古村落為例
空間是通過物來彰顯其自身的存在的,沒有物或物質,空間就無從具體化。以山東海防古村落雄崖所為出發點,源于其空間形態經過三次空間實踐,呈現三個層次的意象:一是“守御千戶所”,即明清軍事防御占支配地位時期的特色建筑和廟宇,二是歷史轉變層面的改造和建設的空間,三是古村落保護戰略空間。以古村落的空間演變為例,從不同的空間格局中去描述時間敘事在空間中的排列,意在確定空間結構要素對行為產生影響而使之發生改變。
(一)軍事防御空間與時間敘事
明代防衛海疆的主要措施是在沿海府州縣和沿海重要之地建衛、所,筑城堡、墩臺,守以重兵。“雄崖守御千戶所”的設立就是在這個大格局下應運而生的。城設四門,并于沿海一線設立椴村、王騫、王家山、公平山、望山、青山、米粟山、北漸山、陷牛山、朱皋、白馬島共11座烽火墩堡。[19]城門、烽火墩堡是具有特色的空間要素,其軍事特性貫穿并滲透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使得當時的社會生活有組織地進入支配與服從、中心與邊緣的多層結構中。據《即墨縣志》載:“雄崖守御千戶所設正千戶兩員,副千戶兩員,百戶五員,吏目一員。共有京操軍春戍250名、秋戍319名,守城軍51名,屯田軍77名。”[20]此時明朝對“衛所”采取的是“屯田制”和“軍戶世襲制”政策。仿照歷史上的屯田制,雄崖守御千戶所又于沿海分設八個軍屯,由屯田軍駐防;而屯田是朝廷分封給千戶和百戶的,由他們駐領,皆為世襲;屯田則分配給軍戶耕種。軍屯中的每位軍士授田五十畝,稱為一份。耕種臨近所城土地的軍戶,還兼有守城的職責,他們三分守城,七分種地。清雍正十二年,雄崖所裁并歸即墨縣,屯田歸公,原來的軍戶成了民戶,就地居住,分給土地耕種。[21]
土地作為空間的重要作用開始顯現,農業生產對土地的依附和農耕制度的年度周期制約使民戶的生存空間相對固定在一定區域。在特定的時空制度下,“衛所”職能逐漸轉變,使得聚落住民由先前基于軍事目的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步向普通的大眾化生產生活方式轉變,聚落內部也相應出現了更多世俗功能的建筑和設施。據記載,雄崖所城內外共有廟宇13座,其中,城內有關帝廟、天齊廟、觀音殿、城隍廟、三官廟、先農壇、九神廟。而這些廟宇以其獨特的象征意蘊,映射了空間中人們的時間感。如三官廟,殿內有天官、地官、水官。相傳,天官能賜福,地官能赦罪,水官能解厄。在天旱時,人們到三官廟求雨,三官因與百姓榮辱禍福密切相關,備受崇拜。先農壇則供奉著先農、司農、司薔,正月十一逢會,人們燃紙燒香,磕頭膜拜,祈求豐年。九神廟作用則在于每遇洪澇、旱災、病疫,人們前來祭祀,祈求消災祛難。[22]在調研過程中,據一位87歲的老人講,“這些廟宇在當年每逢農歷初一、十五早晨和晚間的鐘聲、鼓聲、誦經聲朗朗入耳,逢年過節燈火通明、香煙繚繞”。
楊慶堃指出:“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幾乎每個角落都有寺院、祠堂和拜神的地方,寺院、神壇散落于各處,舉目皆是,表明宗教在中國社會強大的、無所不在的影響力,他們代表了一個社會實在的象征。”[23]而筆者通過對軍事防御空間生成機制的串聯,發現在由“軍戶”沿革為“村民”的過程中,個體自我時間被嵌入在一種超驗的時間之中,人們在心理上更多地是依靠神靈來舒緩心中緊張。在與傳統農業生活的不斷磨合中,形成表達獨特地方化意義的生產時間、作息時間,“以農為本”、農事節律成為時間安排的軸心。
(二)改造建設空間與時間敘事
1960年,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明確指出:以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所有,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現階段農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這樣,絕大部分土地無償轉歸為生產大隊所有,由生產大隊統一使用,少量歸公社一級所有,生產小隊沒有土地。據《雄崖所建置沿革志》載,1956年4月,即墨、即東兩縣合并為即墨縣,雄崖所隸屬的區、鄉和人民公社名稱多變。1961年,雄崖所屬豐城人民公社,以城中十字大街的東西大街為界,劃分成南雄崖所和北雄崖所兩個行政村。[24]而原來明清時期遺留下來的13座廟宇也大多被拆除,城內廟宇或被改為生產大隊辦公室,或成為居民住宅。可見,空間本身也許是原始賜予的,但空間的組織和意義是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經驗的產物。而以“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為主題的空間構造賦予社會層面什么樣的時間觀呢?這里以案例進行呈現。
案例1:陸某,女,1944年生。當時(20世紀六七十年代)農忙時節,四五點鐘就走,一直干到中午12點回家。你家里有老人的,有公公婆婆在家給做熟飯,你可以吃現成的,還能休息一會兒。當時我1966年12月嫁過來的時候,公公剛于一個月前去世,家里也沒有婆婆,我得回來現做飯,還得照顧孩子。匆匆忙忙回來做熟吃完了,小隊一吹哨,麻溜就得走,去晚了要挨罰。
案例2:黃某,女,1942年生。我們這代人基本上都有三四個孩子,即便拖著好幾個孩子,為了不耽誤掙工分,也設法克服困難去出工。孩子剛會走那工夫,我就把他帶上,一天都不耽誤的。
在訪談中,他們反復念叨的主題就是:“那會隊長說了算,叫你去你不得不去”,“你要不去勞動就罰你,扣你工分”。此時,以“生產隊長”為影像的時間觀描繪了“先集體、后個人”的時間安排策略。然而,這種強有力的時間結構,是由當時政府確定并支配的時間體系所構建的,且空間結構在制度安排上配合了這種時間政治。因此,時間作為一種社會建構,被社會制度、社會習慣和人際互動所鞏固,并形成體制。
(三)生態保護空間與時間敘事
1978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土地開始包產到戶,改革開放號角吹響中國大地。1982年國家公布首批24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1986年,國務院公布第二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提到了保護“歷史村落”的概念。雄崖所古城被青島市人民政府命名為 “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命名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成為山東省僅有的兩處之一。而城內各種廟宇,如觀音殿、玉皇廟開始重修。伴隨現代化進程,曾經被視為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的民間信仰儀式也一度參與到國家活動中,調研中一份關于“雄崖所古城玉皇廟會”的宣傳單顯示其主辦單位為豐城鎮人民政府,承辦單位為雄崖所村民委員會。上邊標有:“玉皇帝賜福:吉祥如意;凡捐資貳千元以上者均贈玉皇廟開光金如意寶葫蘆壹尊。”同時,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鄉村工業漸趨滲入古村。據調查,村里現有項鏈廠、個人養豬場、海參養殖場等,農業勞動者變成了工人。在此過程中,這種由工業發展而導致的群體性時間較之以往發生很大改變,我們仍以相關案例為證。
案例3:韓某,女,1964年生。1986年結婚,1987年我生完第一個孩子后,在家里邊繡花(一種手工活)邊看孩子,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90年代,1994年左右,給別人養魚,別人給工錢,一年給千兒八百的;1997年生完第二個孩子后,就把孩子放在家里,去廠子干活了,主要是去當時的冷庫;干到2003年,孩子六歲的時候,孩子的姥姥說孩子自己待在家,萬一出點事咋辦,得好好照顧小孩。于是開始在家做手工零工,掛項鏈的勾子,一年賺3700~3800元,干了兩年。后來去城里陸續做保姆,在村里項鏈廠上班,現在在鎮上一家紡織品廠,每天早上6∶50走,晚上有時候加班到9點。
案例4:李某,男,1963年生,瓦匠。1985年在鄰村做工的時候認識了現在的媳婦,女方家不愿意,嫌我家窮。我倆去東北干了一年燒瓦,賺了2000多元,回來后給丈人家送去聘禮才結了婚。結婚后,一直干瓦匠,膠州、嶗山、即墨,足跡遍青島各地。時間主要集中在干活上,每天差不多賺200~300元。為兒子在即墨買了房子,娶妻生子。
在訪談中,韓某一直講,“要不是因為自己小女兒在上大學,我才不去干這份工呢,一點自己的時間都沒有。到村里廠子上班,雖然錢少一點,但是起碼中午和下午還有一個小時可以回家來,現在這個時間太趕了”。李某常說的是,“一天不干,少賺300元”。可見,時間在此已經獲得了一種商品的意象,并被感知為確定的時間間隔;而工業生產的時間結構急需時間的這種線性模式,于是人們開始尋求遭遇工業時間的同時,保持私人主觀時間的可能性。
大衛·哈維認為:“我們可以主張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概念必須通過物質實踐與過程創造出來,而這些實踐與過程再生產了社會生活,時間與空間不能脫離社會行為來理解。”[25]因此,我們對古村落的研究不應僅僅關注其空間演變的特征,還應致力于探究空間構造對不同類型時間的建構,即帶有不同目的的空間結構對時間的生產、管制和規訓。就社會背景來說,上述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歷史主體之間的互動構成了時間的意義。然而,國家是想象的共同體,空間結構與時間設置是最能體現人類本質特征的符號表述。我們可以透過時間敘事來理解社會的運作、國家的權力實踐以及意識形態的推廣;反過來,以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亦能很好地認識時間本身及其變遷。
三、古村落的社會時間變遷
就空間而言,雄崖所古村落經歷了由軍事防御為目的到以改造建設為主,最后重新實現“回歸鄉土記憶”的空間實踐;而從時間來看,村落空間同樣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時間,像空間一樣,是人類生活的一種深刻的過程或結構。而人類生活是與作為一種在象征的意義上形成的環境而獲得意義的自然和符號實在交織在一起的。因此,唯有將時間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群體生活習慣等社會性因素結合起來,才能更深刻理解鄉土社會的變遷。這里從主體—自我時間、互動—組織時間、私人—工業時間三個角度來分析。
第一,主體—自我時間。梅洛·龐蒂認為:“我的身體擁有時間,它使一個過去和一個將來為一個現在而存在,它不是一個物體,它創造時間而不是承受時間。因此每一個身體都有它自己的時間,有它的節奏和周期,通過這種運動和行為,它又把這種時間性擴散到圍繞在它周圍的知覺場中。”[26]海德格爾則指出:“出現在孤獨的自我體驗當中的時間,可稱為自我時間。它是以被記起的過去、被體驗的現在和被想象的未來這種形態而投射在存在之上;所以一個人所具有的體驗的類型,它們的時間上的接近,以及它們立體的形態確保每個人的自我時間感是獨特的。”[27]在雄崖所最初的軍事防御空間中,居民由軍戶轉變為民戶,人們在特定的環境中形成了自身的日常慣習,如根據農事進程從事社交、信仰等社會活動,感知大自然周期對生存的意義,與祖先發生情感與精神上的關聯。自我的這些實踐和觀念漸形成了一系列地方性時間機制,進而建構出村落的民俗、歲時、節日、儀式等時間概念。總體來說,傳統鄉村民眾時間是以主體—自我時間為主,此時的時間是特定社會中的人們創制出來的時間。
第二,互動—組織時間。社會時間的一個關鍵的結構特征在于所有社會行動都是在時間上順應更大的社會行動;因此,不僅自我時間被嵌入到互動時間結構之內,而且二者又被嵌入到社會制度的宏觀層次的時間秩序之中。此時的社會時間被解釋為在互動過程中建構起來的人的意義的另一種形式,是每一社會中的制度和組織的組成部分。[28]在雄崖所改造建設的空間中,個人勞動時間、休息時間被“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機制協調組織起來,個人勞動價值被生產小隊長以“工分”的形式給出特定評價和賦予意義;在我們描述的這種時間之中,制度組織時間是完全優先于個體時間的。上述“黃某談到回家吃完飯,隊長一吹哨,就得麻溜走”,可見占據權力位置的人把自身確立為時間資源的控制者。但是當組織對時間的規訓使社會成員感到壓力時,必然引起人們迫切想擺脫現實權威的宰制的愿望,由此來自日常制度時間的變革勢在必行。
第三,私人—工業時間。工業化的到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工作時間的剛性化。即在工業社會,職業規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機器體系的速度所支配的。勞動被按區域大量而精細地分布在空間和時間之中,并且要求根據預先確定的時間間隔來對活動進行一種小心翼翼的協調,而且會把機器時間越來越細的限制強加給人們。因此,根據把時間當作商品的現代觀念,工作時間雖被視作私人時間的一部分,但因雇主購買了雇員的時間,從而把它轉變成了工業時間。[29]雄崖所最后過渡到古村落保護空間,但是工業力量作為一種新生的社會結構,深刻影響著鄉土社會的日常生活。如今的古村落,人與土地之間的自然鄉土關系已漸漸疏離,經濟鏈接方式滲入肌理。村中除了老人還心系土地,遵循著傳統的農業生態時間,青壯年勞力的時間安排已與自然現象沒有什么關系,一種高度精確化的工業時間籠罩在具體時空中。正如索羅金所言,“人類生活原本就是通過帶有自身的動機和目的的不同活動來競爭時間的過程”[30]。
因此,在不同的空間演變狀況下,時間作為一種社會建構,一種用于定位的符號手段,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構想。阿爾都塞指出,每一個結構層面可能包含不同的歷史時間。我們應該賦予每一層一個特定的時間,即相對自主、相對獨立于其他層面的時間。[31]然而,每一個結構層面同時還擁有特定的地理空間,在以下論述中筆者將圍繞空間結構的不同層面來探討與時間的關系。
四、時間變遷的空間結構要素分析
(一)空間文化與時間
黃應貴指出,空間應該被視為文化習慣,包括文化的分類觀念與個人的實踐。他還強調,不同空間建構是由人的活動與物質基礎的相互結合運作的結果。文化在空間格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指,文化是空間變遷中的重要建構力量。當空間被賦予某種文化意義時,便會有特別的象征意義。[32]時間是人們最為平凡和顯著的日常生活特征。要了解一個文化如何建構其歷史時,不可能不先了解它們如何建構他們的時間觀念。戈夫曼曾將日常比作劇場,方法是觀察在這個空間里人們時間上的表演。他因此認為,“任何個體都身處多重時空中。”[33]筆者通過雄崖所空間的轉換,展示了不同的時間價值。最初人們的時間價值建立在農業的再生產上,人們通過在空間中設置一些固定或臨時的象征物,如廟宇,空間經由祭祀的圣化后,世俗空間轉化為神圣空間,便有了儀式時間和世俗時間的劃分,并由此衍生出與自然時序有關的社會活動,如農歷正月初八玉皇廟祭祀、二月初二祭神、三月初九祭山儀式等。此時,時間以個體時間為主,并嵌入到超越時空界限的儀式關聯上。
(二)空間權力與時間
當一個地點在一組既定的歷史環境下生成時,權力關系就成為社會結構的核心。一切權力關系最終都不能夠與行動和日常實踐的領域相分離,不能與具體時空中對行動者直接或間接控制相分離。[34]大衛·哈維認為:“空間和時間實踐在社會事物中從來都不是中立的,他們表現了某種階級的或者其他的社會內容,并且往往成為劇烈的社會斗爭的焦點。因此,支配空間的優勢始終是階級斗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35]而筆者所述的“互動—制度時間”的一個關鍵性結構特征就在于國家借助權力為個人鋪設了一條時間軌道,個人從這一軌道出發,形成恰當的時間表,但個人時間表的設置在時間上是順應更大的社會行動的。在這個意義上,國家設置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化的制度,空間和時間在此都顯示出不可讓渡性,充分體現了國家權威。而最初之“大躍進”到農業生產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國家以“社”為基層控制單位,其根本目的在于以一種社會行動的次序,使地方社會的建構空間按照社會時間的制約,有計劃地開展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對抗私有制的計劃。因此,正如布里奇曼所說:“當事件性質變化時,我們用來指定某一事件發生在某一時間的方法也會發生變化。因此,時間會以不同的外觀出現。”[36]
(三)空間經濟與時間
列斐伏爾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劃,傾向于成為空間的規劃,人們現在通過生產空間來逐利。空間成為利益爭奪的焦點,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線,都納入生產力和產物之中。[37]時間在這個過程中被空間所壓制,并被化約為空間的界限。如中心與邊緣的空間區分通常與時間的持久性有關,那些占據中心的人把自身確立為一些資源的控制者,因此時間上的領先因素已經對空間中的突出位置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38]當前我國鄉村正在經歷巨變,既包括物質生產方式層面,又包括社會結構層面,而最為本質的變遷則發生在時間價值體系層面。以雄崖所村為例,隨著傳統處境由以往 “匱乏經濟”轉變為“豐裕經濟”,人們對金錢的欲望也由“知足”變為“不知足”。而市場通過金錢這一稀缺媒介創造了時間的緊缺,并通過所需要的工作時間與金錢的交換關系來安排時間。由此,原先與農業生產密切聯系的、伸縮性強的傳統時間隨著生產的工業化,開始出現時間分層,即工業組織時間優先于互動時間,而互動時間又優先于主體—自我時間。人們日常生活現狀也只有以節假日為標志得以調劑,且對大多數進城做工的人來說,一般不會有禮拜日,除了國慶、春節等法定假日外,他們一般被牢牢拴在崗位上。于是,在被卷入工業時間的同時,人們產生了將私人時間從工業時間中分離出來的愿望。在調研中,我們時常聽到做工回來的人們對于以往“下地”回來后一起玩耍的眷戀。總之,現在時間的匱乏狀態與各種時間矛盾糾結在一起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處境應該得到社會的重視。
五、結語
費孝通認為:“中國現代的社會變遷,重要的還是被社會的和技術的要素所引起的。社會的要素是指人和人的關系;技術的要素是指人和自然關系中人的一方面。”[39]即隱藏在現代性里的是空間結構的深刻構筑和時間嵌入層面的多樣化。和空間一樣,時間也被納入各種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戰略中,記錄、規約、承載、驅動著人的活動。然而,空間因行為而興,自然也因行為的缺失而廢。時間在空間敘事中,曾依賴于一系列象征物、符號、儀式行為,表述意義、展現價值、表達情感。但在現代社會,隨著人們工作日程安排加快,以及城鎮化的加速,人們的時間日趨被國家經濟的結構性變化所改造。時間的文化價值雖然很久以前已被寫就,但是面對社會變遷,其意義究竟棲居何處值得思考。畢竟,現代人對時間的追憶,“時間焦慮”“時間慌”“鄉村記憶”“鄉愁情結”并不僅僅是因為社會的快速變革所引起的文化恐慌,而是面臨社會轉型所引起的群體心理失衡。所以,以何種方式發揮時間在社會生活中的心理調節意義,從而滿足社會、群體、個人的需要,使三者相處和諧,發揮其在社會中的“安全閥”作用,是建設美麗新鄉村的題中應有之義。
[1][3]景天魁:《時空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
[2](美)L.A.科瑟:《社會學思想名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4]陳占江:《空間認同與社會秩序》,《學習與實踐》2010年第3期,第122頁
[5](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三聯書店,1998年
[6][34][38]德雷克·格利高里 約翰·厄里:《社會關系與空間結構》,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
[7][8][10][14](美)W.蘇愛德華賈:《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商務印書館,2004年
[9]劉勝利:《身體、空間與科學》,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
[11]Durkheim,E..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Glencoe Free Press,1975.
[12](德)諾伯特·埃利亞斯:《論時間》,群學出版社,2013年
[13]方向紅:《時間與存在: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現象學的基本問題》,商務印書館,2014年
[15](美)劉易斯·科塞:《時間觀與社會結構》,載《時間社會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16]Gurvitch,G..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Dortrecht Reidel,1964.
[17](美)史坦利·柯恩:《時間與長期服刑的囚犯》,載《時間社會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18](美)大衛·哈維:《時空之間:關于地理學想象的反思》,載《都市空間與文化想象》,三聯書店,2008年
[19](清)姚夢白:《雄崖所建制沿革志》,藏于即墨市檔案館
[20][21][22][24]孫鑄:《鳳凰·雄崖:歷史資源薈萃》,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
[23]金耀基 范麗珠:《研究中國宗教的社會學范式》,《社會》2007 年第 1 期,第 1~13 頁
[25]Harvey,David.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 Blackwell,1990:p.204.
[26]張堯均:《隱喻的身體: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6年
[27](英)約翰·哈薩德:《時間社會學》,朱江文等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28]Gurvitch Georges.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Dortrecht Reidel,1964.
[29]Soule,G..What Automation Does to Human Beings.London:Sidguick&Jackson,1956.
[30]Sorokin,P.A..Sociocultural Causality,Space,Time.Russel&Russel,1943:p.209.
[31]Althusser,L.and Balibar,E..Reading Capital.London,1970:p.99.
[32]黃應貴:《空間、力與社會》,《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 3期,第 12~15頁
[33]Goffman,Erving.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The Overlook Press.1959:p.106.
[35](美)戴準·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商務印書館,2013年
[36]Bridgman,P..The Concept of Time,Scientific Monthly,1932:p.97.
[37]Lefebvre,H.Space Product and Use Value,in Freiberg,J.W.(ed),Critical Sociology:European Perspective.New York:Irving,1979.
[39]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Spatial Structure,Time Narrative and Rural Life Change
Fang Jingjing Yuan Tongkai
As the basis of people’s lives,space and time record,stature,carry and drive people’s activities.Take an example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we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time narrative arrangement in space from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s.On the one hand,it is intended to define that the spatial structure elements have an impact on the behavior.On the other hand,the author tries to show that time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has been conceived differently in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spatial evolution. “Time anxiety”, “time panic”, “rural memory”,“nostalgia complex” are not just because of cultural panic caused by the rapid changes in society;but the group mental imbalance in the fac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w urbanization,social change,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