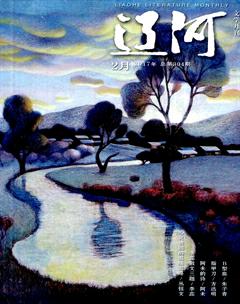黑洞
遲慶波
1
我走進籬笆院時已經是午夜兩點。天空中飄著細雨,隱約能聽到“殺殺殺,殺殺殺”的聲音,我不知道腦海中為什么突然間會出現這個不祥的詞匯。走在我前面的傅國華扯了一下我的袖口,用眼神示意我趕緊進入房間。
我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用遲疑的目光打量著周邊的環境。火車站儲煤場的探照燈的余光掃進院子,能清楚地看清眼前細細的雨絲。籬笆墻有一米二的高度,用的是原木劈成的有棱有角的柈子。黯淡了的燈光和儲煤場的余光釋稀了籬笆墻的慘白。我摸了一把杖勒子,是針葉林中那種細長的日本松,主人用十號線把它和杖柈子捆綁成一個整體,無疑是牢固的。我依舊不放心,手掌用力壓了壓,給我的信息回饋是:即使兩腳踩上去,絕對不會出現我意念中的那種意外,并且能夠迅速地逃離現場。多年以后,退休了,細細想來,如果出現了某種意外,也許是最好的結果。
傅國華挽起我的胳膊,把我塞進了籬笆院的門。
籬笆院是這家飯店的名字。我不知道老板為何做了這樣一個土得掉渣的招牌,不過,和這個環境倒是十分匹配,也許,意念中的返璞歸真會在籬笆院中得到慰籍。
餐廳的衛生還沒有打掃,有些杯盤狼藉;水泥地面上仍留有斑斑駁駁的泥腳印,顯示著夜晚中推杯換盞的輝煌與燦爛。有兩男一女正在墻角的一張餐桌上斗地主。其中一男子看見傅國華,急忙站起來,慌亂中碰倒了一只水杯。無人顧及的杯子,在桌面上畫了一個不規則的半圓,“啪”的一聲摔碎在地面上。
男子只顧扭動著腰肢,越過餐桌旁邊紅紅綠綠的塑料凳子,握住了傅國華的手。
傅所長,這大半夜的,來吃飯?
傅國華說,值班,餓了,所以就來了。
傅國華在撒謊。我暗想,警察撒謊,臉都不紅。
傅國華是礦山派出所的所長。男子遞給傅國華一支香煙,點燃。又遞給我一支,說,您是金龍煤礦的總礦長吧?
我一怔,問道,您怎么認識我?
男子答道,礦工們經常說起您,經常說起您。他無意中加重了語氣,嘴角翹起的同時淹沒了偶爾露出的狡黠。我摸出打火機,沖他一咧嘴,點燃了香煙。
那男子說,傅所長,在老地方就餐?
傅國華搖搖頭,單間也不方便,就在李梅的房間吧。
那男子對著手里握著一把撲克牌的女子喊道:李梅,去把你房間收拾一下。她就是李梅?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她兩眼。李梅站起來,瞅了一眼傅國華,迅速地收回了目光。我隱約感覺到,李梅的目光里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究竟是什么,我又找不到準確的答案。
我和傅國華跟著李梅,穿過一道逼仄的走廊,來到后院,進了李梅的房間。
燈光是淡紅色,房間里就顯得浪漫而溫馨。炕上的被子沒有疊起,一少半被角兒重疊在紅色的被面上,露出了潔白的褥面。 淡紅色的燈光浸染了褥子的潔白,暖色基調就在我的腦海中氤氳成一片梨花帶雨般的畫卷。窗子開了一扇,夏季后半夜的風依舊有些瘦硬,帶著細雨的濕潤,輕輕撩起窗簾的一角,“咕咚”一聲砸在了炕上。
李梅匆忙把被褥卷起來,雙膝跪在炕上,關閉了窗子,拉緊了窗簾。這一系列動作相當嫻熟。這是一個十分麻利的女人。
李梅沖我笑笑,轉身出了房間。我爬到窗前,掀起窗簾的一角,看了一下外面的環境。細雨中的籬笆墻若隱若現;籬笆墻不遠處是火車站,能清楚地看到或紅或綠的信號燈。我想,如果有意外,可以跳出窗子,翻過籬笆墻,迅速地消失在夜幕里。
2
夏夜是寂寥的。
我拿起手機,撥打了傅國華的號碼。手機屏幕上顯示的時間是二十三點。我問傅國華在哪兒,他說在派出所睡覺,沒有值班。他問我什么情況,我說寂寞,能否出來聊聊。他說哪兒,我說在“人民橋”上。
我倚在橋欄上,抽了三支煙,傅國華才來。他問我,多久沒回家了,我說,有一個半月了。他又問,什么時候回去,我說,得等到雨季過了。
傅國華點燃一支煙,笑著說,你就是膽小,井口又不是你們家的,該回就回。
我把兩肘頂在護欄上,橋下的江水“轟轟轟,轟轟轟”甚是駭人。
傅哥,去年下游的江堤決口,淹沒了一座煤礦,死了七十六人,你不會不知道吧?
傅國華不做聲,仰視著天空。
天空一片猙獰,沒有一絲星光。傅國華嘆道,是啊,所以,我也不敢回家。我問他,傅哥,你不敢回家,是為公還是為私?
傅國華把尚未燃盡的煙蒂彈出去,亮光劃出了一道漂亮的拋物線。他淡淡地說,我說為公,你信嗎?
我說,我信。
他拍拍我的肩膀,說,兄弟,別扯淡了。
我說,傅哥,你要不當礦山派出所所長,你弟弟的煤窯能開成嗎?
傅國華哈哈一笑,說,兄弟,沒有你,我弟弟的煤窯能開成嗎?
我覺的,傅國華這個人不簡單。天空中滾動著的烏云壓在了我的心頭,要下雨了。
我和傅國華沿著江堤漫無目的地走了好久。我真佩服他的腳力,盡管他比我大了十七歲,仍然把我拖累得有些疲憊。
傅國華攔下了一輛出租車。我問,去哪兒?傅國華說,喝茶去。我跟著他上了車。
傅國華對司機說,去籬笆院。
我的心陡然間提到了喉嚨,上不去,也下不來。
出租車的燈光像黑夜里幽靈的眼睛,能看見雨刷器在擋風玻璃上不停地搖擺,“沙沙沙沙”的聲音刺穿了我的耳膜。
房間里是寂靜的,“沙沙沙”的聲音似乎一直跟隨著我,我分不清是雨刷器的聲音還是雨水的聲音。
房門輕啟。李梅把茶具放在炕上,我不敢相信,在這偏遠的煤礦小鎮上,還會有這么精致的茶具。是李梅的,還是老板的? 我搖搖頭,想這些干嘛呢?既來之,則安之。
李梅端來了兩碗肉絲面,傅國華吃得很快,大約兩分鐘的時間。我不清楚是餓了還是做警察養成的習慣。
當我吃完的時候,傅國華一杯茶已經喝完。李梅坐在靠窗子的一邊,拿起茶壺,為我斟滿一杯茶,茶杯很小,比牛眼珠子大不了多少,翡翠色的杯壁晶瑩剔透。杯與壺的色澤似山谷涌泉,自然流動,合二為一。盡管房間里的燈光是黯淡的,依舊能看清茶水通透而不渾濁,我把杯子端在唇鼻之間,芳香涌入鼻腔穿透肺腑,恰如空谷幽蘭一般。杯子的厚重與茶水的柔軟相擁,溫暖了我鼻梁上的鏡片,悄然間升起了兩片薄霧。薄霧朦朧了李梅,我忽然意識到,她,就是那朵空谷中的幽蘭。
傅國華呷一口茶,雙目的余光射向我,問李梅,你認識他嗎?
李梅把目光投向我,雙手捧著杯子,笑著說,傅哥,不認識。你給介紹一下唄?
傅國華把我做了極其簡要的介紹。李梅笑著,伸出了手。我輕輕地握了一下這個女人的指尖。對于這個女人,我早有耳聞,在礦工宿舍里無數次想象著她的模樣。在井下以及和工友的會餐后,很多人總是把這個女人掛在嘴邊,甚至繪聲繪色地毫無遮攔地描繪著她身體的每一個部位。很多時候后,在和我愛人同床共枕時,也經常浮現出意念中的李梅的影子。呼風喚雨之后的寧靜,我經常在黑暗中自責,這種看不見的犯罪感吞噬著我,直至夢幻中的另一個世界。
3
傅國華走了。
李梅的外衣薄如蟬翼,高聳的乳房籠罩著朦朧的面紗,額頭上滲出細碎的汗珠。她說,哥,現在做嗎?
我知道,她說的“做”是指什么。我搖搖頭。
李梅一怔,說,是沒準備好嗎?我一時找不出合適的詞匯,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不過,眼前的這個女人和我意念中的那個影子比較起來,更具有女人的味道。何況,這是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女人,比起那個影子要更現實更豐滿更具有誘惑力。
是第一次吧?
我點點頭。
這種情況我見多了。來的次數多了,就習慣了。
李梅脫去外衣,一片潔白瀉下來,像掛在空中的瀑布,房間里頓時明亮起來。她站起來,解開牛仔褲的腰帶,褲子一點一點往下脫落,瀑布一點一點在升高。慢慢地,慢慢地,瀑布真正的懸掛起來,照亮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嚯嚯嚯,嚯嚯嚯”的流水聲從天國傳來,像天宮里奏響了悠揚的音樂。
房間的隔音并不好。隔壁傳來了一個女子“啊啊啊,啊啊啊”的叫聲。我猜想,也許是籬笆院的老板是故意把房間設計成這樣的格局。“啊啊啊,啊啊啊”的聲音迅速膨脹了我的荷爾蒙,把我一腳踹進了那一片潔白之中。流水沐浴著我身體的每一個部位,傾瀉而下的瀑布的速度加重力把我深深地砸入水潭之中;舒緩的音樂從水面拂過,覆遮了所有的波瀾壯闊。
我感到有些窒息,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氣息濕潤了她的前胸,如雨后的梨花掛滿了水珠。
我昂起頭,不敢看李梅漂亮的眼睛,她的眼睛會說話。冥冥之中,我聽見李梅輕輕叫了一聲,哥。
哥?我對這個字特別敏感,特別是女人說出這個字。我急速膨脹了的血管里的血液直灌頭頂之后,像泄了氣的皮球快速地癟了下去。
我忽然看見小妹站在教室的門口,鞋子和褲腳都濕漉漉的,她一只手擦著小臉上的汗,一只手把裝滿干糧的籃子遞給我,輕輕地喊了一聲,哥。然后,轉身,向學校的大門口跑去。我知道,小妹還得跑十五里的山路回家干活來供我讀書。還沒等我叫一聲小妹,她的影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那一年,她十二歲。
我整個身軀疲軟下來,全無斗志。
我坐起來,雙手捧在臉上,拭去汗水中溶入的李梅的體香。
李梅也坐起來,眼睛傳遞給我的是莫名其妙的詢問:哥,你怎么了?
別叫我哥!我低沉的聲音喊道。我自己也感覺到,目光里射出的一定是犀利的寒光。這束寒光里隱含的信息是對李梅最嚴厲的警告。
我忽然意識到,我的警告對于李梅來說是毫無意義,也是毫無道理的。她知道什么,她又能知道什么呢?我不能這樣對她。我摸到枕邊的眼鏡架在鼻梁上,對著李梅笑了笑,說,對不起,對不起。我的道歉是真誠的,但我又覺得玷污了“真誠”這兩個字。
顯然,我的舉動把李梅嚇著了。她赤裸著身體坐在那里,一動不動。我說,李梅,對不起,剛才,我想起了小妹,她,曾經和你一樣,做著相同的職業。我仿佛看見了小妹胳膊上那塊紫色的疤痕。
4
翌日,我在辦公室接到了傅國華的電話。他問我,“做”了沒有,我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問他,你為什么對這件事感興趣,不會是害我吧?他在電話里壓低了聲音,正色道,你把一塊采區劃給了我弟,這是多大的恩情,我怎么會害你?我說,不要再提采區的事,這件事到此為止,讓礦上知道了,我就完蛋了!
傅國華問,你說話方便嗎?
我說,我剛從井下上來,辦公室就我一人。我再一次提醒傅國華,不要再提采區的事。
傅國華說,我就喜歡你謹小慎微的這股勁兒,和你這樣的人辦事,最穩妥。你把各種不利因素都考慮得十分周到。
晚上我請你吃飯,老地方。不等我回答,傅國華掛了電話。
我對著電話喊了一句:我又犯不到你手里,你牛B個鳥?
孔乙己酒館是小鎮上最不起眼的飯店。傅國華喜歡這里,我也喜歡。最重要的是這里清凈。傅國華最大的優點是不喝酒,我的酒量是半瓶啤酒。我曾經問過他為什么滴酒不沾,他說,他參加過珍寶島戰役,本來要提升排長的,因為酒后偷了部隊一千發教練彈,然后就復員了。雖然他說的時候輕描淡寫,但從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這件事對他打擊很大。
傅國華點了兩個菜,一個雪中送炭,一個醋溜腰花。雪中送炭,就是山楂罐頭和銀耳的組合,傅國華最喜歡這道涼菜。
我要了一瓶冰鎮啤酒,傅國華要了一瓶冰糖雪梨。
傅國華說,李梅給我打電話,說你什么也沒做,說你是個好人,今晚請你去喝茶。
我說,傅哥,你別忽悠我,李梅怎么能有你的電話?
傅國華喝了一口冰糖雪梨,說,干我們這一行的,什么人的電話都得有。
我半信半疑,一時又找不到反駁他的證據,只是感覺到他和李梅的關系不一般。我暗自思忖,我和李梅的接觸,會不會是一個圈套?
傅國華是精明的,他說,兄弟,我不會害你,我弟弟還要指你掙錢呢。
我覺得胡亂猜測朋友,有些不地道,就開玩笑說,你弟弟的井口,不會是你的吧?
傅國華一臉的嚴肅,說,我只是幫我弟弟一點小忙,怎么會是我的呢?
傅國華轉移話題,不談井口,又提起李梅,說,你要去,就后半夜,前半夜,她要“干活兒”。我說,我懂。
李梅領著我穿過逼仄的走廊,來到她的房間。炕上的被褥很整齊,就像軍營的“豆腐塊”,棱角分明。我的腦海中浮現出昨晚被褥的凌亂。李梅讀懂了我的心思,說,我今天沒“干活兒”一直在等你。
我說,是沒有“活兒”?
李梅莞爾一笑,說,“親戚”來了。我先是一怔,繼而讀懂了她莞爾一笑里暗藏著狡黠,明白了她說的“親戚”是什么意思。我說,昨晚,對不起。
李梅給我斟滿一杯茶,遞給我。我刻意躲避著她的手指。
我又吃不了你,不用這么拘謹。
我吸了一口茶,能聽見滿屋喉嚨響。
你和老傅很熟?
李梅喝了一口茶,說,不是很熟。
你怎么有老傅的電話號碼?
哥。李梅停頓了片刻,我的心緊了一下。
哥,你別問了。李梅的眼睛瞅向別處,很快又恢復了平靜,說,你是個好人,昨晚……
我暗自好笑,我是好人,怎么會到這兒來?我打斷了李梅的話,說,昨晚,我有心理障礙。
是因為你妹?
嗯,我看到你,就想起我妹妹。我妹妹也曾干著和你一樣的“活兒”,她遇見一個變態的人,每次的時候,那個人就抽打我妹的臂膀,他從她痛苦的叫聲中尋找著快樂。
你妹可以拒絕他啊。
那個人很有錢,我妹為了錢……
我的牙齒咬住了杯子,讓茶水升騰的薄霧擠壓住眼眶中的潮濕。準確地說,小妹是為了讀大學的我。
李梅未必能理解我,但她一定能理解我妹妹。她好久沒有說話,眼睛直視著我,但目光中沒有了攝人心魄的清澈和神韻,出竅的靈魂仿佛游離到另外一個世界。我不知道她為了誰。
游離的靈魂也許走得太遠了,彼此的默默無語似乎都感覺到了對方的尷尬。
你和很多人不一樣。李梅像是自言自語。我意念中的李梅應該是不拘小節的甚至是狂放不羈的。這種意念的來源并非起于傅國華,盡管是他讓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認識了這個女人,但是,我還沒有了解她。或者說,我面前的李梅和工友嘴中的李梅判若兩人。一個是三十出頭風韻十足且狂野的站街女;另一個是溫婉的憂郁中略有羞澀的小家碧玉。我分不清究竟哪一個是真實的李梅,這里面又隱藏著怎樣的玄機?盡管我喜歡這個女人,盡管我有著生理上某種十分渴望的沖動,但在心靈深處的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還沒有被這個女人完全占領。我必須在有了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之后,才能完成向往已久的美妙瞬間。我必須順著李梅的自言自語和她繼續聊下去。
有什么不一樣?我反問李梅。
你像文化人。李梅給我斟滿水。
我只不過比別人多念了幾年書。
你以前是老師。
你怎么知道?我突然覺得,我問了一句廢話。
你別管。但是,我不知道你為什么去了煤礦?
我可以抽煙嗎?
李梅從包里拿出一盒煙和打火機遞給我。在火苗和煙卷親吻的瞬間,我想:李梅怎么知道我的過去?
我深吸一口,咽了下去,讓煙霧在我的腹腔內慢慢循環,而后,從鼻腔中徐徐飄出。我說,我領著學生踢足球,把一個孩子的腿踢殘了。所以,我就到了煤礦。
李梅問,沒有更好的選擇?
我說,有。但煤礦掙得多。我和你殊途同歸,都為錢。
李梅笑了,說,今晚“做”嗎?
我說,你家“親戚”不是來了嗎?
李梅說,我騙人的,為等你。“親戚”每個月月末來。
5
下過一場中雨,又下過兩場小雨,天氣便一直晴好。
我去李梅家是兩周以后的事情了。
通化市和通化縣縣市重名,是兩個不同的行政區域。我是通化市人,李梅是通化縣人,我所在的煤礦坐落在通化市和白山市交匯處的駝峰嶺,翻過駝峰嶺,就是白山市地界了。李梅的家和遼寧省接壤,僅有一橋之隔。我的家安在通化市區內,李梅的家在農村。
李梅領著我來到一家靠近大道的農家門口,告訴我這就是她的家。夕陽的余輝灑在暗紅色的鐵門上依然能感受到一股燥熱襲來。鐵門虛掩著,有一扁指寬的縫隙。圍墻是村里規劃過的,整齊劃一,紅色的琉璃瓦在夕陽的余暉里熠熠生輝。李梅推開了一扇鐵門,門軸的旋轉在鐵與鐵的摩擦之后發出一股刺骨的寒流。房子的外墻壁上貼著橘紅色瓷磚,流水般的光亮在輾轉騰挪,和房頂的琉璃瓦的顏色形成錯落有致的動感。窗子很大,是那種白色的塑鋼材質,像兩池清澈見底的湖水分列在房門的兩側。花墻上有兩盆“浪不夠”正開得嬌艷。我暗自思忖,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富足的人家,那么,李梅為什么要從事這樣一種職業呢?現在的問題是,容不得我有太多的思考,我所面臨的,是如何面對李梅的愛人。
李梅拉開房門,請我先行,我在遲疑的同時,看見一老嫗正在燒火做飯,水蒸氣從鋁鍋蓋的邊緣竄出,發著“嘶嘶嘶嘶”的聲響。老嫗手握玉米秸送入灶坑,灶坑里立刻光亮起來。老嫗見有人來,急忙想站起來。她手把灶臺,努力往上起,沒有起來。她一只膝蓋跪在灶前,又進行了第二次努力,依舊沒有站起來。
李梅從我的身邊擠過去,雙手攙起老嫗,輕輕地叫了一聲“媽”。
老人家瞅瞅李梅,又瞅瞅我,眼睛里滿是歉意和尷尬,說,你看看我這腿,就是不爭氣,平時不這樣,越有客人來,怎么還這樣了呢?梅啊,快把客人領到屋。梅,你把拐棍遞給我。
李梅把一根山里紅樹杈做的拐棍遞給了她,對我說,這是我婆婆。
我仔細端量著這位老人的腿,已經嚴重彎曲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英文字母“O”。她的腳離不開地面。鞋底和地面的摩擦發出“刺啦刺啦”的聲響。
我扶著她,進了李梅的房間。李梅在廚房里忙著。
我問李梅的婆婆,你這腿?
她說,老毛病了,滑膜炎。大夫說是什么“膜”沒有了,要手術,什么進口的國產的我也弄不明白。只是苦了李梅這孩子。
李梅的愛人就在家種地?
現在是。地也不多,就六畝。光靠這點地不解決問題。孫子在鎮上的中學念書,住校。需要錢啊。又加上我這老病,硬是把李梅這孩子“逼”出去打工了。
我發現,這老太太十分健談。我又問,為什么兒子不出去打工呢?
我兩個兒子,原來都在石膏礦。大兒子在礦上做運輸工,翻車,把腿砸折了,就被礦上辭退了。二兒子,啊,也就是李梅的對象,是石膏礦上的掘進工。這個工種掙錢多,這孩子太拼命,結果,得了矽肺。老太太又說,矽肺你懂吧?
我說,我懂,是一種職業病。這種病目前在世界上還無法治愈。我的喉結蠕動了一下,把后一句話壓在心里,沒有說出來。
院子里傳來一陣急速的咳嗽聲。“咳咳咳,咳咳咳”驚起一陣塵土,把斜陽壓下去,紅霞托起來。
李梅的丈夫回來了。
6
夜幕攜燥熱熄滅萬家燈火。
空曠的炕上只剩下我一個人,李梅和丈夫擠在了婆婆的房間。我在想,是否是我的到來,破壞了他和她的久別重逢?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樣想法。我在或明或暗的煙蒂中詢問著答案。
這個答案我不知道尋找了多久,只覺得眼瞼有些沉重,冥冥中有人在晃動我的胳膊。是李梅。
李梅把一根手指放在我的嘴巴上,另一只手在拉我的胳膊。
我和李梅在夜幕中向村西頭走去,大約有十分鐘的路程,來到了和遼寧省接壤的石橋上。石橋周圍是一片一片的玉米地,“啪啪啪”正在拔節。不知名的蟲子“親親親,親親親”地正在興頭上。涼風從河面上走過,露在半截袖外的胳膊陡然間鋪上了一層細碎的小米粒。李梅靠近了我的臂膀,感覺到她的體溫從肌膚上向我傳來,霎那間溫暖了心頭的震顫。她告訴我,再走兩米,就是遼寧省的地界了。
李梅說,你敢跨越嗎?
我說,你敢我就敢。
她的手握住了我的手,說,我和他談過了,愿意和我走。我想起了跪在灶臺前的老嫗。我說,你婆婆怎么辦?
李梅說,大哥和大嫂可以照顧她,也許,這是最好的選擇。他的身體狀況你也看見了了,別讓他種地了,你能安排一個不出力的活兒嗎?李梅的手握緊了我的手,我感覺很有力量。
我說,就他的身體狀況,安排在礦上是不可能了。她的手沒有了力量。不過,我接著說,我可以安排在外包隊,工資兩千。 她的手又有了力量,手指間藏有一種余暉脈脈的溫情。
李梅說,會不會累?
我說,這個你放心。我又試著問她,為什么不求一下傅國華呢,他說話比我有力度。
李梅說,他操我的時候什么都行,提上褲子,我就是個夜壺。
李梅的心情忽然沉郁起來,緊緊抱住了我的腰。她昂起頭,對著我的嘴唇,輕輕地叫了一聲“哥”。她的腹部在用力,用力,一直把我擠到正在“啪啪啪啪”拔節的玉米地里。
如果說李梅是煤礦上的一眼井口,那么,此時的我就是一名掘進隊員。當年,我手握鑿巖機在巖壁上作業的時候,為了讓巖屑快速地從眼孔里吐出,不斷地用一米八的鋼釬快速地抽插。鑿巖機的反作用力撞擊著我的小腹,“兩彈一槍”便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此時,我很想把李梅當做一眼井口來開采,兩只手不由自主地摟緊了她的細腰。
李梅的手握緊了我的手,慢慢地,慢慢地,把兩只手向上抬起,抬起,直至她的胸前。李梅反轉了我的手背,把我的手心一點一點溫柔地覆遮了帶有溫度的山尖。她的手引領著我的手,在山尖的周圍一遍又一遍的上下左右地覆遮。
玉米一片一片地倒下。
一張綠色的大床是那樣的柔軟,軟得似乎把她和我掩埋起來,瞬間變成了垂直的自由落體,下沉,下沉。血管迅速膨脹,洶涌澎湃的大河把這張綠色的大床溫暖。“兩彈一槍”顫抖起來,鑿巖機的鋼釬深深地插入巖壁之中……
蟲子“親親親,親親親”地在星光下演奏著動人的樂章,任由美妙的音符在夏夜里四處流淌。
7
婆婆坐在院子里,嘴角上煙卷的燃燒一明一暗,高高揚起的臉龐和星斗進行著無言的對話。
李梅膽怯地叫了一聲媽,聲音在喉腔里打了一個結,顫抖著從唇邊擠出來:您什么時候學會了抽煙?
婆婆把手指放在了嘴的正中,另一只手急速地擺了擺。
李梅攙扶著婆婆回臥室,我忐忑地站在黑暗中,聽見婆婆說,你快睡吧,我和你媳婦在院子里聊天呢……
8
礦山派出所坐落在駝峰嶺腳下,省道303從旁邊穿過,順著蜿蜒的山路再走五百米就是火藥庫。我每次領取礦用炸藥和雷管,都到傅國華的辦公室閑聊一會。
我停下車,看見傅國華正領著一幫人在砌大門垛。其中有七八個人我都認識,還有幾個也面熟,但叫不上名字。
我問傅國華,你怎么把我的礦工弄來給你干活?
傅國華笑著說,里面說,里面說。
我端著傅國華遞過來的水杯,眼望著干活的礦工。傅國華說,別瞅了,都是你的人。嫖娼。
傅國華看我滿臉的疑問,說,這不前幾天下雨,山水急,把大門垛子沖歪了,我重新砌一下。
我說,你直接跟我要人不就妥了嗎,何必破壞人家的“好事”?
傅國華說,管你要人, 那不得欠你人情啊!
我說,你怎么能抓這么多人?
傅國華呷一口茶,沒有直接回答我。
你想把他們怎么處理?我又問了一句
你放心,我又不罰款,干完活就讓他們回去了。傅國華又說,你把李梅的愛人弄到外包隊了?
我說,你消息挺靈通啊?
傅國華說,水泵房這個活兒,適合他干。李梅給你好處了吧?
我睨視一眼傅國華,沒有說話。
拉完了炸藥,下了礦井。我沒有直奔采區,爬過一道“上山”,去了水泵房。兩臺“B80”水泵“轟轟轟,轟轟轟”地喝著水,把四周的巖壁震得瑟瑟發抖。127燈泡要比礦燈亮得多,我關閉了安全帽上的礦燈,看見李梅的丈夫蹲在蓄水池旁,用一根杏條棒在潮濕的地上翻蚯蚓。礦井下的蚯蚓長不大,不像田地里的蚯蚓那般紅潤。李梅的丈夫用雷管的紅綠導線把蚯蚓拴起來,吊在防護支架上。蚯蚓在空中“勾勾呀呀”地蠕動。一條,兩條,三條……共九條。他一邊翻找,一邊欣賞著吊在空中的蚯蚓。有時候他會注視很久,連眼睛都不眨。
他沒有發現我的到來,他太關注那些吊起來的蚯蚓。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并沒有搞清楚他為什么那么喜歡把蚯蚓吊起來。
我走過去,輕輕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哆嗦了一下,沖我笑笑。我指了指蓄水池,用手做了一個反轉的動作,大聲說,別掉下去!
機器的轟鳴淹沒了我的聲音。我把手高舉過頭頂,意思是水很深。他顯然是讀懂了我的意思。慘白的臉露出一點笑容,手,擺了擺,意思是不會。
他站起來,嘴張成“O”型,兩腮劇烈地抖動。他弓下腰,我隱約能聽到“咳咳咳,咳咳咳”的聲音。
9
下過兩場小雨,又下過一場透雨,東北的春天真正到來了。
駝峰嶺上的山杏和梨花次第開放。粉紅和銀白相互浸染,芳香順著大山的褶皺“嚯嚯嚯”地流淌,把整個山川的瘦骨嶙峋掩埋。
李梅的丈夫死了。
是掉到水泵房的蓄水池里淹死的。
李梅委托我全權代理有關事宜。我和外包隊隊長進行了交涉,為李梅討到了十六萬元的賠償費。外包隊隊長很委屈,說,他一定是自殺,心理有問題,經常摧殘他挖出來的那些蚯蚓,正常人能這樣嗎?我說,去去去,他那是寂寞。隊長迫于我的權利,沒有和我爭辯。煤礦死個人,像死只螞蟻一樣簡單。民不追,官不究,斯人已逝矣,唯有金錢來平衡彼此的利益。
我問李梅,十六萬元的賠償費是否滿意,她說,哥,我真的十分感謝你。我自言自語地說,他究竟是死于意外還是自殺?
李梅說,哥,石膏礦還有一種職業病。
我問,什么病?
李梅說,在石膏礦一線的工人,連續干多年,不能生育。
我一驚,脫口而出:那孩子?
李梅讀懂了我的意思,她沒有回答。
李梅丈夫的死,很快被礦工們遺忘了。因為他們又有了新的話題,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大地震更加令人關注。不久,礦上貼出了募捐通知。要求礦工每人200元,領導干部每人500元,上不封頂。工人的捐款,由單位代捐,從本月的工資里扣除。
一天, 我正在辦公室里換工作服,當地政府送來了一封表揚信。表揚信用一張大紅紙
寫成,表彰我捐款兩萬元。我莫名其妙,什么時候捐的兩萬元?我說,你們是不是搞錯了?他們說,不會,名單里確實是你的名字。
我仔細品味著表揚信的每一句話,希望找到一絲端倪。紅紙上的字的確不敢恭維,張牙舞爪呲牙咧嘴,像野獸。
我沒有找到想要的答案,便給傅國華打電話,問他是不是你搞的鬼?傅國華一頭霧水,對天發誓,說,我絕對沒有“毛病”。
我看他不像撒謊的樣子,也不便繼續追問。
我把電話打給高中同學,他在鎮政府當副鎮長,讓他幫忙查詢一下事情的原委。兩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我怕這是一個圈套。
傍晚,我接到同學的電話,說是一位女同志代捐的,由于數額巨大,當時的工作人員讓她留下姓名,就寫了你的名字。
可能是我做賊心虛,立刻想到了李梅。
傍晚,我打破常規,直接去了籬笆院。老板說,李梅昨天就走了。
籬笆院老板見我發懵,就說,籬笆院再沒有李梅這個人了。他搖著頭,去了后廚。
我出了籬笆院,撥打了李梅的電話。無人接聽。
我連續打。最后聽到的是:您撥打的電話是空號。
我很郁悶,沿著江邊走了很久。
在孔乙己小酒館,我撥打了傅國華的電話。傅國華說,讓我等半個小時,正好有事要找我。這時,我的手機收到一條短信。我掃了一眼,是一個陌生的號碼。內容是:不要再和傅國華來往,千萬不要再把礦上的采區劃給他。切切!!
我的眼睛中立刻有了李梅的影子。問,為什么?
時間仿佛凝固了,我在焦躁中期待著手機屏幕上出現想要的答案。
李梅回復:我給傅國華做了兩年的線人。哥,我懼怕頂在額頭上那黑洞洞的槍口。
我腦海中瞬間浮現出那些砌大門垛子的礦工,同時,看見了李梅那雙驚懼的眼睛。
我的手指劃動了一下手機屏幕,那兩個刺眼的感嘆號像子彈穿過槍膛留下的劃痕。
李梅又回復:哥,記住籬笆院,不要找我。另外,那座小煤窯,不是他弟弟的。
我突然覺得恐懼,腦后似有冷風襲來。我本能地躲閃,一回頭,看見傅國華正站在門口陰鷙地看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