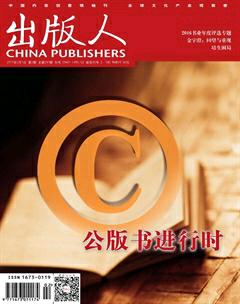鐵門檻里的詩人
楊帆

“他是非常君子的一個人。”談到好友趙麗宏,詩人西川如是說,“不管時代變得多粗鄙,他始終優雅地做著自己。”那是在前者詩集《疼痛》的一場讀者見面會上,對于西川的這番評語,趙麗宏本人不置可否,隨后嘉賓接連不斷地拋出觀點,身為主角的他也只是側臉靜聽,偶爾微微點頭或搖頭,其幅度之小也頗難用肉眼捕捉。當麥克風最終交到他的手中時,趙麗宏像個大男孩般略帶靦腆地向在場的讀者致歉:自己不太會說話,也有些怕說話。他的語速很慢,音調平淡如水。
幾天后再次見到趙麗宏,是在第十屆全國“作代會”的間隙。提著白色手袋匆匆從會場趕回的他婉拒了記者在沙發區落座的請求,“還是椅子舒服”,旋即從不知何處“變”出三枚冬棗交到記者手里,又主動為記者倒滿了面前的玻璃杯——面對比自己年輕很多的記者,這位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沒有絲毫的架子,你甚至難以想象他會有激動或者憤怒的表情。在他溫潤明澈目光的注視下,記者腦中縈繞的卻總是見面會上西川的一句發問:“在當下,沒有被夸張的文字往往不為人見,那么像麗宏兄這樣一位謙謙君子,其文字的深刻源于何處?”
詩緣
在改革春風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鮮有不知道散文家趙麗宏的,不過多數人都同記者本人一樣,是在課本和試卷上與這位作家“邂逅”。據不完全統計,趙麗宏的散文僅在中學課本中就達三十余篇之多,堪稱當代作家被課本收錄之最。然而在更年長一些的讀者心目中,在散文家的身份之前,趙麗宏首先是一個詩人——早在1980年代,趙麗宏的詩名便已響徹文壇,留下了《火光》等經典作品。隨后幾十年,趙麗宏筆耕不綴,散文寫得多起來,也有小說作品面世,而詩歌卻不曾一刻離開他的身畔。
“詩歌曾是我的救命稻草。”趙麗宏告訴《出版人》。文革年間,面對一盞飄搖不定的油燈,下鄉插隊的知青趙麗宏在肉體的饑乏與精神的孤寂中掙扎。“在日記本上,我寫勞作的艱辛,寫大自然的撫慰,寫對親人的思念,寫我的困惑與憧憬……在這段人生中最困苦的歲月里,是這些詩給我安慰,給我勇氣,讓我在黑暗中看到有光在前面。” 趙麗宏由此和詩結緣,接下來就是半生的難解難分。
在趙麗宏眼中,文學體例本無高低,但對詩歌,他似乎有種特別的偏愛:“散文、小說里的表達往往更加曲折;能直接喊出靈魂聲音的,正是詩歌。”其他的文字,他漸漸學會用電腦來寫作,只有詩他堅持用筆寫,數十年來從未中斷——閑暇時、旅途中,甚至在某些“不那么好聽”的會議上,他都會拿出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信手寫上兩句。
盡管寫詩的時間多源于零碎,但趙麗宏的詩中靈光乍現的句子卻并不多見,“更多的時候就像釀酒一樣”。2015年的一個秋夜,他在夢中聽到了父親的聲音,“他在呼喚我,說自己迷路了。接著我仿佛看到他在墓園中徘徊,找不到自己的墓穴,因為墓穴長得都一樣。墓碑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塌,我從夢中驚醒,發現自己仍在床上,枕邊全是淚水”。
這個夢被他寫進了詩里:
我迷路了,迷路
父親的聲音遠了又近
我迷路了,迷路
墓園那么大那么深
分不清何處是夢的盡頭
一次又一次醒來
枕邊印著冰涼的淚痕
在上海一場詩會上,一位誦者讀完這首《迷路》后靜靜地返回后臺,淚如泉涌。目睹這一幕的趙麗宏知道,一個同樣敏銳的靈魂被觸動了。
門檻
面對這個顯得有些喧鬧的世界,趙麗宏的安靜也許像是一種逃避,但他更愿意將其視作堅守。“一個作家身上,可能會發生幾種改變。一種是讓自己變得更獨特更深刻更優雅,這也正是我的追求。”趙麗宏說,“還有一種改變是媚俗,是去迎合物欲的時代,迎合上面人的需要和下面人的喝彩。這種改變對于作家而言可能是一場災難,最后會讓他失去自己。”
趙麗宏這種安靜,不僅表現在生活中,也流露于詩筆下。“詩歌是文字的藝術。”趙麗宏表示,“我在寫詩的時候,從不用生澀、抽象的詞句。我想寫詩最高境界應該是以樸素、簡單的文字,來表達深刻的思想和豐富的情感。”
這是一種境界,用更加形象的話說,這是一個詩人邁過“門檻”的表現。“門檻”論出自詩人、評論家邱華棟之口,用來形容創作者的寫作經驗和人生閱歷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所發生的質變,“許多人寫字,終究實在門外徘徊;邁過這道門檻,才知里面別有洞天”。
顯然趙麗宏也經歷過從門外到門內的過程:“年輕時的文字很清晰,層層遞進,要把思想表達得清楚明白;現在不會這樣,更多的是從感受、思索的過程處著筆,未必就不深刻。”稍作停頓,他又補充道:“所謂深刻不是你要發現什么真理,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靈魂中真實的悸動表達出來,引起讀者的共鳴。”
他堅信一個優秀的詩人,應該是對世界、對人生、對人性、對生命有著獨特見解的,而要想寫出好詩,則要靠真誠的表達和與眾不同的表達方式,而前者尤為重要,“只有發自靈魂,詩歌才能打動別人”。
初心
評論家張定浩把《疼痛》視作趙麗宏漫長詩歌寫作生涯中的一次深深的后撤與收縮:“從中我們可以看見他對自我的回視和對死亡的眺望,他邀請死亡進入他的作品,并將自身集聚成一束更為有力的向死而生的光。”
通讀《疼痛》,這種壓迫感是如此的鮮明——無論是對病痛與肉體的重新審視,還是對逝者的沉重追思,都能讓讀者感受到死亡這一無法回避宿命的迫近。那么詩人在寫下這些詩句的同時,也在凝視著死亡嗎?
“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不必回避。我的詩句中可能有焦灼、有掛念,但絕沒有絕望,更不會有詛咒。我并沒有試圖靠近或者遠離這一生命的必然過程。”趙麗宏說。他表示,文學作品應該引人思索,讓人更加熱愛生命。也正是因為文學的存在,讓生命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我想我的詩即使寫到了死亡,應該也能起到這樣的效果。在黑暗中掙扎,是為了讓讀者找到光明的存在。描繪死亡,為的是讓每一個活著的人更珍惜生命。”
“以不變應萬變,還是當年那顆心。”近年來,趙麗宏曾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說出這句話。在遙遠的灰暗的時光里,對光明、對生命的追求,正是他寫作的初心,這一點直到今天也未曾發生變化。在《疼痛》的最后,一首題為《痛苦是基石》的詩完美地詮釋了詩人對痛苦的理解:
歡樂是外殼
痛苦才是本質
……
學一學打夯人吧
把痛苦當做沉重的基石
夯,夯,把痛苦夯入心底
深深地,深深地
是的,痛苦是基石
有它,才可能建筑歡樂的樓閣
與詩集中的其他49首詩作不同,這首詩并非最近寫就,它是趙麗宏在1982年的日記本中找到的。“這首詩在當時被出版者忽略過,但的確是表達了我對生活最深刻的理解。盡管第一首詩和最后一首詩相距三十多年,但這種感覺于我是一脈相承的。”趙麗宏說。
精裝《疼痛》的書殼為紗布所覆蓋,這正是設計師為詮釋詩集所做的巧思。撫摸著棉線凸起血管般的紋路,詩人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