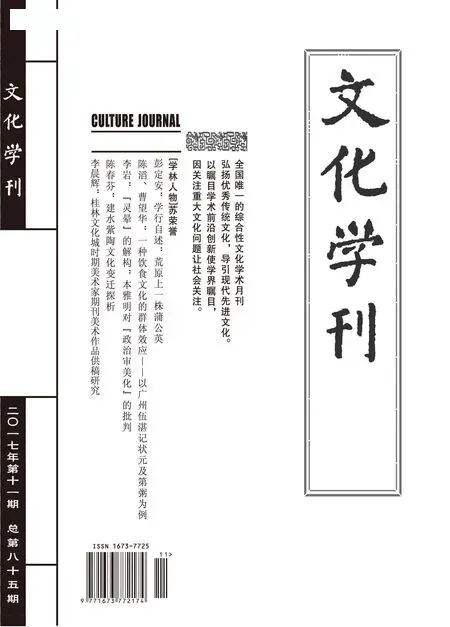生態女權主義的生態觀芻議
孫以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191)
【文化視點】
生態女權主義的生態觀芻議
孫以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191)
生態女權主義者以“自然”與“女性”之間的同構性為邏輯起點,深刻闡明了生態危機的根源與“父權主義”文化具有緊密的相關性。因此,生態女權主義者拒斥“人類中心主義”,主張以“女性原則”的包容性來克服“父權主義”的“反生命性”,從而實現自然和女性的解放,但這種化解矛盾的路徑探討依舊停留于理論批判和“倫理批判”的層面。
生態女權主義;女性原則;生態觀;同構性
20世紀70年代,生態女權主義伴隨西方社會的環境運動而蓬勃興起,并在西方獲得了迅速發展。生態女權主義主張“自然”和“女性”之間具有天然的關聯性。它的核心論點是,認為“貶低自然”與“貶低女人”之間有著歷史的同構性。生態女權主義者之所以對“自然”予以關注,緣于他們力圖通過分析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根源,進而建構人與自然、人與人的新型關系,實現自然的解放和婦女的解放。當然,毫不諱言地講,生態女權主義者嘗試以“女性原則”的恢復來克服人類所面對的生態危機。
一、“理論前提”:自然、女性的同構性
生態女權主義者認為,“自然”和“女性”具有擬似的一致性。當然,這種一致性是通過類比“自然”與“女性”的“孕育”功能來予以鮮明闡釋,正如C.斯普瑞特奈克指出,“大地與子宮都依循相同的宇宙節奏而運轉”。大地孕育的河流隨月的盈虧而漲落的節律與女人子宮的來潮具有無可比擬的相似性,“或者說自然造化力量的相似表現:即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生兒育女,并把食物轉化成乳汁喂養他們,大地則循環往復地生產出豐碩物產,并提供一個復雜的容納生命的生物圈。”[1]生態女權主義以此作為其理論的前提要件,構成其理論內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文化神話”:生態危機的根源
生態女權主義者把以上的邏輯向縱深緯度推進,也即進一步探尋“自然”與“女性”為何會具有內在結構的一致性?女權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不僅揭示了女性受歧視和被貶低的根源,而且也將清晰地闡明生態危機的根源。毋庸置疑,生態女權主義者是從文化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與解答。他們認為,二元論的思維定格是造成上述災難的罪魁禍首,因此,鉗制歐洲人世界觀的二元思維方式便首當其沖地成為生態女權主義者批判的對象。[2]生態女權主義者對笛卡爾所開啟的“身心”對立的二元論思維方式進行了歷史追溯。他們窺探到,希臘哲學就有這樣的“基因”存在,它形成于性別與階級差別的基礎上。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指出,現實世界是由永恒的理念世界、上帝與沒有固定形態的物質組成。造物主以永恒的理念為基礎將繁雜的物質形態匯聚成型,這就構成了可感領域與可知領域的二元對立。他指出理念高于現實,現實是對理念的模仿,因而,現實永遠是不完滿的。而柏拉圖主張靈魂應當過有道德的生活,否則,“它將變成一個女人”。[3]至此,柏拉圖的理論景觀便呈現出男人、女人和動物的等級框架結構。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建構和柏拉圖具有相同的理論邏輯,他指出,“男人高等,女人劣等;男人統治,女人被統治”。[4]這明顯地勾勒出女性遭受貶低的思想酵素,即男性較之于女性所顯示出的優勢,一種“父權制”的隱約顯現。
人類經歷中世紀的煉獄,啟蒙運動勢所必然地開啟了人類理性思維的靈光。啟蒙時代是一個崇尚理性的時代,一切都要經受理性法庭的審判和拷問。然而,理性、文化等是與“陽性”(男性)相關;情緒、身體和自然與“陰性”(女性)相關。[5]顯而易見,“陽性”(男性)相對于“陰性”(女性)而言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因為“男性”代表著權力、控制等元素。至此,這里就凸顯出了“理性”對“自然”的支配與駕馭,因為“理性支配自然”根源于“男性支配女性”和“陽性控制陰性”的邏輯;同時,這也深刻詮釋了生態女權主義者的理論前提:“自然”與“女性”的內在同構性。而“理性”在生態女權主義者看來,它蘊含有“父權主義文化”的基因。正是在這種二元分立的格局主導下,理性把自然界視為自己的工具和實現自己欲望的場所,進而造成人與自然的矛盾日趨加劇。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社會生態危機的根源,就在于西方父權制文化中的男性主導原則扼殺了女性原則。”[6]對此困境,生態女權主義者認為只有實現自然的解放才能實現女性的解放,反之亦然。
三、“善的理念”:自然、婦女的解放
生態女權主義者為了化解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矛盾,倒向了“生態中心主義”的陣營。另外,他們也受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對人類的理性至上主義給予了無情的批判。為此,他們主張對自然應當給予同情和關切[7];主張恢復“女性原則”來對抗“父權制文化”(理性),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矛盾的和解。席瓦認為“女性原則”是以“包容性”為基礎的[8],它本身含有多樣性、開放性等意蘊。由此看來,女權主義者以“女性”的創生性、包容性來代替“父權主義”的摧毀性和“反生命性”,進而彌合由古至今以來所造成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裂隙。但這不可避免地又陷入了以往形而上學的泥淖之中。總而言之,女權主義對生態問題根源的探討和解釋可謂是別開生面的,但當透視其理論邏輯時,我們便會發現他們的解決路徑依舊停留于純粹理論解釋和“倫理批判”的層面。馬克思曾諄諄告誡:哲學家們不應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更在于改變世界。[9]
[1][2][5][7]C.斯普瑞特奈克,秦喜清.生態女權主義建設性的重大貢獻[J].國外社會科學,1997,(6):62-64.
[3][4]羅斯瑪麗·魯瑟,郭海鵬.生態、女權主義和精神:為了一個適于居住的地球[J].江蘇社會科學,2014,(2):4.
[6]鄭湘萍,田啟波.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生態女性主義比較研究[J].深圳大學學報,2014,(3):71-77.
[8]Vandana Shiva.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Survivalin India[M].London:Zed Books Ltd,1988.50.
[9]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
【責任編輯:周丹】
C913.68
A
1673-7725(2017)11-0006-02
2017-09-06
孫以寧(1992-),女,遼寧鞍山人,主要從事科技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