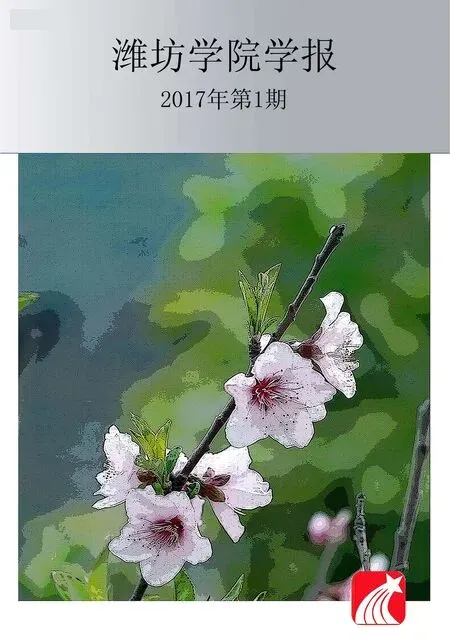兩種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和李侃等人的《中國近代史》之比較
范美琪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 200241)
兩種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和李侃等人的《中國近代史》之比較
范美琪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 200241)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和李侃等人的《中國近代史》是學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本文對兩個文本加以比較,其中包括對中國近代史的時間范圍界定和書的主線、人物和事件評價以及方法論的詳細對比,試圖探究造成諸多差異的原因。作者的寫作背景和所使用的歷史研究方法對這些差異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蔣廷黻;李侃;中國近代史
學界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著作有很多,而我之所以選蔣廷黻和李侃等人的著作進行比較,是由于無論從作者本身來看,還是從內容和寫作方法來看,兩者各具特點,具有較強的可比性。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被稱為近代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從中可以窺見他那一代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響的學人,在思考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關懷社會進步、主張政治改良的普遍心態。而李侃等人所著的《中國近代史》是高等院校的教科書,代表了大陸官方對中國近代史的闡述。因此,我將通過對比兩本著作來探討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雖然兩本書論述的主題都是中國近代史的內容,但其著述方法、立場、具體內容都有所不同,通過內容比較,以期窺見其所不同之處,進而思考造成如此不同之原因,從而開拓近代史研究的新視角與思路。
一、文本比較
宏觀上,就其主線而論,李侃等人主要是以反帝反封建及革命的發展為論述的主線,主要敘述了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一時期各個階級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而蔣廷黻主要分析了自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前夕近代中國歷史上依次遞進的四個“救國救民族”方案的內容、性質、成敗和歷史教訓。從這可看出,主線的不同造成內容的差異,兩本書在論述重點上的不同,造成其即使在論述相同內容時其側重點也是不一樣的。因此下面我將從微觀上對這兩本書進行比較。
(一)對中國近代史時間跨度的界定
對“中國近代史”時間的界定是有一些爭議的,如徐中約所著《中國近代史》是指1600年到2000年長達400年的歷史,而通常我國學界的“中國近代史”是指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余年的歷史。李侃等人和蔣廷黻都是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這一點是毫無異議的,但李侃等人所著的中國近代史是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運動這80年的歷史,蔣廷黻由于側重于把近代化作為整本書的線索,他把中國近代史看成是中國近代化的歷史,因此書中并沒有很明確的時間界定,但通過細讀我們可以認為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時間的界定大致是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前夕這一段時期的歷史。也就是說,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時間的界定比李侃等人對其所界定的跨度要大一些,因此,從宏觀上來分析,蔣廷黻所著的《中國近代史》所涉及的內容跨度要大些,李侃等人所著的書中就不會涉及五四運動之后的歷史。兩本書在對近代史的時間界定上雖有些區別,但都論述了近代史上發生的幾件代表性事件及其人物: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從林則徐到孫中山。因此,這并不妨礙我們就其書中的共同性人物和事件進行對比。
(二)人物和事件評價
蔣廷黻和李侃等人在書中對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是有很大差別的。在人物評價上,如對于林則徐的評價,李侃等人指出,“他不愧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先進人物”,[1]在李侃等人的書中,林則徐是一個禁煙和愛國英雄,而這也是大陸官方對林則徐的評價,但是,蔣廷黻卻認為林則徐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2]蔣廷黻認為林則徐意識到中國比西洋落后而不敢公開提倡改革,把自己利益放在國事前面,他認為真正的林則徐是一個把個人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的人。同樣的,對于諸如義和團、太平天國等的評價,兩者評價也是有天壤之別的。李侃等人對它們主要是持肯定態度,高度贊揚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操和反帝性質,同時從它們的歷史局限性來對其作出批判。蔣廷黻雖然也不乏正面的描述,認為“他們也是愛國份子”,但重點卻是在于揭示他們的愚昧和無知。諸如以民心抵抗洋槍洋炮;義和團興起的原因居然還有“說教士來中國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國人的心眼以煉丹藥;又一說教士竊取嬰孩腦髓,室女紅丸”。[2]此外,對于《北京條約》,李侃等人所著書中把它作為喪權辱國的條約,開放通商口岸便利于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心地區,而蔣廷黻則認為簽訂條約“固然是禍,也可以是福,看我們振作與否。”蔣從中國近代化的角度出發來分析簽訂條約對中國的影響,認為其使我們中國開始了外交的近代化,是奕訴 斤與文祥拋棄了閉關時代,使中國更快融入到國際社會中。對同一歷史事件進行完全相對的解讀,并且都言之有理,這對開拓我們的思維,促使我們從不同角度反思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差異的原因
作品出自作者之手,形成如此差異的原因首先就應從作者本身出發,并且結合當時的寫作背景進行分析,同時,書本內容的差異與方法論的不同也有著密切聯系。
(一)個人經歷和寫作背景的不同
蔣廷黻(1895-1965),出生于湖南邵陽的一個中等農家,早年留學美國,1919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美國“新史學”的倡領者魯濱遜的弟子卡爾頓-海斯。歸國后歷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歷史教授,參與創辦《獨立評論》。1935年起,以書生從政,任民國政府高級外交官,1931年和1934年分別出版《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選輯》,為外交史學發展為一門分支學科奠定了基礎,他從外交史研究中越來越感到許多問題不能局限于對外交往方面作觀察,必須追溯到民族性、國民性、社會心態乃至經濟變化、社會結構等方面。這就促使他對自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歷史的探究與思考,從而從外交史研究擴展到近代史研究。而《中國近代史》是1938年初從駐蘇聯大使任上歸國后在等待任命期間所撰寫的,全書五萬余字,受政治氣候影響,解放后此書在大陸絕版,直到1987年才首次在大陸重版。
李侃(1922-2010),中學時起便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在學校開展的秘密反滿抗日活動,1958年調中華書局工作,之后成為中華書局總編輯。而他所參與編寫的《中國近代史》的產生是跟當時社會環境有關聯的。由于“文化大革命”時期,高校中國近代史課的教材遭到批判全盤否定,中國近代史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是非被顛倒,沒有一種適合高校正常教學使用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因此,在1975年李侃先生與龔書鐸、李時岳到哈爾濱參加研討聯合學者編著的《中國近代史》會議,他們決定聯絡幾位高校教師,自編一本適合于高校文科使用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以應教學需要的共識。最后編寫和修改定稿過程,克服了當時政治局勢跌宕起伏的干擾,《中國近代史》一書終于在197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3]因此,該書對中國近代史的敘述比較系統、平穩,但他的官方性質決定了他同時也具有意識形態性。
不同的個人經歷和寫作背景導致兩本書的內容有差異。蔣廷黻所受的是西式教育和訓練,注重實證研究,但《中國近代史》寫于1938年,當時蔣廷黻擔任國民黨職務,因此文中也會不自覺地帶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性,蔣的從政經歷使這本書具有很強的政治現實性。而李侃等人主要接受的是國內教育,并且整本書是根據中國近代史教材的基本要求編寫的,著書的出發點決定了此書的性質。
(二)方法論的不同
由于寫作背景的不同以及所代表的立場之不同,造成他們在資料選用方面的不同。蔣廷黻在美國求學時,正是“新史學”占主流地位的時代,“新史學”以實證主義為思想基礎,重視史學的社會功能與實用價值,主張史學革命,“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不僅受到“新史學”的影響,而且受到“新史學”的基石進化史觀的影響。”[4]蔣廷黻非常注重史料的搜集與考訂,注重用實證的方法探求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系。他在這本書的《總論》中,一開始就從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整體的進化史觀著眼,通過中西文明的歷史對比指出中國需要全盤西化,由中古狀態發展成近代化,近代化成為貫穿整本書的主線。因此,蔣對人物事件的評價都是以“近代化”作為衡量標準的,且結合“沖擊-反應”模式來解釋中國近代史的現象,中國在受到西方的打擊后開始對其回應,客觀上促成了中國走向近代化,這一模式體現于他所總結的四個方案中。因此,蔣廷黻是按照一整套西方的理論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
李侃等人則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寫作中國的近代史,以反帝反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革命為論說的主線,對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中國革命性質、革命對象及革命目標,中國社會階級的劃分,中國近代的主要社會矛盾,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無產階級革命等,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來闡釋的,并且具有較為統一的解釋。由于李侃等人主要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寫作此書,因此,與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相比較,李侃等人所編寫的這本所涉及的具體內容更全面,在分析這一時期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之外,他們還涉及到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內容。
因此,雖然兩本書敘述的都是大概相近的一段歷史,但由于所采用的方法不同,造成內容上也具有很大的差別。同時,這兩本書都具有其局限性。
三、結束語
雖然蔣廷黻致力于把政治宣傳與史學分析分離開來,力求站在中立的立場來做分析,從而達到尊重事實的效果,但當個人在力求客觀的同時,主觀因素也會帶入所寫內容中,這是無不避免的。蔣蔣廷黻想要秉筆直書,他的個人經歷難免會影響其書中的思想,如蔣廷黻在書中主張“在國際生活中尋找出路”等與國民黨當時的政治主張是相一致的,且在分析三個方案失敗及原因等方面后,最后提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中國的最后出路,時代的局限性造成蔣廷黻的這本書也不可避免具有局限性,但并不影響蔣廷黻這本書的歷史價值,蔣廷黻在著此書中的思考方式及其方法仍值得我們學習與研究。而李侃等人所著之書因其所具有的官方性質也成為它的局限性,內容上必將意識形態化,自然這本書使用的方法也主要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歷史事件的。
把大陸學者所作的教材《中國近代史》和一個曾擔任國民黨職務的老一輩史學家的《中國近代史》結合起來閱讀不失為全面了解中國近代歷史的有效辦法。通過以上比較,可以發現李侃等人的著述中唯物史觀占有指導地位,而蔣廷黻立足于“新史觀”,把近代化作為貫穿全文的主線,二者之間的差異明顯。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是歷史研究方法論體系中一個部分,我們不僅要站在唯物史觀的角度上充分認識和分析問題,還要適當應用其他方法來開拓我們的視野,從而使自己的史學方法論體系更加完善。此外,比較研究重在研究差異及造成差異的原因和彌補彼此缺失的途徑,通過以上之比較,雖然歷史學家們奉行“秉筆直書”,力求客觀,但政治立場、個人經歷等方面的不同對于同一個問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范式也會不盡相同,我們需要見賢思齊,通過不斷吸收新穎觀點來實現學術研究的進步和繁榮。
[1]李侃,李時岳等.中國近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4.
[2]蔣廷黻.中國近代史[M].武漢:武漢出版社.2012.
[3]陳錚.李侃與中華書局幾部書的編輯出版[J].出版史料,2010,(13).
[4]沈渭濱.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
責任編輯:孫延波
K09
A
1671-4288(2017)01-0075-03
2016-08-19
范美琪(1992-),女,江西贛州人,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