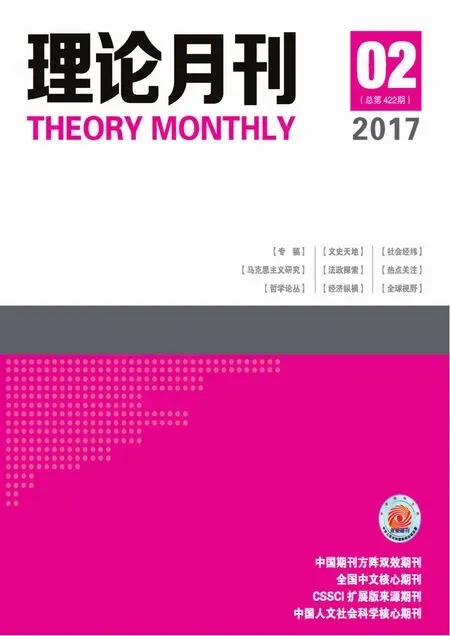論日本“神道”與中國思想的關系
□史少博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陜西西安 710126)
論日本“神道”與中國思想的關系
□史少博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陜西西安 710126)
神道是日本從太古就有的宗教信念并按照其宗教信念行事的綜括名稱。日本神道雖然是日本固有的信仰,不僅是日本民族創作、純粹固有的東西,而且還具有包容性、應化性,以佛教、儒教為首,包容了道教、陰陽五行說、老莊思想等,可以說日本“神道”與中國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第一,“神道”之詞借用于中國的“中文詞”。第二,日本的“神道”是儒教化的“神道”。第三,即使日本近代國學者的“復古神道”極力排斥中國思想,也擺脫不了中國思想對“復古神道”的影響。第四,日本近代國學者講“神道”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式的。第五,日本闡釋“神道”的古代經典中融入了中國思想。
日本神道,中國思想,關系
關于“神道”的內涵,日本在“《名法要集》中,對‘神道二字的意思’解釋道:‘神是天地萬物之靈宗也。所以,陰陽不測謂之神。道是一切萬行之起源也。所以,非常道謂之道。總的器界、生界、有心無心、有氣無氣,都是我們的神道。”[1]40《名法要集》即《唯一神道名法要集》,是日本吉田神道理論的集大成書籍,是吉田神道的理論根據。可見,日本“神道”圣典對“神道”闡釋中的“陰陽不測謂之神”,就出自我們中國的《周易》。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認為:“第一,‘神道’一詞在最古老的文獻上用例的意義,是指自古以來作為日本民族風俗的宗教(包括咒術)信仰。其次,‘神道’一詞往往指神的權威、力量、行動、伎倆、地位或神衹、神本身等等。第三層意思,是指兩部神道,即唯一神道或垂加神道那樣第一層意義上的神道,或也可以解釋為在第二層意義上的、對神代傳說附加上‘思想’上解釋的這個‘思想’,換言之,是指某種有神學意義的東西,或者說就是‘教義’。……第四層意思,以某個神社為中心而形成的有特異性的神道流派,譬如伊勢神道、山王神道之類。第五層意思,則是指日本之神的教誨或規范,也即被認定為日本獨特的政治或道德規范意義的‘神之道’;這主要是受了儒教之影響,而又建立一種能與之對抗的神道,即針對儒者所謂圣人之道、先王之道而創造出來的‘神之道’,德川時代的學者們在此意義上廣泛地使用了‘神道’一詞。國學者們所謂的‘神之道’或‘皇神之道’,也屬于此類。第六是指所謂神道的各種宗派。”[2]1-6另一位日本學者小山松吉認為:“我國天神不僅借鑒了支那漢民族的拜天、祭天,而且還崇拜祖神、按照祖神的意志決斷事情,這個祖先教即我國神道。于是,在我國神道中,第一,把祖先天御中主神的神裔作為國家的主權者敬仰;第二,信奉高皇產靈、神皇產靈二神的神裔,作為主神崇拜,同時繼承祖先的意志,輔佐主權者;第三,崇拜天神即輔佐御中主神并崇拜產、靈二神。尊崇這三條,是上至皇族、下至國民全體的義務。不僅是原來祖先崇拜中只是舉行祖先的祭祀,而且也是要遵循祖先的意志決斷事情。隨著神道的發展,后世又出現了俗神道,又出現了關于佛教與道教的對抗性的種種意見,又出現了兩部神道、垂加神道等等流派,盡管非常難理解,但是神道的本源,總起來神髓之道是我國之道。并且我國之道,是敬神、崇祖這一點的回歸。”[3]199-200日本還有學者指出:“神道是我國從太古就有的宗教信念并按照其宗教信念行事的綜括名稱。神道是日本固有的信仰。……神道不僅是日本民族創作、純粹固有的東西,而且還具有包容性、應化性,以佛教、儒教為首,包容了道教、陰陽五行說、老莊思想等,產生了多種類型的神道,但是其根本仍然全是日本性的東西。……尊崇我國建國祖神的理想、敬仰神道的威靈、堅守皇室的尊嚴與國體的卓越,以圖謀我國的存在與發展,是民族信仰。”[4]35-36
日本的“神道”,一般來說有神社“神道”、民俗“神道”、教派“神道”三大系統。日本“神道”一般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公元七世紀至十一世紀的奈良平安時代,這一時期被稱為日本的“古代”。在此階段“神道”從原始宗教向古代宗教進化。第二階段為大約公元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的鐮倉到室町時期,這一時期被稱為日本的“中世”。在此階段,日本的“神道”教理也逐漸系統化。這一時期的教派主要有:天臺神道(也叫做日吉神道)、山王一實神道、伊勢神道(也叫做外宮神道或者度會神道)。還有公元一四六九至一四八七年室町文明年間的吉田神道,也稱為卜部神道、唯一神道。第四階段為公元一六○三至一八六七年間的江戶時期,也稱為日本的“近世”時期,此時期的神道派別主要有吉川神道(也叫做理學神道)、垂加神道。還有江戶元祿年間到明治維新前后,日本國學“四大人”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創立的“復古神道”,主張根據日本的經典《古事記》、《日本書紀》等來闡釋日本的“神道”,排斥用儒學、佛學闡釋“神道”。“神道”的發展經歷了以上四個階段后,到明治維新后,為了神化日本天皇的絕對權威,以神社神道為國家神道,并且利用“神道”作為日本的精神支柱,而推行了軍國主義。但是,無論從什么角度去理解“神道”,都繞不開“神道”與中國思想的關系,分析如下:
1 “神道”之詞借用于中國的“中文詞”
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認為:“‘神道’這一名稱最初是一個中文詞,在中國已經在各種意義上使用著。……根據古典的記載,‘神’這一詞語的中文含義,首先作為名詞,第一指的是宗教咒術上的意義。概言之,是擁有超越人類的力量或能力,以某種方式驅動著人們生活的東西。……第二,是宇宙的,或者是宇宙本身擁有了玄妙之力或作用,于是被稱為了神。《易·系辭傳》里的‘神無方而易無體’,以及‘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之神即是此類。……第三,存在于人的神,也即今天一般所說的‘精神’這一概念的來源。……最初的例子可見《莊子》的‘天地篇’和‘刻意篇’,其次可見《淮南子·原道訓》的‘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再就是把‘神’一詞當作形容詞來用。道家用語的‘神人之神’,便是對得道之人而言的形容詞,稱中國為‘神州’,以天下或帝位為‘神器’,也是這一類的用法。……以上是古典里的‘神’一詞的意義,后來大都繼承了這一用法,只是宗教意義上的神,隨著宗教思想的進步,被賦予了新的內容。……‘神’既然有如此多的意義,神道之名當然也會如此了。‘神’這個詞在宗教意義上,特別是被作為了祭祀的對象,于是祭祀、祈禱,還是宗教本身,都自然而然地被稱作了‘神道’。……在《日本書紀》里,作為日本民族風習的神之崇拜被稱作神道,是宗教意義的神道一詞在日本的運用。”[2]9-13
日本學者沖野巖三在其著作《日本神社考》中指出:“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神’字,是支那(中國。本文作者注)的文字,與日本的‘かみ’(中文譯為:神。本文作者注,下同)字,本來的意思是不一樣的。‘神’字左邊是‘示’字右邊是‘申’字,剖析‘示’的話,‘示’是‘二’與‘小’的合體字,‘二’是‘天的意思’,‘小’是指‘日月星之三’。也就是說看到天上的日月星辰,人間就知道吉兇禍福,這就是‘示’。并且‘神’字中也有‘社’字、‘祭’字、‘祀’字的偏旁,都與這個‘示’字有關。‘神’字的右邊偏旁‘申’字,本字是‘電’字,九月是雷鳴閃電之月,所以古人把九月叫做‘申月’(一般陰歷七月為申月,可能這里所說的九月是陽歷。本文作者注)。這個‘申’字與‘示’字合起來造了個‘神’字,在支那人的心里,神就是天,可以說是以靈妙不可思議的威力示意人間。然而,在日本的古代,‘神’好像沒有這個意思。”[5]143
“神道”這一名稱與中國思想密不可分。“神道這一名稱在歷史上如此被運用,而到了后世則將之日語化,稱為‘神之道’。然而,原來的日語里面,也明顯有‘神之道’這一詞語。但‘道’這一詞語的含義只是中國才使用的。‘道’最初是‘人步行之道’,以后轉化為人的行為規范,事物存在之法理,……神道之‘道’便是從此意轉化而來的。也有‘儒道’一詞,也有以佛教為‘佛道’的,都屬此例。在日本,后來以慈遍(注:慈遍,是鐮倉時代末時期的神道家)使用‘皇道’,賀茂真淵(1697-1769)使用‘神代之道’和‘皇神之道’,本居宣長(1730-1801)使用‘神之道’、‘日大神之道’、‘日之御國之道’等等,都是根據中國的習慣用語,賀茂真淵和本居宣長之所以使用這些詞語,都是想用日語盡量表達出‘道’的含義。盡管使用神道的舊名稱也無大礙,但特別創造出這些詞語,固然表現了他們作為國學者的姿態,可實際上在這種意義上所說的‘道’,繼承的都是中國思想。”[2]14-15可見,“神道”、“神之道”都繞不開中國思想對其的影響。
即使極力排斥中國思想的近代國學家平田篤胤闡釋的“惟神為之道”,追溯根源也與中國有關。正如日本學者分析:“平田篤胤(1776-1843)在《古史徵開題記》等著作中提到‘惟神為之道’、‘隨神之道’,這里的‘惟神’或‘隨神’都是指的是‘神ながら’一詞。”[2](P15)而“‘神ながら之道’的日語原意,‘な’為助詞,相當于中文的‘之’,‘がら’為性質。‘神ながら’的本意為‘神之本來性質’,于是‘神ながらの道’的原意則為‘從神代傳來的、神之本意、不加任何人為因素的日本固有之道’。后來‘神ながら’被書寫為了中文的‘隨神’或‘惟神’。”[2]17-18津田左右吉指出:“《日本書紀》中的孝德天皇大化三年條里的‘惟神’文字被訓讀為‘神ながら’,同時也有‘惟神者謂隨神道亦自有神道也’之注,……然而‘惟神’作為一個詞語來使用的例子,中國不是沒有,我們前面引用過的《晉書·隱逸傳》的‘序’里,則可見到‘處柔而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可以推測《日本書紀》的編者讀過《晉書》……究明了‘神道’的名稱有各種含義,其本來是從中國拿來的成語。”[2]17-18可見,就連日本學者也認為日本“神道”的名稱及其含義,都是借鑒中國的。
2 日本的儒教化“神道”
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認為:“江戶時代前半期,是指所謂國學者的神道說興起之前的時期,這一時期神道思想的特色,在于帶有強烈的儒教色彩,稱其為‘儒教化神道’也不過分。”[2](P144)例如吉田神道的經典《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中就闡明了其“神道”中融入了“儒教”,正如日本學者指出:“‘為了潤色唯一,為了榮耀神道,廣泛地了解三教的才學,專心鉆研我們神道的根源,亦何防之有哉。’……對于外來思想,兼俱既不排外也不媚外,而是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所以他并不是頑固不化地拒絕異邦的三教,而是用開放的寬容的心態來接受。正是因為運用外來的‘三教的才學’來‘鉆研我們神道的淵源’,所以采用外來思想并沒有損壞神道的純粹性。……以日本(神道)為種子、根本,中國(儒教)為枝葉,印度(佛教)為花和果實的根葉花實論,……在日本的土壤上生根發芽的神道這棵樹木能夠枝繁葉茂,開花結果。”[2]67-68可見,日本的“神道”中不僅融入了中國的儒教,還融入了印度的佛教。
再例如日本的垂加神道也可以說集中國的陰陽學、易學、朱子學之大成,并且“垂加一方面講日本的神道,其著作里卻多用漢文,連所謂秘傳或口傳也是用漢文來書寫。……最主要的理由,還是因為他們是儒者,擺脫不了尊崇中國的儒者習氣。”[2]145-146而“陰陽學”、“易學”、“朱子學”當然屬于中國的儒學,可見日本的垂加神道可以認為是儒教化的神道。“在用儒教思想來論述神道的神道者之中,屬于伊勢神道系統的度會延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認為堯舜禹之道、孔子之道和神道相同。其理由是,三種神器為儒教的智、仁、勇三德的體現,而三種神器是天照大神賦予的,于是神道即大神之道。……很早以前,藤原惺窩便說神道和儒道同一,并使用了‘天照大神的成規’一語(《千代本草》),林羅山也認為,神道是儒道,是‘圣賢之遣’。”[2]146-147伊勢神道“無疑是由外宮的神職人員們建立的學說,流傳至今的所謂《神道五部書》(《天照坐伊勢二所皇太神宮御鎮座次第記》《伊勢二所皇太神鎮座傳記》《豐受皇太神御鎮座本紀》《造伊勢二所太神宮寶基本紀》《倭姬命世記》),便是它們的經典。”[2]58由此可知,日本著名的神道的其中派系伊勢神道,使用儒教思想闡釋神道。
即使排斥儒學最甚的本居宣長,也沒有擺脫使“神道”儒教化,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分析:“排斥儒教的本居宣長之說,其實明顯是從儒教思想變形而來的。只是在本居宣長的思想里,說神是日本之神,并非中國之圣人,以及我國的皇族是同一血統,和不同王朝中國的先王不同這兩點上,有很大的意義,必須從這來看道的性質和成立。”[2]219由此,也可以說日本神道是儒教化的神道。
3 日本近代國學者的“復古神道”也無法擺脫中國思想的影響
日本近代國學家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主張“復古神道”,尤其是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竭力排斥中國儒學。然而即使本居宣長、平田篤胤極力排斥中國儒學,但是仍然擺脫不了儒學對其思想的影響。正如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分析:“本居宣長針對到此為止的神道家們引進佛教思想和儒教思想而建立的神道的做法,力圖排除外來思想而講日本固有的或純粹的神之道,平田篤胤則繼承發展之,這似乎是一種定論,但是事實還是有些出入。不僅是平田篤胤,連本居宣長也主張‘神之道’,在所謂‘道’的問題上,可以看到中國思想起著很大的作用。”[2]211
為了能把先進的理念和前沿的新生兒救治技術傳授給當地的醫護人員,提高新生兒搶救成功率,陳正副院長特地在當天下午的授課中主講了一堂“2016版新生兒窒息復蘇指南”,并現場傳授了操作要點和注意事項。
日本近代的國學者本居宣長、賀茂真淵,極力推崇“復古神道”,正如“神道家從否定‘神道’的角度講新的神之道,在所謂的國學者中是從本居宣長開始的,但在探討本居宣長的思想時,首先得了解賀茂真淵的見解。因為賀茂真淵也說‘道’,講其道為‘神皇之道’、‘古神皇之道’(《新學》),‘皇神之道’(《歌意考》),以及‘神代之道’(《國意考》、《書意考》)。其中也有講和歌和日本語的問題的場合,但是更多的是說‘道’為最廣泛,具有根本意義的東西,存在著和儒家所說的中國的‘道’不一樣的‘我國之道’,認為其道為‘誠之道’等意義上的道。這里所說的‘神皇’或‘皇神’,是政治意義上的皇室的祖先,從而也是古代神之道,也可以說是‘古道’(《歌意考》)。……神道家們早就講‘道’的存在,講作為古帝王之道、皇祖之道的大神之道,這些不用說都是拿中國思想來套用日本的事情。”[2]212這與賀茂真淵講的“復古神道”中的“道”有關系,日本學者分析:“賀茂真淵的研究與老子思想有很大關系。……不同時期真淵的老子觀確實也有變化。”[6]11
然而,“國學者們企圖把中國思想(及佛教思想)從神道中驅除,但實際上不可能做到,本居宣長的思想中基于中國思想的很多,平田篤胤不但繼承之,在其思想中還直接引進了一些中國的東西(對佛教也是如此),到了平田篤胤的流派,這種傾向更加顯著,在各種問題上隨心所欲地附和中國思想。(平田篤胤在其著書里,有很多用漢文寫的序,不管其動機如何,尊重漢文便是和國學精神背道而馳的,這也許體現了他的思想的另一個側面)他們認為日本也有所謂‘道’,且說其道具備古典,這也顯然來自中國思想;因此學者必須著作古典的解釋書,但如此看法并不能闡明古典的真正意義,在‘道’的問題上,連本居宣長也不免如此。”[2]259
日本近代國學集大成的人物賀茂真淵的“神道”觀,無論怎樣排斥中國思想,還是繞不出中國思想對其思想的滲透。正如“賀茂真淵則認為,日本語有一定的法則,是‘天地神祖教誨之語言’(《語意考》),這是來源于把人們生活所必要的事物之初始全部歸結于古帝王的中國思想,而講懂了和歌能知曉世上的治亂,以歌教化民,治世全靠君主一個人的心(《新學》、《國意考》),也是同樣的思想。以道為古之道,認為古代行其道時便是治世的思想,在賀茂真淵的著書里也隨處可見,且都來源于中國思想。……賀茂真淵從荻生徂徠的立場出發,反對儒教思想,認為仁義禮智是人自然擁有的(《國意考》),這簡直就是孟子思想,從而也是朱熹的思想,單從此點上講,賀茂真淵也不可能全面排斥儒教,雖然排斥了,還是要依據荻生徂徠解釋儒教。”[2]212-214因此,日本近代國學家對中國思想雖然極力排斥,但是實際中對中國思想還是有意無意地進行了借鑒,也無法擺脫中國思想對其的影響。
4 日本近代國學者講“神道”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式的
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認為:“在講神道時國學者的整體思想和思維方式都是中國式的。我們已經說過,既然是講‘道’,本身便是中國式的:既然中國講‘道’,所以想到日本也有‘道’之類的事物,還有便是為了和中國的‘道’那樣的事物相對抗,于是認為日本也有日本之道,或者是以某種方式講日本之道,而其‘道’被當作是神之道。認為這個道是由古典顯示的,所以學習古典,即是明道,其實這些都是學問上的學道,這個道是繼承了古典中說的作為古之道的中國思想。”[2]262
并且津田左右吉認為日本講“神道”的方式與中國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沒有西方人思維方式的思辨性、實證性。《日本書紀》里引用了大量的思想,也采用了中國的思維方式,而日本的“神道”闡釋,大都繞不開《日本書紀》。津田左右吉進一步分析:“卜部家神道,說神道的要旨是忠孝或五倫之道,拿來儒教道德的思想,講神道是天皇統治天下的大道……白川家神道,依據祭政同訓說講祭政一致性,說陰陽五行和生生化育的同時,又采取本居宣長之說,他本著‘惟神之神道’、‘惟神之古道’之類的稱呼(見《神衹伯家學則》)。……在這一時代,出現了主張從儒家的見地來建立神道的主張,這即是水戶的學派。……如會澤安認為,儒教的人倫五常是天地自然之大道,日本和中國相鄰接,故風氣人情也相同的,日本的上古時代里也有和儒教之道相同的道施行著,其表現為建立了正確的君臣之義,而天地自然之道則和‘惟神’之義相聯系(《讀直毗靈》、《新論》)。……水戶學者的這些思想,還因為其依據于中國思想和儒教思想潤色過的《日本書紀》的文字來思考問題,比起《古事記》更重視《書紀》,所以偏執地信奉中國思想、儒教思想,從而表現出據此來講日本神道的態度。……那么講神道的人,又是如何使用中國思想(以及儒教思想)來建立自己的學說呢?……是以固有的中國思想來看待各種事物,例如套用陰陽說、五行說、朱熹的理氣說,講‘道’是日本上古時代便有的,以‘神道’為皇祖制定的政治的和道德之教。……根據數字,對‘五神’套用‘五行’之類,……如果有什么類似的地方,便當作什么東西,如認為‘高天原’是靈魂登高而去的‘天’;以‘記紀’等中的神或被稱之為神故事中的人物為道教中的神和中國的古帝王,便屬于此類。”[2]264-270
然而,雖然日本神道家講神道,雖然思維方式是中國式的,但是其思想還力求是日本式的,正如津田左右吉指出:“垂加思想便是如此,其思維方式雖是儒教式的,站在儒教思想的立場上的,卻因事而已,講神道和儒道的不一致。例如以神道為基礎,講日本是皇室萬世一系,沒有禪讓放伐之事,這是因為君臣名分已定,不可改動的思想和表述,拿此事和儒教道德的君臣概念相契合的同時,認為此事實際上是日本的特色,比儒教政治之道優越。”[2]149但是,無論如何日本近代國學者講“神道”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式的。
5 日本闡釋“神道”的古代經典中融入了中國思想
日本的學者沖野巖三指出:“日本稱為神國,但是對作為‘神國’根源‘かみ’之語的研究,從鐮倉時代才開始,而鐮倉時代,實際上是對支那、印度的心醉謳歌時代,那時候沒有研究日本自身的宗教的意識。”[5]144-145由此看出,日本對“神道”的認識,從一開始就深受中國與印度思想的影響。在日本,《古事記》與《日本書紀》被認為最古老的經典,“原來日本最初的神,在《古事記》中記述有:五別天神、神世七代。在《日本書紀》中有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因此,在《古事記》中有五別天神,而在《日本書紀》中沒有;而‘國狹土之尊’在《日本書紀》中有,而在《古事記》中沒有。角杙神、活杙神在《古事記》中有,而在《日本書紀》中沒有。……實際上,日本的‘神’與支那‘神’的意義大不相同,但無論如何也有相同的意義。……至到鐮倉時代,一直受儒教、佛教的影響,沒有純粹的日本自身的研究。北條貞時執掌政權的正安年間,神衹權大副正四位下卜部懷賢(兼方),在解釋《日本書紀》的時候寫到:‘かみ是人,也是圣。’在日本這是最初解釋‘かみ’,可以稱他為學者。總起來說,卜部懷賢斷定‘神’的屬性,不僅是特別珍貴的,而且也是特別古老的,也可以說,其學說直接受了儒學與佛學的影響。”[2]146-147
日本某些學者試圖為了與中國思想分離,并且對中國思想排斥,于是“由一些特殊的學者構建的被稱為‘神道’的理論。然而在其理論的建構中,作為民族風俗習慣的神道被當成和佛教、道教、儒教相對立的,所以為了和那些宗教或政治道德的教義相對抗,建構了神道思想體系。”[2]268但是無論如何也是無法與中國思想剝離的,正如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分析:“在構建神道理論時,又是以記錄了神代故事的古典為根據,或者是以古典解釋的形式來進行的,而這些古典本身就是模仿佛教、道教或儒教的經典而建立起來思考的,所以這些學者的知識其實也還是依據佛教思想或中國思想構建的。”[2]268日本學者小山松吉認為:“我國精神文化,是依據《古事記》產生的,《古事記》是日本國民必讀的經典。”[3]157《古事記》中上卷是神代卷,中卷是神武到應慶天皇,下卷是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其實中國的儒教傳入日本是在《古事記》中提到的應慶天皇時代,正如日本學者指出:“外國思想傳入我國最早的是儒教,那是應慶天皇時代。”[3]12即使某些日本學者認為日本的固有文化經典《古事記》,然而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也認為:“《古事記》序里,……有著拿道家思想來相配的傾向。”[2]78又:“作為伊奘諾尊居所的‘日之少宮’,在《古事記》里這個神衹座的地方被記載為近江的多賀宮,這也是基于把日之少宮的‘日’看作是‘陽’,從而解釋成少陽之宮,于是便和倭的東北方的多賀之宮扯上了關系。……這也是根據《說卦傳》里的八卦分別對應父母及三男三女之思想,而《易緯乾鑿度》的注里所說的天之九宮的說法,于是作為少男之宮的艮,也還是東北方。”[2]40可見,被極力排斥中國思想的近代國學者極力推崇的日本固有文化經典《古事記》,不可否認也受到了中國思想的影響。
綜上所述,日本“神道”與中國思想的關系,主要體現了“神道”與中國儒學的關系。可見,中國的儒學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即使日本認為本土文化的“神道”也擺脫不了與儒學的關系。
參考文獻:
[1]今井淳,小澤富夫,編.日本思想論爭史[M].王新生,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津田左右吉.日本的神道[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3]小山松吉.日本精神讀本[M].東京:日本評論社,昭和十年(1935).
[4]雄山閣編輯局.異說日本史·宗教思想篇下[M].東京:雄山閣出版社,昭和八年(1933).
[5]沖野巖三.日本神社考[M].東京:恒星社,昭和十二年(1937).
[6]鈴木暎一.國學思想の史的研究[M].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
責任編輯 劉宏蘭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2.004
B95(313)
A
1004-0544(2017)02-0020-06
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15XZX005)。
史少博(1965-),女,山東德州人,哲學博士,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